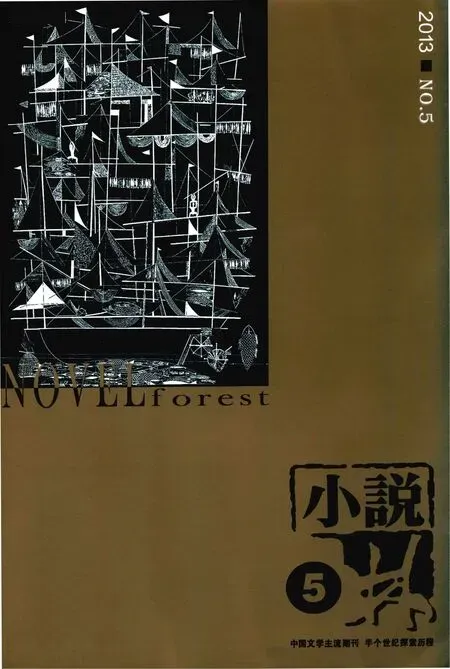班得瑞音乐
◎姜 凯
一
为什么不呢?这里简直就是咱孙女的天堂。那个乡下老太太像老鸭一样干瘪着嘴,边跩着走路边呱呱说着。为什么我儿的车和你的老婆的车撞在一起,你老婆不死,我的儿命没了,难道你老婆他娘的是九尾猫的命。天下没听说这个理。扔下可怜的孩和我这老不死的,哪个来管。城里满大街是疯子,一群疯子。她身上发霉的柴草味在房间飘散着。那个黄头发孩子伏在窗台上,手指在玻璃窗上乱划着。
老桐嘴唇绷成一条线杵在墙角,一股酸乎乎的热流在食道内往上涌,就像无数的虾米一样在游动。
老太太一头白花花的发和鸡爪子般的手,神经质地哆嗦着。她一会儿在墙角上一堆破书烂本子中翻来翻去,一会儿停下来用死鱼眼睛盯着老桐,嘴角泛着白沫子絮叨着。大街上全是疯子!不孝的兔崽子,好好的在村里待着有多快活,贱命,跑到城里找死。讨个吊死鬼的老婆,一脸的寡妇相。呸,一群疯子。苦命哪!连棵乘凉的树都没了。
她嘴上的白沫子嚣张地抖动着,抬起头沾着眼屎乜斜着老桐问,卖废品的吧,找点儿卷旱烟抽。老桐鸽子一样,机械地点点头茫然地看着空气。他的视力不好,被市医院确诊为视神经损伤。他走到墙角在一个黑箱子打了一下,他总觉得有一条黑色的狼狗怒目横眉尾随着老太婆进来。
她蹲在那儿把空白无字的纸撕下,摞在一起,放在一个紫花布的三角兜子里。老桐也许是不愿听她撕纸的声音,走到里间,拿出了一条黄色有条金龙图案包装的烟,递到她眼前。
她站起来,龇着黑黄的板牙接过来,塞在花兜子里,说,没有工夫和你扯这些大道理,快给几个钱,天杀的坑死我了,早饭还没有吃,还要回乡下赶路呢。
那个三四岁大的小女孩子伏在窗台向外面看着,已过正午,淡黄的阳光,照在她营养不良苍白的脸上。
老桐躁动不安地在原地踱着步,拿出黑色的钱夹子,正从里面掏钱。老太太上前一步抢过一张大票,一阵风般提着花兜兜消失在门口。
他磕磕绊绊地追了出去,下午的小街,白色刺眼的路面静悄悄,街旁梧桐树叶动也不动,连鸟声也没有。
叶子按摩诊所,六个黑色的大字,深刻在白漆刷的木板上。还有贴着的那张几年如一日,无论白天和晚上都在龇着白牙,向你笑的大美人照片。她是叶子,诊所的老板,可是,天气这么好她却不在这里,扔下老桐一个人,像空气一样,似有似无地存在。
一切变化有些让他无所适从,千万个小虫在噬咬着心,一丝寒气在眼前飘浮。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问,叶子究竟去了哪里?空空的街上没有人回答。
他踅转回屋,摸索着蹲在孩子的跟前疑惑地看着。屋中那个小女孩子,对于老太太的走,也不哭也不叫,似乎她与她丝毫没有关系。这好像就是她的家一样,她还在胡乱地刺刺地划着窗玻璃。
日子真是奇怪,凭空中又多了个孩子。他恍惚地从冰箱的保温格里找出了几袋牛奶。又不知从哪儿翻出几个发黄的香蕉,一股脑儿地全堆在小女孩的白瓷砖的窗台上。
一下午,他都自己固定在明净的窗台前,被某件事缠绕着。
外面那棵绿萌深深的梧桐树下,蝶飞蜂游,一两只梧桐叶子随风飘落着。
街面洒着金黄,一阵又一阵风吹来吹去的。街上的人又多了,如蜂如蝶,游织着。整个一天的时间,都没有人进来。只是偶尔有跑来跑去的狗狗,慌慌张张跑来跑去突然驻足,或者瞪大了眼睛,或者,歪着脖子,向里屋的这个大鼻子的男人张望着。
总得弄点儿吃的,既使自己吃不下,那个小黄头发的孩子总不能饿着,何况自己一整天也没有吃什么了。他下定决心要做一道像样的大菜,犒劳一下自己和那个与他有关联又没有关联的孩子。他在开冰箱取一条红鲳鱼的时候,尽量不去想但还是想着稍后把这个孩子怎么处理,是报警或者就这么无声无息养活着。看着那条鱼茫然地看着他的时候,想报警的决心消失了,听天由命吧,也许她就是来投胎过的孩子吧。
天黑了,那道菜好不容易摆到桌子上,小孩子真的好像在家里一样,丝毫不陌生,也许是饿了,对桌上这盘油淋淋的鱼睁大眼睛看着,用筷子夹过去,噘着小嘴吹着热气,悄悄地吃着。老桐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慢慢地喝着。
七八天的时间过去了,老桐原本混混沌沌的生活,原本一天自己都吃不上一顿饭的日子,因为多了个小不点,多少有些生动。这个小东西有个很怪的名字,叫花生米。她总是把手指塞在嘴里,围着老桐身前身后像小鸟一样一时不停地飞。
因为有了这个孩子,他会常常想起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的事,一想到心就痛,眼前就什么也看不见。
晚上,老桐想到孩子喜欢吃鱼,就又做了盘红烧鳕鱼。花生米小心地吃着,老桐倒杯红酒慢吞吞地饮着。
门开了,一丝茉莉花的香气随着走动的身躯,送到他的鼻孔里,一个一袭黑衣的长发女人走到近前。
女人刚说句,这是叶子诊所吗?小孩子就像小喜鹊一样扑了上去。女人抱起孩子惊喜地叫道,花生米——我是她妈妈。
平静的夜晚,多了个小孩又多了个妈妈,一时老桐涨红了脸,有些结巴地说,坐、坐、坐。没吃吧。
女人也不客气四下环顾了一下,放下黑色皮包,脱了黑外套,用手向下扯了扯藕粉色绒衣,就坐下了。
女人小口吃着怕被噎着一样,细嚼慢咽着。老桐为她倒杯红酒,她轻声说谢了。她盯着他看着,他也那样柔和地看着她,又似乎看不懂。她摇晃着酒杯,红色透明的液体在杯内,眩晕地转,她小声地说,我叫黄凤,在腐败一条街的亨得利大酒店做服务。叶子呢?是你老婆?她在哪儿?身体没受伤吧?
老桐眼睛有些湿润说,其实她已经早就不在这个诊所了。就是今天晚上在哪儿和谁睡在一起,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他说得有些激动,猛猛地喝了一口,酒呛入气管里,他拼命地咳嗽。他似乎在眼前又看见什么东西了。想拿出一片药吃,掏出瓶子来。可是又突然停住。她探出身子,拿过药瓶,上面写着“地巴唑”和“维生素B1”、“维生素E”的药,她不明白,看了瓶子上的小字“哦”了一声,她轻轻地把药放下。
花生米不吃了,跑到沙发上,在女人的皮包翻来翻去。金色的口红,橘黄色的钱包,几条粉色的口香糖,还有一个橄榄绿色的帆布包。花生米粉嘟嘟的小手拉小包的拉锁,掏出了一个银白色的CD机。
老桐问,你喜欢听歌?那女人回头看了看,低头说,一个盲人客人在旅馆发高烧,我给他找了医生,他病愈后,送给我的。我听不太懂,但听了心挺静的。
花生米眯缝着眼睛美美地鼓捣了一会儿,那个圆饼饼似的东西,竟发出了声响,飘出了一丝曲子。流水般清澈,森林绿叶葱葱,隐隐约约,似梦似幻。
屋外闷得好像下雨前的天空,只有女人茉莉花花香气和音箱流出的曲子。
老桐恍惚又换了个时空,眼睛模糊地经常在身前身后摇尾乱转的黑色的狼狗不见了踪影,一天头晕的感觉没有了,好多日子家中没有女人的香味了。
一晚上,他都把自己置身于那个一生中从没有去过的山谷,森林绿叶下,虫鸣,鸟唱,飞瀑溅起的泡沫在屋内相互缠绕舞蹈着,忘记了屋中还有别的人存在。好像这支曲子攫住了他的灵魂。
她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说,其实,那个死鬼半年前的夜晚喝醉了,把我打出家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还是愣愣地看着她说,那你怎么办?她没有回答,小口品着鲳鱼数落着孩子的奶奶,不应该把孩子送过来,给别人添堵。她告诉老桐,她不是和老桐放讹的。
老桐出神地在听着音乐,从不多说一个字。她见此状态说,你喜欢听,就把它送给你吧。
天黑了,他们没有聊什么。黄凤洗涮完碗筷,边擦地边对老桐说。这半年她也没找到房子,就在宾馆将就着。她太累了,不知能否让她住上一夜。老桐还在听曲子说家里有房间,随便住吧。女人把孩子的小衣服和老桐的袜子拿到卫生间唰唰地洗了后,扯着孩子回里屋睡去了。
窗外一片光亮,整夜被梦搅得神情恍惚的老桐被一泡尿憋醒了。撒完了尿他看到桌子上一张报纸上,用药布蘸着红药水写的些大字,他费劲地看看,上面写着,哥,我上班先走了,孩子在这住了几天,真是对不住。在你的枕下我放了三百元钱,那个CD就送你了。知道你视力损伤,多保重。叩谢,黄凤。
老桐把报纸叠了起来,走到客厅的床边,一摸枕头里边一卷钱老老实实地躺在床单上。
他走到厨房里,白铁锅里鸡蛋羹荡着一股葱花香味和热气飘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皱着眉头坐下了。
二
叶子诊所,门前一棵梧桐树,金黄的秋风吹过来,卵形的叶子。风铃般弹奏着那种声音,如佛乐,如天籁一般,让人一下子就融入到季节的风里。叶子喜欢用大枣、莲子、金桔、枸杞烧开了水,放在凉杯里,一点点慢饮,看着时光,一点点地西移。她也许是太累了,给自己来点儿小资的情结。
叶子好几天没有上班了,蹲在阁楼里,打着盹儿,像小猫咪一样轻轻打着鼾声。对面米黄色的牌子是燕子美发中心。几个男孩女孩,站在灰色的瓷砖上的,躺在木椅上的,听着歌的,摆弄着手机信息的。
叶子喜欢静静地透过小窗,俯视着这一群青春热情的小玩意儿。她看到自己也坐在他们的中间,或打着手机,或玩着那些闲得无聊的小游戏。
她自己的少年,则是一片荒芜的风景,似乎在她的记忆中,死掉了。
她拼命地喊叫着妈妈,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她妈妈的头上跳着舞。只听“扑”的一声,妈妈反夺过菜刀,砍下去。鲜血从她继父的头发上淌下,那个发酒疯的铁路小站长稻草人般倒下。鸡爪般的手松软,她挣脱开,发疯地挣脱开,提上沾着鲜血的蓝色牛仔裤。看见母亲直着双眼,看着滴血的菜刀在地上闪着红光,她们相互搀扶着,在雷雨闪电中,逃了。
一块黄渍渍的雨布顶在头上,就是她们娘俩巴掌大的天了,乘着茫茫的大雨,一列南下运煤的火车。黄朦朦的外面,是龇牙咧嘴的雷电,下面是娘俩两颗颤抖的心。在雨中,在雷电中,向着不知名的命运方向前进。在雨中的夜行中,她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下体不断地流着鲜血,被无情的雨冲淡了,渗入煤中。她觉着天上飘着红月亮就是自己,要吞噬满天红色的云、雷电和大雨。
白发苍苍的妈妈领着说着胡话的女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硬是凭着一双能烙黄油大饼的手,养活了娘俩儿,在一个叫黄蜡香的饭店站住了脚。妈妈已经没有了眼泪,便给人家干着活计。渐渐地生活稳定,她又把她送到了一家初中学校去读书。但是女儿多了项毛病,偶尔会看见,天空飘着红月亮,吞噬一切的生物。
她又仿佛看见王院长乱蓬蓬的灰白头发的大脑袋一直在她的胸前拱,空气充满了酒精味和大葱味,她几乎是从一甜蜜的梦中被惊醒,一切向上爬追逐红月亮的梦想,就此打住。
每当想到这些,她的心里就潮流奔涌,坐下来享受阳光和音乐的心,就会被外面远处的隆隆车声所绞碎。那个狗娘养的院长的亲戚夺了医务处主任的位置,一个女人不能这么地沉下去。那个狗日的晚上,那硬如木棍的许诺进入她的身体,不可名状的滋味,出自肺腑的疼痛。
她打了个电话,细细打扮了一番,看都没看老桐一眼就出去了。
而此时的老桐正坐在紫色的真皮沙发上,模糊地透过窗前的梧桐,在看着她一瞬间即逝的影子,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宿命中上辈子谁欠谁的缘故,也许他就是这辈子来还回的那个,但他不是她的乘龙快婿,他也不是她的白马王子,他这辈子自从遇见她,也活该让自己的脑袋,长在她的头上。他几乎成了她手中的棋子。
当初叶子一身白纱,在大学虽然都是学医的,但她是学校有名的哲人。当时学医的那帮傻瓜们,谁也不懂得厚脸皮的处世之道时,学心脑血管的她,天天带着个大墨镜手捧着一本李宗吾黑皮的《厚黑学》。同寝的姐妹,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争强好胜,就直接给她起了个外号厚黑姐。
老桐虽然和叶子是大学同学,但是他是自费补了个N市大学的卫生事业管理系的。起初,他是不敢正眼看她,只是偷偷地看着她风姿绰约的背影。一次暑假回家,当那时的老桐还是小桐时,他爸老桐当时是S县副县长,来学校用黑色的皇冠车来接他时,同为老乡的他,胆战心惊斗胆到寝室问她能否同车回家,她才正式看他一眼,但还是没吃他那一套。从此,他就再没有动过歪念头。直到快毕业那年,命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看上去与众不同的她,居然对他穷追加不舍,原本和N市医药局长白胖胖的女儿处得火热,正准备安身立命在N市的小桐,还是屈服这个叶子,与那个撕心裂肺的胖子拜拜了。
但也恰恰是这一步,使叶子回到了家乡,顺利地进了市医院成了心脑科的一个主治医生。小桐则次之被老桐安排到了一家不怎么样的商业医院。叶子也不负重望,而与小桐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然而,正当老桐要把叶子送到市医院的医务科科长的位置,把小桐调到医药局的时候,一场事故,让所有的故事都发生了转弯。
叶子的闺蜜铁英为了能让林区派出所所长弟弟攀高枝,想拜在老桐的门下,让弟弟组织了一场山上打猎。结果越野车下山时,翻车了,老桐摔死了。小桐摔坏了头部,变成了老桐,总看见眼前不断闪烁的火光。市医院确诊为视神经损伤,住了一段院出来了,视力恢复了,但是时好时坏,不能激情、激动、愤怒,不能忧愁。总之,伤神动感情的心动都会让他瞬间失明。医生说只能这样,不可逆的。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叶子的能力,她像一只粉色的蜘蛛在银亮的网上跳来跳去。老桐死了,她哭泣了好多天,谁也不知道这个好看的儿媳有这等孝心。
三
那个女人走了之后,他似乎已经不记得她是否到来过,究竟在世界上有没有她这个人的存在都是个未知。没有几个人来上门,他每天没事,有了张望大街的习惯。似有似无地看一看,模模糊糊过去的车和行走的花季少女,还有对面的转起来没完没了的黑白条纹的好像童年时看的万花筒似的。他觉得身上没有压力一样,轻飘飘地活着,所有的欲望,好像没有释放的地方。
他背上忽而冒起了凉汗,身后被一只黑狗追着,他气喘吁吁找不到出路。之前的症状又出现在眼前,无论是白天与晚上,某件致命的事会不约而至,就好像整个人要沉下去,沉到万丈深渊,就忽然有了那个念头,这一辈子就完了。他又坠入湍急的激流中。
他大汗淋漓地就把CD打开,听一听那个如流水般的音乐。那股在匣子里憋了好久的曲子,如一股奔涌的泉水,潺潺而流,在森林中穿梭,山泉,小鸟,狡兔,蛙鸣蝉噪,蝴蝶纷飞。
他在窒息中终于爬上岸,透了口气。
他无聊地打发患者,睁一眼闭一眼的,懒洋洋地一点生气也没有。人家还抻着脖子,看着他的脸,以为他病得很严重。他不知内心所关注的什么。也许那个大脑中远去的穿黑风衣的细腿的女人更吸引着他的目光。
不知为什么,他淘米的时候,喜欢多放上一两碗,等香喷的米饭熟了之后,他望着那么大锅米饭发呆。耳朵偶尔会听到屋内传来孩子和一个女人的窃窃私语声。
那是夏末的一个黄昏,他昏沉地睡去,睡梦中总有个人站在他面前微笑。他心情也好极了。这个人这么熟悉,如瀑布似的黑发,浅黄的眼仁,勾魂得让他不能自拔。一定是叶子。他要站起来,去抓她的手,醒了。对面果真站着一个穿黑风衣的人影。他站起来看了又看,走近了看,一个女人芥末黄的卷发大黑眼睛深陷,红唇膏微笑着,他心突地一跳,是黄凤。
她站在那,沉沉的眼皮述说着她好像一夜没有睡觉。
这时外面淅淅沥沥,由小到大下起了雨。雨点儿淘气地瞎蹦着,胡乱地敲着诊所的玻璃窗。她显得特别疲惫,困倦地坐在黄黑格子呢绒沙发上,喝了一杯老桐递过的苏打水。
老桐走去又回来,摸索着拿出三百元递过去说,我不可能要你的钱。他执拗地把钱直端着,不看她只看地面。她知道他太犟,把钱接过,欺他视力不好,又偷偷地塞在他的床单下。
他们草草地吃完饭,她没有去清理碗筷,而是借着外面下大了的雨声,昏昏地睡着了。
他守着她,看她沉沉地睡着了。他觉得她好像很冷,就为她拿了件棉线花毯子盖上。他的手,感觉到她鼻子呼出的热浪。他用手试着去摸她的头,觉得有些发烫。他想一定是不小心感冒了。他真想不起来家中还有什么药了。她的包里一定还有什么她吃的药。他不停地翻找,口红,小包的口巾纸,口香糖。这是什么,一张化验单。他想她是有病了,他试着拿到灯前努力地看,上面写着有革兰氏阴性双球菌,血液显阳性,培养检到支原体,衣原体抗原阴性。看了半天才明白,她得了淋病。一个漂亮女人能在大酒店做什么?他的大脑轰轰作响。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暴雨,疾风,雨点像炒豆子般。
他觉得屋内说不上有多少个人影,都是与这个女人有关。她穿着一袭黑装,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白骨精。她的身上在白晳的皮肤下满是紫黑针眼。她成了万恶之蛇的化身。老桐白着眼看她。她这条黑蛇,在激动地扭曲变形。老桐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不停搜寻着自己的药片。可是他眼神恍惚,他只好伏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着。眼看着那条黑蛇在不断地僵硬。
外面的雨,下得小街都看不到人。天空紫铜色不断闪着雷电。
那个蛇一般的女人醒来,颤抖着站立,迈步像婆娑的树在移动。老桐有些抓狂了,双手歇斯底里薅住自己的头发说道,你走吧,我不要看到你。
他把她皮包里的东西扔了一地。
黄凤看着地上散落的银色的口红,小包的口巾纸,绿色的口香糖,还有那张躺在地上幸灾乐祸的化验单。
女人呆呆地走出去,走进狂风暴雨中,她蹲在门口的一角,被雨、闪电狂洗着。
老桐木桩子般立着。
雨点狂击着,地面白花花的豆子,叉子般的闪电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撕裂着天空。他把她拽了进来,她紧紧地搂住他哭着说,我真的没处可去了,我不想死,我还有花生米。
她蜷缩在一小块地毯上,像一块破布,身上的雨水洇透了地毯,像一朵牡丹花。他闷头地走过去,倒了杯红酒喝着。
雨停了,一群麻雀掠过,唧唧喳喳。屋外兀自繁华热闹,屋内静静的。
她发着高烧,满嘴说着不着边的胡话。他只好关上诊所,把她送到医院。
她的病全要治。他每天面无表情地探望她。半个月后她出院了,她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他把她接回了家。高烧好了,那种病还得需要下个周期去检,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革兰氏阴性双球菌。血液是阴的是阳的。她说她有一天他会还他钱的。他还是冷冰冰的。她检查了,那个病已经治愈了。第二天她要走了,她把被褥子铺到了他的身旁。他们都冷冰冰的,好像对这个世界不信任,更不信任自己,何况自己的存在。他们谁也没有看谁一眼,就好像躺在那里的两棵毫不相干的梧桐树。没人说话,仿佛就是屋子中的一张桌子和另一张桌子,一把木椅和另一把木椅,紧挨着不睡觉,就一直望着黑夜到天明。
天亮了,他睡了,她为他做好了饭,还是鸡蛋羹,她说过他喜欢喝羹时“秃噜噜”的声音。
她静静地走了。
四
打掉已经怀孕三个月的孩子,她擦干眼泪,挺起胸膛,醉心于天天跟着一个在市委工作的同学和朋友,打成一片,打牌喝酒。化悲痛为力量,想不起了那个曾经在她的子宫中生存了近一百天的生命,每天坐着黑色的豪华奔驰轿车飞来飞去。
她指着老桐的鼻子说,他娘的,破医务处处长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给我还不稀得给他玩呢。吊儿郎当的商业医院,给咱破院长当咱们都不干,咱自家开诊所,挣大钱,他商业医院还得给咱们开工资,一分也不能少。她让他坚持拜师学了按摩之类的。
当老桐还在思念他的爸爸时,还在想着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是否真是因为她的妈妈,不慎跌倒而将其流下时,她已笑容满面,容装焕发,背着班卡奴的黑色包,带上浪琴表,成功地从市医院,跳槽到水务局当上了办公室主任。
随着叶子匆匆忙忙来去的脚步,老桐的工资关系则转到了叶子的市医院,工资照开。叶子诊所在一片鞭炮声和叶子的狐朋狗友喝彩中开业了。
为之铺平道路的同学组成了一蜘蛛网,而叶子就是这个网的舞者。在每次她与这些人酒宴回家之后,他眼睛不太清楚地看到什么,但是冥冥中,他能从她的身上的玫瑰香气里嗅到男人的香水,味道介于冰与米兰香之间,其中还夹杂着一股似有似无烟草味。他清楚叶子是最不喜欢烟的味道,就是因为他有十多年的烟龄,因为与她住在一起才不吸了。
冬夜,老桐睡得正香的,被谁踢开的门声惊醒。他摸索着打开灯,被一股刺鼻子的酒精味直熏得他胃水上返。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里屋,却发现床上空空的。他又踅到卫生间,开了橘黄的灯,叶子穿着黑皮衣服跪趴在洁白的坐便上睡着了,地上和便池里洒满她吐的黄色的污物。他皱着眉抱起她,身子软软的,头耷拉着黑发如瀑布般洒下。脸红红,轻轻熟睡。他无奈地抱她上床。为她脱衣服。他看见她粉的内裤湿了一片,小便失禁了。脱去内裤时,她的私处黏糊糊,看上去是白色液体,剌鼻的味道直冲他的鼻子。他明白了,她……
她醒了,天空微微发白,老桐不在床上,他一定是昨晚又喝那该死的红酒,睡在沙发上了。她觉得谁为她脱去了内裤,下体有些异样,她起身去了卫生间,老桐有好一段时间没有那事了。她试着回忆起了昨夜的事,她想起来了,觉得是梦中老桐站在赤身裸体的她跟前,站了好久。一股酸溜溜似乎是血液的东西从胃部喷了出来,是黄色的。她觉得青白色的房间和白瓷的坐便,还有墙上的瓷砖上的飞天的女人,都是红色的,天上挂着红月亮,她又掉入记忆之中。
他有时看明白又看不明白的世界里,他整天更深深地陷入黑色的陷阱中不能自拔。周围阴森看着他的是绿幽幽的狼或者狗的眼睛。
他在一个人静静地举起红酒酒杯冥想时,清楚地看到叶子背后的这个似人似狗的模样。中等身材,小三角眼睛,白白净净的,说话低声细语,有着中国儒家所定义的男人形象,大忍,又有着坐了政府机关的典型的阴诡类似太监的形象,低三下四,骨子里含着恶毒的东西。他就站在叶子和他之间,每当他们俩赤身裸体血脉贲张,欲要苟合时,他都会勇敢地出现,如站在透明的隔壁,那种阴郁,让人不寒而栗。
于是,他总会让喘息不止的叶子大失所望,她甚至会砸碎屋中那面镜子,会在他的肩头上狠咬一口,直至鲜血淋漓。她在狂笑望着空中。
不知为什么老桐对于女色,好像在内心中根本不起什么生化反应,他的雄性荷尔蒙好像在历史上某一天突然在他的肾上腺终于停止分泌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中性人。尽管,来按摩的女人这么热的天,穿得圆胸袒露如粉团般,拔火罐,按摩,肌肤之亲,但是,他仍旧两眼无神地看着地面,显得疲惫不堪,丝毫看不出亢奋的样子。虽然,他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有时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靠手去抚摸。
渐渐的,他们之间变得无话可说。不再像以前那样,像狗一样用鼻子在她的脸上脖子后,闻来嗅去。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一起上床了。她不再有激情像一只母狗一样地喘,他也不像一只饿狗用舌头在她如玉的肤体上舔来舔去。
她回来时,他的目光总是避开她柔媚的目光,或者绕到她的身后呆呆地看,或者在忙乎着什么,低眉低眼,一遍遍地洗着手。要么就是对着窗户,默默地喝着红酒。
不久她就在市电视台晚上公示的拟提副科级人员名单上出现,一周之后,一个金秋的下午,她到普美镇去任副镇长了。
五
她走了再也没有来。生意不好,小街空荡荡的。他想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总有一天会就这样死去。他的视力时好时坏,不能激动,也不能兴奋。就是看着电视,也会因为某个情节,使肾腺素分泌过多而会突然失明。
对面的美发厅也黄了,换成了一家鲜花店。两三个小女生店员,一水水都生得白白的,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小白牙,见谁都是笑嘻嘻的,见谁都鞠躬,像小日本似的。她们天天把插在蓝桶里的百合花、玫瑰花什么的从屋里屋外搬来搬去的。那无根的花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还在装腔作势地争芳斗艳。
那些小女孩们也会跑来借一把笤帚,或者手碰破了口,就咧着小嘴跑过来,大叔大叔一口叫着,可怜巴巴地让他给用药洗洗擦擦。这时喝着红酒,老桐的心情似乎还好一些。
这时总会有屋中的音乐流出钻到小女孩的耳朵里,她侧着耳听了听,再听,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就问他叔叔啊,什么曲子这么清远,宁静,好悠然。他也不知道,就说反正是一位阿姨拿过来的,心烦时就听一听,想事想人时就听一听,挺有意思的。
他听着听着,有时思想就溜号,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看着窗对面这些小孩子,像嫩葱似的一个个,这个年龄活着,多有意思。他可以重新回到学校,那里怕是最乏味的初中也好,情窦初开,可以把叶子假设在哪个班,哪个座位。一点一点地接近,攀谈。也许一轮金色的月亮升在墨蓝的空中,他还会送她。想到这他不自觉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思维又跑差了。他这样一天天过着,饿了,就打开冰箱随便吃根火腿肠,煮袋方便面什么的。一天天就这样混着。
他斜躺着,闭上眼睛感觉到窗外的光线,由炽白渐渐变为金黄,朦胧中睡去。忽闻到一阵菜香扑鼻,眼看着,叶子长发如瀑,扎着蓝花的白底的围裙。是谁轻轻地嗨了一声,声音太轻了,像飘飘过来的一丝雾。他无奈而好奇地睁开眼睛。
一个浅黄色头发,深锁着细眉,丹凤眼下眼袋青色的女人,已经把一盘油炒笋尖端了上来,还有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他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
他们俩人就坐在桌子旁,一言不发地吃着。只有香气在屋中伴着音乐在缭绕。她说,我在一家大服装商场,给人卷裤角,熨衣服。他没吭声,只是一个劲地响吃着。她几乎在自言自语。
吃完了,他的胃口好极了,几乎把桌上所有能吃的,都吃了个精光。忙乎完了,他就看大街。她收拾碗筷。不停地擦地擦墙面。她推出洗衣机,注水,把屋内飘着汗臭味的大堆的衣服、裤子、袜子洗了,扯了窗帘,被套,床单。一下午的光阴,屋内屋外,像挂万国旗似的,花花绿绿。她在一旁看着他娴熟地在给两个花旗招展的女人按摩、拔火罐。在女人们的白白的后背还有肥腰上,摆弄着。
她试图在探查他对女人那个股沟时的表情,以为他会想入非非,起码能在他脸上,看到雄性荷尔蒙,看他的太阳穴的青筋活跃,不断咽着唾液,眼睛放光。但是她失望了,他的有关那些的表情,在他的身上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来。他似乎疲倦地看着她们把上衣和裤子褪下来提上,尽管露着各种鲜艳无比大红大紫大绿的内裤,他还是麻木,玩弄着他的手掌,面对细嫩如粉的皮肤,他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而且像是在战场上拼搏一样,每活动一次,那个伏在桌上的女人就要配合地“吭哧”一声。
她们付了钱,他毫不犹豫将钱塞在紫檀色老板台的抽屉里。她翻箱倒柜,给他找来衣物,而且颜色浅灰的,是那种很薄的棉料。她从里面把诊所的大玻璃门反锁上。把他扯到里屋,让他上下身的衣物换下,她又从自己的大黑皮包里掏出了为他买的白色内裤和背心,她知道他有穿背心的习惯。她把脸微微转过去,他木然地脱着,一点一点脱着,慢吞吞的。她等不及了,亲自上前粗鲁地扯去他的袜子,外裤,内裤,上衣,背心。他简直像个孩童似的赤身裸体坐在那儿。她审视他的胴体,像妈妈审视自己的孩子。仅仅是犹豫了片刻,她就飞快地给他穿好衣服,又给他扯了扯衣服的后襟,把他往前一推,她兀自拿起他的有着酸臭汗味的衣服出去。
她一切都做完了。她看看时间,接了个电话,她对他说,我该走了!她把她的皮包拿起来,递给他,说,这里有些钱,生意不好时就花它吧。我攒下的,干净。他茫然地看着她往出走说,你要去哪儿?
门口只有风卷着梧桐的叶子在慌慌张张地沿大街疯跑着。一辆警车不知什么时候停在门口,两个陌生男人坐在车里向外面张望着。黄凤披着黑风衣神色忧郁地往出走。她好像老了许多。她低着头走近老桐跟前,低泣地说,哥,我没有犯毛病,我家的死鬼原来是贩K粉的,他的同伙犯事了,警察在死鬼住处翻到点东西。她妈妈来了一口咬定是我的。我是无辜的。相信我。
老桐张着嘴惊呆了。
黄凤说,等我。
老桐茫然地看她。
她上了警车,风卷着梧桐的叶子追着车奔跑。
六
晚上,她回到家里。老桐正生气地等她,可是尽管他睡了不知多少觉,时针已敲响了两响,楼外万家灯火早已熄灭了。她踩着舞步回来了。她看他的眼神是那么迷离,看他的眼神像看陌生人的眼光。不一会儿,才就张嘴,打着哈欠,流着泪,淌着鼻涕瘫坐在床上。出了一身的冷汗,迷糊地起身呕吐着。他疑惑地给她量血压时,发现她的胳膊上有麻麻的小点,仔细拍打之后发现是针眼。他明白了,他两眼闪烁着小星星。他从她的包里找出了写有帕罗西丁的瓶子,打开了瓶盖,他发现里面根本不是什么帕罗西丁,他品尝了一口,是……他知道她做了什么,在背后吸着什么。
终于有一天他们能够坐到一起了,那是一个黄昏。晚风,橘黄色,昏昏的行人。欲睡的空气,即使滚滚而进来的,也如恋人的热吻。
叶子诊所大玻璃门,被擦拭得光洁明亮,似空无一般。
窗外,高楼射过来的夕阳金子般的光线,远处钟楼的钟声整整敲了六响。没有人再来这里,到处都是高楼的眼睛闪着光。
她望着大街的一角,定定地看着他,说散了吧,别把两个人绑在一起,整天泡在黑色的地狱里。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他不看她,内心不想看她,也许是没有勇气面对她刚才说的话。他喃喃地说,分开?分开。我的周围布满陷阱,你身后总尾随着一条黑色人面的狼狗,也许不分开有一天我们会同归于尽。
她淡淡地说,你可能是病态,应该去治疗一下。
他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诊所还是你的名字,你的那张站在门口的图像别换。他两颗豆大的眼泪滚滚而下。
她沉思着,有些厌烦地把脸扭向窗外。
也就在第二天,她就消失了,消失在空气里。
屋内来苏水的味道跑出来,跑到街道上,混着梧桐的花香,在行人身上缠绕着。路边的行人穿来穿去。
三个中年女人从街对面扭着屁股,划过来。一个黑白花,一个一身芽黄,一个大红。乱蓬蓬的头发,像三朵云,飘过来。她们好像很有钱的样子,也许刚吃完大馆子,吃什么生蚝、海参,所以还来平平胃。她们仰着脖子,呀呀指手画脚了一通,一起拥到叶子按摩诊所。
一张瘦白的脸,黑洞洞的大眼睛,从里面探出头来,茫然地看着她们。男人歪着头好像一直看不懂这花花绿绿的女人,死盯住她们,金属一样的声音,说哪个先按摩?
一个瓜子脸女人蚊子般声音,说,她们俩拔火罐,我全身推拿,单我全买了。男人摆摆手,说里屋。左边墙壁上开了一个门,一张白帘,魂一样被风吹飘着。那两个人难为情,还是一个挨一个进屋,掀去上衣,露出整个肥肥白白的脊背。
老桐不一会儿,就在她俩的背上扣上了满背亮莹莹的灯泡。瓜子脸嘻嘻哈哈地说着,昨晚在梅山公园的路上,一个女的开着红色的广本,和一辆紫色的桑塔纳撞在一起。桑塔纳车翻到左边的深沟里,男司机死了。可是真倒霉,女的还有个男的夹在车里,血流了一地,两人痛得鬼哭狼嚎。那个女的一身白衣服被血浸透了。男的是我家老公叔伯弟弟,姓景,是市委办主任。她独自脱去裤子,等老桐上手。老桐听完了,脸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手却没离开瓜子脸摆了半天白屁股上的肥腰。
这时,手机响了,是叶子的同学铁英,她告诉他,叶子出车祸了,车上还有一个男的,两个人都住在圣大医院。
不一会儿,一辆警车开到门前,下来两个年纪轻轻白净净的警察。一个瘦的问,你是叶子的丈夫吧?一个大个子有胡子的拿着本本,瞎记着。老桐说原来是,我们早散伙了。
那个瘦警察说,叫叶子的总是喊叫我的红月亮叶子诊所。
老桐摘去口罩,长叹了口气,傻子般坐在椅子上,翻白着眼睛,徒然感到自己已掉进那个绿幽幽的湖里,发光的鱼贼眉鼠眼地溜来溜去,那个阴着脸的死命地拽住绿绒绒的水草的男人,扯住叶子的手,叶子一袭白纱衣,圆睁着眼睛。他们面对面,呼吸着……
两个警察生气了,在屋内跺脚骂着。胖子骂道,他娘的全疯了,坐在车上的不是叶子的男人,是她的男人他妈还直翻白眼,掉疯子窝了。说完,两人分别拍拍老桐的嘴巴,一个皱着眉头,一个笑哈哈地出门上车走了。
七
三个多月过去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了,叶子诊所的牌子也脏了。那个笑眯着眼看你的大美人,也被风撕裂开了,一片两片三片地被风吹走了。诊所每天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来。他几乎每天不吃什么,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行了。周围有好多只狼狗,睁着人眼在怒视着他,马上就要把他吞噬。躯体即将坠入黑色深渊,他觉得这次彻底完了。自己很快地像窗外的叶子一样被风带走。
终于有一天,雨夜静悄悄的,他熬不下去了。他已经把白药末倒在酒杯里。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准备把它服下,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红酒旋转在杯中。
他想那个碟子的曲子也不错,让它送自己上路吧。那支曲子被打开,让它在屋内环绕着,他抓紧这音乐的须蔓,在波涛骇浪中寻找什么,也许这音乐之藤是他生命的索道。空虚缥缈的音乐,一尘不染的音符。每一种旋律,每一个停顿,每一个音符,都在紧紧扣着心弦。城市的喧嚣,尘世的凡俗,都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被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乐曲所覆盖。
钢琴的琴键上轻轻滑过,一缕惆怅,月光似水,繁星窃窃私语,小桥流水,大海波涛,风的声音在耳旁掠过。
当黎明临近,第一缕阳光照在乐章上,撩人心弦的声音便随着露珠而来临,清澈透明,仿佛来自一个世纪前的纯净,有着出生婴儿般的毫无杂念的眼眸让人的心随之荡漾,让人的灵魂也随之缥缈。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世界的存在,只记得那优美的音符残留在耳际,梦幻的旋律。人生在世,经历的风风雨雨,那种沧桑与优雅,在音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夜过去了,虽然他很困惑,但毕竟那杯红酒还是放在那,没有喝下去,听着外面熙熙攘攘人群声,看到金色光线射到室内,他肚子有了饥饿的感觉,于是他困倦地走向厨房。
他每天都在听,他想兴奋地向外大声呼喊,以释放种种的压力与困扰。那曲子中从自然而来的气息沁人心脾,采撷的大自然音符滋润心灵。用透明的,神秘的,陌生的,缥缈的,充满朦胧气氛的音色,让他忘却这个压力重重,繁杂喧嚣的世界。它让自己那个不安分的灵魂,不渲染,不激动,一切安然听命于自然的流露和命运的安排。
虽然在喧嚣中不能理解这种感受,当自己爱的人,成为了别人的另一半的时候,这种感受,只有深在其中的人知道是何等的滋味。
他仿佛被这音乐的涓涓细流把自己的躯体一点点分解,注入湖中。
不是吗?很久以前,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仿佛音乐告诉你爱过了她,你应该觉得幸福。
他被这音乐攫住了灵魂,正双手伸平,昂着头,挺着身躯在向阳光的天空飞升。
铺着绿牡丹的棉线单子,盖着一条粉红的被单的老桐像在欣赏一幅美术作品似的看着空中的谁。
音乐似水般流出鸟声,花语,泉水潺潺流动,风吹飘雾。这时有人敲门声,他没有动。好像是一道白光进了屋,来到近前。他嗅到了音乐之中的茉莉花香气,他颤抖地起来,几乎要哭出声来,他知道谁在近前。那双纤细的手捧住了他的脸,长满胡子的脸。
他终于没有哭鼻子,而是颤声地问,你终于回来了,告诉我那是一支什么曲子。
她泪流满面,亲着他的脸说,亲爱的,是班得瑞音乐。
外面梧桐树叶在秋风中舞动,一只金色的鸟在树上跳来跳去,不知在唱着什么美妙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