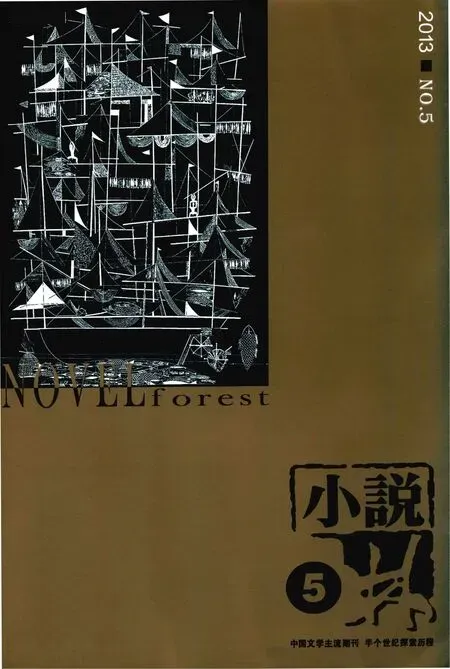一座城市的诱惑
◎墨 凝
这些天我和妞妞一直分着睡,我睡外间卧室,她睡里间卧室。
半夜妞妞推开外间卧室的房门,赤身裸体站在床边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在梦中。妞妞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就像一条身体微凉的泥鳅,哧溜钻进了被窝,手直截了当就奔向我的下身。我的下身和我的上身一样,疲软无力,一蹶不振,处于深度睡眠中。
妞妞说了句脏话,忽地掀开开满紫荆花的夏凉被,把我赤条条地晾在床上。她一骨碌下了床,连拖鞋也没穿,脚掌摩擦着地板发出细微的声响。她光着身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黑暗中她在茶几上摸到“红河88”,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啪地打着了火机,点着了,随手把火机扔在玻璃面的茶几上,又是一声脆响。
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能睡着,那我就真是猪了。我睁大眼睛,望着屋顶,屋顶是一片虚无的黑,我就对着屋顶说,别瞎折腾了,睡觉吧!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呀,睡不着!妞妞的声音就像屋顶上的黑暗冷丁压下来,我感到透不过气来。
沉默中,我能听见她在沙发上抽烟时发出的呼吸。我想象着妞妞一个人光着身子在客厅沙发上吸烟的落寞,就再也躺不住了。
我直挺挺地走进了客厅,从她手里抢过香烟,按死在茶几上。妞妞说过,她抽烟的样子很拽,可我按死烟蒂的动作也一定很拽。在她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把她按在了沙发上。黑暗中她瞪大了眼睛说,你干啥呀?我学了一句她的语言说,你懂的。可我怕她不懂,就补充了句,给你疗伤!
自从她随我从云南来到黑河后,她就一天天开始萎靡、颓废、消沉。刚开始是轻度的失眠,最后是整夜不能眨眼。本来她已经很久不吸烟了,可失眠的折磨和痛苦让她又开始吸烟了。女人吸烟和男人借酒消愁没什么区别。妞妞吸烟只吸一个牌子的,“红河88”。而且从不自己去买,总是以黑社会般的口吻指使我说,给买包烟。我不动。她就更加强硬起来,别磨叽,到底给不给买!于是我就显得很贱地颠颠跑下楼,买回了烟,还要捎带回一只打火机。
一次没有“红河”,我就买回了一盒“哈尔滨”。我觉得都是烟,吸一口冒烟也就行了。就像借酒浇愁的人,大都不会在意酒的品牌。可妞妞却把我买回的“哈尔滨”烟扔出老远。说,我只抽我们家乡的烟。没有“红河88”,“云烟”也行。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样矫情。别把我的溺爱当成你放纵的资本!
她说,你别磨叽,我不抽了可以吧。
我把那包“哈尔滨”香烟捡回来,扔在沙发上。刚才我们在沙发上翻滚的时候,有东西硌了下我的腰,用手摸出来,香烟盒已被压扁了。
我知道不被原谅/心该往哪里游荡/是谁划走我们的船/能让你死心地向往/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启航/夜晚的美有多长/思念情绪在发狂/风筝一辈子只会为/一根线在天空飞翔……
妞妞起身到卫生间连灯也没开,冲洗了下身子,就走回里间的卧室。卧室里立刻传来樊凡带死不活的歌声。
笔记本电脑就在床上。可以趴着,坐着,躺着玩。妞妞登了QQ,打开了空间。樊凡这首《燃烧的翅膀》,就像燃烧的寂寞,成了她空间的背景音乐。每次她打开空间,这歌声都带着一种穿透力,穿透宁静或忧伤。
妞妞说过,可以没有男人,但不能没有电脑。搂着电脑睡觉,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之所以和她分着睡,和电脑有直接关系。我想睡,她却没有睡意。噼里啪啦把键盘挠得山响,她的小手像猫爪遇到了键盘,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灵活。我不想睡的时候,她却搂着电脑睡着了。
有时候我强行把她从电脑上扯下来,硬搂进被窝。她却喊,你这是强奸。一撒手,她又把铁丝腿的床上电脑桌搬到眼皮底下说,怎么我都睡不着。不玩电脑,我会死。
惹不起,我还躲得起。于是我就到隔壁卧室睡。她愿意噼里啪啦挠到什么时候就挠到什么时候,我索性不管了。管也管不了。
我横躺在沙发上,手里摆弄着那盒压扁了的香烟,放在鼻子下闻着。一丝诱惑的烟味,透过精美的包装,抵达我的肺腑。我拆开香烟,弹出一根,虽然有些弯曲,但还是香烟。我把烟叼在嘴上,打着了火机。我是从不吸烟的,刚吸一口,就被呛得嗓子眼发痒,想咳。可我憋着,我不想咳出声来。
可我还是听见妞妞光着脚下床的声音,“唰唰唰”一阵脚面摩擦地板的声响,她就站在了我面前,依然是光着身子。
我没有抬头,可我能感觉出一双明亮的眼睛正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妞妞的不足就是皮肤有些黑,可眼睛大而明亮,睫毛也长,大眼睛弥补了她身上的不足。她最骄傲和最在意的也是这点,在深圳宝安区福永一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一个女孩伸手去摸她的睫毛,看是不是假的,被她一巴掌打开了。你妈,你的睫毛才是假的!
人长得黑,长长的睫毛再被说成假的,还让人活不!妞妞的性格有些不像女孩,缺少女孩的文静和温柔。妞妞对我说这件事不久,和我一起逛中央街重城商场,在一家化妆品柜台前,妞妞挑选睫毛膏。可柜台的女主人忽然惊讶地说,呀,你的睫毛真长,接的吧。妞妞“啪”地撂下手里选好的睫毛膏,扯着我就走,睫毛膏坚决不买了!
妞妞站在我面前,伸手从我的嘴里抢过香烟。你再抽,你就死定了!黑暗中她的眼睛瞪得很圆,长睫毛忽闪着。
她嘴上叼着抢过去的香烟,转身回到卧室的床上,继续聊天。我知道她聊天的QQ好友,几乎都是深圳的朋友或死党。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摆弄着压扁的烟盒,心里有些不舒服,甚至恼火。
妞妞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至少还有女孩的羞涩。可现在居然毫无避讳地光着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虽然拉着窗帘,虽然是黑夜,可我还是感到不是那么回事。
女人还是矜持点好。为此我说过她,可她总是有一百句等着我。你就装吧,最恨装B了。
改变什么都别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因为伤不起。
外面微弱的光亮透过粉色的窗帘,天已经放亮了。我走回卧室,迅速穿上了短裤。然后穿过客厅,拉开窗帘,走到阳台前。外面除了扫大街的,还有包宿的学生三三两两走出对面的网吧,路上偶尔有蓝色的出租悄然驶过。
妞妞的卧室里已经没有了声音,每天到了这个时间,大约早晨四点多的时候,她才会下线,或抱着被子蜷缩着,或放肆地伸展开手脚,在疲惫不堪中昏睡,一直睡到下午一点多才能起来。也许她的失眠不是失眠,而是把睡眠弄颠倒了。
以前她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就是这样晚上加班,白天睡觉。那时候虽然累,但很幸福。开工资的时候,她就和罗楚金出去喝酒。罗楚金是她的男友。
罗楚金是湖南人,做得一手好湘菜。妞妞喜欢吃辣的,他炒的菜正合她的口味。每天都是男友炒菜做饭,妞妞洗碗。早晨牵着手去上班,晚上趴在床上看电视。妞妞喜欢看周立波的脱口秀,罗楚金就陪着她看。
在外面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几杯啤酒下肚妞妞就会显得很兴奋,又蹦又跳又唱的。罗楚金说,我老婆是酒疯子,沾上酒就疯。
两个人虽然好到了相互称呼老公老婆的程度,可两年后还是分了,似乎没有原因。这年头就是这样,分与合不需要原因。
妞妞是云南怒江傈僳族的,能歌善舞。这些东西不用学她就会,因为她就是那个品种。这话是我说的。她喜欢唱本民族的歌曲,也喜欢唱快歌。
傈僳的歌曲我听不懂,可没关系,因为她很少唱,只有喝多了的时候才唱。即使去酒吧和歌厅,也没有傈僳的歌曲,所以她唱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我能听懂的快歌。比如蔡依林的《说爱你》:
一开始,我只顾看着
你装做不经意,心却飘过去
还窃喜,你没有发现我,躲在角落
忙着快乐,忙着感动
从彼此陌生到熟,会是我们从没想过
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这一大段“Allegro”她一口气叨咕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喘不过气来。可她面不改色,轻松得很。跳舞她也喜欢激烈的,她的头、腰、臀扭起来是那样的漂亮、和谐、性感,就像无骨的蛇。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她上辈子是舞娘。
第一次和妞妞见面,是在云南西部客运站,也就是这个时辰,早晨四点多。那时她和罗楚金分开不久,分开后她就离开了深圳,跑回了老家。晚上在兴苑路曾氏宾馆8511大床间,她要和我拼酒。于是我们去附近沃尔玛超市买回了十二罐易拉罐啤酒,几袋牛肉干。又在宾馆下面的饭店要了两个简单的小菜。回到房间,我们开始喝酒。
还没喝上两罐,她就开始耍赖。甩掉拖鞋从地上跳到床上,在床上撒娇,又蹦又跳,就是不下来。
她不喝,我也不勉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和女人较真。
她娇小的身体,让我有怜香惜玉的不忍。可能是那晚我喝多了的缘故,洗澡上床后,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就忘记了怜香惜玉。
第二天起来,她用一种娇嗔的眼神看着我。我本想说一句歉意的话,可说出的却是,想不到你还挺扛折腾的。她很干脆地瞪了我一眼说,你妈!三个字的骂人话,被她省略了一个字,性质就变了,也耐人琢磨了。我被她的可爱逗笑了。
本来妞妞随我来黑河,是不想再去深圳继续打工了。我们说好了,做生意。开个对俄罗斯的商店,老毛子的钱好赚。实在不行,兑个旅店,盘个酒吧也行。
我们收集街上发放的各种信息小报。小报上什么信息都有,买房卖房的,出兑招聘的,寻狗找人的,挂失认领的……
新年后,我们几乎足不出户,每天都把头埋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小报里,哗哗地翻着,翻得手指都是黑的。在流水般的声响中,我们寻找着希望。一天我说,要是天天这样哗哗数钱就好了。妞妞撇了撇嘴说,你咋笨成这样?有这些钱谁还用手数,放点钞机里唰唰就完事。
这期间顺着报纸上的信息,我们去过文化街“123酒吧”和兴安街一家半地下的旅店。妞妞说,去酒吧和旅店都要晚上去,晚上才能看出效果。
看不出,你还有点经济头脑。我说。必须的。妞妞很得意。
在云南和妞妞去过几次酒吧,我们去的酒吧在一个胡同,狭长的胡同里“夜色镇”、“彩之南”、“98主题”一家挨着一家清一色的小酒吧。小酒吧大都是对兜里没有多少钱,晚上无聊想找个地方发泄或胡闹的年轻人的,光喝酒不吃菜,顶多来上一包十块八块的瓜子和爆米花。酒水七十到一百二十元钱一打不等,一打十二瓶。歌曲是碟片里放出来的,听起来乱糟糟的,和酒吧的气氛很相配。
我,妞妞,还有妞妞的朋友阿白兔,阿白兔的男朋友小勇,去过几次“夜色镇”酒吧。酒吧里灯光昏暗,墙壁色彩陈旧,酒桌的木板有几寸厚,火烧火燎的颜色。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酒吧,听着山人乐队的“三十年前找不着,今天找到了。今天找着小姑娘,不是我的哟。可惜了,可惜了……不是我的哟。”不郁闷的人也会郁闷起来,那些已经忘记的和正在忘记的往事,忽然间就涌上了心头,脸上是笑容,心里是苦的。似乎是灯光下泛着暧昧泡沫的啤酒和我们过不去。一杯接一杯地往下灌,灌得天昏地暗。妞妞的心里一直没有放下罗楚金,喝多了就一遍一遍拨打一个再也无人接听的电话,一遍一遍跑去卫生间喊着我要去深圳。阿白兔眉头紧锁,我命好苦,二十岁就在KTV里混,混了四年了,连个男人都没混明白。四年找了三个男人,第一个穷得要命,第二个吸毒,小勇是个卖臭豆腐的,我不嫌弃。可他比我小三岁,就以小卖小,袜子都是我给洗。小勇去厕所的时候,阿白兔边说边落泪,她哭的时候很迷人。小勇从卫生间回来的时候,阿白兔已经擦干了眼角的泪痕。小勇一副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我苦笑,端起酒杯和他撞得山响。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自寻烦恼,动不动就无聊、颓废。坐在酒吧里“抽一口烟、喝一口酒、撩一下头发”神吹海聊一通,立马就找到了自我。如果能设计个像“夜色镇”那样主题的酒吧,让年轻人夜夜在里面疯,在里面寻找,然后让他们的情绪顺着卫生间的马桶,哗哗地流走。钞票也就会哗哗地流进我们的兜里。
这样想着,我和妞妞在一天晚上八点多,去了“123酒吧”。老板在电话里告诉我们说,酒吧里六个单间,四张卡桌。环境老板一点没夸张,和电话里说的一样一样的。夸张的是没人,酒吧里空荡荡的,老板一个人抱着吉他在吧台里哼哼呀呀着。出了酒吧,大街上空荡荡的,我和妞妞的心也空荡荡的。
酒吧在北方不好使啊,我们北方人没下酒菜是喝不下酒的。我说。
妞妞没有搭理我,而是唱起了酒吧老板在我们进去时哼哼呀呀唱的曲子:道边没JB树,河里没JB鱼,刮风下雨……
旅店我们也是晚上去的,进去了,我们就出来了,几乎没有站脚。昏暗的灯光下坐着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女人,老女人面前摆着一张学校废弃的秃了三个角的课桌,显然她是店主人。店内散发着一股腐朽的气息,似乎是从她身上发出的。
妞妞逃也似的边走边说,真要兑了这样的店,用不了多久,我也和她一样发霉了。
跑了半个月,我们也没有找到一家满意的。妞妞总结说,人家不要的,就一定不是好的。不找了,歇歇吧。
妞妞不抱希望了,我也泄气了。毕竟开店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没有了哗哗翻报纸的声音,日子就在寂寞中枯燥下来。就像一条汹涌的河流,仿佛一夜间就停止了流淌,河床露出来,裂痕开始向深处纵横。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妞妞有了变化的:信息报一眼不看了,不是整夜抱着电脑不撒手,让自己深度失眠,就是斜躺在沙发上嘴里叼着一根烟,在我面前摆出一副颓废的样子。抑或像今天这样,一丝不挂忽然就出现在我面前,也不需要什么前戏,直接奔向主题,一种无法排遣或释放出来的压抑状态。
一个人对所爱的人就像对待一个易碎的花瓶,总是小心翼翼的时候,也许情感就疏远了。可我没有办法不对她好,一个女孩,一个在黑河没有一个亲人的小女孩。如果我让她不舒服,就等于全世界和她过不去。
我找借口不参加聚会,找理由不出去和朋友喝酒。只在家里陪着她。长这么大,只会做猪肉炖粉条、鸡蛋炒西红柿几个简单家常菜的我,在她“我知道不被原谅,心该往哪里游荡……”的QQ音乐中,我学会了南方菜:清炒油麦菜、肉片炒莴笋、葱花鸡蛋饼和油炸开江鱼……几乎每道菜都放辣椒。因为没有辣椒她饿着也不吃。我这样做不是让她感动或感恩,只是想改变她的心情。一个人的心情好了,一切也就会正常起来。
五月的一天,妞妞忽然对我说,陪我出去买几件换季的衣服好吗?她的衣服是该换了,去年秋天在云南买的那两套,颜色有些深了。
我们几乎半个月没有出去逛街了,走在街上,妞妞似乎有些陌生地对我说,你们这个城市怎么这样啊。城市不是谁的城市,可妞妞一个你们,就把自己从这个城市划了出去。爱一个人,爱一座城。我明白无论我怎么努力,妞妞最终还是要离开的,或许现在就有了离开的想法,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
黑河小城外表很亮丽,也很规矩。可妞妞就是看不惯。她说,为啥把房子都盖成洋葱头样的呢?
那不是洋葱头,那是欧式风格。和对岸俄罗斯的房子一样的风格。我耐心地对她解释说。这是近两年城市亮化工程的结果,最初楼顶也是平的。
妞妞说,哦,我明白了,在深圳叫穿衣戴帽工程。我说,对,一个意思。
可我不明白。妞妞说,为什么跟着人家屁股后跑,学他们的风格?这不是崇洋媚外吗?
我说,这和崇洋媚外没关系。
妞妞说,那和什么有关系?
我说,我不清楚。
妞妞说,还是嘛。
我无语。因为现在有些事情谁也说不清楚。我承认妞妞虽然偏激,但一针见血。记得去年我们议论南海问题,她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她说,武大郎无能,怨不得西门庆猖狂。
上了招手停,妞妞说,这就是你们城市的公交车?
我说,在黑河不叫公交车,叫招手停。没有固定的站点,路边上你一招手,车就停。冬天的时候,伸不出手来,抬抬脚——车也停。
这叫啥玩意儿呀。妞妞一脸的不屑。我说,自动投币,挺方便的。除了车型小点,和大城市里的公交车没啥区别。
妞妞没有接我的话茬,而是用挑剔的目光在车内扫视着。她指了指自动投币系统下的铁箱子。铁箱子上是两行不干胶粘贴的红字:亲朋不交一元钱,司机被罚十元钱。
知道深圳公交车上写的是什么吗?妞妞说,“来了,就是深圳人。”、“文明让我们快乐。”
话题越扯越远。我不想再扯下去,就说,这和我们有关系吗?
妞妞说,没关系。
到了华富商场,和妞妞转了几圈,也没买成一件衣服。妞妞不是嫌花色不好,就是嫌样式不新颖。
陪女人买衣服很麻烦,可我还是耐心陪着。每试穿一件她都要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的,她都看不中。她看中的,我看着都不好看。记得第一次给她买衣服是在丽江,因为第二天要去玉龙雪山,她身上穿着单薄的T恤,怕她冷,我带她去了美特斯邦威。她试着一件黑色的半截纺织面料秋装,在镜子前扭来扭去,问我,好看吗?我说,你穿什么都好看。她说,那买吗?我说,买。于是开票,交钱。就这样简单。事后,妞妞抱着我的胳膊说,第一次穿这么贵的,三百多块呀,让我妈知道一定给骂死了。可今天我们总是猴吃麻花——满拧。
转了一下午,只买了两件内裤,一件我的一件她的。走出华富商场的时候,我说,你还是去深圳买吧,深圳一定有适合你的。
她瞪着不瞪就已经很大的眼睛瞪着我,半天也没有说一句话。转身下台阶的时候,迎面她和一个边走边打电话的男人撞在了一起,那男人看了她一眼,眉毛挑了一下,连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
妞妞喊,你给我回来!那人站住了说,你想咋的?
妞妞说,请给我道歉!
那个男人眉毛又挑了两下,转身又走。妞妞还要喊住他。我说算了,他也不是故意的。
妞妞不平地说,我最讨厌这种不懂礼貌,又牛哄哄觉得自己很拽的男人。拽什么拽呀,说句对不起很难吗?
晚上,玩着电脑的妞妞忽然就不玩了。喊我说,以后我不玩了,你玩吧。我不知道她发的是什么神经。嘴里说好,我玩。可我没有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女真的小说《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
妞妞说不玩就真的不玩了,我以为她累了,就走进卧室。妞妞佝偻着,用被子蒙着头。我感到不对劲儿,就一下掀开被子。一脸的泪痕的妞妞,把我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想家了吗?想家我送你回去,别哭啊。我有些手足无措。
你别管行吗?她的声音里全是无奈和委屈。
你在我面前,我不管谁管?
妞妞用从没有过的无助看着我说,罗楚金结婚了,结婚前他已经是部门管理了。和我相反,他做什么都认真。
接受事实吧。
我知道他早已经不是我的了,可他结婚的消息,还是让我接受不了!我要回深圳,从零做起,我不能被人看扁!
没人看扁你。我说。
你不懂。她说。
第二天,妞妞一改常态,很早就起来了。起来后头不梳脸不洗,站在窗前一直向外望。外面是一条繁忙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七层的住宅楼。
她在深圳打工的时候,住的是工厂宿舍。宿舍的对面是马路,很早就有人起来,在马路牙子上支起小摊床。什么外婆串串香,麻辣油饼,茶叶蛋,土法烤鸡,扑克鞋垫……妞妞在深圳过第一个生日那天,罗楚金就是在小摊上给她买回了一只棕色的毛绒泰迪熊。妞妞好喜欢,睡觉的时候也放在枕边。还用手机拍了几张不太清晰的照片,传到了空间里面,分享给所有的QQ好友。马路的对面是一家电子厂,电子厂两班倒,整夜都灯火通明。妞妞就是在这家电子厂上班。罗楚金上班的时候,她就站在窗前望,她知道他在那个窗口里面工作。她上班的时候,他也站在窗前望,因为他也知道她在那个窗口后忙碌。
哗哗翻信息报纸的声音没有了,现在噼里啪啦敲打键盘的声音也消失了。生活安静得有些可怕。妞妞每天都站在窗前向外望着。此刻,一个城市成了她的牢笼,一个城市成了她的梦想。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她望到第十天的时候,我把两张车票放到她的面前。她拿起车票陌生般地看着,看着,眼睛里就蒙上了雾水。
我送你去深圳。我说。
我欠你的太多了。她说,还是我自己走吧。
就让我送你到哈尔滨吧。我擦去了她脸上冰凉的泪水说。
她感激地抱了抱我,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晚上,我和妞妞登上了K7036次,黑河——哈尔滨的列车。
两天后,我把她送上哈尔滨——广州的T238次列车。她说你下车吧。可在我转身的瞬间,我看见她的脸色好苍白,眼帘无力地垂了下来。她的表情让我忽然想起,在昆明玛利亚妇产医院我们打掉第一个孩子的情景。
我在外面等着,护士把脸色苍白的妞妞从手术室里推出来,在门口她看见我,无力抬起头,无力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无力地垂下了眼帘。
我的心忽然间好痛,除了不舍,更多的是担心。我了解她的脾气,没有在车上停留。
可我从这节车下车后,绕到后面,又从另一节车厢上了车。我上了车,车就开动了。我补了一张去广州的车票,我要默默地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
T238次列车在运行三十七个多小时后,终于在我昏昏欲睡中抵达了广州东站。一路上我走到她乘坐的车厢,远远看过她几次,都没有被她发现,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悄悄跟着她。她的左边坐着个中年妇女,手里捧着本《读者》合订本,看得入神。前面是一个头发蓬乱的民工摸样的年轻人,低头吹着刚泡好的“康师傅”。年轻人的身边是个胖子,胖子的头斜靠在背椅上,昏昏欲睡中不断地嘎巴着嘴,像是嚼着什么美味。
列车一站一站停泊,又一站一站出发,把一个个终点,变成起点。如果人生的终点和起点,也像列车一样有着轨迹,我们是否都能准确抵达呢?妞妞蹙眉发呆,她在想什么呢?
车上我们发过几次短信,我问她到哪里了的时候,车正驶进长沙站。她的短信也飞进我的手机,打开短信是简洁的两个字:长沙。我想笑,可笑不出来。
这之后我就睡着了。在要下车的前十多分钟,我跑过去找她,可是座位上已经没有了她的身影。去问周围的人,周围的人都摇着头,奇怪地看着我。
她是在什么时间,什么站下的车呢?为什么没到站人就不见了呢?她究竟去了哪里呢?一堆的疑问,像梦,我找不到答案。
心该往哪里游荡,是谁划走我们的船,能让你死心地向往……一首熟悉的歌在耳旁缠绕着。不知道是响自心底,还是来自外面。
我一个人走出广州东站,我知道深圳不远了。可我没有继续往深圳方向走,而是迷茫地向一座陌生城市的深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