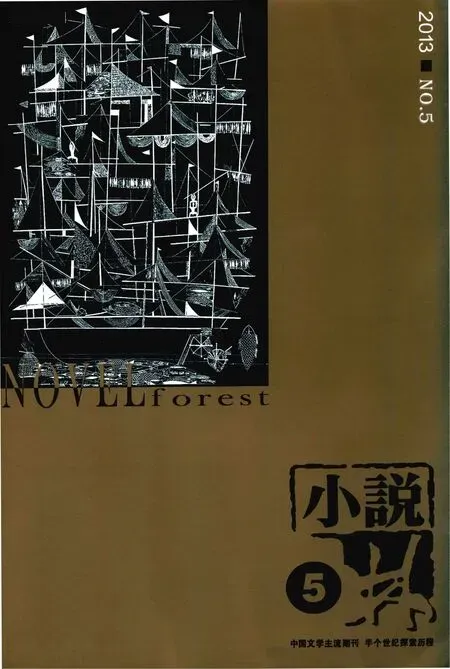斑鸠
◎张建祺
一
圈子已经醒了,但是懒得起来,于是躺在床垫上抽烟。
这个小房间里只有两件家具,一件是这张放在地板中央的弹簧床垫,另一件是他用木板钉在床头的小架子。架子上有一个很老的金属闹钟,旁边摆放着几个小纸盒,在监狱服刑的那几年,他的工作就是糊这些纸盒。
圈子一边抽烟,一边望着窗口。透过两扇窗帘间一米宽的缝隙,他看到一群鸽子在这片狭窄的天空中往返穿梭,这使他有些想念他的那些鸽子了。
抽了两支烟,圈子摸起拖鞋边上的《圣经》随手翻开,读到了《利未记》第十二章:“她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她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她赎罪,她就洁净了。”
在这段话里,圈子有四个字不认识。
“操,这说的都是啥呀?”
圈子叨咕着,将《圣经》丢到一边,穿上拖鞋走出房间。
圈子的老娘住在另一个屋子,听到这面发出响动,就喊他。
他正举着餐桌上的茶缸子往嘴里灌凉白开,没法应声。
“圈子!”老娘的声音提高了些。
圈子放下茶缸子,皱着眉推开了老娘的房门,一股熟悉的恶臭扑鼻而来。
“哎呀,我去他奶奶的……”圈子挥手在鼻子前扇着,“妈,这大热的天你怎么不开窗啊?”
“我怕受风。”
圈子走到床边,拉开老娘盖在腰间的毯子看了看。
“今天感觉咋样?”圈子问。
“疼。”
几年前,骨癌使她的右腿从膝盖部分被截掉了,去年复发又截到了腿跟,如今手术创面长满了菜花状的东西,房间里的恶臭就是由它发出的。
圈子把她的毯子盖好,问:“你叫我啥事?”
“我想让你帮我把加湿器打开。”她说完拉开毯子,重新亮出了长着菜花的右腿跟。
圈子打开加湿器等了一会儿,水雾喷薄而出。
“这玩意儿有用吗?”圈子盯着这台熊猫造型的加湿器。
“大夫让我用的。”
“大夫?他们的话全是放屁,”他说着弹了熊猫一个脑瓜崩,“你药吃了吗?”
“我没水了。”
“你早喊我啊。”
圈子出去给她的保温杯续满热水端了回来,放在嘴边轻轻吹着。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上班?”
“这阵子公安抽风,又他妈抓赌,麻将馆得关一阵子避避风头。”圈子说。
“早就让你找个大酒店,当个正经八百的保安。”
“你以为大酒店里就干净?窝娼聚赌更邪乎,我还得跟傻逼似的在大厅杵着,处处受人管不说,工资还比现在少四百。在麻将馆我愿意坐就坐着,愿意躺就躺着,一天一包好烟供着,中午一荤一素吃着。”圈子抿了一口水,说,“能喝了。”
老娘把床头柜上的几个药瓶子依次打开,汇聚了小半把药片和胶囊,一股脑儿塞进嘴里。
“看你这么吃药都瘆的慌,别噎着。”
她喝了口水,仰头把药顺了下去,问:“你一会儿干嘛去?”
“玩儿。”
“三十好几的人了,总出去瞎玩儿什么?”
“还不是为了躲你们教会那帮老太太,没见过这样的,一下午一下午在咱家泡着,还连嚎带叨咕的。”
“啥连嚎带叨咕,我们那是唱诗祷告,对了,你今天祷告了吗?”
“嗯。”圈子含糊地应着。
“把昨晚的粥给我热热吧。”
二
傍晚,圈子走出街口的台球室,穿过十字路口,走进了东升街夜市。
夜市上灯火通明,卖小吃和小商品的摊床排列在路边,人行道上是一家又一家的烧烤大排档,豪饮啤酒的人们大声喧哗着。
在卖麻辣串的铁皮车和炸臭豆腐的小摊之间,大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前摆着一个正方形的炭火炉,炉上的铁网整齐地排列着几十个毛蛋。
圈子在炉子前蹲下来,看着大胜。一直低头摆弄毛蛋的大胜抬起头,目光撞上近在咫尺的圈子。
“操,吓我一跳!你啥时候回来的?”
“有一阵子了,”圈子递给大胜一支烟,“下午在台球室玩的时候听说你在夜市,好家伙,这顿好找,你替刘瘸子在鸭子圈蹲了好几个月,他就给你这么个破地方?”
“不错了,一分钱不用交,干赚。”
“卖这玩意儿能赚几个子儿?”
“你可别小瞧这东西,我在孵化场成筐收,在这论个儿卖,你笨寻思,一本万利啊。”
“别他妈吹了,哎,赵秃子现在干啥呢,你把他整过来,咱哥仨聚聚。”
“你还不知道呢?”大胜惊奇地盯着圈子,“让人家扎死了。”
“啥时候的事?”
“就去年这个时候,有人欠了点儿钱,找他去平事儿,秃子还以为自己多好使呢,在家吃完晚饭,穿着个大裤衩子,趿拉双拖鞋就去了,到茶馆,人家对方连话都没和他说,掏刀直接干死。”
“那帮人哪儿的啊?”
“听说是打南方过来的一帮,”大胜给几个毛蛋翻了个儿,问,“你现在整啥呢?”
“孙三儿承包了个社区活动中心,开麻将馆,我在那儿帮忙呢。”
“听说孙三儿这逼养贼抠。”
“对我还行。”
“郭傻子在开发区整了个夜总会你听说了吧?挺大扯,养了一帮小崽子给他看场子,你要是过去的话肯定比现在挣的多。”
“拉倒吧,他买卖太大,不好干,”圈子拿起一只毛蛋吹了吹,“你怎么不过去?”
“那帮小崽子里有几个以前是黄四喜手底下的。”
“大汽上摸包的那帮?”
“对,就他们,我跟他们不对付。”
圈子剥开毛蛋咬了一口。
“我可不是舍不得东西,”大胜说,“我这毛蛋你少吃,不干净。”
圈子把嘴里的毛蛋吐了出来,手里剩下的大半个扔出老远。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晃晃悠悠地在夜市走着,一路上向大排档里吃饭的客人推销着他手里的赃物手机。
“小五子,过来!”大胜招呼着。
小五子颠儿颠儿地跑了过来。
“去,给我整点儿大串,再整几瓶啤酒,要凉的啊。”大胜说。
“哎,”小五子答应着,转头看到了圈子,“呀,圈子?”
“去你妈的!”圈子踹了小五子一脚,“圈子也是你叫的?叫爷。”
“爷。”
“滚吧!”
小五子转身跑向不远处的新疆烧烤摊,过了一会儿,举着一大捧羊肉串跑了回来,随后又提来几瓶冰镇啤酒。
“给我看看你的手机。”圈子说。
小五子像变戏法一样,从衣服和裤子口袋里掏出七八个手机。
“这个给你三十行吧?”圈子掂着其中一个。
小五子迅速把手机夺了回来,一把塞进裤裆里,脸都绿了。
“这是苹果的。”小五子说。
圈子一只手捏着小五子的脖子,另一只手要从他的裤裆里掏手机,小五子挣扎着。
“操,你是不是欠削?手拿开,麻溜儿的。”
小五子仍然死死地护着裤裆,说:“爷,要不然你揍我一顿吧,这手机少一千我肯定不能卖。”
圈子松开手,在小五子屁股上踢了一脚,小五子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看着他的背影,圈子问:“谁跟我说的来着,说这小子当年犯了点事儿,他爸捆一身炸药去派出所把他要出来的。”
“听他吹去吧,”大胜喝了口啤酒,“他爸就是个打工的,鞭炮厂爆炸给炸死了。”
圈子吃着羊肉串,盯着炭炉上的毛蛋,突然想起了早晨在《圣经》里看到的一个生字。
“哎,我问你个字儿,左边是个七八九的九,右边是个鸟,是啥字?”
大胜琢磨了一下,说:“应该是种鸟吧。”
“我还不知道是种鸟?我是问你这字念啥?”
“那谁认识去?”
“你不是卖毛蛋的吗?”
“毛蛋又不是他妈鸟下的。”
三
圈子和大胜喝到很晚,两人面前的炭炉早已熄灭,泡大排档的人也大多散去,一阵阵微风吹来,带着路旁沉积的馊泔水和尿骚味。
往家走的路上,圈子见街口的拉面馆还亮着灯,于是进去点了一碗拉面,用两层塑料袋装着带了回去。
圈子轻轻打开门,蹑手蹑脚换拖鞋。
“回来了?”老娘在房里问。
圈子推开她的房门。她床头的台灯亮着,肚子上倒扣着打开的《圣经》。
“我给你带拉面了。”
“我不饿。”
“明天我去一趟向阳乡。”
“干嘛去?”
“上我七舅家取鸽子,都和大胜说好了,借他那台小面包车去。”
“晚点儿去吧,先去相个对象。”她把肚子上的《圣经》合起来放好,“今天唱诗班你孙姨来看我,说给你物色了个姑娘,二十四,带着个不到五岁的丫头。”
“离异的?”
“丧偶,男人死两年了,以前开车跑长途运输,在高速公路上撞死的,你孙姨说这姑娘挺能干的,在咱们东区菜市场烀苞米卖。”
“二十四……”圈子琢磨着,“岁数小点儿吧,人家能愿意吗?”
“她家是乡下的,现在领着闺女在这儿租房住呢,人家提出的条件就是城里户口,有房子,别的啥也不挑。”
“她知道我的底子吗?”
“你孙姨没跟她说,就说你在一家私企当保安,等你俩处好了,再慢慢渗透吧。”
“你们这帮老太太也挺能忽悠啊,”圈子笑,“不是信教不让撒谎吗?”
“去去去,”老娘推他,“早点睡觉,明天精神头儿好点儿。”
回到自己房间,圈子拉好窗帘,轻轻挪开地上的床垫子,抠开一块地板,取出一个绒布包裹的小包。他将绒布小心翼翼地展开,露出一支乌黑的“五四”式手枪。
这支枪是圈子他老爹当年在工厂保卫科工作的时候搞来的,他无意间发现了老爹藏匿的这件宝贝,连圈子他老娘都不知道这支枪的存在,老爹去世之后,圈子就将它藏了起来。虽然圈子从来没把枪拿出过这个房间,更没开过枪,但是拥有这支枪,使他心里觉得特别踏实,他始终认为有了它,就一定能干大事。
圈子拉出弹夹,将里面的四颗子弹退出来,放在手里掂了掂,仔细观察了一阵,又一颗颗压进去,然后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潇洒地将弹夹拍进枪内,举枪慢慢对准房内的每一面墙,最后,他认真地瞄准天棚上的灯泡,嘴里学了一声枪响。
四
圈子的老娘一早就拄着拐来敲他的房门,催促他洗脸刷牙。
洗漱完毕的圈子从洗手间走出来,老娘递给他一件长袖白衬衫。
“这天气你让我穿长袖?”
“谁让你往胳膊上刺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着就不像好人。”
老娘将衬衫硬生生塞到圈子怀里。
圈子换好了衣服,从房间里走出来。等在门口的老娘仔细打量了圈子一番,伸手将他领口的扣子系严。
“妈,我看你是恐怕我热不死啊。”
“净瞎说,”老娘照着圈子的脑袋拍了一巴掌,“照照去。”
圈子走到门口,看着穿衣镜里的自己,皱着眉说:“我怎么觉着自己跟中学生鼓号队的傻逼似的?”
“我没看出傻来,你好好瞅瞅,多像知识分子。”
很像知识分子的圈子随站台上的一大群人挤上了公交车,尽管车上所有的窗子都开着,但还是像蒸笼一般,圈子的衬衫很快湿透了,他接连解开衬衫上方的三颗扣子。
开出两站之后,汽车前方响起了“叮叮叮”的警示铃声,横在马路中间的铁道旁,黄黑相间的升降杆缓缓降下,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女人在路旁挥舞着小旗子。汽车停下之后,一辆运载货物的火车从远处缓缓驶来,最终像蜗牛爬行一般在公交车面前一节节地展示着它的车厢,汽车上汗流浃背的乘客们纷纷咒骂着这辆火车的速度。
圈子一声不吭地看着车前经过的火车,这使他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当时也有一条这样的铁道横穿东升街,经常有运送货物的火车从那里驶过,圈子和大胜、赵秃子总是喜欢把铁皮瓶盖或者钉子放在铁轨上,然后坐在远处的路沿上等着火车经过时把它们压扁,那些压扁的瓶盖可以和别的孩子赌输赢,以赢来更多这样的瓶盖,压扁的钉子可以磨成小刀,用来刻木头或者肢解蜻蜓和蚂蚱。但是这种等待很不确定,有时火车很快就会来,有时则会等上小半天。
圈子和大胜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赵秃子把他那枚当做宝贝一样的金色瓶盖放在了铁轨上,然后跑到路边直勾勾地盯着它。偏偏那次火车来得非常晚,当火车由远及近的时候,赵秃子呼啦一下站了起来,像一个老人注视着几十年未见的情人一样看着火车,可惜当火车经过之后,那枚金色瓶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赵秃子那天哭得特别伤心,几乎是撕心裂肺。在他还活着的那些年,这件事经常被圈子和大胜拿来开玩笑。
汽车终于开动,圈子也从回忆中跳了出来,但是一个问题却难住了他——他怎么也想不起赵秃子的大名来。
到了东区菜市场,离汽车的终点站已经不远,所以车上没剩几个人。圈子下了车,发现天空中连一丝云彩都没有,火辣辣的太阳无遮无拦地烘烤着地面上的一切。
圈子来到菜市场入口处,抖着衬衫领口扇了扇风,又将两只袖子卷起来,走进冷冷清清的市场。
一辆掉光了外漆的小三轮车上点着炉子,炉子上是一只巨大的铝制闷罐,里面沸腾的水中塞着满满的苞米。这辆三轮车旁站着一个皮肤黝黑、有些微胖的姑娘,她就是孙姨介绍给圈子的淑娟。在淑娟脚边的地上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她穿着一双翠绿的塑料凉鞋,身上是皱巴巴的连衣裙,此时她正用苞米叶子折叠着什么东西,胳膊和腿上布满了被蚊子叮过的红疙瘩。
圈子抽着烟,站在不远处的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儿这对母女,然后用脚碾灭烟头走了过去。
初次见面,圈子和淑娟都很拘谨,简单打过招呼之后就再也无话可说。小女孩躲在淑娟腿后,一会儿偷偷看圈子左臂上那把线条粗糙的“尚方宝剑”,一会儿又看他右臂上那只构图拙劣的老鹰。
“今天货不太好卖?”圈子扬起下巴指了指那一大锅苞米。
“没到时候呢,一般中午饭那一阵这一锅就没了,下午还得再烀一锅。”
圈子苦苦思索,但再找不出什么话题。为了缓解气氛,他伸出手去,想摸一摸小女孩的脑袋,可小女孩头一偏,躲过了圈子的手,转身跑开了。
“慢点儿,别摔着!”圈子朝小女孩的背影喊道。
小女孩头也没回。
“她听不见,”淑娟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发烧弄的。”
圈子愣了一下,问:“也不能说话?”
淑娟点了点头。
“治不好了吗?”
淑娟沉默地盯着那锅苞米。
“要是能治就得尽量治,孩子这么小,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圈子说。
“谁都知道这个理儿,但是治病的钱咱一般老百姓家哪能拿得起,”淑娟低头舔了舔嘴唇,“这孩子天生命苦,认命吧,这就是我们娘俩的命。”
圈子点了支烟思索着,但也没想出什么解决办法。
“孩子叫什么名?”圈子问。
“赵兰芳,小名芳芳。”
“芳芳……”圈子嘟囔着点了点头。
一支烟的工夫过后,圈子向淑娟告别,并约她有空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出来吃顿饭。淑娟拿出一个塑料袋,装了几个苞米,非要让圈子带回去,圈子自然不肯要,但是淑娟拎着苞米追出去很远,圈子实在推辞不过,只好一手接过苞米,另一只手从兜里掏钱。
“你要是拿钱,就是埋汰我。”淑娟按着圈子口袋里的手,双眼盯着他。
圈子发现,这个年轻女人的眼里有一种特别坚定的东西,虽然他无法彻底了解其中包含着什么,但这双眼睛投射出的眼神却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五
圈子到大胜家的时候,他正和一个面色苍白、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喝着酒。
“二毛子,你应该认识吧?”大胜向圈子介绍那个人。
“知道,桥北大毛子他弟弟嘛。”
圈子坐下来抓起一绺豆腐丝放进嘴里,刚嚼两口就吐了出来。
“都他妈馊了!”
“谁让你现在才来,没看这是啥天气。”
“你俩都喝一上午了?”
“可不咋的,就等你了,你不说早晨过来取车吗?”
“办了点儿事,耽误了,”圈子朝大胜伸出手,“车钥匙给我吧。”
“都这个点儿了,你还往乡下跑啥,消停坐这儿喝酒吧,哪天再去。”大胜按着圈子的肩膀。
二毛子拿起一只杯子控了控水,给圈子满了一杯白酒。
“二毛子也刚回来吧?”圈子问。
“一个礼拜,”二毛子说,“社会变化太大了,就说公共汽车吧,非得前门上后门下,车上也没卖票的了,说什么主动投币,还有‘嘀嘀’打卡的,都给我造蒙了。”
“正常。”圈子举杯与二毛子撞了一下。
“我刚才还和大胜聊到你,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二毛子说。
“还凑合吧,你呢,回来有啥打算?”
“大胜要整个买卖,我琢磨着跟他干。”
圈子差点一口酒喷出来,笑着指大胜:“我操,就他?前天我跟他一起在夜市喝的酒,他那买卖我亲眼看着呢。”
大胜说:“不是,你听我说……”
“啥不是?”圈子打断大胜,“你自己说,那一晚上你总共卖出去几个毛蛋?我都不好意思埋汰你——六个!”
圈子说完笑个不停,而大胜和二毛子却面无表情。
“大胜研究的是个大买卖,”二毛子严肃地说,“他说你今天过来取车,寻思咱哥仨一起研究研究。”
“啥大买卖?我听听。”圈子点起一支烟。
“东升街口的工商银行。”大胜说。
圈子认真地看着大胜,随后又笑起来:“不可能,你俩别他妈逗我了。”
“这么跟你说啊,”大胜严肃地看着圈子,“一会儿喝完酒,你就滚你的蛋,我和二毛子单独商量,省着万一事儿炸了再粘上你,成吧?”
“操,说的就好像我怕事儿似的,”圈子笑,“我现在也他妈穷得腚眼冒光,一块儿商量商量吧。”
三个人边喝边讨论,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掰扯了半天,最终敲定了一套。
天黑下来的时候,二毛子喝不动了,要先走。圈子和大胜起身送他,二毛子刚走两步就一屁股坐地上了,圈子和大胜连忙把他搀了起来。
“没事吧?”大胜问,“不行就在我这儿住吧。”
“我没事,”二毛子摆了摆手,“就是太长时间没喝酒的事。”
目送二毛子出了门,圈子和大胜又回到桌旁。
“他是因为啥事进去的来着?”圈子问。
“吸完毒抢出租车,傻逼,赶上人家司机刚换班,就他妈抢了几十块钱。”
“抢出租车他行,抢银行这事他能行吗?”
“你说呢?你以为他像大毛子那么有尿儿?不嗑药他连出租车都不能抢。”
“那你把这事儿跟他叨叨啥呀?”
“他有门路,能从俄罗斯边境那头搞到枪,你能吗?”
“我也有枪啊。”圈子说。
“我他妈知道你裤裆里有一杆。”
大胜笑着,“啪”一口唾沫吐在了地上。
六
周末的午后,深浅不一的乌云堆积在天空中,但雨却迟迟没有下来。
圈子驾驶着大胜那台已经修补过无数次的微型面包车,从向阳乡往市区开去。面包车的后面装着一只大鸽子笼,里面是他那十几只鸽子。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淑娟,芳芳坐在她的腿上,开心地左顾右盼。
三人在圈子的七舅家一起吃过午饭之后,彼此熟络了很多。尤其是芳芳,此前对圈子还有些畏惧,但此时她正用食指在圈子右臂上按照那只老鹰的线条描绘着。圈子觉得有些痒,同时也很舒服。
“别闹,叔叔在开车。”淑娟将芳芳的手抓了过来。
圈子不明白为什么,明知道芳芳听不见,淑娟却总是和她说话。
芳芳趁淑娟不注意,又伸出手指在圈子的老鹰上戳了一下,淑娟赶忙抓住她的手腕,而她挣扎着指向车后面的鸽子笼。
淑娟明白了她的意思,笑着和她解释:“不对,叔叔胳膊上那只是老鹰,老——鹰;笼子里那些是鸽子,鸽——子。”
芳芳盯着淑娟的口型,跟着微微张了张嘴。
“你今天跟我出来跑了一天,得少卖不少钱吧?”圈子问。
“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孙姨帮我看着摊儿呢,也就少卖一锅吧,下午那锅没人烀。”
“又是教堂唱诗班那个孙姨?”
“对,那老太太人真不错,热心肠,总帮着我们娘俩儿,就是有一点挺磨人,动不动就让我信主。”
“我妈也是,她们信主那帮老太太都那样。”圈子笑着说。
“那你信了吗?”
“就算是信吧,”圈子想了想,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下次她要是再劝你信主,就跟她说‘我信了’,我就是这么打发我们家老太太的。”
当车子经过一个河边的时候,芳芳想要小便,于是圈子停了车,淑娟带着芳芳钻进了一个灌木丛。
圈子把面包车的后门掀开,让鸽子透透气,随后一个人站在河边抽烟。
未等一支烟抽完,他忽然听到背后有鸽子呼啦啦飞起来的声音,回头看见芳芳在面包车后头望着天上越飞越远的鸽子开心地笑着,而淑娟焦急地看着天空直跳脚,如同她这么做鸽子就能飞回来。
圈子把烟扔进河里,朝面包车走了过去。
“圈子,你看,这……”淑娟无比愧疚地说,“我一眼没照顾到,这熊孩子把鸽子笼给打开了。”
淑娟越想越气,拉过芳芳的胳膊,抬手就要打她屁股。
“哎,你打孩子干吗?”圈子拉住淑娟,“鸽子这玩意儿认识家,一会儿就飞回我七舅那儿去了。”
“真的假的?”淑娟半信半疑地看着圈子。
“你没见过养鸽子的?它要是一飞就没影儿,这帮玩儿鸽子的还不得天天掏钱往里续?”圈子笑着说。
淑娟琢磨了一下,说:“也是啊。”
“再说了,就算回不来也犯不上打孩子啊,不就是几只破鸟儿吗?”
圈子的劝慰似乎并不太奏效,驱车回市区的一路上,淑娟仍然三句话不离鸽子,言语间处处透着歉意。
到了圈子家楼下,他将车锁好,要带淑娟和芳芳去附近吃饭。
淑娟提议说:“既然已经到楼下了,我顺便上楼看看大娘吧。”
“还是别去了,我家味儿不好,你也知道我妈那情况。”
“那怕啥的,我心不脏,我以前那口子昏迷了好几天才咽的气,屎尿都是我给擦。”
无论圈子怎么说,淑娟仍然坚持,还几次要冲到街对面的水果摊,准备买些水果去看他老娘。最后圈子不得不抱起芳芳,用一只手拉着淑娟粗壮的胳膊,几乎是连拖带拽地将她弄进了街口的面馆。
圈子给她俩各点了一碗拉面,又要了四盘小菜和一瓶啤酒。
芳芳的筷子使得还不是很灵便,只会用它卷着面条在碗里笨拙地搅来搅去,好不容易弄进嘴里半根,却留下一大绺面条挂在碗沿儿,另一端堆积在桌子上,随后她会抓起桌上的面条重新投放进碗里,再次用筷子费劲地卷着。如此循环往复。
圈子握着那瓶啤酒坐在她们娘俩对面,一直看着芳芳吃面,最后终于忍不住对淑娟说:“你喂她吃几口吧。”
“都这么大的孩子了,让她自己吃,”淑娟说,“本来就又聋又哑,如果自己再不要强,什么事都得有人帮着,我要是有一天没了她自己怎么生存?”
圈子没再多说,对着瓶嘴灌了几口啤酒。
这顿简单的晚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饭后,圈子送淑娟和芳芳到了公交车站台。
“哪天你要是有工夫,上我家吃点儿饭去吧,我给你扒拉俩菜。”淑娟说。
“成。”圈子点了点头。
公交车开了过来,淑娟带着芳芳上了车。圈子目送着汽车开动,芳芳在窗子里朝他挥了挥手,他也笑着抬手回应了一下。
七
随后接连几天,圈子的老娘身体状况始终不是很好,因此圈子也没出门,直到老太太的病情稍稍有所好转,他才把车给大胜送回去。
“我还以为你把我的车开跑卖了呢。”接过车钥匙的时候,大胜笑着说。
“你这破车谁买啊?”圈子说着递给大胜一支烟。
“说正经的,这几天我没闲着,又去踩了几趟点儿。”大胜用打火机点上烟,吐出一个并不是很圆的烟圈,“保安还是那个黑瘦子,咱就按原计划干吧。”
圈子点了点头。
“就是二毛子那狗杂种没影儿了,不行就咱俩,我想想办法也能整着枪。”大胜说。
“他不能把咱俩点了吧?”
“他敢?我杀他全家!”大胜瞪着眼珠子。
“行,咱俩就咱俩,少一个人还少分一份儿钱呢。”圈子说完拍了一下大胜的肩膀,“我先走了,你弄着家伙了就给我个信儿。”
“哎,你在我这儿喝点儿再走呗。”
“我有事儿。”圈子回头朝大胜摆了摆手。
转了两趟公共汽车,才到了近郊淑娟租房的地方。圈子在街边溜达着,找到了一家还算大点的食杂店,买了好几种儿童零食。
圈子到淑娟家的时候,她还在厨房忙活着,圈子想要帮忙,她坚决地将他推出厨房。
淑娟租的房子很小,除了那间兼做餐厅的厨房,就只剩下一个洗手间和一个卧室。圈子推开卧室门看了看,房间里最醒目的是一张双层吊铺床,芳芳正趴在下铺看一本彩色的连环画。
圈子轻轻走进卧室,坐在吊铺另一侧的椅子上抽烟。芳芳很快闻到了烟味儿,于是转过头来。圈子朝她笑了笑,拎起路上买的零食放到了她面前。
淑娟在门口探进来半个身子,说:“还剩最后一道菜,正炖着呢,马上就出锅。”
“你们怎么没弄张床啊?”圈子问。
“搬进来的时候吊铺就在这儿呢,都一样睡,何必再自己掏钱买呢。”
淑娟说完又回到了厨房。
夜里的时候,芳芳早已在上铺熟睡,微醺的圈子和淑娟黑着灯在下铺相互摸索着。
淑娟饥渴难耐的状态令圈子始料未及,她狠狠抓扯着圈子的皮肉,就像一头急于将猎物撕碎的狮子,又像一个好久没接触过活人的吸血鬼,贪婪地舔舐、吸吮着圈子颈部的动脉,相比之下,反倒是圈子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显得有些放不开。
“咱别吵醒了孩子。”圈子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说了句话。
“没事,”淑娟剧烈喘息着,手上的动作并未停下,“她又听不见。”
圈子不再吭声,任由淑娟投入而疯狂地摆弄。
第二天一早,圈子还未睁开眼,就闻到了从厨房传来的煮苞米香味。
他醒了醒神,起床穿好衣服走进厨房。
“起来了?”淑娟问。
她的表情和语气都非常自然,就像昨夜两人并未发生过什么。但圈子却很尴尬,甚至不敢看淑娟的眼睛。他在昨夜之前还是个处男,这一点使他感到多少有些丢脸。
“我先走了。”圈子说话时,眼神像心虚的贼一样在厨房里胡乱游荡。
“吃个苞米再走吧,马上就好。”
“我还不太饿。”
“那你今天几点回来?我好掐时间给你做饭。”
淑娟如同在说一件他俩已经约定好的事情,这使得圈子再无矜持的余地。
圈子想了想,说:“把我妈的晚饭安顿好我就过来,也就六七点钟吧。”
淑娟点了点头,随后认真地翻动起锅里的苞米。
八
也许是圈子的老娘见儿子的情感生活走入了正轨,所以彻底放下心来,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葬礼办得很简单,一切程序都按照基督教堂的规矩。圈子的老娘没有穿中国传统的寿衣,而是穿着白色的基督教“荣归服”。在火葬场的告别厅里,孙姨所在的唱诗班合唱了几首葬礼用的赞美诗。在这场葬礼中,圈子始终没掉一滴眼泪,只是很沉默,反倒是淑娟哭了一场又一场,在她的影响下,芳芳也一直眼泪汪汪。
葬礼的答谢午宴是在一家小饭店办的,大胜和圈子的其他几个朋友坐在同一张桌上,除了这一桌,剩下的三桌全是信基督教的老太太,所以显得大胜这桌异常吵闹,如果单独看大胜他们高声嚷嚷着推杯换盏,也许会误以为这是一场婚宴。
答谢午宴只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散席后,圈子站在饭店门口送走了所有来宾,淑娟也带着芳芳回了菜市场,唯独大胜还陪在圈子身边抽烟。
“咱们那件事什么时候办?”圈子问。
大胜琢磨着说:“要不然就明天吧,我看再拖下去咱这事儿就干不成了,你说呢?”
圈子点着头,眼睛越过车水马龙的街道,看着马路对面商场促销舞台上的杂技表演。
第二天,圈子早早就起了床。
他推开床垫,取出那支“五四”手枪,一遍又一遍地拆下弹夹和子弹,反复地认真擦拭。最后,他把枪重新用绒布包裹起来在腰间插好,穿上一件长外套走出了家门。
天气虽已经稍稍转凉,但圈子穿着外套走在街上还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他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经过了一家又一家银行,在每家银行的门前,他的步子都有些迟缓。
步行很久,圈子来到了江边。他点了一支烟,双手插着口袋凝视江面。一艘白色的轮船从远处驶了过来,圈子看着它从眼前经过,缓缓向江的尽头航行。
见轮船走远,圈子把腰间的绒布包拿了出来。他将绒布的四角打成了两个死结,迟疑片刻之后,他用力地把这支枪抛向了江心。
傍晚,圈子再次来到东升街夜市。
大胜仍在老地方烤着毛蛋,见圈子来了,随手拿起一颗毛蛋递给他。
“吃吧,这次我进的货挺新鲜。”
圈子接过毛蛋吹了吹,边吃边说:“我想再管你借趟车,礼拜天带淑娟和孩子去植物园玩儿玩儿。”
“没问题,赶快去吧,要是等过阵子树叶黄了就不好看了。”
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聊起闲天,不过彼此都只字未提原本决定好却又莫名流产的抢银行计划,仿佛他们从来就没策划过这件事。
当大胜正眉飞色舞地和圈子说毛蛋这两天卖得多好的时候,突然就住了口,神情紧张地看着路口刚刚停下的一辆“桑塔纳”,圈子也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桑塔纳”里下来两个人,朝夜市这边走过来。
“是他妈便衣,”大胜紧张地嘀咕着,“二毛子不会真把咱俩点了吧?”
圈子没吭声,始终盯着那两个人的动向,发现他们正向大排档里兜售手机的小五子靠近。在离小五子不远的时候,那两人一起扑了上去,掰着小五子的胳膊将他按倒在地,其中一个人给他戴上了手铐,随后在他的身上搜出来好几个赃物手机。夜市里的人们全都朝他们那里张望,直至他俩将小五子按进“桑塔纳”,车悄无声息地开走。
圈子和大胜不约而同地用力咽了一口唾沫。
周末的植物园游人不少,圈子领着淑娟和芳芳心情愉悦地游览着,半路经过一个卖小玩意儿的摊床,圈子给芳芳买了一只大风车。
圈子太多年没来过这儿了,不仅是新增的人造景观,即使是那些长椅和垃圾桶也已经与他记忆中的大为不同,他更想不到这里还新建了一个“百鸟林”。
“百鸟林”实际上是一只巨大的笼子,将植物和鸟类都关在了一起。笼子外,每隔数米就悬挂着一块介绍一种鸟类的宣传板,上面写有鸟类名称、产地、习性,并配有实物照片。
“对,就是这个字儿,就他妈是这个字儿!”在经过一块展板的时候,圈子突然指着上面的一个字嚷嚷起来,“淑娟,你知不知道它念啥?”
淑娟凑过去仔细看了看,说:“鸠(究)。”
圈子愣了半晌,惊叹道:“你挺有文化啊,这字儿你都能认识?”
“字下面不是标着汉语拼音吗?”
“拼音你也认识?”
此时的圈子已经对淑娟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在老家当过两年小学民办教师,教语文。”
圈子瞠目结舌。淑娟看着他那夸张的表情,咯咯直乐。
芳芳不喜欢看鸟关在笼子里,所以用力拉着淑娟的袖子往前走。
圈子依然留在原地,好奇地把脸凑近展板上的斑鸠照片仔细观察。
“这不就是鸽子嘛。”圈子叨咕着。
当他把脸从展板前移开的时候,发现淑娟母女已经走远,连忙小跑着追了上去。追至近处,圈子突然加速,一把抱起芳芳向前冲刺。芳芳兴奋地笑着,把手里的风车高高举起,风车上五颜六色的叶片迎风飞快地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