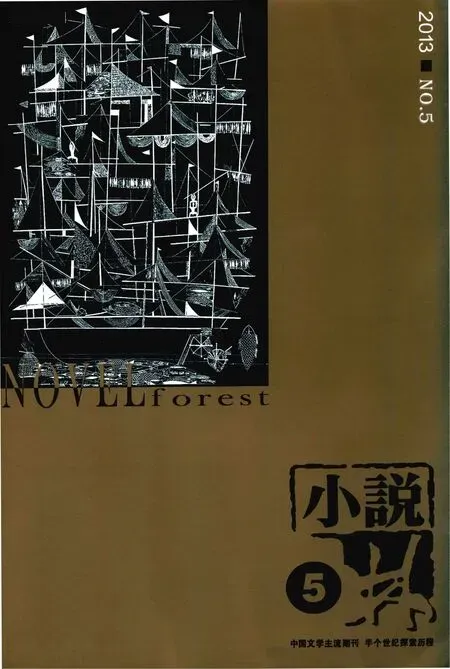箫声
◎于戍贵
只要没有风雨掺和的日子,一早一晚都会有箫声飘进村落,低回婉转,如泣如诉的旋律让人荡气回肠,甚至撕心裂肺。
刚到村上挂职,有些事情是不便过问的,起码不便多问。因为问了对我不一定有益处,没准儿还会引起某些反感。临来前,混迹官场多年的爸爸也曾为此嘱咐再三。
这特殊的箫声让我生出好奇心,打小被强制补习钢琴电子琴的经历告诉我,没有多年积累的扎实功夫是很难吹奏出这样厚重的曲子来。
我忍不住去找老马。
老马近六十岁的年纪,是当地出生的人,独身,为人和蔼可亲。在村里当了半辈子更夫,在村民面前挺有威望的,说话往往比村长还好使。比如有邻里纠纷,家庭不睦,青年男女的婚事,他出头上前去说和或撮合一下,大多就平息,就成就了。
村里许多工作,只要他能做的都会帮着去做。
我来村上当副村长,村上只好买了锅灶,设立一个简易伙食点。他因此又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每天给我做三顿饭。当然,他每天也不用再去侄子家吃饭,就和我搭伙了。
村民们没有对我俩这个伙食点表示反对,原因可能是伙食费由上级财政部门补助,不足部分由我个人出资解决,不用向村民身上摊派。
现在的村民是很讲实际的,只要不伸手从自己腰包里向外掏钱,村里的事情没谁乐意多管多问。拿他们的话讲,那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问及箫声的来源,还有吹箫人的身世,是我和老马一起吃过晚饭以后的事。我泡了一杯淡茶,老马叼起一根廉价香烟。这时候谈话往往会更融洽,更放松,更容易让人与人之间少有距离感,产生一种唠家常的亲切。
老马听了我的问话说,吹箫人是个半疯,姓尚,外号尚疯子。老马怕我一时难以领会,补充说,就是过去朝廷尚书那个尚。年龄比自己还要大几岁。大名叫尚……老马顿了顿,眼神直板板地盯着我的眼神。我知道他一时想不起来了,就在表情上,也在心底里帮他用劲儿。
老马果真没想起来姓尚老人的大名,就说,看我这记性,不服老不行啊,就在嘴边儿,一时还真说不出来了。这要放到当年……老马觉察出再说下去没意义,就转而说道,也是的,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问起过他,你这冷丁一问,一时就真把我给造蒙住了。这样吧,明天会计上班来,你让他查查低保底子,那上边有,前年给尚疯子办了低保。
不用,名字不主要,说他外号就可以。
尚疯子一辈子没娶媳妇,没在村子里住过。哦,也不是,是他摊过那把事儿之后,逃出村子,就再也没回村里住过,一直住在南甸子老山头上一个地窨子里。
哦,是这样,那马大爷,您能说一说他老人家摊了什么事情吗?
这有什么不能说,又不是当年那会儿了。只是,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好在你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听我慢慢给你唠扯。我说过这记性不如当年了,咱就想到哪块儿说哪块儿,中吧?老马征询着问我。
中,中,咱就随便唠唠,这样最好。我急忙表态。
尚疯子摊的事儿拿现在来说早已不是个事儿了。可在当时那会儿可是大事儿啊!
尚疯子成分不好,他爷爷在世时,家里置办过十几垧土地,也养过十几匹骡马。当然,入社时,这些土地骡马还有十几间房屋都被分了,成分也被定成富农。他爷爷一股急火死了。他爹人品挺忠厚,文化大革命前后挨批斗次数很多,但没人对他下狠手。咱农村人,都讲不太清楚什么路线政策,也不太在意家庭成分,倒是很注重人缘儿的。你若是平时在村里处个好人缘儿,就是真批斗你时也没人下死手祸害你的,大多走走样子就拉倒了。可样子必须得走,那可是上着纲线的事情,含糊不得。
尚疯子那次出的事儿起因其实不怪他,怪他奶奶,是由他奶奶引起来的。当时,家家户户的墙上都贴着毛主席画像,各式各样的都有。别看尚疯子的奶奶眼瞎,人却很刚强。尚疯子他妈死得早,好像在他十来岁时他妈就死了。伺候他们爷俩的活计都是他奶奶一手操持。那时候她奶奶只是眼神不好使,还没瞎透。
事件打一根针引起,就是缝补衣服用的针。那时满村子都是土房子,妇女们习惯做完针线活后,随手把针插在墙上,再干活时随手拔下来就用,图个方便嘛。
尚疯子的奶奶眼神不好使,每次用完针也插在身旁的墙上。下次再使时,拿手在墙上一划拉就能摸到,拔下来,用手摸着针鼻儿,三番五次抠吃着纫上线,就开始给儿子、孙子缝缝补补。
那次,纯是赶巧儿,尚疯子的奶奶不但把针插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上,而且是插在毛主席的眼球上了。按理说这也不该算什么事情,毕竟是个瞎老太太做的事,又是无意的。可不知道哪个多事的娘们儿就把这件事给传扬出去了,弄得满村子人都知道了。就有人胡咧咧,说尚老太太仇视毛主席,故意想扎瞎他老人家的眼睛。
这件事不知咋的就被工宣队知道了,特意下来调查,还要向上面汇报调查结果。
这么一折腾,这件事情就闹大了,说是影响恶劣,后果十分严重。大队革委会决定晚上开尚老太太的批斗大会。
尚疯子当时也就十八九岁,在镇上念中学,当时叫农中,也就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半耕半读。当时在我们农村,有很多这样的学校。
尚疯子放学回家,见奶奶哭哭啼啼,方知事情真相。奶奶在他心目里那是没人可比的亲人。谁要动他奶奶,那就是挖他的心肝啊!
那天,恰巧爸爸跟大车去县城拉化肥,不在家,保护奶奶的主意他就在内心暗暗打定了。
晚饭一过,大队民兵连长就带着一名基干民兵(其实就是社员)酒气熏天地来到尚疯子家,要带尚老太太去批斗会场。
尚疯子不知哪来的勇气,急赤白脸与民兵连长争辩说,你们饶过我奶奶吧,她是个瞎子,不是故意的!
民兵连长也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干部,当然不会把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崽子放在眼里的。故不故意你他妈知道个六,黄嘴丫子没褪,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赶紧给我滚开!
那我替我奶奶去挨批斗,总可以吧?
吆嚎——没看出来,你小子茬口还满硬,行,那就一块儿带走!
那不行,带我行,不能带我奶奶!尚疯子有些激怒了。
少废话!滚开!民兵连长无耐性了,向身边那位民兵一挥手说,进去带人!
看你们谁敢进去,针是我扎的,要带就带我。尚疯子急眼了,脖子红了,脸色青了,拉出一副拼命的架势。
你他妈反了!民兵连长挥手就是一个耳光,打得尚疯子眼冒金星。
尚疯子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咆哮着,一头撞向民兵连长。民兵连长哪能料到一个地主崽子敢对他下手,毫无防备,一下子被撞得连退好几步,跌倒在地。
要说啥事儿都赶巧儿,当时墙根儿立着一把搂柴禾的铁齿耙子。民兵连长倒下后,半拉脸正好被耙齿不深不浅扎了两个洞,弄得满脸血糊淋啦的。民兵连长连声叫着,反了,敢打老子,真他妈反了,给我伸手,把这小子给我往死里打!
那个民兵马上冲尚疯子动起手来,可你说怪不,尚疯子真是一股急劲,那个小伙子愣是没撕巴住他,他发疯一样闯进屋,转身拎出一把菜刀,两眼放着凶光,把菜刀举得高高的,叫喊着,谁不怕死,就上来!
哪有不怕死的主啊,民兵连长捂着胸口率先蹽了,一边跑一边把话茬磕磕绊绊撂下了,好小子,你、你他妈有种就给我等着!
尚疯子也不示弱,等着就等着,大不了你枪毙我(当时大队有一支半自动步枪,任由干部们悠悠荡荡挎来挎去的,打祸害庄稼的猪狗,也打河塘里的野鸭)!
民兵连长一跑,那个民兵也随后穿了兔子鞋。
尚奶奶眼睛不好,耳朵还有些背,等她听见屋外像是有吵闹声,摸出门来,弄清楚所发生的一切,惶恐得浑身发抖,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她颤抖着声音连连叫着,小兔崽子,你这是放着地祸不惹惹天祸啊!还不快跑,赶紧跑吧!
尚疯子气呼呼喘个不停,我不跑,看他们能怎样,大不了一死!
小兔崽子,你混账!你这是拿鸡蛋碰石头你知道吗?到啥时候胳膊也拧不过大腿呀!你不跑,我就死给你看!老太太真的一头撞向屋门。
尚疯子急忙抱住奶奶,连叫着,奶奶,你不要这样,我走,我听你的!泪水混着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尚疯子真跑对了,没一会儿,民兵连长领着十几个人赶来,都拿着家什,当然也挎了那支步枪。没抓住尚疯子,就把院子里、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个稀烂。然后把老太太像拎小鸡一样带走了。
经过这么一闹腾,尚疯子奶奶的罪行倒显得无足轻重了。尚疯子罪过重大了,打了民兵连长和民兵,还动用了菜刀,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是公然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党,反革命啊!惹上这个罪,轻者判刑,重者枪毙!
批斗会暂停,几乎全村的人马连夜出动,灯笼火把,吵吵嚷嚷,搜捕尚疯子。
第二天,公社来人了。来的不光是干部,还有十几个大队的民兵连长也一块来了。首先是开会,研究抓捕反革命分子。先是公社领导讲话,极具号召力,表示要全民总动员,一定要抓住这个反革命分子,为民除害。同时,公社领导也号召要有计划,有策略,有目的地进行抓捕,不能吵吵嚷嚷一窝蜂,暴露目标,等于给阶级敌人帮忙送信。
各大队民兵连长都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大致都是一个腔调,集中本大队全部民兵,实在不行把全体社员都调出来,人多力量大,把犄角旮旯都搜到,让反革命分子无处躲藏,插翅难飞!
民兵连长被尚疯子撞在胸口上,不敢大声说话,尤其脸上留着几个血痂,无颜面上讲台。本大队的表态发言是由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副连长刘山杏做的。
刘山杏穿一身绿军装,长发过膝,编了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一张团脸遍布红光,两只大眼目光专注。一只手抓着辫子,一只手挥着拳头,每说一句话,辫子就跟着抖动一次。她用清丽的嗓音高声讲道:反革命出现在我们向阳大队,这是我们全大队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的耻辱,尤其是我们革命青年的耻辱。我们全体民兵,特别是共青团员,一定要牢记毛主席指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光正面出击抓捕,还要讲策略,与反革命分子斗智斗勇。现在正是夏季,蒿草树木长的茂密,反革命分子随处都可以隐藏,对我们从正面进行抓捕十分不利。那我们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利用反革命分子的亲友、家人去做感化工作,顺藤摸瓜,早日找到他的藏身之地,然后抓获,绳之以法!
刘山杏还表示,这几天先不要揪斗尚疯子的奶奶和爸爸,稳住他们,利用他们当钓饵,免得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眼下,农田施肥,拔大草,封垄的活计一环紧套一环,正进入关键阶段。抓反革命分子重要,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不能忘,农业生产更重要。这两样工作哪一样都得抓紧、抓好!
公社领导非常赏识刘山杏的观点,当即表示,各大队民兵先不上,坚守自己生产队继续搞好农业生产,别影响咱们公社农业学大寨的标兵地位。因为一周以后,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现场会就要在咱们公社召开,农业这块必须搞出个高标准的样子来。抓反革命分子的事由刘山杏带领本大队少量精干民兵负责,采取搜查与思想工作相结合,争取早日把反革命抓捕归案。
老马讲到这里,哈欠连连,着实困了,说,反正咱们日子长着呢,明天,明天我再接着嘞嘞,中不?
我急忙说,中,中。
第二天,老马同样先点燃一支劣质香烟说,我忘了细说一下刘山杏了。她当时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比我大七八岁,也就是说比尚疯子大四五岁的年纪。土改时她爷爷当过贫协会主席,他爸爸也在大队干过,是典型的根正苗红。
刘山杏皮肤很白净,一张团脸,一笑俩酒窝,长一双大眼睛,双眼皮,让人感觉满脸都抹了蜜,看着心里都甜滋滋的。
最特殊的是她那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能垂到膝盖以下,干活时悠来荡去的,不是刮秸秆上,就是耷拉到泥土上,很碍事。她就是舍不得剪掉,没办法只好经常把辫子围绕在脖子上。
刘山杏为人很有心计,能写会画的,大队的各类板报、大字报、宣传画都是她写她画。字写得相当秀气,画的山水、人物、花鸟也跟真的一个模样,谁见谁夸。
哦,对了,有一点不知她是犯的哪一门子斜气,她爱听尚疯子拉二胡,吹口琴,尤其最爱听他吹箫。
尚疯子祖辈儿不知谁会这一手,留下来这几样乐器。尚疯子也奇怪,打小就爱鼓捣这些东西,无师自通,十多岁就演奏得有滋有味儿了。
每当尚疯子吹箫的时候,刘山杏好像真魂出窍了一样,整个人就傻了。目光呆呆的,像个木偶,眼神盯着尚疯子的嘴巴,一眨不眨,就要流出一汪水儿似的。脸色还跟着尚疯子所吹出的声音变幻色彩,一会儿桃红,一会儿苍白,一会儿又血一样鲜艳了。
这时,你别说有她喜欢的蝴蝶、蜻蜓飞过,就是拿手在她眼下晃几晃,她眼皮都肯定一眨不眨,像是根本看不见。
那时她是个女社员,白天要劳动的,她就趁中午或晚上听尚疯子吹箫。一听就是大半夜,没完没了的,有时连饭都不顾得吃。可第二天干活时,根本看不到她打哈欠,耷拉脑袋,打瞌睡。
据说尚疯子也怪气,每次有刘山杏听箫,他都能吹到忘我的境地,都能找到一种新感觉,进入一种新状态,达到一个新高度。
刘山杏家里很反对她与尚疯子来往,可能是成分相差的原因吧。她就不让尚疯子来家里吹箫,而是去他家听。
家人还是表示反对。刘山杏就反驳说,他是黑五类的后代不假,可他吹的曲子是《红梅赞》,是《东方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革命歌曲呀。他本人也不是反动派,他是毛主席划分的可以团结的对象啊。我是团支书,我不带头团结他那要谁去团结他?弄得家里也没有理由再深说什么了。
有一次,公社组织文艺汇演,她极力推荐尚疯子参加。他演奏的就是洞箫独奏《红梅赞》节目,得回来一张大红奖状,挂在青年活动室里,那是很了不得的事,别说村里人了,就连我这个半大小子都跟着荣耀呢。
刘山杏与尚疯子之间肯定没有破格的地方,这是全村人都认可的事情,没有丝毫含糊的。那一年刘山杏已经订婚了,对象是个公社干部的儿子,是个当兵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在兰州当空降兵。身材高大,面相帅气,一表人才,几个尚疯子捏一起也比不过的。
那时候,军人是啥?军人就是姑娘们眼里的王子啊!谁要是能嫁个军人,我的天,整天连嘴巴都合不拢啊!
刘山杏穿的那身绿军装就是对象邮回来的,崭新碧绿的颜色,还是四个兜的干部服呢。
尚疯子是个小毛孩子,比刘山杏小着四五岁的年纪不说,他跟那位军人相比,无论自己本人还是家庭条件都天上地下。退一步说,如果刘山杏就是不在意尚疯子家庭出身,真对他有想法,是肯定不会与军人订婚的。
我记得很清楚,刘山杏是和尚疯子去参加公社文艺汇演以后不久,才和那个军人订的婚。
这么说吧,全村人都认定,刘山杏的人品与她的容貌一样,绝对是响当当的。
怎么说呢,他们之间没有男女那种东西,可还有一种相通的地方,肯定是因为吹拉弹唱产生出来的,各自都装在心里头。有一种装得很深很重的东西,是别人难以想清想透的。这人啊,有些时候,有些心思,有些做法别人真就没法琢磨透啊!哦,你是大学生,有知识,你说我说的这些有点儿道理吧?
有道理有道理。我赞许地说。
老马换了一支烟接着说,当年有人猜测,尚疯子当晚跑出家门并没有跑出村子,是直接跑到刘山杏那里去了。把事情详细与刘山杏一说,刘山杏深知尚疯子这祸闯大了,就把他藏匿在自己住的屋子里。待她虚张声势,跟着全村人漫山遍野搜查回来之后,又亲自连夜把尚疯子带出村去,藏匿在老山头的地窨子里了。即使刘山杏没有亲自送尚疯子,也一定跟他说清楚去老山头的路线,没准儿还画了草图,因为她具备这个能力,只要三笔两笔就搞定了。
然后,尚疯子一路飞奔而去。
当然,这些都是村里人的猜测,谁也没有亲眼看到。
后来,刘山杏的死,好像就更能证明人们这个猜测有一定道理。
听到老马突然说出刘山杏的死,我的心猛然向上一揪。怎么会是这样?
老马一时也表情凝重了,拿烟的手有些发颤,烟灰瑟瑟飘落,头也埋得很低。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下去,声音明显苍凉一些了。
那是尚疯子出逃的第三天中午,天气阴得那个瘆人,跟一汪水似的。到处都黑漆漆的,好像后半夜似的,看啥都模模糊糊的。
那时,我十三四岁,在生产队还是个半拉子,跟着爷爷看甸子。我们爷俩挣一个整劳力的工分,他六分,我四分,一个老半拉子,一个小半拉子。好在活计不累,可以满大甸子疯跑,找鸟窝,捡鸟蛋,套鸟儿,采野菜,采蘑菇,抓鱼,抓蛤蟆,抓蝴蝶,抓蜻蜓……草原就是我的世界,想干啥干啥,没人管。
当时,一过村子南面这道江坝,就都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草甸子,满甸子都长着一人多高的苫房草,也有一些柳蒿、黄蒿,还有成片的柳条通。但面积都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满甸子长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苫房草。
农时一到处暑季节,全队男女社员,牛车马车都得出动。男社员每人臂弯里夹紧一把钐刀,刀杆两米多长,刀口紧贴地面,将身子大幅度扭动着。那使得可是真力气,稍稍偷一点懒,草趟子打不透,就会有几根野草站立着,出你的丑。钐刀每抡动一次,就有近半尺宽的苫房草被打掉,向着一个方向倒地,集拢在一起。打草人抡动四五下钐刀,就随之把身体向前移动大约一只脚的距离。打断的草茬上点点滴滴冒出白浆,像牛奶。爷爷说是草的眼泪。打草人只抡动几下钐刀,脸上的汗水就流到脖子里,后背的衣衫湿湿的,贴紧皮肉上。
女社员毕竟力气要小一些,就拿镰刀一刀一刀割草,或把男社员打下来的草捆成草捆。她们也冒汗,拿毛巾或衣角把脸色擦抹得更红艳了。
打草的活计一干就是半个多月。
基本上都是这样分工的:男社员打草,女社员捆草。捆完的草要对应着码好,码成黄瓜架的形状,有利于通风晾晒,待干透时垛成大草垛。待秋后打完场,江面上封了冻,用大车小辆运往江南岸哈尔滨郊区的阎家岗饲养场出卖,换回一些现金给社员们分红过年。
打草的日子,我和爷爷就有了明确的活计,是每天上下午各越过一次江坝,回到村子的大井里担回一担水,供社员们饮用。其他时间我胡乱地跑过来跑过去,打过草的甸子没有高草阻拦了,跑起来轻快多了。
我常跑去看女社员捆草。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刘山杏,她穿一件蓝花衬衫,两只衣袖挽到肘弯处,手脖上缠一条白色手绢。有特点的是两只大辫子,围着脖子缠绕一圈儿,剩下的部分在背后悠过来荡过去的。看得时间长了,我眼睛都被撩花了。她弯腰捆草时,辫子还常常往下掉。有时候她正捆着草,来不及收拾辫子,草茬子刮在辫子上,草叶子粘在辫子上,我都想帮她理一理,然后拿起来缠绕在她脖子上。可这只是我的想法,没敢伸手。辫子掉的次数多了,刘山杏就把辫梢叼在嘴里,一副狠歹歹的样子,把脸憋得通红,新鲜极了。
有趣的是她还抽空逗引我,问我想不想说媳妇,想说就在这帮姑娘堆儿里选选,看上哪一个了,她帮我说媒。她说她是团支书,管着她们,保准儿一说就成的。当时把我臊的,脸上都冒火了。她和姑娘们哈哈大笑,一片银铃声顺着大甸子传出老远,弄得男社员都住下活计,回头看着。连许多鸟叫都暂停了。
有一天我刚走到老山头地窨子跟前,见刘山杏与两个姑娘从地窨子后面走出来,叽叽嘎嘎的,有说有笑,像几只鹅鸾鸟儿。有高草挡着,她们没看见我。我却看到她们走出来的准确位置了。我以为她们大女孩子也到这里找鸟窝,下鸟套儿。我当时想搞点恶作剧,把她们的鸟套子偷走。可我围着老山头转一圈儿,根本没有鸟套儿,只找到两团沾着鲜血的窗户纸。当时我还以为她们谁受伤了……后来才懂,嘿嘿,都这么多年了,想想就可笑……
说得远了,跑题了,你别笑话我啊。
那天我被从没见过的乌云吓得往家跑时,遇到了刘山杏。她当时戴一顶大檐草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看不见她的脸。她穿的好像是一件男人的衣服,灰蒙蒙的颜色,又肥又大的,不合体。这些都掩盖的很好,可我还是从盘在脖子上的大辫子认出了她,全村里就她有那么大的辫子,独一无二啊。
她腋窝里夹了一只铝饭盒,走得慌慌张张,很是快。
我与她照面的地方正好是江坝上。当时,我是从坝外坡爬上来要往家赶;她正巧是从坝里坡爬上来准备往大甸子里去。相遇时,我们各自都愣怔一会儿,很短促,但我们各自都感觉到了。
愣怔过后,是刘山杏先迈开步子,奔向坝下的大甸子。我回头望了一下她的背影,眨眼工夫就淹没在草丛里了。
我当时真的不知她去干啥,只是十分纳闷儿,这天阴成这样,她胆子可真大啊!
我到家没一袋烟的工夫,一场冒烟大雨就下起来了。这场雨足足下了一下午。你说分量有多大吧,把田里的庄稼,甸子上的草全压趴下了。平地的水都没过膝盖了,哗啦哗啦往低处流淌着。
雨停后,刘山杏的家人满村子找她。问到我时,我就把她下雨前赶往南甸子的过程说了。
全村子的人都出动了,在南甸子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她。当时,人们想到了会出现什么不测的事情,但没到亲眼见证时,还都抱有良好的期望。得说,人人都盼着刘山杏不出事,毛发不缺地回来——
发现刘山杏时,已经是秋后了,人们打草的时节。
漫山遍野,遮天蔽日的野草被人们一点一点吃掉了。草甸子上光秃秃亮起了一片白茬子,小蚂蚱一跳都看得真真切切了。
哦,你看我,先前跟你提到老山头了,可没说明白。
在草甸子深处,大约离村子十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叫蚂蚁河。河道很窄,十几步宽的样子。对岸有块高地,叫老山头。这上面挖有一处地窨子,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具体是谁挖的,记不清了。但能藏身,这一点就足够了。遇上操蛋的天气,看甸子的人或者放牧的人到里边躲躲风,避避雨。晌午头去里面躲躲日头,睡个懒觉。
刘山杏的尸体就在对着地窨子的蚂蚁河里发现的。离地窨子不足二十步远。说是尸体已不准确,应该说是遗骸,因为当时就是一堆白骨了。
收拾遗骸时,人们发现她的两条腿骨插在河底淤泥里足有二尺深,这就告诉人们,她在奔向地窨子时被河泥陷住了,两只脚越挣扎陷得越深。随之而来的大雨不但掩盖了她的呼救声,也把整条蚂蚁河填塞得满满涨涨了……
人们在河泥里抠出的两样物品没有腐烂,一件是那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足有四尺长;一件是那只铝饭盒,生了一些绿色的锈斑,洗洗刷刷,锈迹就脱掉了。
按照家人的意思,刘山杏的尸骨就地掩埋在地窨子旁边的老山头上了。当时,大队往上汇报说,刘山杏是乘风雨之时,独身寻找逃犯,不幸落水身亡。公社报到县上,不久,县上授予她模范共青团员称号。这一点,县志上有所记载,是这样写的:
1970年6月28日,沿江公社向阳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刘山杏同志,携带食物,只身潜入荒野抓捕反革命分子,因途中遭遇暴雨迷路,不慎落水牺牲。当时经县革命委员会、团县委批准为模范共青团员。
老马声音嘶哑地讲完了这段故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没再出声。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感笼罩着我。为了排解这份沉闷,我说睡吧,马大爷,天色不早了。老马依旧没有吱声。我只好独自躺倒在床上,呼吸着越来越浓重的烟雾。
一段日子里,我没再问起这个往事,老马也没提及,好像我们都有意回避这件事情。
市里实施大湿地建设开发项目,沿江一带需退耕还水,还林,还草。县里镇里连续开会,研究征地、搬迁事项。
开发项目涉及征用我挂职这个村江坝内侧近千亩耕地,草原,鱼塘。踏查,丈量,动员,谈判,签协议,林林总总,很是繁杂。尚疯子栖身的老山头属于项目中心区,是第一批搬迁对象,动员他搬迁回村属于相对容易做的一条线工作,村里指派我负责。
我对去老山头的路不熟,对尚疯子不熟,还有年龄差距不容易沟通,就约老马与我同去老山头。老马说要借台自行车。我说还是走走吧。
我们走上江坝时,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老马说这里就是我讲述中的草甸子,现在啥也看不到了。
老马目光望着远方说,一家伙征用这么多耕地,得少打多少粮食啊!这究竟是对是错啊?
我答非所问地说,这么大面积征用,涉及千家万户,光核实面积,签订合同,对付钱款这些工作就够忙乎到年底了啊。
老马介绍说,脚下的江坝这些年几次加高加固,比当年已经宽了很多,上面的砂石路也是后来铺的。
老马指着一处堤坝豁口说,这儿就是当年他遇到刘山杏的地方。刘山杏就是从这里一头扎进草甸子,再也没能回来。
我仔细瞅着自己脚下这条当年刘山杏急匆匆走过的路,仿佛能从中寻找到她的脚印。
我们说话很少,走得也很缓慢,花费两个多小时时间,来到了这个叫老山头的地方。
老山头不过是一块高于周围几米的小沙丘,只有两亩地大小。
首先出现在我眼中的,是一片山杏树,足有几十棵的样子。
老马说,尚疯子每年都会在刘山杏的坟墓旁栽植一棵山杏树。也就是说,只要查一下树木的数量,就知道他待在这里的年头了。
有的树木枝干矮小,却枝叶繁茂;有的树干不仅很粗壮,还斑斑驳驳长了一些疤痕,看得出树龄已很长了,枝叶稀疏,却绿意正浓。
掩映在树丛里的一处土丘修整得十分规矩。老马告诉我它就是刘山杏的坟墓,看得出,清明时节刚填过土。
走过树木坟茔,我看见了那处地窨子,因为半截挖在地面下方,凸现在地面的部分真不比那个坟茔高多少。老马说当年那会儿,这个地窨子要比现在高一截的。
地窨子浑身都是泥土结构,雨水冲刷,使得高出地面的部分袒露出一种叫塔头的东西。老马说,当年这种东西既能垒砌房屋,也是取暖的优质材料。蚂蚁河里长得最多,一到冬季,河水干枯,遍布河底的是清一色的塔头,黑黢黢的,每一个都比人脑袋大。人们两个人一副架儿,在一个相对较沉重些的圆木两头上各拴一根麻绳,斜挎肩上,站稳脚跟,一同用力把圆木悠向站立着的塔头,塔头应声倒下。然后装车运回家去,大多数用作取暖,也有人为第二年春季盖住房,盖鸡架狗窝猪圈做准备。
地窨子正面门上,还有门旁的小窗上镶嵌着的两块小玻璃告诉我,它与原始部落是有些区别的。
我们拉开破旧的一扇小门走进屋,视线适应了好久,才看到里面的老人,一头稀疏白发,两目暗淡,面皮枯黄,身子骨还不错,驼背很严重,身高跟老马讲述的尚疯子难以对上号了。初夏已到,一身草黄色的棉袄棉裤还穿在身上,显得更加肥大。
对我们的到来,老人像毫无觉察。
我看到,老人身边摆放着一张正方形小饭桌,桌上放了两双筷子,一只碗,另一个是乌突突、没有光泽的正方形大号铝饭盒。
老马用下颏点指一下铝饭盒,我明白了,那是刘山杏的遗物,里面肯定装着那双大辫子。
我仔细看了一会儿,终于看见老人的枕边,放着一只紫红色的竹竿,两尺多长的样子。
我知道,这就是每天两次把声音传入村子的洞箫。据说,这种乐器,在近处听,并不响亮,可在几里以外听时,声音依旧是那么清晰可辨。
我伸出手,想和老人握一下手,老人没有反应。
老马告诉我,自打刘山杏的尸骨埋在这里,尚疯子就来这里居住了。当时就有人发现他了,可没有任何人向上级举报,过了两三年,政策宽松了,更没人管了。后来,上面落实政策,说他没罪,村上给他盖了两间砖房,几次动员他回村里居住。他当时很听话,都跟着回村里了,整天摆弄这只箫,不管谁说啥,他也不瞅你,不吱声。可没过几天,他都会趁人不注意,又跑回老山头。这么说吧,只要一听到箫声,不用看,尚疯子保准儿跑了,房子里保准儿空了。
人们认定他这是疯了,就叫他尚疯子。
后来,村里就不再往回接他了,一个孤老头子,哪儿住还不是住啊。像他这种情况,那要是搁过去是没人管的,有句嗑儿说过,道死道埋,路死路埋,狗肚子里是棺材。
村里后来出头做工作,把他的两亩口粮地调换到老山头跟前,他侍候起来很方便。每年还按五保户标准,照顾他一些米面豆油衣物。
老马一直喊着把我们的来意说给尚疯子。老人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老马说,你看他就这样子,整不出个子丑寅卯,就安排搬吧。
第二天,村长安排一辆农用三轮车,由我支配给尚疯子搬家。我又找老马同去,老马说自己身子不舒服,还说他就那么点儿破烂东西,你带开三轮的去就行了。
开三轮的小伙子很熟悉路线,逢年过节,村上给尚疯子买些米面都由他开车送去。
搬家过程很顺利,行李碗筷装好后,我和小伙子搀扶尚疯子上车。尚疯子怀里抱着那只铝饭盒,那只洞箫斜插在脑后的脖领子里。
整个过程里,尚疯子还是没说一句话。
搬回村里,我安排尚疯子临时在村部居住,白天同我和老马一起吃,晚上和老马睡在一起。这样,他没机会再跑回老山头,我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在村上居住一段日子,尚疯子没什么反常举动,一次也没往回跑,就是不再吹箫了。早饭前晚饭后出去走上一阵子,怀里抱着铝饭盒,脖子后斜插着那把洞箫。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见尚疯子很规矩听话,我又叫来那辆农用三轮车,把他的行李衣物装上,送他到镇上五保供养院居住。那里条件相对好些,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有厨师,还有好多老年人为伴。主要是村里也少一个负担,不能专门雇一个人看管他啊。
我想,尚疯子会适应那里的生活,晚年会生活的很好。这是自己挂职期间办的一件好事、实事。
几场大雪把隆冬季节推到眼前,我的挂职任期即将结束了。
一天,村长在自己家里为我摆设了告别酒宴,喝得尽兴,晚上关掉手机,睡得很沉。老马连喊带推把我弄醒了,五保供养院来电话说尚疯子失踪了。
我迷迷瞪瞪问,他能上哪去啊,回老山头了?
老马说我想起来了,刘山杏是腊月初一的生日,以前尚疯子回村住时,这一天也会跑回老山头去的。
我匆匆穿好衣服,拿起手电筒,和老马一起走出村办公室。
外面风雪正急,雪花打在脸上热辣辣疼,灌入衣领,袖口很凉。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深了。这样的天气,没人敢出车,也没人敢坐车,我们只好步行赶往老山头。
跟头把势,鼻青脸肿赶到老山头时,天色微亮了。
老山头被白茫茫的积雪覆盖着,一时难以辨别地窨子的位置。我们通过那片山杏树辨别到地窨子,手脚并用,把门口的积雪简单清理一下,打开门,里面不见尚疯子。
我们像两只泄气的皮球,瘫在地上。
老马说坏了,尚疯子要是困在半道,非冻死不可。
我也紧张起来。
我们爬出地窨子,天色更亮一些,能见度好多了。
我分辨出刘山杏坟茔的位置,把目光投向那里,周身不免一颤。一座雪雕矗立在坟前,两手平稳端着洞箫,目光凝重,神情专一。
一时间,风也停了,雪也住了,只有那低回婉转、如泣如诉的箫声充斥着我的耳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