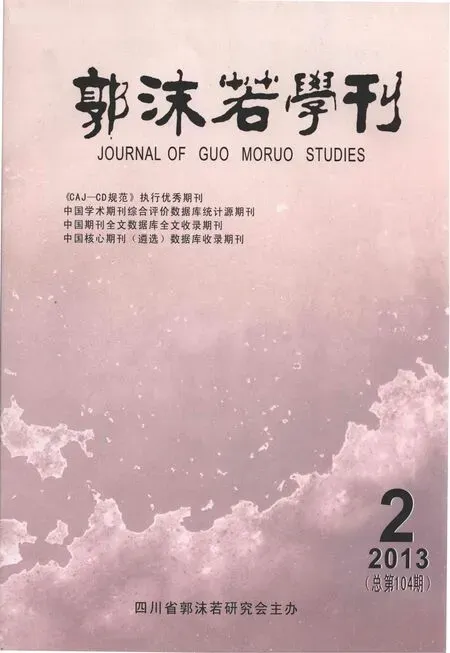转译之困与惑——谈郭沫若的俄苏著作翻译
王 慧 孔令翠
(1.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10065;2.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1)
一、转译之故
十月革命的成功大大鼓舞了仍处在灾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一批有志之士开始把目光从欧美、日本转向俄苏,矢志从俄苏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俄苏文化与文学,开始译介俄苏著作,包括文艺作品。由于当时懂俄语的人很少,很多翻译只好通过从英语、德语或日语本转译成中文。郭沫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了开始了转译俄苏文艺作品的工作。
由于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鼓舞,郭沫若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性主义的影响,但已开始初步具有从争取个性解放为目标发展到以争取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基础指导下,他的翻译选择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以前的浪漫主义抒情文学作品的翻译转向社科著作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懂俄语的郭沫若依靠其他语种转译或合作翻译俄苏著作,先后转译或合译了屠格涅夫揭露俄国社会黑暗的《新时代〉、布洛克等人的《新俄诗选》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分,尤其是《战争与和平》,虽然不能做到善始善终,但在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却值得称道。而这些作品的翻译,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思想意识,使他从政治上一步一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上积极投入到具体的革命运动中,同时也使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方向有了相应的改变。他开始逐渐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把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用文学的力量去推动社会革命。
二、转译之路
(一)翻译《新时代》,憧憬新时代
《新时代》(今译《处女地》)是俄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创作的小说。郭沫若据德译本并参照英译本转译屠氏的这部小说,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署名“郭鼎堂”,1927年5月再版。
屠格涅夫是郭沫若在日本接触的第一位俄苏作家,受其影响较深。据郭沫若自述,1921年4月1日他与成仿吾一同乘船,途中读了成仿吾随身携带屠格涅夫的德译本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由于与《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产生了共鸣,诱发了他后来对该书翻译的兴趣。他在谈到翻译《新时代》的感受时说:“《新的一代》这书,我现在所深受的印象,不是它情文的流丽,也不是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却是这里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他认为,《新时代》这部小说能给予中国读者的,除了“这书里面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以外,还可以把它当作中国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看那俄国的官僚不就像我们中国的官僚,俄国的百姓不就像我们中国的百姓吗?”他在翻译后也对原书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强调中国社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列宁的俄罗斯”。与今译名《处女地》相比,郭沫若的《新时代》这个中译名无疑更具有象征意义,寄托了译家对未来美好中国的憧憬。
早期郭沫若的很多翻译都是在贫困中进行的,是摆脱生活重压努力的一部分。翻译《新时代》亦不例外。他曾说过:“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是在这前后先先后后化成了面包的。”
除了翻译《新时代》外,郭沫若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其他作品。1921年1月,他翻译了屠氏1878至1888年在《欧洲导报》连载的小品文。此外,1928年出版的《沫若译诗集》收录了他1921年翻译、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的一组图氏诗,有《睡眠》《即兴》《齐尔西时》《爱之歌》《遗言》等,取名《图尔格涅甫之散文诗》。他在《〈图尔格涅甫之散文诗〉序》中对其诗大加称赞说:“此诗集最脍炙人口。”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不但影响了郭沫若的思想,还影响了郭沫若的诗歌与小说创作,这从他的《拟做〈我的著作生活回顾〉》的“五、向小说的发展”中反映出来。
(二)翻译《新俄诗选》:希望推动时代潮流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接受,郭沫若对翻译原苏联文学作品十分向往。他在1929年再一次借助转译翻译了由苏联诗人布洛克等15位俄国诗人的23首诗作辑成的《新俄诗选》(又名《我们的进行曲》)。上海光华书局初版,1930年4月再版。该诗选为我国汉译出版的前苏联早期诗歌集,郭沫若因此而成为最早译介前苏联革命诗歌者之一,顺应了我国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潮流。
这本译诗集是译家与李一氓根据巴比特·道希、亚莫林斯基共同译编的《俄罗斯诗歌》(Russian Poetry)第二部合作翻译出版的。郭沫若在该诗集翻译时起的作用类似于林纾。由于语言障碍,译稿先由李一氓译出,后由精通诗歌创作的郭沫若对照英译本严格改润。他对合作者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氓兄的译笔很流畅,造语也很有精妙的地方,读他的译诗多少总可以挹取一些原作的风味”,而且还公开说,有好几首诗,如柏里的一首,叶贤林的一首等等,他差不多一字未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与苏联断交,不许出版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刊。郭沫若只好想尽办法规避,在署名和书名两个方面做文章。署名为L.郭沫若译,其中“L”为仍在国内的李一氓姓的首字母。之所以不敢用真名,是因为被迫寄居日本的郭沫若出于保护处在白色恐怖下的李一的人生安全。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查禁,1936年7月,上海大光书局为易名为《我们的进行曲——新俄诗选》继续再版,内容一字未改。卷首有郭沫若的小序。
郭沫若在《新俄诗选》的序文中指出,《诗选》收录的诗,虽然还“不足以代表苏联的精华”,但读者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大潮流和这潮流所推动着前进的方向”;当国内读者渴望读到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崭新的文学作品时,人们如果把这本《诗选》同旧时代的诗相比较,那么,“除诗的鉴赏外总可以得到更重要的一个什么。”鉴于当时的出版环境,这个“什么”的具体所指郭沫若不便明说,但读者是完全可以领悟到的。
郭沫若弃用原诗集名《我们的进行曲》而改用《新俄诗选》,足见郭沫若多么希望此译诗集能够起到推动时代大潮流和让读者明确该潮流所指引的方向之作用,但是由于原诗集艺术水准的制约,它实在难以担当起译家寄于的重任!
翻译马雅科夫斯基诗形为楼梯形的《我们的进行曲》使他对诗歌翻译有了新认识。他在1962年3月15日在谈到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诗歌时发表了自己对诗歌翻译的意见:“外国诗如果是白兰地,那么,就应该把它译成茅台;不要译成白开水,而且加上一些泥沙。”
附带补充一下,在俄苏诗歌翻译方面,郭沫若还翻译了俄国诗人都布罗柳波夫的《“死殇不足伤我神”》,收入《沫若译诗集》。
(三)翻译《战争与和平》:体验一波三折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公认的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之一。托翁的《战争与和平》是卷秩浩繁的长篇小说。这部巨著以史诗般的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
早在1920年,还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就在《巨炮之教训》中刻划了托尔斯泰的形象。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动手翻译托尔斯泰的这部巨著。虽然翻译介绍托尔斯泰并非从他开始,林纾就翻译过《现身说法》,但是《战争与和平》还没有人完整翻译过,以致鲁迅1928年时还发出了“至今无人翻译”的感叹。
郭沫若是中国翻译这部列宁称为“了不起的巨著”的第一人。尽管不懂俄语,但是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从军经历在当时的翻译家中极为罕见,这使他仍然成为最理想的译者。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在托尔斯泰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而且从我国翻译介绍欧洲长篇小说来看,也是较早的一部。[7](P157)
郭沫若在《初会瞿秋白》中介绍了翻译的背景,一是出于解决吃饭问题:“当时生活十分窘迫,上海的一家书店托人向我交涉,要我翻译这本书,我主要的是为了解决生活,也就答应了。”二是应瞿秋白的邀请:“秋白劝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
《战争与和平》最早为郭沫若独自据德译本并参照英、日译本转译,1931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但只译了三个分册,自1931年起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后来出版社因经营方面的原因而停止出版,故郭沫若未能把全书译完。郭沫若在1940年1月23日为《战争与和平》第一部的《序》中介绍了翻译这部世界巨著的情况以及中途停译的原因。
《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上)1931年8月5日上海文艺书局出版,(下)1932年1月15日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第一分册(上、下合)1932年10月10日3版。第一分册1934年2月10日4版,第二分册1932年9月25日出版和1934年2月10日再版。第三分册1933年3月15日初版,1934年2月10日再版。上海中华版为合订本,出版年月不详。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10月出版1-3分册合订本。1939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41-1942年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首次联合署名。上海骆驼书店1948年1月初版,1948年8月出第3版。
虽然他不懂俄语,但是他的翻译还是非常严肃和负责任的。他依据Reclam(即德国莱克拉姆出版社)版的德译本转译(郭沫若谓之“重译”),同时用英译本和日译本参照。在翻译过程中,他发现了Reclam版的德译本省略得太厉害了,于是便放弃德译本而改用加内特(Garnett,英国女翻译家)的英译本为蓝本转译。他在翻译时发现“号称是从原文直译的”(1941-1942:1)米川正夫的日译本,事实上也是加内特英译本的转译,这就坚定了郭沫若用加内特的英译本继续翻译的决心。
郭沫若经常强调,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读译作,而是刺激大家去学外文,同时也刺激自己去学外文。他对这部书“本来是十分爱好,并十分希望把它完整地介绍过来的。”
在他众多的译作中,郭沫若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十分爱好”、“十分希望”的措辞来评价。俄语能力的不足也曾刺激他想把俄文学好,将《战争与和平》彻底改译。学好俄语是郭沫若思想转向以后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从过去的着重于欧美的翻译转向以苏联文学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但由于工作太忙,年纪偏大,俄文基础较差,虽然尝试过,但“时辍时续地终就没有成器”,彻底的改译最终也未能如愿以偿。
郭沫若和这部著作的翻译再次联系在一起是由于抗日战争期间一位叫高地(即高植)的青年写信给郭沫若,表示愿意把这部小说译完,用他们两人的名义出版。郭沫若答应了,于是由郭沫若、高地合译的《战争与和平》就由重庆的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了。
在此之前,郭沫若在日本时有一位叫邢桐华的年轻人俄文程度比较好,他曾经对郭沫若表示想把这书继续译完。郭当时十分高兴,积极鼓励他趁早动手翻译。于是,邢桐华1937年春在东京出版的质文杂志上刊登了翻译预告,但在他尚未着手迻译之前却遭了日本警察的迫害,把他抓去拘禁了一段时间,并强迫出境。邢桐华回国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先是参加抗战后是因为疾病,《战争与和平》的翻译也就一直没有着落。
眼看就要成为泡影之时,郭沫若意外地收到了高植的信:“最近我从原文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全部译成,约一百万言。先生的译文从前拜读过,有些地方与原文小有出入。……因为本书的前部有很多的地方用了先生的译文,甚至可以说是试验的校补,所以我很愿意和先生以合译的名义出版,假如我的名字不至影响先生的威望,在我是十分荣幸的。”
高植批评了郭译与原文“有些地方与原文小有出入”。这很正常,因为依据的文本不同,郭沫若依据的是英译本,而高植依据的是原著,所以这“出入”的责任未必就是郭沫若的。但郭沫若对高的批评不但丝毫没有怪罪之意,而且还认为他的态度谦和,特别是能帮他了结一桩多年的心愿,自是喜不自禁,立即回信支持他迅速出版。高植由于参考了郭沫若的译本,于是邀请他在译著上联合署名,郭沫若除了表示“十分荣幸”外,还劝他不要如此客气,坚持认为“有些不妥”。不妥的原因是会窃取高植的美誉,因此他诚恳地向读者谦虚地奉告:“我在此次的全译上丝毫也没有尽过点力量,这完全是高君毅仁的努力的结晶。假使这里面的前半部多少还保存了一些我的旧译在里面,那也只是经过高君淘取出来的金屑,金屑还混在沙里面的时候,固是自然的产物,但既经淘取出来,提炼成了一个整块,那便是完全是淘金者的产物了。”
其实郭沫若也不是“丝毫也没有尽过点力量”。他仔细阅读了译稿,认为高植译笔简洁忠实。他还从译者个人的性格讨论翻译的关系,觉得高植的性格谦充缜密,适合翻译这部巨著。他对高植“在目前军事扰攘的时期,高君竟有了这样的毅力来完成这样宏大的一项工程,并且工作态度又那样有责任心,丝毫也不敢苟且。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佩服的。”高植是邢桐华的朋友,翻译《战争与和平》,也算了却了邢桐华的一项宏愿。
据李今介绍,为了统一不同译者的语言风格,高植对郭译部分进行了校补,去掉了原译较为文雅的色彩而使译文显得直白一些。
如果说此前与钱潮和李一氓之间的合作是在同代人之间进行的话,那么这次应邀与高植的合作则是两代翻译家之间的对话,体现了老一代翻译家的胸怀和关切,也体现了年轻一代翻译家的努力与景仰。两代人之间的取长补短在总体上保证了对原作理解的基本正确和表达的基本传神,因而自然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1947年骆驼书店的再版就是证明。不过由于董秋斯对郭沫若“列名”的批评,1951年文化生活出版了单独署“高植”名的新译本。
郭沫若与高植合译这部巨著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进行的。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在发生动摇,全国军民也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候。这部作品的适时翻译有利于鼓舞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该巨著的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2年,新文艺书店出版了郭沫若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1891-1967)等著《黄金似的童年》,但相关资料十分匮乏,本文难以深入研究。
三、转译之困与惑
由于不懂俄语,郭沫若翻译的俄苏作品都是通过其他语种译本转译而成。尽管也下了很多功夫,参考了多种译本,但是翻译质量未必尽如人意。高植曾批评郭译与原文“有些地方与原文小有出入”。原因主要在于依据的文本不同,郭沫若依据的是英译本,而高植依据的是原著。茅盾的批评很不客气,认为“此书译笔颇多费解之处”,主要是因为用了过多的“美丽”文言字眼,归化的色彩太浓。
郭沫若本人也认识到转移的艰难与困惑。他深知翻译《新俄诗选》这类非一流诗人作品的困难,何况还是转译,这使得这项工作难上加难:“原来译诗是一件很难的事体,况这本书又是重译,这里当然含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不过国内的人很渴望苏联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所以目前在便宜上也只好以重译的办法来疗慰一般的渴望。”生活压迫更使得转译质量雪上加霜:“更加以书店要急于出版,我是边译边寄,书店也就是边印边出,因此连那书里面的人名地名(据高地君的统计有八百多)都译得前后参差,译文的草率自无庸说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其说是译者本人,还不如说是社会:译者为生活所迫,出版商抢译抢出无视翻译规律。
翻译就意味着损失,没有任何一种译本可以完全反映原作的精神。转译本本身良莠不齐,译者尽管可以参考多种译本,但仍然无法彻底把握原作本质。这不但给翻译本身带来巨大的挑战,就是在原文意义的转达方面,也可能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转译的次数越多,译作的质量也就越难以得到保证,后来被依据原文翻译的作品所取代也就理所当然了。这告诉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尽可能不要转译。郭沫若以他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弥补弥补了《鲁拜集》转译之不足,而其转译之俄苏作品则给译界、读者甚至译家本人都留下了难以破解的困惑。
[1]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的一封信[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郭沫若.新时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3]黄淳浩编.郭沫若自叙[C].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4]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6]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郭沫若.《战争与和平》第一部·序[M].重庆: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1-1942).
[9]郭沫若.初会瞿秋白[A].郭沫若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董秋斯.《战争与和平》译者序[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12]茅盾.汉译西洋名著[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