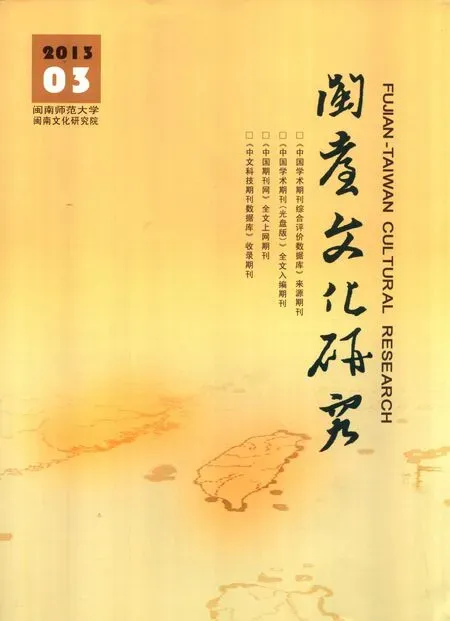浅谈陈淳文学作品中的艺术风格
李蕙如
(淡江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吴之振《宋诗抄·序》:“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人喜欢繁华落尽的淡泊之美,一种勘透世情的知性反省之美。不单就诗而言,所作文章亦然。就陈淳作品中的写作技巧来说,其诗文并没有太多的雕饰及修辞,大多来自作者生活的实践体验所引发的哲理性思考,以启迪人心为重点所在。因此,以下则针对陈淳的作品,整理出三项艺术风格:文以载道、从容自适、理中有趣,并分别举其作品加以印证。
一、文以载道
针对宋代儒者主张文以载道的问题,许总提出“然则理学家为何又不废诗作?”的问题。且明白指出需要到儒家的文道观中找答案。儒家向来重视文道关系,然从“文章经国之大业”到“文以明道”,对文的强调显然在于其作为道的载体作用。宋代理学家将道的地位推向极端,文自然进而成为道的附庸,因此反对害道之文,却并不反对传道之文,于是对闻道关系的认识从“作文害道”、“文以载道”逐渐演变为“道文一贯”。朱熹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并加以解释“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明确要求:“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如此,诗在理学家手中,已完全融入性理之学的范畴之内,而理学诗实际上也就成为理学思想的诗化形态。由此看来,宋代理学家诗作虽多,题材亦富,但却全然可以归结到阐发其哲学思想这一出发点上来,同时,由于理学家作为道德伦理之学,理学诗中所阐发的哲理也就更多地集中于人生哲学的范畴。如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流传至今的诗作多达一千余首,实际上已成为南宋诗坛一大家,但其诗学思想的核心显然仍在阐理明道。陈淳亦可做如是观。
宋代理学宗祖周敦颐在其道德哲学著作《通书》第二十八章中提及“文以载道”说,为理学家的古文观念定下了基调:“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又云:“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所谓“圣人之道”即指“中正仁义”,也就是“文”所应载之“道”,但周氏并未废于文辞。程颐则严格区别“圣人之文”与“词章之文”,并从创作角度指出二者的特征,提出“作文害道”,以严斥“词章之文”。程氏将周子“载道之文”归结到“圣人之文”而做为文章典范,禁绝“学为词章”。朱子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周、程的基础上建立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承袭周、程,鄙视徒为词章之美者,谓“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另一方面则从道德本体角度对载道之文的创造及艺术风格进行论述。如陈淳所作的《闲居杂咏三十二首》,每首皆体现文以载道的创作,以下列举数首为例:
《仁》
仁人之安宅,在心本全德,要常处于中,不可违终食。(《北溪大全集》,卷三,页三。)
《夫妇》
夫妇亦大端,乾男而坤女,一言在有别,不可欲败度。(《北溪大全集》,卷三,页四。)
《目》
目所以司视,视正乃为明,非礼谨勿睹,睹之则为盲。(《北溪大全集》,卷三,页五。)
《隆师》
师者人之范,辨惑正吾疑,苟不就有道,怅怅其何之。(《北溪大全集》,卷三,页六。)
不仅是诗,陈淳的多数作品体现着文以载道的传统,把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感情,乃至于学术主张、政治观点写入其中,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思辨清楚地呈现出来。除受时代环境及师说影响,本身个人资质纯朴、又以讲学为业,因此为必然结果。如陈淳所作的《君子谨其独箴》、《君子戒谨所不睹恐惧所不闻箴》诸篇,说理明白透彻,或教人“只于平时事未萌芽,己所未闻,己所未睹,即须自力戒谨恐惧,战战兢兢,临深履冰”,或教人“防遏人欲,无使劳生,兹续前功,相次加密,大本达道,表里为一”,说理明确清楚。
理学家遨游于精神领域,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主体,置于广袤的宇宙之间,寻找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宋代理学家“内省而广大”的思维特点,不仅表现在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上,也表现在独立思考的精神崇奉上。由于拥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思维境界,因此,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态度。如《枕屏铭》一文,表面是在说“枕”与“屏”,其实以此戒警,陈淳写道:
枕之为义,以为安息,夜厥宁躬,育神定魄;屏之为义,以捍其风,无俾外人,以间于中。中无外间,心逸体胖,一寤一寐,一由乎天。寂感之妙,如昼之正,可通周公,以达孔圣;夜气之清,于斯以存;仁义之良,不复尔昏,咨尔司寐,无旷厥职,一憩之乐,实汝其翼。(《北溪大全集》,卷四,页九。)
“枕”的作用是让人休息安神的,“屏”则用以挡风的。看似平常之物,却在陈淳笔下被赋予高度的意象。从枕、屏的寤寐间,可知天地寂感,并通达周公孔子等圣贤,可见说理意味浓厚。宋学做为一个新儒学,其探索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所谓内圣工夫、所谓的圣贤气象,皆是强调仁义礼智的五常关系,使人在内省修养中臻于与天合而为一。正因为如果,其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也反映在文学的重理节情上。
二、从容自适
从历史和文化的坐标来看,理学诗的形成自有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因素。同时,为便于说理,理学家对于诗歌史上平淡质朴一路的诗风特别钟情。缘于宋代思想文化尚理的时代氛围,与宋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重建相适应,儒学复兴亦成为宋代文化的显著特色。其实,不只限于诗,陈淳为文亦有自然朴实之风,他所表现的是一种从容自适的艺术风格。如在《遭族人横逆》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要之摠摠皆吾外,于我内者庸何伤?达人大观等毫毛,不为欣戚留心胸。刚应以柔逆以顺,噪应以静暴以恭。红炉点雪不少凝,曲直胜负何所量。况乎他石可攻玉?火经百炼金始刚,坚吾志节熟吾仁,理义之益端无穷。(《北溪大全集》,卷二,页四。)
“横”是横行,“逆”则有反其道而行之意,“横逆”二字意谓陈淳在人生中的挫折。陈淳尚有《邻舍横逆》与《横逆自广三绝》。在《邻舍横逆》中说:
茫茫薄俗沸蚊蛆,礼义全无一点余,只得杜门对贤圣,专来教子读诗书。千般横直休干
己,一切是非无问渠,若救乡邻为被发,风波转起挠吾庐。(《北溪大全集》,卷三,页十。)对于邻舍薄风俗、无礼义之举,陈淳只能反躬己身,以圣贤诗书为业。因此,尚有《横逆自广三绝》,兹移录如次:
汤文事小岂为迷,物我从来绝町畦,胸次洞然天地阔,本无南北与东西。(《北溪大全集》,卷三,页十一。)
乐天一说见轲书,岂是高谈强解渠?牛马蚊虻无足校,不须芥蒂此襟裾。(《北溪大全集》,卷三,页十一。)
仁人方寸万机空,片逆何能介此中,视尔恰如风动竹,在予安有竹嫌风。(《北溪大全集》,卷三,页十一。)
横逆之事,陈淳看得很淡,并不因此影响其心志。对于这些挫折,他只将其视为淡如风般,对于开展己身的修养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透过此组诗歌材料,也理解他生命的进程与困境,展现出一种达观的心态。对于自己的遭遇,认为有如金必须接受火的试炼般,充分显现从容自适的特殊意味。又如其诗作《分水岭》亦然,他写道:
宝贝山前去,琼瑶世界行,蜡鞋穿瑟瑟,竹杖独铿铿。
冻色迫毛窍,寒光射眼睛,酒亭何处认,速欲一壶倾。(《北溪大全集》,卷三,页二。)本诗中透露陈淳在寒冷的冬季出游,当冻色与寒光的逼迫下,只求有一壶酒可以温热己身就足够了。此外,在《和傅侍郎至临漳感旧十咏》中,其中一首写道:
云移月色爽人看,与趋潮声迅拍栏,自是与民同乐地,何妨一整复前欢。(《北溪大全集》,卷四,页四。 )
从该诗浅显易晓的文句中,可以看出陈淳从容之感,有美好月色好看、潮水拍栏之声可听,因此得以狂欢尽情。总的来说,陈淳的这类作品虽然平淡质朴,却透显出从容自适的艺术风格,同时,这种写作风格也反映出作者拥有的旷达心胸。
三、理中有趣
宋代知识分子往往集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特点,也就造成诗与哲学的贯通联结。在儒学复兴的广阔背景上,哲学精神的浸染和泛化,正是宋诗哲理化进程的内在的深层的支配力量。从诗与哲学的关系看,“宋人诗主理”这一重点特征的形成,显然正是哲学的思辨精神和思维方式向诗学领域渗透的结果。邵雍曾说:
物物皆有至理,吾侪看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张南轩亦说:
不可拘执于言语文字、经义圣训,意在理旨,要在涵味触发。近人钱穆亦对理学诗有以下看法:
理学者,所以学为为人。为人之道,端在平常日用之间,而平常日用,则必以胸怀洒落,情意恬淡为能事。惟其能此,始可体道悟真,日臻精微。而要其极,亦必以日常人生之洒落恬淡为归宿。至于治平勋业,垂世著作,立功立言,斯则际会不同,才性有异,亦可谓是理学之余事,不当专凭以作一概之衡量。
钱钟书对于“理趣”曾有定义:
惟一味说理,则于兴观群怨之旨,背道而驰,乃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者;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譬之无极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鸟语花香,而浩荡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
如此说理,即可达到“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的艺术效果,利用具体物象来传达抽象之理,能产生无痕有味的审美感受。
由于宋诗的议论化的创作倾向,造成诗歌的抒情性愈趋淡化,而导致诗歌的哲理性不断强化。理学家大量描写细事琐物,往往能别开生面地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加以观照,生发出深刻的哲理思考,即使在短小的绝句中,宋诗也能显现出浓郁的理性色彩。短短的几个字,占尽了议论化、哲理化,以及冷静思考,多面观察的特点。陈淳虽不以写诗闻名,然其诗作亦富有理趣,如《赴调归忧时题壁》:
上林一株木,其大千百围,栽培自上古,婆娑荫八维。
云何岁月老,颓衰复颓衰,守者勿灌溉,伐者交剥椎。
木根既不固,枝叶何所依,心骨又有蠹,皮肤何能为?
安得善场师,转回阳春熙,变却久悴态,如彼正茂时。
坐令万蠹蚁,稍托庇命丝,嗟嗟难尔必,慨然动长悲。
(《北溪大全集》,卷一,页十四。)
该诗从描写一株老木入手,经由岁月侵袭,衰颓老根,枝叶也无所附依;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叹息老树的可怜遭遇,其实真正意旨从诗名即可窥得一二。对于赴调一事,深感其忧,故题壁为念。诗歌的内涵虽具有哲理性,但因为能巧妙的融写景说理于一体,故读之不仅不流于枯涩乏味,更在诗中生动的景物感染之下,有所触发想象,或领略诗人的哲理意蕴,使诗歌不仅兼具感性之诗美,亦有理性之启迪。又如《依方宗丞和林签判赏梅追璧水之韵》:
冰玉精神清且凝,不嫌霜雪惨于刑,传来春信严明地,吐出阳和节爱亭。(《北溪大全集》,卷三,页五。 )
孤艳迥凌仙子桂,余香暗及庶民星,寻盟壁水浑闲事,好整和羹入帝庭。(《北溪大全集》,卷三,页五。 )
程杰在《梅花意象及其象征意义的发生》一文中言:
众所周知,汉末魏晋以来,中国文化进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时代。人的生活人的情感及其文学表现得到了重视。随着抒情思潮进入发展,诗人们的心灵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敏感于自然物色的刺激,为其所吸引、驿动兴奋与颤栗,表现于文学作品,则是越来越倾向于从“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的直言其概发展为“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的感物起情。梅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其他许多草木鳞羽一起走进诗国的“万花筒”的。
而到了唐宋时期,由于植梅风气的兴盛,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加上画梅之风盛行,唐宋的咏梅作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越了南北朝从冰清玉洁的霜雪后,传来满地春天的气息。诗中描述梅花的孤艳、余香,其实也暗寓君子的高洁情操。情理交融,含有诗人深刻的情感在内,因而能自然感动读者,而非一般语录讲义式的道德宣讲。又以陈淳《和人咏梅韵》为例:
不妨雪压与霜糊,友结松筠鄙橘奴,特放孤标先暖觉,肯随众卉望春逋,疑将水月为精爽,端借琼瑶琢体肤,闯出一元生物意,促兹引领万容姝。(《北溪大全集》,卷三,页九。)
虽不知陈淳此诗为和谁之作,然就该诗言之,此处突显梅花的高洁与身为众卉首领之因,对于梅花生出物意,引领万花,皆给予高度的肯定。又如《丁未十月见梅一点》、《丙辰十月见梅同感其韵再赋》,皆将梅花喻为君子、仁者,对于其洒落万物之光,清妍姿态予以称扬赞赏。表面写梅,其内涵意蕴实际上却是在于象征一种典范的品格气节。此外,尚有莲、葵等植物描述。如《湖斋对莲》:
平湖花叶乱相撑,恰对幽斋小榻清,万绿浅深非作意,千红浓淡总无情。好观物态群嘉萃,从识乾元一理生,占毕暇余时与玩,会子心处有谁评。(《北溪大全集》,卷三,页六。)这首诗从诗名可知乃陈淳对着莲花,心有所感而成。他从书斋一望,恰好可看到莲花。从万绿浅深与千红浓淡中,识得乾元一理,确实不忘理学身分。又如《对葵》中将葵的姿态描写得栩栩如生:
淡黄相枕五重靓,浓紫深藏一窍浑;熟视绝无妆点态,细看不见剪裁痕。(《北溪大全集》,卷三,页七。 )
此处将葵比喻为美人一般,虽然好看,却予人深藏不露之感,使人看不出其妆点姿态与剪裁痕迹,其美可谓浑然天成。谈到天气,诸如《三月十一夜纪候》、《久不雨》、《贺傅寺丞喜雨二十六韵》。以下则举《三月十一夜纪候》为例:
春光正浓二三月,气候不作春和柔,白昼炎炎若盛夏,半夜漆漆如老秋。(《北溪大全集》,卷二,页十二。)
从本诗中可以看出陈淳朴实的文风,不多加雕琢的文句,真实地将春天气候的怪象显现出来。明明应该是和柔的春天,白昼与半夜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一如炎炎盛夏,一如凄凄老秋,这也正是俗谚“春天后母面”之故。因此,陈淳特记为本诗。此外,他在《贺傅寺丞喜雨二十六韵》中有一段写道:
人解戚容为驩忻,岁转凶兆为丰阜,从知天人本一机,气脉流通有如许。(《北溪大全集》,卷二,页十三。)
本诗写作背景是由于当时久未下雨,在烈阳炽热下,田野焦枯、新秧干萎,农民及太守均心急如焚,如伤体痛心般难受。所幸久逢甘霖,万物得以滋生。陈淳将此丰阜情形归于天人一机之故,认为天人之间彼此生气相通,因上天有所感以致降雨予民,蕴含民胞物与的精神。
四、结 语
由于陈淳的思想核心是理学,理学精神实际上更为深刻地贯穿于文学发展的全程,其文学上的主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学精神的衍射和表现。理性化特征的展现,既是陈淳哲学高度发展的结果,更体现了他观察事物的独特角度。这样的理性思辨,也促使他以通达的精神形成一种对于人生的新看法,那就是不被普通的喜怒哀乐所左右的冷静的人生态度。归纳来说,陈淳文风质朴、重在说理,大多数的散文皆注重在说理传道上,此外,并运用诗歌的形式阐述哲理,所谓“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表现出宋诗言理的重要内容。惟少许诗作颇富生动气象,使人发觉其感性一面。
注释:
[1](清)吴之振:《宋诗钞·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1 册。
[2]相关讨论见许总: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3](明)吕柟:《周子抄释》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5册,第12页。
[4](明)吕柟:《周子抄释》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5册,第14页。
[5](宋)朱熹:《朱子语类》,卷 139,第 37 页。
[6]以上两篇皆见于:(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 4,第 10 页。
[7]参考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8]钱穆:《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 年,自序。
[9]钱钟书:《谈艺录·随园论诗中理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28页。
[10]同前注,第 231 页。
[11]“以议论为诗”在诗歌上是具有特色、价值与历史意义。相关数据可参考张高评:《破体与宋诗特色之形成─以“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赋为诗”为例》,《成大中文学报》第二期,1994年2月。
[12]程杰:《梅花意象及其象征意义的发生》,《南京师大学报》第四期,1998年,第112页。
[13](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咏古诗序》,卷2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