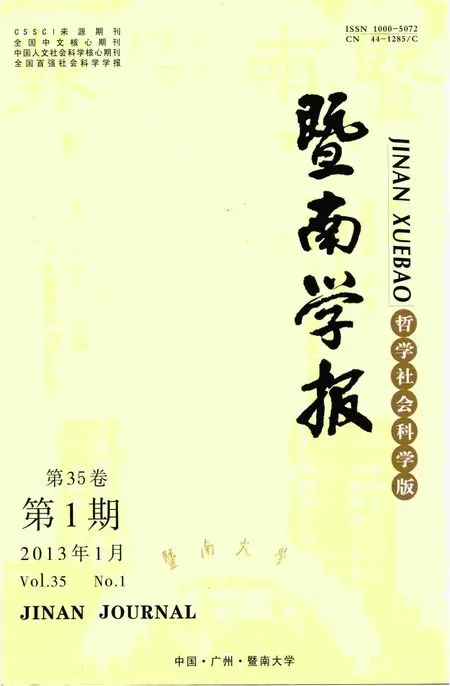如何“现代”?怎样“主义”?:评梁秉钧、张松建对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
李章斌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九叶”诗人为代表的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领域,相关著述非常丰富。但是,综合起来看,在论述的系统性和严谨性、观点的新颖、史料的全面与扎实等方面,有两本体系性的专著非常值得注意,即香港著名诗人、学者梁秉钧198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反抗的美学:1936-1949年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和最近张松建出版的《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前者由于没有中文译本,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国内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而后者刚出版不久,目前对其予以响应的论著尚不多见。这两本专著不仅思路和观点相似,而且方法论上的相通之处也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后者直接受到了前者的影响。笔者下面拟对这两本著作简要地评述,另外还将就该领域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与两者商榷,以探寻新的研究途径和角度,对于具体的问题不作详细的展开。我思考的问题包括:
1.梁、张论著中所建立的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论述体系明显地受到了1960-19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带来了什么收获和局限呢?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他们对待这些理论本身的“态势”有怎样的内在矛盾?
2.梁、张论著和很多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著作一样,也有明显的整一性、本质化的论述体系。如果要瓦解这些体系的话,但又为了不让研究变成单个作家的零散研究的话,那应该如何建立论述体系和脉络?
一、比较视野下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粱秉钧的《穆旦与现代的“我”》和《从辛笛诗看新诗的形式与语言》在国内学界都曾引起重要反响,它们也是穆旦和辛笛研究的两篇经典范文,由于国内读者对它们比较熟悉,此不敷述。不过,它们实际上都是其博士论文《反抗的美学》的章节。由于此论文的全文并未有中文翻译,因此国内的学者注意到的并不多。但是,从现在来看,它依然代表了迄今为止的40年代现代诗歌(或者“九叶”)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准。此文提出了很多在现在依然值得思考和再出发的问题,比如: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和语境的关系应如何检视,40年代的“城市诗”的特色和性质,穆旦的自我抒写与自我认同,辛笛诗歌的形式演变与新诗的发展,唐祈的时间观,唐湜、唐祈、杭约赫的政治乌托邦想象,等等。这一系列发现的取得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烛照显然是不可分离的,例如史皮尔斯对“城市诗”的系统论述,加利尼斯库对文学现代主义的时间问题的思考,史本德对现代诗人的自我形象的观察,等等。
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比较文学的学科训练,梁秉钧在其论述中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多个问题的讨论中创见叠出。例如在讨论唐祈著名的长诗《时间与旗》时,他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艾略特对唐祈的“影响”上,而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以“平行研究”的方法深入地探讨了唐祈与艾略特时间观念的差异与思想背景的分歧。他指出,艾略特诗中的时间旨在批判人精神上的虚妄,他对时间的否定实际上是在否定人对当下的、无意义的现实的执迷,这种时间观念显然来源于基督教。而唐祈的时间批判则有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在《时间与旗》中,“时间朝向的目标不是宗教的永恒乌托邦,而是政治乌托邦,它承诺社会变革,这里对于时间的焦虑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下的焦虑。” 张松建在梁秉钧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时间与旗》具有《荒原》的批判精神,但没有升华为普遍主义的人类文明的深长忧思,而是更具中国化、本土性的艺术向度……把视觉图象、历史记忆与政治乌托邦交融渗透,遂奠定都市现代性的错位奇观,既凸现国族想象的时代印记,也预示中国新诗与西方典范的分道扬镳。”两者的分析不仅出色地解释了唐祈诗歌的特色,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本质也是颇有启发的。
而且,梁著对待西方理论有着较高的自觉性和选择性,这与部分国内学者随意挪用西方理论以阐释中国文本的“贴牌加工”路数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梁秉钧在考虑加利尼斯库提出的现代主义的“五种面孔”理论时,就认识到其中的三种类型——“先锋、颓废和媚俗”——并不适用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因为“先锋是美学上的极端主义和‘探索’精神,因此被视为美学现代性的领头羊,它反对秩序、清晰性甚至成功的观念,与之相联系的是游戏、滑稽、神秘化以及下流的实用玩笑”,由于中国有更加僵化的传统,这使得诗人很难接受“先锋”体现的新奇与激进主义。这种比较视野有助于发现西方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差别,并界定后者的独特之处。
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一书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梁秉钧的研究路线,在其基础上,张著无论是在研究对象、材料方面,还是在视野、方法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扩展,可以说反映了40年代现代诗歌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首先,张著突破了梁著主要以“九叶”为主的研究范围,将其扩大到西南联大的王佐良、杨周翰、俞铭传、罗寄一,中法大学的叶汝琏和王道乾,沦陷区文坛的吴兴华、路易士、沈宝基等,以引起人们对这些“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加以关注,全面认识40年代现代诗歌版图。这种研究视野受到了解志熙的一些观点的启发,后者在1999年一封致叶汝琏的信中说:“可惜的是,目前研究者只把眼睛盯在‘九叶’诗人身上,而不知杨周翰、王佐良、罗大冈、吴兴华、王道乾以及您本人也在这方面多所贡献。诚如您所说,以艾略特和奥登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派诗的确在30-40年代的中国诗人中影响甚大,‘可以说是主导的’,但另一方面,法德等大陆现代派诗其实也对中国现代派诗的成功起过虽然并不那么显眼的但却相当深刻的作用……直到40年代罗大冈、王道乾和您本人,都是深深汲饮着法德现代诗的新诗人,其成就并不比受英美现代派影响的诗人们逊色。”张著通过对这些“被遗忘的诗人”的深入研究,丰富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定义。张著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史料的丰富和全面,他广泛涉猎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两百余种文学期刊和二十余种报纸副刊,他对原始材料的掌握之丰富不仅在40年代诗歌研究领域,就是在整个现代汉诗研究界也是不多见的。
在研究方法上,张著不仅和梁著一样考虑到运用西方理论的选择性的问题,还进一步考虑到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性问题:“现有西方学者的现代性论述能否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现代主义诗作的分析?与作为典范的西方现代诗相比,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性何在?”他提出:“本书注意文本、观念与历史间的互动,必要时融入社会史的内容,建采‘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双重焦点,争取把文本、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他注意到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左翼知识分子阵营扩大化的趋势,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证等历史、思想背景,并试图与文本的分析、论述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论述更具本土性的向度。
二、“西方——中国”天平的两端
但是,在“西方理论——中国文本、语境”这样一个天平中,梁、张二著明显地偏向了前者(虽然他们都对这种做法的危险有所认识),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还是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当作了一种规范性的测量标准和目的论式的价值,而且其论述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整一性和同质化趋向。这集中地体现在梁著的核心论题“反抗的美学”上。《反抗的美学》导论中认为:
为了从前文的理论讨论中抽取出某些观念,以定义中国的现代主义者的特定性质,我想把“反抗”一词作为关键概念,来解释中国这一代的现代主义者在面临着各种社会、文化和语言束缚时所做出的反应。反抗的美学包括多种关键态度:它反对它自身的文化(特里林),批判传统(豪),以“现在”面对“过去”(史本德)。从语言方面来说,它反抗传统语言或者商业语言(罗兰·巴特);就它与读者的关系而言,它偏离了作者和读者的熟悉关系,偏离了熟悉的语符(洛特曼、福克玛)……总的来看,它就像加利尼斯库所观察的那样:反抗传统,反抗资本主义文明,甚至反抗它自身。
梁清晰地标示出他用来定义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人的理论观点和来源,这些理论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松建专著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论几乎全出自西方1960-1980年间,而这正好是西方左翼批判理论最为流行的时期。此时的现代主义理论大都通过“反抗”、“否定”、“偏离”这一类批判姿态来定义自身,而梁对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定性也是“反抗”美学。这种视野在处理这些诗人看待城市、商业文明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坛的态度,处理日常语言的方式等问题上都有说服力和解释力。
但是,单纯的反对、否定美学依然无法充分说明现代主义诗人在面临历史、文化语境时的复杂态度,也无法充分体现其艺术创造的丰富含义,无论是对于西方诗人还是中国诗人而言都是如此。虽然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时期大约是1890-1950年,但是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系统性论述却在六、七十年代才大量出现。应当注意到的是,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大多有明显的左翼批判倾向,这种批判视界未必能和西方诗人本身的视界融合在一起。虽然有部分诗人(如庞德、早期奥登)的创作中确实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但是显然也有大量的诗人并非如此(如瓦莱里、里尔克等)。在反传统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详后)。
而对于中国而言,仅从“反对”(社会、文化、语言等束缚)角度来定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可能远远谈不上全面,甚至也谈不上准确。就他们与传统的关系而言,确实有部分诗人有反传统倾向(如穆旦);但是有的诗人也在寻求与传统协商、对话,积极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如辛笛、吴兴华),他们与传统和主流文坛的关系不仅限于“反对”和“偏离”,而是更为复杂和立体。这一点张松建在其专著第九章中也有详尽的讨论。
而就40年代现代主义诗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言,他们反对和批判的对象远不止城市文明和资产阶级文化,甚至主要不是这两者(对于某些诗人而言),而且这两者在40年代的中国都不是很发达。例如,穆旦虽然在30年代末期写过少数批判中产阶级庸俗生活的作品(如《蛇的诱惑》),但是这些作品只是艾略特那些著名范本的模仿而已,并未和穆旦个人的体验深刻地结合起来(其实穆旦早年也未有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因此到了40年代,这类取自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题材反而在他的创作中消失了。唐祈、杭约赫40年代对城市文明(尤其是上海)有不少批判性的描写,也有反资本主义的内容,他们与左翼诗人的关系也极其密切。但是他们反对的并非是如加利尼斯库所说的资产阶级文明的“理性、功利、进步理想”,而是非理性、非人性的前现代现实,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同时恰好又在期待一个理性、进步的政治乌托邦,这种左翼视角与60年代以降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视野并不一样。
而且,这些诗人对社会、政治现实远非“反对”那么简单,其中也有认可、协商等方面,各个诗人的具体表现也很不一样。例如唐湜、唐祈、杭约赫对当时主流左翼文坛和意识形态有相当大的认同成分(他们有的本身就是中共党员),他们还和左翼诗人臧克家、林宏等一起创办了《诗创造》和星群出版社,其作品中的左翼色彩也很明显。而袁可嘉、杜运燮、穆旦等则与左翼保持了较远的距离(甚至直接对抗),但是袁可嘉也有过与这种意识形态对话的尝试,而穆旦一直对其保持根本性的对立和分歧。“九叶”诗人在对待社会、政治现实方面也有着各自有别的态度,构成丰富的“五线光谱”,仅化约出“反对”姿态则显得过于简单。
把立足点放在天平的一端(西方理论)不仅容易将中国诗人的创作简单化,而且容易忽略他们的创作语境和内在动力。与梁秉钧的论著相比,张松建对这种危险有着更为自觉的认识,他在其论述中着重突出了“中国化”与“本土性”的维度,力图在新诗历史的整体格局中观察现代主义。过去谈论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往往就现代主义谈现代主义,很少关注当时的时代风潮和文艺主流,陷于“见树不见林”之境地;而张松建则充分注意到了现代主义诗人与当时的大众化文艺思潮与左翼诗歌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他指出现代主义诗歌与其他派别“并非决然对峙与对抗的关系,有时候还存在着互相渗透与支援的情形,写实主义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譬如‘七月’派的绿原),现代主义也融合了写实主义的社会指涉(比如杜运燮和穆旦)。这种身份的暧昧性、交叉性与复杂性牢牢地植根于特殊的中国经验,也历史性地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之问题性(problematic)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是非常中肯、深入的观察,它对今后的中国现代主义研究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重要的提示。
但是,张松建在处理中国文本与西方理论的关系时也经常流露出一种“求同”的倾向。例如张松建在《现代诗的再出发》中承续粱秉钧关于穆旦的自我认同的讨论,认为穆旦“嘲笑进化观念,扬弃直线性时间的意识形态,否定五四启蒙遗泽,不加利尼斯库的美学现代性不谋而合。”他认为穆旦的创作在思想主题上完成了加利尼斯库的三个“对抗”(反抗传统,反抗资本主义文明,甚至反抗它自身),“不期然完成了‘美学现代性’的确认”,“建构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现代主义的质素。”然而,从穆旦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实践出发,我们有理由怀疑穆旦是否在40年代就“不期然”完成了70年代加利尼斯库提出的“美学现代性”,是否是在“否定五四启蒙”。穆旦作品中从未明确反对“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理念,而且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考察到,穆旦对新闻、言论自由理念有着强烈的兴趣,对国民党政府和左翼文人的专制作风有自觉的警惕,对反人道的国共战争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对所谓的某些左翼作家构想“光明远景”表示怀疑。虽然西方现代主义的非直线时间观念有着自身的反理性、反启蒙主义脉络,但是穆旦诗歌中的非直线时间理念却并非直接承续这一脉络,而有着明显的社会政治针对性:它首先是对非理性、非人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是对那种光明、进步的“政治乌托邦”远景的怀疑,与其说他是在“否定五四启蒙遗泽”,不如说是承续和发展了五四启蒙运动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理念(当然,他的创作还有超越于此的追求)。
三、西方“现代主义”论述的本质化矛盾和“化约”的困难
过度地倚重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论述并以其为摹本建立整体论述的另一矛盾在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论述本身就有着本质化的矛盾和难以“化约”出某种总体特征的困难。“现代主义”并不是单纯的流派概念,也不是简单的时期概念,它的含义极其复杂,这个概念的外延也不是很确定,而被囊括在它的名义下的各种现象和特征还经常出现相互冲突和对立的情况,这使得对“现代主义”进行本质化、整一性的论述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为困难的。
史皮尔斯在其《狄奥尼索斯与城市:20世纪诗歌中的现代主义》一书开篇直言:“现代主义显然是个不可能的论述的论题。”欧文·豪在其所编的著名的文学现代主义的研究文集《文学艺术中的现代观念》一书导言中也坦言:“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是非常变化多端,难以捉摸,其定义也是令人绝望地复杂。我必须先说明的是,我给现代主义描述的内容经常相互冲突。而且,很难判断某个作家,或者某个作品中的某种倾向是否应该打上现代主义的标记。”他强调:“我不会给现代主义作一个界限清晰的综合归纳,因为我心里没有这种想法,即便有我也不相信它会是有用的。”
“现代主义”不仅含义和性质不好确定,而且其概念的外延也不明确。从欧美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作品集和文论集来看,从1890年到二战时期的很多文学、艺术流派都可以包罗在“现代主义”名义下,比如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等。这些流派有的有直接承袭或者影响关系,有的相互之间并无直接关联,那么它们被归结在一个概念下就颇值得怀疑了。布拉德伯里和麦克法兰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现代主义是未来主义和虚无主义、革命和保守、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古怪的混合体
尽管如此,有不少欧美学者还是力图对“现代主义”做出系统性、整体性乃至于本质性的表述。例如加利尼斯库在其著名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就把其“美学现代性”定义为一个“危机概念”,它包含着三重辨证的反抗:反抗传统,反抗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反抗它自身,因为它把自身理解为一种新的传统或者权威。特里林也指出,现代派文学的突出特色便是对传统文明的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这样的整体论述且不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它是否能全面地描述英美文学都是一个问题。以反传统这个主张而言,它对于部分英语诗人就很难有概括力和解释力。比如艾略特早在20年代就写了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号召诗人追求“非个性化”并融入传统,他还着力从过去的文学传统中挖掘可以重新利用的写作路线和资源(例如他对英国16世纪的玄言诗派的发掘),以用于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之中;而到了晚年,他无论在思想还是创作上都更趋于保守和传统。另一个重要的英语诗人奥登的诗作几乎全使用传统形式(如十四行一类的格律诗、民谣体等),他不断地致力于回顾和发掘传统(例如他对英国“轻体诗”传统的挖掘和创新)。当然,我并不否认他们也有反对传统的一面,但是仅强调这一面则往往意味着把这些重要作家丰富的多种面相排除在所谓的“现代主义”、“现代性”的整体论述之外。把这样的一种理论不加审思地运用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中往往会带来问题。
但是,是不是要彻底瓦解各种关于现代主义的系统论述,甚至取消“现代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呢?著名的现代主义研究者欧文·豪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引述了拉夫佐伊(A·O·Lovejoy)一篇著名的文章《区别各种浪漫主义》中的观点,后者认为:“现在的‘浪漫主义’一词已包含了如此多的意义,以至于就其本身而言,它没有任何意义。它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的功能了。”拉夫佐伊建议人们不要去泛泛地谈浪漫主义,而要去分解出一些系列各自很不相同的浪漫主义,以解决这个词不准确的毛病。豪认识到,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现代主义”一词身上,而且可能更为严重。但他反问道:“为什么在历史上这个词积累了如此丰富的含义和联想?难道这仅仅是人们不准确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吗?而且是不是也存在这种可能,那就是有一种潜在的整体态度,使得这一系列的浪漫主义相互联系在一起呢?”豪指出,分解出一系列的浪漫主义(或者重新命名)可能会给理论分析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很容易落入一种极端的唯名论(nominalism),会把任何历史性和主题性的概括分类都统统瓦解,文学史也就变成了由单个作家组合在一起的一盘散沙”。确实,我们在警惕那些关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论述的同时,也要避免那种唯名论式的吹毛求疵。
但是,欧文·豪并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现代主义”这个词积累了如此丰富的含义和联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设法去化约现代主义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共同特征,从共同点上直接回答它的含义(豪在其文中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我把这种做法权且称为“本质主义”的方法,和下面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相对。这种做法非常通行,但也有着很大的潜在危险:因为现代主义包含着很多差异很大,甚至是对抗性的东西,无法把它化约为同质化的范畴。研究者在对如此广泛的对象进行“化约”或者“求同”的过程中很容易简化,乃至抹杀各对象之间的差异性,把截然相反或者毫不相关的现象扭结在一起,甚至把某些重要对象的核心特质也牺牲掉(前文讨论的梁秉钧的“反抗的美学”论述系统也有这种缺陷)。
第二种途径我称之为历史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途径,这是我认为需要补充的一种途径。其目标就是要把“现代主义”的论述焦点从内部的本质联系(在这种联系确实很少的情况下)转向外部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压力和推动力方面。不妨换种方式来提问:“现代主义”潮流与当时的文坛主流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被称为“现代主义”的诗人在当时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或者,如果他们在当时并未走到一起的话,为什么会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归结到一起?塑造这一整体的“他者”镜像是什么?这一镜像本身有变化的过程吗?比如在中国40年代,为何“现代主义”会成为“现实主义”的对立命题?这一对立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政治含义是什么?
这样一种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意味着不要过多地纠缠于它到底指什么——这可能是严格来说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是要去追寻这个概念具备某种意义的原因和语境是什么,以及它在历史上含义变迁的推动力又是什么(“现代主义”一语的含义不管在英美还是在中国都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变化)。但是,这样一种对待“现代主义”历史主义的处理方式并不能完全否决对作家、文本的正面考察,因为“语境”是特定的写作面对的语境,这种面对的方式无不受到主体和创作者本身的特征的影响。换言之,“现代主义”写作的定义可以从主体和镜像、创作行为和创作语境的相互作用中找到更准确、深入的定义。
四、结语:从“求同”到“求通”
不仅以“现代主义”这种所谓的“风格”视野研究现代诗歌容易走入过分求同的倾向(求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或者求同于某一个中心),而且另外一种常见的研究路径,即某一具体流派的研究视野,也经常走入这种倾向。比如关于所谓“九叶诗派”的研究专著,就有不少都有这种趋向,此不详述。“九叶”本身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群体,他们原本是南北两个诗人群体(北方的原为西南联大诗人,而南方的则为《诗创造》编辑群体中的诗人),他们在1948年才开始聚合,到1949年又戛然而止。关于40年代后期诗坛的分化和“九叶”的聚合,钱理群已有详尽的论述。在1948年之前,“九叶”之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写出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其群体活动和相互影响都较为有限,其共同风格特征和共同文学主张也不宜高估。因此,“九叶”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是值得慎重反思的,过分地强调他们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现在看来问题也是很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排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而仅仅是在警惕运用这些理论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比如掩盖研究对象的语境和内在特质。笔者也不反对任何系统性的研究论述,而仅仅是在探索避免对现代主义诗歌(西方和中国的)进行本质化和整一化论断的方法。考虑到任何系统研究都必须有某些主线和脉络贯穿全文,而前面已经可以看出“求同”和“化约”论述的危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退而求其次,找一种变通的方法呢?与“求同”的方式有别,我这里提出的设想是“求通”。钱钟书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西方诗人和论者虽然有着不同的写作语境和动力,但是他们在遇到某些类似的问题的反应时未尝没有相通之处,而考虑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受到了西方诗人的明显影响这个事实时,则尤其是如此。所谓“求通”并不是(或者尽量不去)化约出相同的趋向和特点,而是去考虑不同的诗人(中西诗人以及不同的中国诗人)面临着那些相似的语境和议题,去看他们怎样做出类似的或相反的回应,而在不同回应中寻找出相同的脉络。
例如,时间问题无论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还是在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人那里,都是一个焦点问题,这并非偶然。“现代”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不同的现代主义作品虽然在质地上有很大区别,但是,“现代主义作品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极端的历史绝境感,潜藏着一种假设,即我们时代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也潜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就欧美的“高峰现代主义阶段”(一战与二战之间)而言,一战打破了人们对历史脉络的期待,使人们感觉人性已经改变(虽然这只是假设),于是“现代”/“现在”的独一无二性被凸显了出来。加利尼斯库也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某种“聚焦于现在的时间自觉意识”。无独有偶,中国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等历史危机,这也使得诗人们也同样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绝境:“历史已经把他们用完:/它的夸张和说谎和政治的伟业/终于沉入使自己也惊惶的风景”(穆旦《荒村》),“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穆旦《沉没》)。但是,中国诗人毕竟是在不同的历史、思想脉络中创作,他们那种看似与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类似的时间观实际上却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目标,并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学者观察到的反理性、反启蒙主义理路拼合在一起。
“求通”也意味着不要把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当作标尺和目标,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在把中国现代诗人和其西方同仁进行对比论述时,能“通”则“通”,不能“通”则不必强“通”之。例如,与大部分西方现代诗人有别,大部分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政治关怀,用夏志清的话来说就是“感时忧国”精神。这种精神要么催生出一种关于自我定位的道德焦虑感(如辛笛的作品),要么萌发一种期待理想社会秩序的政治乌托邦想象(如杭约赫、唐祈),而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很少有这类家国关怀。如果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作为“坐标轴”来衡量这些诗歌的话,可能会有一种不够“现代”的不足之感。可是,在1960-1980年代欧美“现代主义”已成为过去时的时候,表现道德关怀和政治反思的东欧和苏联地下、流亡诗歌反而在西方世界倍受推崇(如米沃什、赫鲁伯、布罗茨基等),而这些恰好是欧美现代主义作品和理论很少触碰的题材。一旦注意到这些事实,就不难明白,题材本身没有“现代”和“落后”之分,而关键要看作家对它的处理和表现是否深刻,是否有创造性。因此,应当避免把“现代”和现代主义理论当作价值标准,在考察这些作品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它们如何“现代”,也要评价它们作为艺术作品的自足性、完整性、开创性和想象力等诸多方面,换言之,要评价它们是否是有价值的“文学”。
“求通”不仅意味着不随意求同和化约,也意味着保持论题的弹性和开放性,以免某一理论和价值标准固定化、模式化。这本身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欧文·豪说:“过去人们急于索要答案,而现代时期的人们则把自身和问题联系在一起。现代主义在到达了某个节点以后,其本质体现在这样的主张之中:真正的问题,值得问的问题,是没有(也不需要)答案的;它只需要反复地问,永远用不同的方式来问。”而以上对于梁、张二著的批评也显然不是“定论”,更不是在贬低两者的开创性价值,而仅仅是在思考如何在两者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更进一步的可能性路径。因为,今后研究四十年代现代诗歌的学者,无论其方法、取向如何,此二种著作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
[1]Ping-kwan Leung.Aesthetics of Opposition: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1936-1949[S].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San Dieg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1984.
[2]Monroe K.Spears.Dionysus and City:Moder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Poet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3]Matei Calineascu.Faces of Modernity[M].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
[4]Stephen Spender.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5]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李章斌 一九四十年代后期的穆旦:内战、政治与诗歌[J].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10,(2).
[7]Irving Howe,The Idea of the Modern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M].New York:Horizon Press,1967.
[8]Malcolm Bradbury,James McFarlane eds.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91.
[9]Lionel Trilling.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J].Partisan Review,1961,(2).
[10]钱理群.一九四八年:诗人的分化[J].文艺理论研究,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