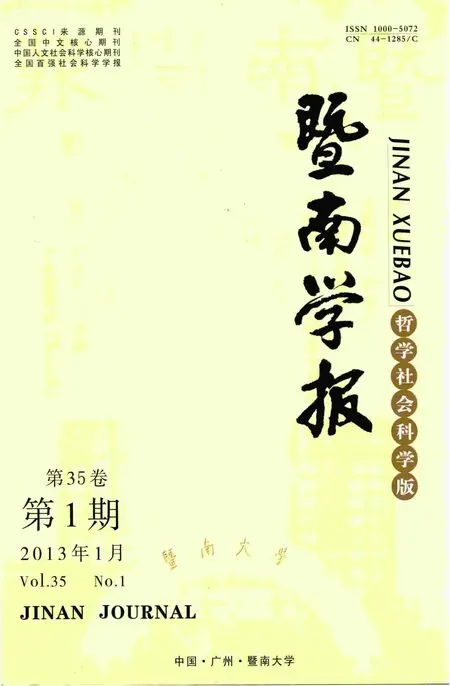山西商人曹润堂与清末蒙旗垦务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9)
在蒙旗垦务研究中,笔者偶阅山西太谷商人曹润堂墓志铭两则,内中均提及曹润堂曾襄助贻谷办理垦务:
《曹公柘庵墓志铭(代)》云:
壬寅,垦务大臣贻将军毂奏调君襄垦事,君请命于母而行,时公私扫地赤立,将军彷徨无所为计,君为之驰驱经年,款乃渐集,然将军忮人也,妒公司多商股,己且无所渔利,稍稍与君为异同。君不能堪,然犹时以良言相匡饬。将军卒不能用,君乃废然引去。越数年,垦事大坏,朝廷遣重臣临边勘验,逮将军下刑部狱。凡以垦案见保荐者,悉与注销。惟君先以龃龉去,人服其高
《曹润堂墓志铭》云:
壬寅秋,垦务大臣贻将军毂奏调君襄垦事,君请命于母而行。时公私扫地赤立,将军彷徨无所为计,君冲寒塞外者类月,创设西蒙公司,复返里集款至十余万金,事乃举。既而,将军以公司多商股,稍稍与君为异同。君乃废然引避。越数年,司其事者皆获严遣,惟君先以龃龉去,人服其先见
上述两则史料,同为曹氏墓志铭,然则前文直言乃郭允叔代他人所作,后文乃“候选知县、霍州学正前太谷县教谕、介休曹子勤”所撰,石碑则系曹润堂子曹中注所立。由此,笔者以为郭允叔文乃是代曹子勤所作,在曹子勤略做修改后交付曹润堂后人。
细读两文,虽部分文字、细节有所出入,然大意则同:曹润堂襄助贻谷办理西盟垦务,筹款有方,不料因贻谷贪墨而最终引退。在检阅有关垦务档案、《垦务调查汇册》、《贻谷奏稿》、《蒙垦续供》等史料后,本文发现曹润堂与贻谷以及蒙旗垦务关系极大,其中原委、经过及结果并非上述两则墓志铭所云那么简单,正是曹润堂创设垦务公司之提议帮助贻谷迅速打开蒙旗垦务的局面,然后垦务公司之设置,也成为后来垦务参案贻谷被革职拿问的一个重要罪状。因此,梳理与辨析曹润堂与蒙旗垦务公司的关系,无论是推动蒙旗垦务研究的深入拓展,还是对加强贻谷垦务参案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蒙旗开垦之舆论与西路垦务公司创设之背景
清制,蒙旗不准私自开垦,但由于生计困难,有清历代汉人入蒙开垦、蒙人私开私垦之举不断。李辅斌的《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珠飒的《清代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第3期)等文对此有初步的研究。此外,《清史稿》志以及藩部等类中均有不少史料对此有所反映。出于“防边实蒙,实蒙在垦”的考虑,晚清诸多疆臣以及有识之士多次进言主张放垦蒙旗。对此,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奏文中曾有介绍:“同治九年,前库伦大臣张廷岳有‘兵不足恃’之奏;光绪六年,前司经局洗马张之洞有‘练蒙兵’之奏;十一年,查办土默特争地大臣绍祺有‘蒙古有租乃能练兵’之奏;十二年,前伊犁领队大臣长庚有‘缠金屯田’之奏。”上述岑春煊所提只是部分,光绪二十三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请开乌拉特三湖湾地方屯垦,既得谕旨,然理籓院以蒙盟呈有碍游牧格其议。二十四年,黑龙江城副都统寿山、国子司业黄思永等均曾主张开垦伊克昭、乌兰察布等盟牧地,察哈尔都统祥麟因言“欲蒙地无私垦,必严科罪,欲蒙员无私放,必惩奸商”
在一片主张开垦蒙旗的呼声中,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月,山西巡抚岑春煊两次上奏清廷,提出放垦内蒙古西部盟旗的土地,最终使得清廷决定开垦蒙旗。
晚期疆臣主张蒙旗开垦的首要原因乃是练蒙兵以拱卫清廷,岑春煊等人强调俄罗斯为边防大患,而现实却是俄人之势日盛强而蒙古之众日就贫弱。如何解决呢?岑春煊曾云:“边臣皆知蒙兵宜练,而苦于无饷。蒙长皆欲自练其兵而苦于无力。是则欲练蒙兵,非筹练费不可,欲筹练费,非开蒙地不可。”
其次,在岑春煊等人看来,蒙地地利是保障垦务成功的必要前提:“今蒙地接晋边者,东则为察哈尔右翼四旗,西则为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十三旗,田地饶沃,水草丰衍。乌拉特、鄂尔多斯两部,依阻大河,形势雄盛,灌溉之利,甲于天下。臣诹之寮属,考之案牍,准噶尔有招垦救灾之案,达拉特有兴屯收租之议,是蒙之便于开地可知”。
其三,蒙旗开垦能开辟巨额筹款之由。光绪十二年,山西巡抚刚毅曾奏云达拉特旗昔岁收租银十万,近所收租钱不及三千串。一旦开垦,则利源大增。光绪二十五年,黑龙江将军恩泽称若开垦札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银四、五十万两。”岑春煊则称“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既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
“开蒙部之地为民耕之地,而竭蒙地之租练蒙部之兵,边实兵强,防密盗靖”,正是岑春煊等人勾画出的方案促使清廷改变蒙旗私放私垦的现象,决定由朝廷放垦以利国是。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2年1月5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从西安返京途中,批准岑春煊开垦蒙旗的建议,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荒地甚多,土脉膏腴,“自应及时开垦,以实边储,于旗民生计,均有裨益。著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即将应办事宜。会同该将军巡抚随时筹议具奏”。
根据贻谷《垦务奏议》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八月等折,我们可以整理出贻谷奉令后的行程与初办垦务概况。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贻谷正式赴晋边督办垦务,二月十八抵达山西太原,四月十八抵达归化、五月十三日抵达张家口,分别与山西巡抚岑春煊、绥远将军信格、察哈尔将军奎顺等悉心筹议办法,最后于绥远城设督办蒙旗垦务总局,后又设丰宁垦务局、张家口垦务局办理察哈尔右翼、左翼垦务;后设西盟垦务总局,分管乌、伊二盟之垦务;设绥远城八旗牧场垦务局,专理大青山后山八旗牧场垦务。
二、曹润堂与西路垦务公司之创设
以今人后世之明可知,贻谷督办垦务事业之关键实际上乃是创设东西路垦务公司,以公司与垦务局相辅而行,公司之创设大大推进了垦务之开展,同时由于垦务公司运作中之诸多弊端使得贻谷最终被弹劾。据史事而论,这一建议实则乃山西商人曹润堂首创。
曹润堂,山西太谷北洸村人,名培德,润堂系字,以字行,别字柘庵,生咸丰三年,卒于宣统元年(1853 - 1909)。润堂出身太谷巨商家庭,以“资雄于并晋间”。先祖曹三喜等人苦心经营,至道光、咸丰年间,达到全盛时期,拥有商号几十处,遍布全国,甚至远及莫斯科、西伯利亚。其经营项目有票庄、账庄等。
光绪十五年(1889),润堂中举。“颇欲得一官以自效于世”,自谓非为俸禄,而图报国,闻国家大事抵掌而谈,同辈咸叹服。然又感科场坎坷,有“不重才华重门第,吾曹读书真失计”之慨。
因家世既饶,而族人“起家积贮者尤众”。培德最终以经商为主业,而族人委其总揽全族商业诸事,培德亦“持其族政以终于家”。经培德苦心经营,曹氏商业日益扩大,所有“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其一手创立。光绪时曹氏资本多达六七百万两。培德经商以求富国,曾有诗云“喜逐陶朱求富国,漫从罗马觅奇书”。在其主持家政时期,支持族人办理开矿、票号以及收复矿权。二十四年,族侄曹中裕曾与福公司义商罗沙第议定借款开矿。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曹润堂襄办晋省商务局事务,胡氏云因曹中裕病故,局中只有一员负责,亟待派员襄理,而曹氏为请假在籍内阁中书,“历练精明,熟悉商务”“令入局襄办一切,商务可期”,结果朱批“所请著不准行”。庚子事变后,山西财政困窘,润堂率先捐资,先以中书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隶试用,后保道员,加盐运使衔。
润堂经商多次到内蒙,于屯田垦务多有建言。二十七年,时有三湖湾开荒之议,知府吴书年两次函邀润堂参与垦务,润堂有诗曾曰:“拟向龙冈学楚狂,荐书连日劝行装。雪镕麦陇春泥滑,烟锁松压塔笔藏。课士多方才自见,屯田无术地全荒,此生屡被浮名误,一事无成鬓已霜。”二十八年二月,当贻谷为督办垦务到太原时,曹润堂曾与山西巡抚岑春煊一道陪同贻谷游览晋祠,并有诗云:“山光不断水盈堤,大帅旌旗望眼迷,十里绿杨春试马,一犂红雨燕御泥,国无荒地勤耕种,民有余闲习鼓鼙,莫道此行徒选胜,采风问俗过桥西。”正是在此时,曹润堂联合同乡山西太谷绅商武洋(当时捐资为“分省四川候补直隶州知州”)禀文贻谷请开垦务公司。
曹润堂与武洋创设垦务公司的具体建议如何,由于资料缺乏无法得悉详情,但是从后来贻谷据此上奏的结果来看的确受到贻谷高度重视与赞赏,贻谷称曹武二人“好义急公,深勘嘉许”。在收到禀文后,贻谷在太原与山西巡抚岑春煊“往复熟筹”认为必须创办垦务公司才能有益于垦务大业。岑春煊曾致函荣禄提到贻谷到晋后,晋商乐意成立垦务公司,承领荒地:“垦蒙一事,固涠安边,利民富国,百世之利,断然可知。历抚臣屡议兴办,皆不竟功,良由事者不得其人,以至蒙旗阻扰,坐失大利。此次得吾师主持于内,霭兄壁画于外,此诚千载一时之良会也。晋中绅商闻霭兄持节来晋办理垦务,颇有议集股设立公司,承领荒地者。上既得人,下复有款,此事之成,跂足可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1902年9月11日),据曹润堂武洋二人之禀请,贻谷奏请设立垦务公司,其大旨如下:
其一,创设原因。贻谷在奏折中明言经过数月以来的博访周咨,垦务亟待妥筹良法。他指出:“晋直盟旗各地宜于树艺,且生计在耕而不在牧”,且“向来私放私开从未能施行官垦以至蒙员受贿,授柄地商,地商包揽假手地户,攘取官地,据为己有。”以察哈尔左右翼为例,贻谷指出已开垦地亩中交纳押荒升科者不过十之一二。贻谷认为在蒙地久为私垦所占的现实背景下,为实蒙防边,不如开垦可兴蒙古利源,又可清私垦积弊。如何开垦呢,贻谷强调由垦局零星散放,“纷扰实多”,应当采纳曹氏建议设立公司预为筹画。贻谷强调成立垦务公司有利于垦务大局,其好处在于:“公司既立有事有统宗,有以简驱繁之权,无户总地商之弊。”
贻谷奏设成立垦务公司的出发点是为了除垦务弊端,另外帮助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解决赔教款项亦是现实动因。因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有“仇教”之举,光绪二十七年,蒙教两造立定草约确认该旗赔款37万两,该旗交给地亩租、现款、粮石等银18万两,尚欠银19万两。教堂欲得银,蒙旗欲抵地,久未结。为解决现款赔付问题,该旗在四成地界内先后凑足二千顷由绥远城将军钟泰招商代放,得价付赔。因“边方苦乏富商,招徕无术”,钟泰与贻谷商议言明每亩按价银七钱算,共计银14万两,归股商承领缴价以付赔款。实际上也就是通过成立官商合股之垦务公司,“赔教之款,即由公司指拨,所报之地即归公司转放。”对于此点,贻谷后来的供稿中指出:”“按西路垦务公司之设系官商合办,重在赎地,为西垦入手之基。”
其二,公司组建方法。垦务公司如何组建?贻谷提出应当采取招股。贻谷指出近来各省办理路矿及公益局厂事务,“率多招集股本,设立公司”,若借鉴此法办理垦务则大有裨益,原因在于:“人情于利之所在罔不争趋,以蒙地多膏腴,边地富商久所讯羡,一经公司招致入股,必多巨款,无难遽集。”
垦务公司的股份如何招集呢?在与岑春煊商榷后,贻谷同意曹润堂二人所请,施行官商合股成立垦务公司。贻谷在奏折中提出东西两路垦务公司股本各十二万两,其中官商合股各半。西路公司之官股,贻谷建议先由山西商务局剩存项下拨给,商股六万两则由曹润堂等人自行筹集,“计成本官商各半,先行试办。”至于赢利,在根据章程官商各半,“总使官商均沾利益,不至畸重畸轻。”
其三,公司如何运作呢?对此,贻谷在随后的奏折中有所明言,贻谷认为垦务公司与垦务局“相辅而行“,凡垦局所到之处,则公司亦随之。贻谷指出除去私垦越垦等有纠葛之地仍由垦局办理外,其余各旗隶属于晋、直各垦局之生熟地一经垦局丈明即可拨给公司承领并由公司交纳押荒银,土地则归公司佃与农人开垦[11]226。
其四,公司之经理人员。由于垦务公司系曹润堂等人首先创议,且润堂等人“家道殷实,乡望素孚”,故贻谷奏请派曹润堂、武洋承办,同时令曹润堂之侄曹中成以及户部主事姚世仪二人会同办理。清廷“如所請行”。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光绪帝朱批曰“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在清廷同意成立垦务公司之后,官商各自开始了筹集股份的过程。官股的筹集看来极为顺利。在同年冬间,山西巡抚赵尔巽由山西藩库陆续拨解银11万两给贻谷作为垦务经费,贻谷从中划拨六万两存于存义公、大德通、合盛元等三家商号,作为西路公司官股本。至于六万两商股,则由曹润堂认招。在清廷同意开办垦务公司之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曹润堂赴归化与贻谷面议开办公司之事。随后,曹氏回晋太谷设局招股。在招股宣传上,宣称先办达特拉地即四成地,次办后套三湖湾等地,即绥远亦归承办,每股 100 两,官商各股共计 1200 股。时清廷规定各省绅商设立公司必须有现款股本呈验,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贻谷令曹润堂“速即补齐”商本六万两。由于一时未能招集六万两商股,故曹润堂先向商号裕盛厚借银六万两以“存备拨用”。十一月初七日,在如数呈验六万两商股后,贻谷饬令曹润堂迅速应行回晋招股抵补,招股完成后应迅即返回公司,“不得稍延时日,致误事机”。
从相关资料来看,曹润堂招集商股的情况并不乐观,也因此迟迟未能返回绥远垦务总局。二十九年三月廿二日,贻谷咨行护理山西巡抚吴廷斌转饬曹润堂如果招集商股六万两后不需再招,“免致股本愈多,股息愈难应付”,并请吴氏就近传询曹润堂“从长计议”。二十九年五月初四,贻谷札派润堂为垦务公司正总办,其侄儿曹中成与贻谷心腹姚世仪为副总办。同年润五月十六日,贻谷以西路垦务招佃、修渠等紧要事务殷繁,总办曹润堂由于集股未回,而公司事务又刻不容缓,因此贻谷调派垦务总局会办候补知府周克昌与曹润堂共同担任西路公司总办,并令曹周二人“和衷共济”。润五月二十日,曹润堂、周克昌二总办联名向贻谷申报即日起启用“奏办蒙旗西路垦务公司关防”。贻谷任命官商各一员共任西路公司总办,目的是希望二人共同负责,以符合官商合办之意旨,但是很快周克昌“赴调川省”任职,而曹润堂因母丁艰未能赴绥远办理公司事宜。不得已,七月十七日,贻谷遂任会办李云庆为总办。
为何曹润堂、武洋不能赴绥远参与西路垦务公司之经营呢?一方面由于曹氏身负招集商股之重任,另外一方面亦有客观原因,即曹润堂因母亲病逝丁忧已经将所有公司一切事宜均令武洋“暂行代办”,而武氏拟定秋季葬父,二人均未能赴绥。故二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山西巡抚向贻谷咨复曹润堂、武洋不能赴绥的原因俱系实在情形。
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贻谷同时札饬曹润堂、武洋称既然二人各有事故不能到绥远办理垦务,因此要求将曹润堂等人所招集之股份与贻谷自己另外招集之股份分别结清,“以免混淆”,同时命令二人将“在省经手支用暨所设分局开支各款著结至八月底止,逐一开列分报本大臣及山西抚部院以便查核。”接到此札后,二人禀复:“遵查太谷所设分局自三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底止,一切动支各款计银陆百贰拾壹两零”。奉到结清股份之命令时,曹润堂招集之股份到底有多少呢?实际上只有383股,每股100两,共计本库平银38300两。由此可见前述墓志铭所云润堂籍贯十万余两殊非事实,实际上远远不如贻谷以及垦务人员等所招集之商股多,光绪二十九年,贻谷自集股本22200两,后来贻谷及垦务人员续集股本54800两,共计77000两,在西路垦务公司前截被结算后,贻谷等人之股均被移入后截垦务公司的股本中。
三、贻谷见利而撤商股
曹润堂等人创议成立垦务公司,其针对者只是西盟而言,即伊克昭、乌兰察布盟两盟杭锦旗、达特拉等十三旗,贻谷受此启发,决议在东盟即察哈尔左右两翼创办东路垦务公司。在奏请成立垦务公司的奏折中,贻谷明言自二十八年二月禀请之后,曹润堂等人以西盟垦务公司未能成立而于垦务一事“观望不前”。在贻谷看来,曹氏所陈系仅就西盟而言,而“东西事同一律”,因此贻谷主张同时在包头、张家口两地各成立西路、东路垦务公司,“招集股份,凡入股者即准核照荒价领地承垦,原入股本将来应分余利,均按该公司初立章程,官商各半,总使官商均沾利益,不至畸重畸轻。”然而由于蒙地膏腴,垦务有利,对曹润堂之招集商股,贻谷由最初的积极支持态度渐次转为消极,最后在垦务公司大获其利的情况下干脆将晋商股本裁撤!
二十九年三月廿二日,贻谷曾咨文吴廷斌请其转饬曹润堂在招集好六万两商股后不需再招。在咨文中,贻谷表达了对曹润堂招集商股进展的不满,认为曹氏不善经理,在贻谷看来,曹氏疏漏之处有二:
其一,曹润堂办理垦务未能“统盘筹算”。贻谷坦称,对于曹润堂设立公司集股承办之禀请,其与前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均表赞同。为实现“以祛除积习秉大公,惩官局之弊端,示商民之诚信”的开办目的,当事者应当“统策始终,力求实际”,而曹润堂“以禀牍批准之日即为公司开办之日”未免不符实际,因而贻谷认为曹氏“所办一切事宜多未统盘筹算”。
其二,曹氏在招集商股方面未能“迅集”且于经费方面又未能“撙节”。从二十八年九月曹润堂回晋招集商股到二十九年三月,曹氏仍未能招集完六万两商股,对此贻谷大为不满。并且,对曹氏招股中的花费,贻谷则认为太过“浩繁”。对此贻谷曾有罗列:自二十八年二月禀请创设公司到当年十月已经花费一千余两之多;自十月到二十九年三月,曹氏请人帮助集股,所花“车马津贴等费及在京刊刻股章刷印股票各项必须之款,约计当在三千内外”;此外曹氏又在太谷设立分局招股,花费又增。因此,贻谷认为垦务公司尚未开办所动用款项即已如此浩繁,“若值畅办之时员役加多,所费更属不赀”。后来垦务局的调查证实了贻谷的担心,曹润堂在太谷招股所用经费、在归化筹办公司所用经费、招股用去“余平三项共库平银四千四百二十二两余”。
贻谷强调其于垦务是“悉心筹划”,既“不诿难于人,亦不坐视其弊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贻谷令吴氏转饬曹润堂商股招集完毕后毋须再招,以免股息无处可开。
事实如何呢?贻谷为何令曹氏不得扩招商股,根本原因在于在筹办东西路垦务公司的过程中,贻谷等人发现垦务大开获利之源泉。奉命查办贻谷垦务弊案的鹿传霖曾有奏折认为贻谷通过开设垦务公司无须本钱而自能获利。按照垦务公司章程规定,凡入股者核照荒价领地。垦地由公司缴纳押荒银,然后任其转售他人。以东路垦务公司为例,上等垦地押荒银为每亩八钱,鹿氏指出该公司非上地不领,“以千顷计地价坐得八万,一反手间即赚银五万矣!东西两公司共领地二万顷,是蒙古报效之地价钱全为公司所蚀。”更令人吃惊的是东路垦务公司并非“先缴押荒然后领地转售”而是先收到所售垦地地价然后再缴押荒银,“是真不费一钱而坐致巨万矣”!
正是如此,在曹润堂回晋招集商股的同时,贻谷亦自招商股,二十九年当贻谷招集到22200两后,随即饬令曹润堂无论是否集足陆万,“速行截至招集”。据后来调查者言,其原因是:“盖斯时东垦获利,正可朋分以充私股矣。故毋须商股也。”在此时,曹润堂已经招集商股383股,除部分用于太谷分局开支外,其余均上交西路垦务公司收讫。
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二十日,贻谷谕令将晋商383股一律退还,并陆续拨还晋省官本银六万两。三十一年(1905)春,贻谷发布《退晋商商股公启》,下令撤退曹润堂所招集之晋商商股:
公司招集股本为联商获利起见,不意西盟垦务春遭匪乱,夏被水灾,睹此情形不独得利恐难,或且致亏商本亦不可知。本大臣创办此举无时不引为疚心。查曹绅经招各股历时甚久,所费甚多,始得三万八千三百两,集款之难,概可想见,且众商股本皆系数世经营积铢累寸,重一言之信故倾孤注之资,各股款既如此艰难,该公司宜如何保护,晋省从前官招商股往往以事无成效重累商家。本大臣招股之时,即引为前鉴,以信示之,并以身担之,以谓纵不获利,断不使受亏耳。今西垦兵水两灾,虽出自意外,倘使嗣后机更不顺手,何以重信而对众商。维今之计,只得从权将众商股本一律清还,其应得之息亦按股付给完璧以归,俾免后累,庶公家以后招股尚可以通商情而开风气,即本大臣鳃鳃之虑亦得以稍安也,此启。
贻谷指出退晋商股本的原因有二:一是西盟垦务遭受匪乱与水灾,公司获利恐难,甚至商本亦有亏本可能;二则晋商股本“皆系数世经营积铢累寸”,系曹润堂历经艰险所招集而得,公司应当善为保护,以免“事无成效重累商家”。具体如何善为保护呢,那就是撤退商股,同时按股付给应得五厘股息。在贻谷看来,虽然“得利较微”,但是商本则毫无所损,“此实本大臣维持商业之苦心也”。同年六月初七日,西路公司副总办姚世伊禀报贻谷已经完成撤退商股的工作:“会同原经手招股之曹绅润堂传知各股商逐一发给”。除股本外,还有二年股息总计库平银 2315 余两。
光绪三十四年当贻谷被下狱调查时,对于撤退晋商股本,贻谷则又提出了另外的原因:“嗣因经理晋商股银之曹润堂请假回籍,其侄公司副总办旋又病殁,晋商股本急待归还,是以三十年底饬将曹绅所招之股三万八千余两筹撤发还,均按股给予年息。”
贻谷撤退商股的真正原因是否真的如前所述系由于西路垦务公司赢利难以预期、曹润堂等晋商急待归还股本、贻谷本人体恤商艰呢?实则不然,贻谷所言只是托词。据西路公司册报可知,自二十九年开办起至三十一年底为止,该公司净得利益库平银十四万两!此前晋商股本被撤退看似保本并获得股息,实则并没有享受到西路垦务公司结算后的余利花红,按照贻谷垦务案发生后所成立的垦务调查局的调查,这些余利花红最后是被贻谷等人瓜分:“无论公司人员非公司人员,皆由贻前大臣为之标分,有亲笔字条称分红各垦员曰诸同事。”在撤退晋商股本后,贻谷等人迅速将西路垦务公司截算,并重新集股另外筹设后截西路垦务公司。由于斯时东路垦务公司正大获其利,光绪三十年四月,贻谷自认东路垦务公司自二十八年开办到二十九年两年间净余利银有十五万二千三百八十八余两。除去花红、公积等费,官商各股实在应得利银有九万七千五百二十八两余。只有将晋商股本撤退后,贻谷等人方可将东路垦务公司私人股份所得利银“搀入冒领地股本”,这样“既分东利,又取西赢,辗转滋生获利无”。
润堂曾有诗云:“屯田有志空怀策,报国无人共请缨。”当其请缨创设公司以开垦蒙旗的建议被贻谷采纳并付诸实践时,垦务公司之进程与结果则远非其所能预料者。尽管曹润堂未能招够所认之六万商股,然则其所招收之三万八千三百两商股在代替偿还达特拉旗教款、成立西路垦务公司的过程中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贻谷在公司成立之初强调官商合办,但是当发现垦务获利甚大时,曹氏所招集之商股最后却被以保护商本的名义撤退。按照西路公司成立时官商各半的约定,公司股本总计12万两,在撤退润堂所照收之商股后,其余商股77000元均为贻谷以及各垦员之自招。而这也突破了官商股本各六万两之初定规定,最后的结果则是贻谷等人进而将前截西路公司结算并私分余利。
不过,对曹润堂而言,幸运的是当光绪三十四年贻谷因垦务弊案而下狱,垦务官员多受株累之时,曹润堂虽然曾创议成立西路垦务公司并被贻谷奏请委派为总办,但是曹氏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调查者知道曹氏仅负责招集商本,“绝不与闻公司之事”,并且由于所招商股旋即被撤退,“一切禀牍并不会衔列名,后之谋利分红筹办后截则更非其所知”。
清季以来的垦务实业中,蒙旗垦务实可谓影响最大者。其放垦之由,实出于“实蒙防边”之虑,通过开垦蒙旗土地,既可清私垦积弊又可兴蒙古利源。蒙旗垦务如何得以开垦呢,垦务公司之创设以及实践,实则功不可没。以公司开办垦务,改官垦之不足,时乃曹润堂、贻谷等人之大创举,以其成效与影响而论,纵向比较则在贻谷督办垦务之后,蒙旗垦务在清季则“毫无进展”,继任诸将军不过调查垦款,催收旧欠而已;横行比较,蒙旗垦务则远胜于张謇创办之通海垦牧公司。然则,通过本文关于曹润堂与西路垦务公司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即便采取了公司这一新式办垦机构,官夺商利的现象仍不能禁绝,实乃近代官商合股公司命运之缩影。更为重要的是,在鹿传霖查办贻谷垦务参案中,创办垦务公司反而被视为巧设,是贻谷以及随员牟取私利、贪污蒙旗押荒的重要措施,而这也是贻谷的四大罪之首。本文的研究表明,垦务公司是在山西商人曹润堂等人提议之下创办的,尽管贻谷后来图利将晋商股本撤退,但不能说垦务公司是巧设,然而贻谷等人在后来垦务公司的运作中,将并未按照清廷商部规定注册公司,将垦务局委员兼为垦务公司人员,由此成为酿成弊案,也成为垦务参案中的一大关键。此外,有必要加强蒙旗垦务中的人物研究。通过对曹润堂的研究,本文认为应当以重要人物为中心,由此拓展垦务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中贻谷就是一个极好的个案。对于蒙旗垦务,贻谷自认办理极难,“强者梗阻,弱者观望,宽之侮至,蹙之变生,敷衍则辜恩,清厘则府怨。”毁之者云其“败坏边局、蒙民怨恨”,誉者赞其“垦放逾十万顷,东西二千馀里。绝塞大漠,蔚成村落,众皆称之”。最后因垦务弊案坐狱,被视为晚清一重大贪污案,然贻谷一概否认清廷所定各罪,个中缘由、经过实值得进一步探讨,惟有如此,蒙旗垦务的原生态历史方能得以进一步展现。
[1]郭允叔.曹公柘庵墓志铭(代)[A].郑裕浮编 郭允叔(象升)文钞(上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2]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中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3]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4]赵尔巽等著.清史稿[C].北京:中华书局,1977.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跦批奏折(第93辑)[Z].北京:中华书局,1996.
[6]胡万凝纂.太谷县志[C],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7]曹润堂.复选木石庵诗钞(卷下)[M].太谷:曹氏自刊,1921.
[8]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D].北京:中华书局,1984.
[9]黄鉴晖主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D].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Z].清史工程档案号03-5372-014,缩微号405-3566,录副奏片.
[11]贻谷.垦务奏议[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2]杜春和等整理.荣禄存札[D].济南:齐鲁书社,1986.
[13]贻谷.蒙垦陈述事略[C],北京:京华印书局,1911.
[14]西北垦务调查局编.西北调查垦务汇册(全)[D],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5]冯曦.绥远垦务辑要[C].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16]贻谷:《蒙垦续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4册[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17]德宗景皇帝实录(七)[C].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5辑)[Z].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
[19]甘鹏云.归绥垦务调查记[C].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20]黄奋生.蒙藏新志[C].北京:中华书局,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