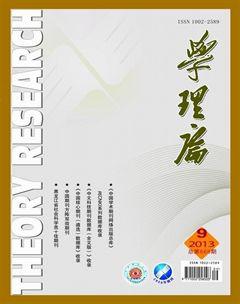唐陵与宋陵神道石刻异同研究
刘晓媛
摘 要:通过对唐陵和宋陵神道石刻的分析比较,来研究其文化特征。宋陵石刻是从唐陵发展而来,继承其很多特征,但又有所发展,归纳其相同以及不同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两朝石刻艺术的特点,以及我国古代陵墓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规律。
关键词:帝陵;神道;石刻;外来文化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01-02
唐代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唐代帝陵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唐陵不仅规模大,制度上也有新的创建和发展,陵墓前大型石刻群的设置,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而后又建立统一王朝的北宋,其帝陵集中分布在河南巩县,北宋帝、后陵以及陪葬的亲王、大臣墓的石刻总数可达上千件,在当地形成特有的文化景观;其形象多样的造型、雕刻手法集中反映了北宋石刻艺术的独特风貌。宋朝虽然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难敌唐代,但其艺术发展水平却独具魅力。以下对两代帝陵神道石刻的组合以及其意义做以简要对比,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两代统治者治国思想的异同。
唐陵石刻包括有:石虎、石狮、蕃像、石碑、石人、仗马及控马官、鸵鸟、翼马、犀牛和石望柱。而宋陵石刻的组合一般较为规整,一般在神道自南至北分别为:望柱、象及训象人、瑞禽石屏、角端、马及控马官、石虎、石羊、蕃像、文武臣、武士及上马石、石狮。在此仅对其组合作一对比。
一、形式相同又有所发展的石刻
1.华表/望柱
唐代陵墓华表较前代造型变化较大,对以后历代影响较深。高祖李渊献陵华表,柱头有石兽,柱础上浮雕首尾相衔螭龙,但献陵华表不见莲花纹饰。乾陵及以下诸唐陵华表形制相近,柱头由兽变为宝珠,柱顶台盘之上和柱身与柱座相接处各浮雕仰、覆莲一周,柱身各棱面线刻蔓草花纹。宋陵各望柱大体形制相同,只是不同时代大小、细部纹饰略有变化。
乾陵以后华表的样式逐渐成为定制,宋陵沿袭唐陵,但雕刻手法却更胜一筹,其柱身雕刻不只有阴文线刻,还增加了减低平调,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与艺术水平。而其共同的莲花纹饰与宝珠造型反映佛教文化对其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2.石马以及控马官
唐陵以乾陵为例,其石马及牵马人(控马官)各五对,左右对称分布;而宋陵的则为马两对、牵马人(控马官)四对,由此可知宋陵的是两人共同管理一匹马,这与唐陵在组合上有明显区别。
但值得注意的是,唐陵除在陵前神道设十匹仗马外,还在陵的北门置仗马六匹,此为宋陵所没有,是唐陵石刻布局的突出特点之一。唐陵北门设六马又可理解为设计者把帝陵作为帝都长安的缩影来安排的。唐陵北门置仗马犹如长安玄武门置“飞骑”、“百骑”(即左右屯营)[1]。这为研究都城布局提供了间接的实物资料,体现唐长安城的布局特点。
3.蕃像
在我国古代陵墓石刻中置蕃像者最早应为西汉霍去病墓石刻中的“马踏匈奴”和“野人”。墓前立石人是源于新疆北疆草原一代的石人石棺墓文化,表示战场的战俘服侍死者,应为中原受西域文化的影响。
在唐陵中发现的蕃像,其意义却明显丰富,如乾陵的61尊蕃像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战俘,他们之中有被征服者、归化者,也有友好国家、地区的使者。在唐陵蕃像中,崇陵蕃像中有的合手打拱、身披帛纱、右肩袒露、双足赤露;乾陵和崇陵有的下身着裙,裙下有周圈莲饰。而且蕃像位置一般居陵墓神道石刻之首,这些均使其具有了积极的政治意义,反映出唐代对友好睦邻的关系和团结各地区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视。
北宋帝陵石刻中仍有蕃像,但数量远不及唐代,仅有三对。其容貌、服侍皆非汉族形态,如永定陵蕃使“圆脸阔鼻,身材矮壮,头戴高顶帽,内穿窄袖袍,外披兽皮披风,戴耳环,佩项饰,胸前坠朵花,腰束绳,绳带前结,赤足,手捧犀角。”[2]
宋代诸皇陵沿袭前代制度设置蕃像,我们知道宋代国力远不及大唐盛世,却又许多域外的使臣前来朝贡,反映了宋时中外以及各民族之间频繁的往来,致使宋朝形成一个中国封建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
4.石人
乾陵、定陵和桥陵石人当属皇宫仪卫,身份可能为直阁将军、殿中将军或侍郎,可以看出此时沿袭了前朝制度。泰陵及以后诸唐陵石人,左文右武,这与当时唐陵石刻追求进一步的对称布局有关,另外也反映了那时朝仪制度的变化。
而到了北宋却有所变化,宋陵中的文武侍臣雕像,武官武装仗剑,文官朝服执翁,正身拱立,一如唐陵。只是唐陵的文武侍臣多至20人,宋陵仅有8人。宋陵石刻文臣执笏相对武臣靠北,武臣拄剑在其后,这足以反映了北宋扬文抑武的官制序班。“各陵此数像均用长石雕成,瘦而高,外形相仿,惟冠饰、玉佩等细部各有不同”[3]。由此,不难得出宋朝的石人更注重形式上的对唐陵的模仿,文武臣各两对,北宋各帝陵数量已成定制。
5.石狮
石狮,又作为门狮,在陵园四门各两对。唐陵石狮造型变化甚大。永康陵和兴宁陵的石狮有明显的隋及北朝作风,但已接近写实,与南朝萧梁人臣墓有石狮作风迥异。昭陵和顺陵的石狮均为行狮,造形上受到了西亚影响,这是写实石狮的代表。乾陵及以后诸唐陵石狮,均为蹲踞,具有某些印度风格[1]。
而在宋陵中,石狮沿袭唐后期造型,但东、西、北三门石狮皆蹲踞昂首向前,唯有南门石狮尺度较大,为立像,似乎更有威慑四方,时刻保卫墓主人之意。
二、变化的石刻
1.鸵鸟石屏—瑞禽石屏
唐高宗永徽年间,吐火罗遣使献大鸟(鸵鸟),高宗将其献放昭陵。(《旧唐书·高宗本纪》)唐朝将鸵鸟雕刻于石屏之上,鸵鸟与狮子都不属于中国本土的动物,而在其故乡人们又将其视为珍禽,统治者将其作为鸾鸟放置于陵墓之前,是具有美好的寓意。笔者认为此处的唐陵鸵鸟石屏是宋陵瑞禽石屏的来源。
宋陵石雕瑞禽之形为马首、龙身、鸟足、雀尾,背有翼。背景衬以山岳,小兽出没其间,与之呼应。其作用与唐代的“莺鸟”有共同之处,意为吉祥之禽,但在形态上已大异于唐代莺鸟之形[4]。
2.石虎位置的变化
石虎,在唐陵石刻中仅见于高祖献陵,陵园四门各置一对石虎,后代演变为石狮,并且成为定制,前文已经叙述。高祖李渊信奉道教,没有把佛教的“狮子”放置陵前,也是不难理解。在宋陵中也有石虎但没有位于陵园四门,仅仅在石刻的行列当中,虎为百兽之王,置于墓前作为警卫。
三、消失或增加的石刻
1.相比唐陵,宋陵中没有的石刻
翼马(天马)。唐代自高宗乾陵开始,诸唐陵(除桥陵为翼兽之外)各有翼马一对,位于鸵鸟与华表之间。翼马来自西域,唐陵置翼马的意义犹如驼鸟,这是中外友好往来见证,也表明了唐代圣君的“怀远之德”。
犀牛,仅见与高祖献陵。古人把犀牛视为神异,如晋人郭璞神化犀牛“力无不倾,吻无不靡”(《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兽部、犀条);又有所谓犀牛行丛林,“露齿前向直指,棘林自开”(《太平御览》卷八九,兽部、犀条),“犀角通天,向水辄开”(《太平御览》卷八九,兽部、犀条)。像唐陵置翼马和鸵鸟一样,置犀牛也是为了表现高祖李渊的“怀远之德”。
石碑。文献记载,“死有功业,生有德政者”都要立碑(高承,《食物纪原》卷八,神道碑条)。唐陵立碑只有乾陵和定陵。乾陵有二碑,居神道石刻北,南门阙台南,左右对称列置。左为无字碑,右为述圣纪碑。碑是为记功德而立,立碑者认为皇帝功德无量,以无量之功德,碑上无法书记,故以无字碑来表现。
定陵只有一通无字碑,已毁。据载其大小、形制与乾陵无字碑相近,其义可能与乾陵无字碑也相同。
2.相比唐陵,宋陵增加的石刻
角端。角端亦名懈穿、膜、独角兽。它也是想象中的神兽,体态厚重肥硕,颇似野猪。《宋书·符瑞志》云:“角端,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奉书而至。”可见角端是作为神兽作辟邪之用。陵墓前设置角端,出于宋朝,前代未曾发现[4]。
象及训象人。陵前置象在东汉时就已出现,汉以后的南北朝及唐朝没有设置。到了宋代,象又被设置在陵墓前,同时又置有驯象人(或称象奴)。永定、永裕、永泰三陵的石象身披锦绣,背置莲花座,长鼻委地,躯体庞大,纯朴可爱,生动传神[4]。
驯象人,亦称象奴。同象一样,驯象人也是北宋皇陵增设的题材。宋陵石刻中的驯象人,也为异国装束,发短卷曲如非洲人,反映外来文化因素对宋代帝陵的深刻影响。
石羊。在我国古代,羊与祥是相通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羊,祥也。”因此,以羊代表吉祥。然而在帝陵前设置羊类石刻,则始于宋代。宋永熙陵前的一对石羊,显得手法简洁概括,富有活力,轮廓清晰,形象优美,无论造型与雕刻技法,为宋陵雕刻之上乘。当地群众有顺口溜:“东陵(永裕)狮子西陵(永泰)象,溥沱(永熙)陵上好石羊。”
武士是皇陵的守护者。石雕武士表现为头戴二梁冠,虎背熊腰,两手拱前,拄宝剑,气宇轩昂。
宫人。南神门内及陵台前各置一对,此像眉目细长,削肩,簪珥,女性的特征甚明显[3]3。以上仅是对唐陵与宋陵的石刻组合作了简要对比,但对于其特殊寓意以及两朝的变化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唐陵石刻艺术手法上表现为大胆的浪漫主义,而宋陵石刻某些方面更注重写实。纵观整个宋陵石刻,既继承唐末五代遗风,也有宋代的独特之处。宋陵神道石刻的艺术特点,继承并发展隋唐以来的传统,在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情感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前进了一步,世俗化大大增强。但相比之下少了前代神道石刻的雄健伟岸的气概。这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对于陵前石刻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慢慢研究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J].文博,1994,(3).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108.
[3]郭湖生.河南巩县宋陵调查[J].考古,1964,(11).
[4]卫琪.略谈宋陵神道石刻艺术[J].中原文物,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