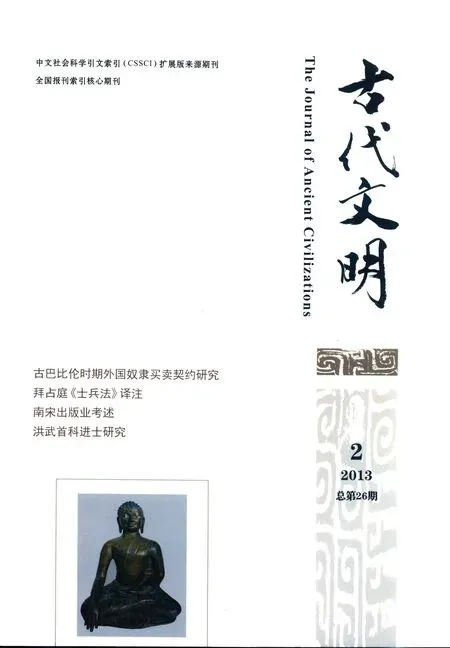“清浊”观与汉晋人物品鉴论
张甲子
一、“清浊”的理论渊源及走向
从先秦文献来看,在以“清浊”对具体物质进行状态性描述时,绝大部分集中于水、气这两类物质,而水与气,又恰是宇宙论中讲万物大化演变时,即在宇宙从混沌的初始状态如何一步步变易出天地万物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介质。前者的理论以《太一生水》为代表,后者的理论以《淮南子》为代表。其中,“清浊”是宇宙生成论中至关重要的链接性命题,在以“道”为宇宙本原,以“太一”或“太易”为宇宙初始的基点上,“清浊”贯穿着宇宙如何生成、如何变化的漫长历程,并将这种历程中的辩证逻辑与天人关系相结合,等同于人类的生存法则及社会理想秩序的建构。
而以气之“清浊”作为思考的理据,就通顺很多。其实在逻辑体系上,论水与论气的阐释层面是一致的,在它们之上是“道”、“太一”、“太易”等,这些都是对宇宙源头进行的纯粹理性思考,而“水”与“气”,则是从多样化的自然界中,归纳出的抽离了感性直观却仍然是实物的符号。尽管它们也是想象出来的,但这种想象,并没有完全脱离客观存在。如上所论,以“清浊”论水难以为继,就是因为既将“水”视为抽象的宇宙本原,又将其视为是生成的具体物质,两个层次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而以“清浊”论气,这种矛盾便不复存在。有此缘由,战国至秦汉间的宇宙生成论在经过抉择后,有“清浊”之辨的“气”论开始大行其道,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观点首见楚简《恒先》,强调“清浊”与“气”的自生。
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第1简)
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第2简)
生之生行,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异性,因生其所欲。察察天地,纷纷而(第4简)复其所欲。(第5简)1
《恒先》中的观点,认为宇宙初始是“恒先”,这在《黄帝四经•道原》中也有,其意基本等同于“恍兮惚兮”之道,是为宇宙的起点。之后“恒先”生出气,宇宙内分出有无,故将自生的“气”定性为宇宙本原。然后“气”分了清浊,天地就出现了。这里面的清气、浊气乃自生而出,气化之初宇宙内一片混沌,清浊二气融合,“求其所生”后,二气化成天地,并充盈在天地间,让天地具有了无限循环性的自生欲望,故“纷纷而复其所欲”,万物皆成。
《恒先》整合了先秦众多关于宇宙学说的话题,这也是战国末年至汉初哲学发展的大趋势,杂家辈出,意图在诸子百家林立天下的局面上,在经历了长期的争论和颉颃后,彼此吸纳兼容,有所采撷、有所承接,在总体上的综合观点愈来愈多,从而建构出一套合理且完整的宇宙图式。
这在《淮南子•天文训》里能看的更为清晰:
其意为,“太昭”是宇宙原初的混沌状态,乃后有道、有宇宙,宇宙生气后,先经天营地,有天地后分阴阳,分阴阳后成四时,四时运转后有万物。《淮南子•天文训》中所言的“清浊”比之《恒先》中的“清浊”,有两点不同:
所谓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生成是空间与时间的结合,成为时空方才完整。整合“清浊”进入到时间的结构,在《易纬•乾凿度》中被体现出来:
但是,“清浊”之分与“气”变并不截然处于同一阶段。万物的形成,由气推动,而气运动的方向,取决于组成的气的内部特性,气变时是在酝酿“清浊”,有“清浊”之分后方有形,形再具备着“清浊”,便有了质。由此,当时间结构介入“清浊”之辨,“清浊”便不再只局限于气论中,单指清气、浊气两种要素,而是能够贯穿在万物生成的各个阶段,气、形、质中皆有“清浊”,阳轻阴重,阳清阴浊,演化为与阴阳类似的清性与浊性。此中,“清浊”是作为阳、阴的本质性要素,被加以审视的。
二、天人图式中的“清浊”论
秦汉哲学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许多自然哲学的因素,迅速地被社会哲学所吸收或改造,注入了新的抽象的、或主观的内蕴,进而方可推天道以明人事。同理,虽然“清浊”刚从秦汉的宇宙生成论中析出,但很快就在天人同构的关系之间,被紧密的构建起来。甚至可以说,以“清浊”论宇宙与以“清浊”论人,几乎同时出现在秦汉的哲学思索中。
导致这样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从“天”的角度出发,宇宙学说中所讲的天与地,本就不是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完全的客观存在物,兼带有“道”的意蕴,最后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与人性上,天地论“清浊”,人必然也要论“清浊”。一方面,从“人”的角度出发,即便各家所论“天”的含义有所区别,天命、天道、天德、天志见解各异,但天人同构是他们共同的命题,人如何与天同构,获得法于道、法于自然的力量。在这样的追问中,但凡与天地有关的逻辑因素,皆会映照到人与人性上。两方面互相交错的思考,造成了不论是讲天人相类、或是天人相感、还是天地人和,“清浊”无不贯穿其中。
《黄帝内经》多从形神角度论之,《春秋繁露》多从性情角度论之,后者更具神秘色彩。但需要指明的一点是,当人的性情命理与天比拟可通,那便夹杂了愈加复杂的天人相感的思想,带有深化的意味。所以,此处讨论的天人相类,是狭义上人的形体与天的形状的同构,是大宇宙结构与身体小宇宙结构相对应的关系,反映在“清浊”论上,主要指依据清轻浊重、清升浊降的特性,论人的身体之“清浊”。
这具体来自三方面的表现:其一,清在阳,浊在阴。从阴阳角度分“清浊”,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清浊”若不在人体的阴阳之位,即为失位,先天则早夭,后天则为病机。而“清浊”并存也有相胜之理,太阳之人血气清,太阴之人血气浊。这里的“清浊”,尚无褒贬之意,单指的是人的体质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由天人同构所出的“清浊”论人,已然涉及到人论的各个方面,尽管有些只点到为止,但分骨相、气质、性情的大致框架已初立,既有形而上的思考,也有形而下的分析,只待后人、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继续完善;同时,又从“清浊”无上下高低,转变为以“清”为尚,而这一点,在有诸多具体事例的汉魏人物品鉴论中被发扬光大,并将“清”确立为人物品鉴的标准,成为人生修身养性的至高准则。
三、人物品鉴的贵“清”倾向
汉晋人物品鉴之风以“清”为尚,诸如清士、清才、清誉、清伦、清中、清识、清悟等词汇屡见不鲜,甚至连进行品评活动的“清议”与“清谈”,也都是以“清”为定语偏正的修饰词,这些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典型风尚。可以说,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人物品鉴对气论“清浊”中的“清”,进行了有意识的抉择,并在长时间内赋予众多的道德意味和审美意蕴,让其不再与“浊”对举,而成为了独立的元范畴,可以继续派生出更多的具有血缘关系的范畴,渐渐形成了以“清”为中心的同中有异的系列。
在人物品鉴中的“清”,是对某一个人整体精神的抽象化且审美化的描述,其中包括此人的气质、个性、习染、志趣、情操等多方面因素,即蕴乎内即充盈流转在人体间,又能著乎外以各种方式来表现。汉晋间用“清”来品评人物,大致要从两个层面视之,即选官方式中的官方层面与人格推崇中的士人层面。这两层面有相互关联的地方,毕竟古代选官制度的主体,即为士人群体,官方对治国理事人才的选拔标准,所推崇的官员楷模,必然与参选人的人格性情密切相关,也一定要符合社会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九品中正制中,“清选”演变为“清途”,两种制度的区别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其中显露出来的对所选士人的不同,更能反映出选官制度对人格品鉴的影响。“清选”的士人,点明了士人对“名”的重视;而“清途”的士人,则点明了士人对“位”的看重。或者说,清选是一种泛指,有清名之人皆能入清选;清途则特指士族名士的入仕途径。名士群体的出现,本就属于人物品鉴的副产物,即使清途为选官制度加剧了弊端,但其涉及到的士人范围,仍在社会的高材英儒之列。如曹植、夏侯玄、李丰、裴秀等人,都曾任清途之官中的“黄散”,不能否认,他们也是被士人所大力推崇的,具有清高人格的魏晋名士,较好的出身和生活环境,使他们比之起普通人,更能在学问的熏陶与人格的塑造中,接近于“清”的气质。
“清选”与“清途”是从选官制度中,延展出对人格品鉴之“清”的首次定位,同时也吻合了由士人群体自发且非制度化的清议中,对人物品行的考察评议、对世俗人格的批判,以及对崇高人格的追求。他们以“清”为重点,肯定了既要重先天出身,又要重后天品行,其中心是由社会选拔人才的政治道德需要,转变为士人自我鉴赏的精神境界与审美需求。
两晋后,尤以清流之士为典型代表,人物品鉴之“清”出现了更多的引申义,扬弃了多从政治伦理品评人物的视角,而转向看重于人的精神壁垒,或论人之才智神采、或论风神气韵,或仪表举止,如“清通简要”、“清蔚简令”、“清易令达”、“清恪简素”、“清允平当”、“清淳真粹”、“清素刚严”、“清亮质直”、“清激慷慨”、“清便宛转”、“结藻清英”、“气候清雅”,凡此种种,无论是对于人生或是艺术,皆通过一个“清”字,订立了最佳的尺度及崭新的见解。
在“清”具有了人的风貌、情感、气质、品格等各种点评式内容后,“清”已然成为魏晋时人最推崇的人格理想,无论从形之容颜,还是从神之风度,都被立为人物品鉴之真谛,凝熔为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生命品格。又因为“清”的内涵是抽象的,其外延既则可与骨、气、神、韵等论人的范畴结合,也可以与正、雅、淡、远等纯审美的范畴结合,又能将哲理的体悟,和直觉的感受结合起来,当两者同流之,便以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至高格调,很快延展到文学鉴赏、艺术评论的相邻领域,独立为中国艺术的精神,这即是“清”给予后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