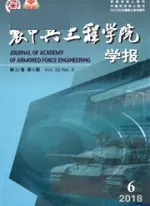超声深滚对高强铝合金超声波焊缝组织与性能的影响
朱有利,谢俊峰,黄元林
(装甲兵工程学院装备再制造工程系,北京100072)
2A12铝合金、2A11铝合金属于2×××系列高强铝合金,具有优良的综合机械性能,在航空工业领域应用广泛。但2A12铝合金、2A11铝合金的可焊性较差,采用传统熔焊工艺焊接时,出现热裂倾向大、热变形严重、焊接强度低等问题[1-2]。超声波焊接技术是一种固态连接技术,具有焊接温度低、焊接变形小等优点,比较适合进行铝合金连接[3]。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铝合金超声波焊接的组织和性能展开了较多的研究:Kong等[4-5]研究了3003和6061铝合金超声波焊缝的组织结构和拉伸力,并根据试验结果优化了超声波焊接工艺参数。熊志林等[6]研究了超声波焊接工艺参数对焊后6061铝合金剥离强度和硬度等力学性能的影响,并采用对焊接表面进行乙醇处理的方法提高了焊接接头的结合强度。
超声波焊接过程中,带有纹理花纹的焊接工具头压入焊接箔材表面,将超声波振动传递到结合界面上,使母材和箔材形成焊接结合[7]。但是焊接工具头会在焊缝箔材表面形成焊接压痕,当焊接件承受载荷时会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从而导致在此压痕处发生破坏[8]。超声深滚工艺是一种新型表面机械强化技术,可在零件的表层和次表层形成强化层并引入残余压应力,同时还具有降低表面粗糙度和修复表面损伤的作用[9-10]。笔者采用超声深滚工艺对超声波焊缝进行了焊后处理,采用有限元方法分析了焊接压痕的应力集中问题,对比研究了超声深滚处理对焊缝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分析了相关的影响机理。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如图1所示,超声波焊接试验采用2块尺寸为100 mm×20 mm×3 mm的2A12-T3铝合金作为母材,以尺寸20 mm×20 mm×3 mm的2A11-O铝合金作为箔材,通过搭焊的形式进行超声波焊接。2A12-T3与2A11-O铝合金的主要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
焊后试样分为A、B两组,对B组试样进行超声深滚处理,而后与A组试样进行对比研究。试验设备为笔者自主研发的USW-Ⅰ型超声波金属焊接机和UDR-Ⅱ型超声深滚机。超声波焊接的主要工艺参数为:工具头振幅30 μm;超声频率20 kHz;焊接时间0.2 s;法向压力600 N。超声深滚的主要工艺参数为:进给速度400 mm/min;步进间距0.1 mm;工具头振幅20 μm;超声频率20 kHz;法向深滚力20 N;详细工艺参考此前的相关研究[10]。

图1 超声波焊接示意图

表1 超声波焊接铝合金材料的化学成分
对焊缝超声深滚处理前后 (A、B两组试样)的组织进行分析,分别沿焊缝的断面取样,采用Nova NanoSEM 650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JEM-2100型高分辨率透射电镜(TEM)观察焊缝的断面形貌和微观组织。SEM试样经镶制、研磨和抛光后,采用体积配比为1%氢氟酸(HF)+1.5% 盐酸(HCl)+2.5%硝酸(HNO3)+95%水(H2O)的混合酸进行腐蚀,使用的纯氢氟酸、盐酸和硝酸的分子浓度分别为45%、35%和65%,腐蚀时间为5 min。TEM试样在焊缝母材与箔材的结合界面处取样,首先由机械方法减薄至50 μm,然后制成直径为3 mm的圆形试样,在氩气中进行离子减薄。
采用X-350A型X射线应力测定仪,通过逐层电解抛光的方法,测定焊缝超声深滚处理前后深度方向的残余应力分布,在距离箔材表面深度约1 mm的深度上测试10个点,每2点之间的深度距离约为100 μm。测定条件为:X射线靶材CrKα,衍射晶面(311),X光管管流5 mA,X光管管压20 kV,交相关法定峰。采用G200型纳米硬度测试仪测量焊缝超声深滚处理前后的微观硬度,加载载荷为10 mN,保荷时间为15 s,在结合界面附近区域测试10个点,每2点的间距为15 μm。
采用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分析拉伸试验试样承受拉伸载荷时,焊接压痕产生的应力集中情况。分析过程中,采用8节点六面体Solid45单元,按照试样和焊接压痕的实际尺寸建模。考虑试样的对称性,建立1/4对称模型。焊接铝合金的弹性模量E=206 GPa;泊松比υ=0.3。从A、B两组中各取3个试样进行结合拉伸试验,采用CMT4304型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试样的结合拉伸力。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组织结构
图2为超声波焊缝超声深滚处理前后的断面形貌。对比图2(a)、(b),超声深滚处理前,超声波焊缝表面存在深度约为200 μm焊接压痕;超声深滚处理后,焊接压痕基本被去除,形成了比较平整光滑的焊缝表面,改善了焊缝表面质量。这是因为超声深滚处理在焊缝表面产生强烈的塑性变形,使焊接压痕的凸峰和凹谷发生材料塑性流动,从而消除了焊接压痕。
从图2(c)、(d)观察超声波焊缝的结合界面可以发现:超声深滚处理前后的结合界面(图中波浪虚线所示)形貌基本相同,箔材与母材相互交错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出现氧化物;孔洞和裂纹等焊接缺陷;但超声深滚处理后焊缝的箔材区域发生了更加强烈的塑性变形,使该区域的组织在焊缝断面深度方向上排列更加致密。

图3为超声深滚处理前后结合界面微观组织的TEM图像,RD为超声深滚处理的滚压方向,ND为焊缝断面深度方向。从图3(a)、(b)可以看出:超声深滚前的结合界面区域上,母材和箔材的微观组织存在差异,结合界线(图3(a)中黑色曲线)左侧的母材组织以位错缠结、位错胞和亚晶为主,右侧的箔材组织主要为尺寸约为1 μm左右的细小等轴晶粒,这分别是超声波焊接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回复和连续动态再结晶组织[11];超声深滚处理后,结合界面区域上无法观察到母材与箔材晶粒之间的结合界线,这是因为母材与箔材形成了比较均匀一致的层状亚晶组织。这表明:超声深滚处理减小了结合界面区域的母材和箔材之间的组织差异,使二者晶粒之间结合得更加紧密。值得注意的是,图3中结合界面区域基本未发现第二相粒子,这是因为超声焊接过程中结合界面区域产生了较大的塑性变形和温升,使结合界面处母材和箔材的第二相粒子破碎溶解[12]。
2.2 纳米显微硬度
图4为超声深滚处理前后超声波焊缝的纳米显微硬度分布曲线,其中虚线代表结合界面处。超声深滚前,结合界面两侧的箔材与母材的硬度基本相同。由于原始2A11-O铝合金箔材的硬度小于2A12-T3母材的硬度,因此超声波焊接过程中,相比母材,此区域箔材发生了更大的加工硬化。

图4 超声深滚处理前后超声波焊缝微观硬度
但是结合界面区域的硬度小于其两侧的母材和箔材,这是由于超声焊接过程中,结合界面区域发生了动态回复,连续动态再结晶以及第二相粒子溶解,造成此区域硬度下降[11-12]。
超声深滚处理后,焊缝箔材区域的硬度明显增大,这是由于超声深滚处理在焊缝的表层和次表层产生滚压塑性变形,使得焊缝箔材区域进一步发生加工硬化。由于超声深滚处理产生塑性变形主要集中在距离焊缝表层较近的箔材区域,对母材区域影响较大,因此母材区域的硬度变化不大。
2.3 残余应力
图5为超声深滚处理前后超声波焊缝的残余应力分布,图中竖直虚线处约为焊缝的结合界面。图中显示:超声深滚处理后,超声波焊缝结合界面的残余应力由56 MPa减小为-44 MPa,而且超声波焊缝表层和次表层的最大残余压应力值由85 MPa增大到144 MPa,残余压应力层的深度由处理前的0.4 mm增加到处理后的1 mm。

图5 超声深滚处理前后超声波焊缝残余应力分布
2.4 焊接压痕应力
图6为承受拉伸载荷时,对具有焊接压痕的结合拉伸试验试样进行有限元应力分析所得的第一主应力云图。可以看出:试样箔材的焊接压痕处存在应力集中,最大应力值为230 MP,而箔材的名义应力仅为126 MPa。因此,计算得出焊接压痕形成的最大局部应力与名义应力的比值[13],即应力集中系数KT约为1.8。有限元应力分析表明:焊接压痕形成了明显的应力集中,成为试样的危险部位,在试样承受载荷时容易发生断裂,降低了试样的力学性能。

图6 结合拉伸试验试样第一主应力云图
2.5 结合拉伸力

图7 结合拉伸力试验试样
图7中试样A、B分别为超声深滚处理前后的结合拉伸试验试样。通过超声波焊接将箔材分别与2块母材焊接在一起。从图7中可以看出:超声深滚处理前试样的箔材表面存在明显的焊接压痕;而超声深滚处理后试样的箔材表面产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基本去除了焊接压痕。拉伸试验后观察发现:超声深滚处理前试样的断裂位置位于焊接压痕处;而处理后试样的箔材与基材在结合界面处脱落。
图8为超声深滚前后试样的结合拉伸力,可以看出:超声深滚处理前试样的平均结合拉伸力为1.012 kN,而处理后的平均结合拉伸力为1.652 kN,表明超声深滚处理使超声波焊缝的平均结合拉伸力提高了36%。其中,超声深滚处理前,试样平均结合拉伸力的相对标准偏差为19.5%,处理后的相对标准偏差减小为12.1%,这是由于焊接压痕使试样的结合拉伸力产生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图8 超声深滚前后试样的结合拉伸力
2.6 超声深滚对焊缝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超声深滚处理在超声波焊缝表面产生材料塑性流动,基本消除了表面焊接压痕,形成较为光滑平整的焊缝表面,而拉伸试验中焊缝的断裂位置由焊接压痕处转移到箔材与母材的结合界面处。表面超声深滚处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焊接压痕所形成的应力集中,这是超声深滚处理提高焊缝结合力的主要原因。
另外,超声深滚处理在焊缝的表层和次表层产生沿RD方向伸长的塑性变形,并形成层状亚晶组织。超声深滚处理结束后,未发生塑性变形的区域回复收缩,使塑性变形区域产生残余压应力,因此增大了焊缝残余压应力的深度和应力值。超声深滚处理前,结合界面上存在焊接残余拉应力,会降低焊缝结合性能。而超声深滚处理消除了结合界面上的焊接残余应力,并形成一定的残余压应力。这是超声深滚处理提高焊缝结合力的另一原因。
超声深滚处理产生的塑性变形使得焊缝组织进一步发生动态回复,处理前存在差异的结合界面组织转变为处理后均匀的层状亚晶组织,使母材与箔材晶粒之间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也有助于增强焊缝的结合力。
[1] 周万盛,姚君山.铝及铝合金的焊接[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75-76.
[2] 李奇,赵军军,张平,等.7A52铝合金便携式搅拌摩擦焊接头的组织与性能分析[J].装甲兵工程学院学报,2010,24(4):73-76.
[3] Yang Y,Janaki Ram G D,Stucker B E.Bond Formation and Fiber Embedment during Ultrasonic Consolidation[J].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2009,209(10):4915-4924.
[4] Kong C Y,Soar R C,Dickens P M.Optimum Process Parameters for Ultrasonic Consolidation of 3003 Aluminium[J].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2004,146(2):181-187.
[5] Kong C Y,Soar R C,Dickens P M.Characterisation of Aluminium Alloy 6061 for the Ultrasonic Consolidation Process[J].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2003,363(1):99-106.
[6] 熊志林,朱政强,吴宗辉,等.6061铝合金超声波焊接接头组织与性能研究[J].热加工工艺,2011,40(17):130-132.
[7] Hiraishi M,WatanbeT. Improvement of Ultrasonic Weld Strength of Al-Mg Alloys by Alcohol Adhesion-ultrasonic Welding of Al-Mg Alloys[J].Welding International,2004,18(5):357-363.
[8] Kim T H,Yum J,Hu S J,et al.Process Robustness of Single Lap Ultrasonic Welding of Thin,Dissimilar Materials[J].CIRP Annals-manufacturing Technology,2011,60(1):17-20.
[9] 朱有利,李礼,王侃,等.一种超声深滚与滚光一体化抗疲劳制造技术[J].机械工程学报,2009,45(9):183-186.
[10] 李礼,朱有利,吕光义.超声深滚降低TC4钛合金和修复表面损伤的作用[J].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2009,38(2):339-342.
[11] Mariani E,Ghassemieh E.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of 6061 O Al Alloy during Ultrasonic Consolidation:An Insight from Electron Backscatter Diffraction[J].Acta Materialia,2010,58(7):2492-2503.
[12] Sato Y,Kokawa H,Enomoto M,et al.Microstructural Evolution of 6063 Aluminum during Friction Stir Welding[J].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A,1999,30(9):2429-2437.
[13] 姚卫星.结构疲劳分析[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