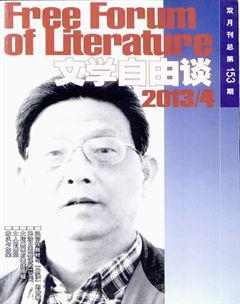浮躁蜕变的知识阶层
何东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大抵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在朝,一个在野。
在朝的自然很是风光滋润,他们依附在政权周围,出谋划策,帮忙帮闲,著书立说,治国安邦。这其中也有不少奸宄弄臣助纣为虐、祸国殃民。其反面或灰色的代表人物如:李斯、蔡京、秦桧、李义府、王钦若、丁大全、赵文华、和珅、曾国藩、李鸿章、严复、陈公博、康生、张春桥等等,就既是大知识分子又是大恶魔妖孽。在朝的知识分子因为是既得利益者,在长期的宦海沉浮中许多人渐渐蜕化、异化,并与统治者抱成一团,难分难解。而那些良知未泯,严于自律,出类拔萃的英杰,譬如:苏东坡、白居易、王安石、范仲淹、海瑞、于谦、林则徐等等虽有所作为,但终究难成气候且每每结局凄凉。
在野的知识分子则大都身世坎坷,穷困潦倒,甚至一生不得志,但相比之下要纯粹、正直、清白、高尚得多。敢说、敢想、敢干、敢于开创新思潮新风尚新流派的才俊骄子代不乏人。这些人因为不在朝,不领俸禄,不掌权柄,不同流合污,没有在染缸里浸泡过,因而也就清白干净,自由狂放,尖锐深刻,桀骜不驯。譬如“竹林七贤”、“竟陵八友”、“初唐四杰”、“扬州八怪”,譬如韩非、李白、杜甫、陶渊明、李商隐、孟浩然、柳永、张岱、关汉卿、吴敬梓等等。
还有一类人处于两者之间,他们先在朝,后在野,为统治者忠诚服务过,可又因特立独行,思想异端,个性硬朗,触犯权贵,而被当政者所不容,最终只得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譬如战国的屈原、唐代的陈子昂、南朝的谢灵运、南宋的范成大、金代的元好问、明朝的李贽、清时的黄宗羲等等。这类人为数也不少,且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独立人格,先锋思维,创新探索,故终成大器,作品、精神两不朽。
在朝的、在野的、半在朝半在野的才子文豪学者秀士芸芸读书人,多支合为一股,这就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精英,他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有人说:知识分子是圣贤的传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总之,读书人、教书人、文化人乃至于整个知识阶层,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是体面的,也是寄之于大敬重大希望的族群。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也都竭力搜罗人才,笼络文化人,让知识分子来为自己的一统江山服务(大规模的战乱及“文革”等特殊时期另当别论)。所以,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朝的知识分子,其生活水平政治礼遇历来皆高人一筹。即使是在黑暗的清朝末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比之于劳工阶层也是明显高得多。
1949年,之后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改造,弄得文化人灰头土脸、杯弓蛇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个性尊严荡然无存。1957年反右,率真迂拙的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一脚踩倒在地,差一点永世不得翻身。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厄运横祸更是从天而降,“臭老九”们斯文扫地,朝不保夕,许多人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场浩劫,应该是让知识分子们刻骨铭心幡然醒悟了。然而,灾祸刚过,才得到些许宽松安抚,许多昔日的阶下囚、“四类分子”、九死一生者便好了伤疤忘了疼,闭着眼睛念歪经,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原本牢牢夹着的尾巴又高高地翘起当大旗挥舞了。
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物欲横飞的金钱社会里,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渐渐异化、变质、沉沦。好像无论在朝的、在野的、或半在朝半在野的知识分子,都扯下温情脉脉的面纱,丢弃手中的旗帜,抛开肩头的道义,一头钻进了孔方兄的怀抱里。下海的、办班的、兼职的、做顾问的、当吹鼓手的、甚至招摇撞骗贪污受贿抄袭剽窃走私制毒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即使是一些坚守道德底线颇能自控尚未下水湿身的知识分子,在滚滚红尘的熏染刺激下,也终于耐不住寂寞,厌恶了清汤寡水的日子,开始理直气壮向钱看了。
某大学某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一炮走红后,即以《品三国》一书迅速致富。这倒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知识就是财富嘛!遗憾的是,紧接着他又将以前品质一般,很难卖动的书也重新包装再版一并搭上顺风车广为销售,糊弄不明真相的发烧友。这就有失学者风度了。
更有荒唐者,有个湖南的写手竟公然宣称:“希望自己能被富婆包养”,以脱贫致富,为安心写作创造条件……
试想,知识分子到了这种不检点不自爱的地步,他还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敬重吗?还有资格引领当代社会文明的先进潮流吗?
冷静观察,当代知识界也不乏献身理想、追求道义、敢破敢立、无私无畏、铁骨铮铮的士子豪杰。即使是在最艰难最恶劣的气候环境下,也还有出类拔萃的学者、思想者、探索者、先行者奋不顾身地坚守正义,捍卫真理,寻求光明。譬如:胡风、陈寅恪、罗隆基、王造时、马寅初、储安平、顾准等等就是其杰出代表。又比如李慎之先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成都燕京大学上学时,即是争民主反独裁的学生领袖,大学毕业后为了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投奔延安,饱经磨砺,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三十一岁即成为中共十一级高干,先后担任过周恩来外交秘书、邓小平外交顾问……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可谓是红透了心的“三朝元老”。但就是这样一位“老派共产党人”,却在非常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李先生在其晚年更是反思忏悔,大彻大悟,脱胎换骨,全然不顾个人得失,拖着老迈病弱之躯,奔走呼喊,披肝沥胆,劳神焦思,奋笔疾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读来让人惊心动魄,豁然醒悟,感慨唏嘘。这样的大丈夫真君子,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的翘楚吗?
知识分子群体与生俱来也理所当然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精英、是圣贤的传人、是人权公理正义法治的捍卫者传承者,是监督制衡统治阶层缓解社会矛盾推动文明进步的巨大力量。然而,如果这个群体一旦在权力金钱利益的收买腐蚀下大面积堕落蜕变,自觉不自觉地与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独立坚定的政治力量,就不可能发出真实迥异的自由之声,就不可能产生监督制约的平衡作用,甚至连封建社会都能包容的一点点“清议”、“直谏”、“公车上书”、“开坛讲学”、“政见答辩”都不复存在,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人权也就只能是一块轻飘飘脏兮兮的遮羞布了。
毋须讳言,如今的知识阶层异常浮躁,蜕化、堕落、变质者绝非小数。与前辈先贤们相比,可能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信息和谋生技能,但他们却丢失了深厚的学养、远大的抱负、高贵的德性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在英国,一个莎士比亚就刷新了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在俄罗斯,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令皇室贵胄胆颤心惊;在德意志,一个名叫歌德的诗人就推动了一场“狂飙突进运动”;在意大利,一个但丁就为“黑暗的中世纪”挖掘了坟墓……
在我们中国,固然也有不少名垂青史的大家巨擘,如老子、孔子、庄子,等等等等,但他们留下来的遗产,精华有限而糟粕太多,甚而顽固性的腐烂毒素直到当今还在麻痹毒害着人们的精神,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鲁迅、胡风、陈寅恪、张志新、林昭等等先进知识分子当然难能可贵,但他们的声音显得那么微弱,他们的抗争显得那么单薄,他们的宏愿显得那么虚幻缥缈……
在中国大陆,仅就近百年历史而言,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过后,紧接着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性风暴的扫荡,摧残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根本,扭曲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意志,阻塞了芸芸众生的从善之途。
改革开放后,粗浅层次的反思启蒙加上西风东渐海洋文明的缓慢熏陶,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民本理念、人权诉求有所苏醒、回归和提升而且已经不可逆转。
然而,经济改善所带来的初步繁荣,使得“犬儒主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又重新抬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频频冲击下,许多文化人陶陶然飘飘然昏昏然戚戚然惶惶然愤愤然而又不知其所以然,刚刚有所修复的理想中的“象牙塔”仿佛一夜之间便轰然坍塌了。
当读书人、教书人、文化人、学者专家名流大师争先恐后,铆足劲儿,甚至不顾廉耻地爬上商品世界的金字塔时,知识分子的高贵偶像也就被世俗的魔杖击得粉碎。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腐蚀下,他们成了没有灵魂的工程师,没有社会良知的文化人,没有理想夙求的家奴式学者,没有奉献追求精神的“水晶玻璃花”。
如今,我们还能在暮气沉沉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鸦雀无声千篇一律僵化死板中找到多少“五月花号”轮船上先知先觉的乘客?还能找到多少甘愿抛弃富贵荣华从容领受西伯利亚严寒的俄国“十二月党人”?还能找到多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贤者义士英雄豪杰?
知识群体的沉沦、浮躁、蜕变,必然带来社会大面积的病毒感染;中上层文化人的失态终将引发底层劳动者的心理失衡乃至精神塌陷;社会精英集体无意识甚或集体有意识地丧失道义、丢弃责任、贪恋既得利益、疯狂聚敛财富,将国家的振作复兴的责任丢弃一尽。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伙,变着花样厚着脸皮鼓吹陈腐教条,从阴气森森的古墓里抬出一具具政治僵尸,以所谓的“精英治国”理论,“儒学立国”理论,“权威效应”理论等等来扰乱人心。他们身为知识分子却诽谤民主人本,臣服苛政强权,愚弄善良民众,把“儒释道”遗传的精华与糟粕配上新鲜的佐料搅拌在一起制成现代风味的“汉堡包”、“麦当劳”、“特色快餐”卖命地兜售,为封建意识形态张目,企图停滞历史车轮,安享政治暴利。
笔者丝毫没有贬低、丑化当代知识分子的意思。知识阶层中确实有着许许多多道义的守护者、真理的探索者、科学的开拓者、民族复兴希望之设计构建者。这其中,不乏专家、英才乃至时代的楷模、未来的圣贤。
我们反省反思,是为了去污除垢,净化自身;我们卸下镣铐冲破禁锢,是为了施展拳脚,轻装前进。这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应有的襟怀。这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受恩于人民的哺育教化充盈着智慧才华的知识分子群体必备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