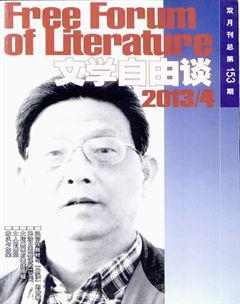写作野心与写作胆量
石华鹏
一
对于我国当前小说创作的情形,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天壤之别的结论,应了那句老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从量上来说,可谓繁荣一片,雄冠全球,但从质上来说,震撼人心,有传之久远潜力的小说太少;从“吹捧派”评论家眼中来看,重要收获,史诗品格的鸿篇巨制遍地都是,触手可及,但从真诚踏实的读者眼中来看,让他们趋之若鹜,追着读、重复读的小说凤毛麟角;从娱乐消遣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小说风光无限,但从艺术创造性的角度来说,乏善可陈。
这些七嘴八舌的结论,究竟哪一种或者哪几种才是我们小说真正的现状?如果我们非要得出一种判断不可的话,那么它只会把我们带入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论争当中,消耗掉生命。其实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无解并不意味着不去追问:我们的小说怎么了——它总是不令人满意、不令人自信?
有人说这个最好又最坏的时代,是最适宜伟大小说诞生的时代,但我们的小说烹饪家们却似乎正在辜负这个时代,并没有为我们烹饪出小说的大餐来。诚然,关起门来,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一排一排排列在那里,看上去壮观无比,也声名十足,但是把这些小说放到世界文学的格局当中,无论是横向与同时代的别国比较,还是纵向与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比较,我们又能抽出几本小说与它们自信地摆在一起呢?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也为了把中国小说拿到世界文学的秤上去称一称,每有世界级知名度的文学“大腕儿”来中国,或者中国学者在外见到那些世界级知名度的文学“大腕儿”,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是:您对当代中国文学有什么看法?您知道中国哪个小说家?读过他什么小说?但是对方的回答总是让我们陷入尴尬之中,因为他们如外交辞令一般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答案:“事实上,我对当代中国文学也所知甚少。我希望能弥补这一不足。”
比如,前段日子库切来中国,有人问他:“你眼中的中国文学是怎样的?”他便是如此回答的——“事实上,我对当代中国文学也所知甚少。我希望能弥补这一不足”。略萨来中国访问,在与中国作家热烈的交谈中,自始至终他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甚至也没有对中国文学给予片言只字的评价。还有比如马尔克斯、奈保尔,他们没有来过中国,我们的学者在外碰到他们,他们的回答也大致如此。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们近三十年来,尤其进入新世纪十多年来的小说,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并不受别人的重视和尊重。
局限和问题出在哪里?在对这一问题众多分析和谈论中,我记住了两个有些新鲜的词汇:中老年危机和虚构疲劳。意思是说我们那些一线的小说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如今都已进入中老年了,如果您是一个有心的读者,一路跟踪读他们的小说,会慢慢发现,他们虽隔几年就有新长篇问世,但创造性和深刻性均不如从前,创作进入“中老年危机”了。再者,随着身份地位稳定,生活越过越安逸,与下层现实越来越隔阂,现实的疼痛感和愤怒感在他们的小说中已难以见到,他们写作的素材主要来自二手渠道,所以虚构的疲劳感像病一样弥漫在他们的小说中,让读者提不起阅读的兴趣。
的确,中老年危机和虚构疲劳是当前小说病灶的两种表象,小说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创造,没有了梦想,没有了这些,那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了一堆在现实生活后面亦步亦趋的行尸走肉般的文字,如此文字是立不起来的,立不起,则行不远。
我们不得不继续往下追问:造成“中老年危机”和“虚构疲劳”之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一句话可以概括:写作胆量的丧失。写作没有了胆量,便不会有激情、不会有直面真实的勇气、不会有否定和冒犯,这样的小说当然不会有感染人的力量。秘鲁小说家略萨说,“虚构小说的存在不是为了反映现实,而是为了否定现实,将现实变为非现实。虚构小说是我们心中饥渴和焦虑的缓冲剂。”我们的小说只有模仿生活的低级现实,自身都没有饥渴和焦虑,又谈何缓解读者的饥渴与焦虑呢?
二
说到写作胆量,我们还要说到另一个词:写作野心。写作胆量与写作野心,是两个不同的词汇。写作野心,有写作的愿望、目标、理想之类的意思,表示写作上想有所作为;写作胆量,有写作勇气、格局、胆识、气魄之类的意思,它是实现写作野心的某种方法和方式。如果您读过许多当前的中国小说,也读过许多外国小说,把它们做一对比,您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诸如题材开掘上的差异、艺术探索上的差异以及小说家内心自由度的差异等等——如果您还想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找到一个根本性的缘由的话,我有一个感觉:咱们中国小说不缺写作野心,但缺了写作胆量。一句话:野心大,胆子小。
我们有获奖、获大奖的野心,也有写出伟大中国小说、写出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小说的野心,但眼下看来我们的野心并没有实现,应该说有一些小说已经靠近伟大的边缘了,但止步于最后一两步,即止步于最后的胆量上,可谓心有余,胆不足,我们少了让这种写作野心变成现实的写作胆量。回头想想,世界上那些一流的小说,无不写得“毫无顾忌”,写得“自由无比”,写得“胆大包天”。
这种“胆大包天”的写作胆量具体是指什么呢?我想用几位小说家的几部小说来说明,大致有这样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敢写、敢写得深入。比如拉什迪的《羞耻》。《羞耻》的胆子很大,它影射了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和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近代史,书中人物影射了巴基斯坦两位主要政治人物:布托和齐亚·哈克。因被怀疑影射,导致该书在巴基斯坦遭禁,拉什迪本人也被指控犯有诽谤罪,并被两个家族后人追杀。拉什迪不仅敢写,而且写得深入,说影射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对读者的征服,拉什迪借巴基斯坦这个舞台演了自己的节目——对羞耻的探讨。他的目光聚集在“羞耻”上,他要探讨的是极致的羞耻会将一个国家带到哪里去?羞耻的根源来自哪里?再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菲利普·罗斯《沉重的肉身》、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等都是有勇气、敢冒犯的伟大小说。
二是表达上有突破的胆量。艺术上的突破是很难的,在小说两三百年的历史中,卡夫卡、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等几位在小说表达边界上有新的突破,每位突破者都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师。虽然难,但小说家还是必须要有胆量去开拓小说新的表达疆域,当今世界,比如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算一个小说表达上有突破的作家。《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边的《立体几何》是他最重要、最玄妙的文本之一,它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麦克尤恩在小说表达边界上的突破,也就是说在卡夫卡的变形、马尔克斯的魔幻之后,麦克尤恩为小说历史贡献了“麦克尤恩式的玄妙”——让人物消失或者蒸发。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麦克尤恩的小说都做到了与众不同,成为真正的先锋。再比如因《麦田守望者》名扬天下的塞林格也是一位艺术表达上胆大的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开辟了一种新的小说表达方式——小说是生活谜语的制造者。作为解密生活的手段,小说不提供答案,只提供想象,这让小说走向了真正的开放。或许时间会证明,《麦田里的守望者》给塞林格带来了巨大声誉,而真正让他不朽的则是他的《九故事》等这些短篇小说。
三是精神上的胆量。所谓精神上的胆量,是指小说家和小说是否具有面对重大而艰难的精神问题的眼光和能力。我们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小”:小生活、小感觉、小体验、小眼界、小胸怀,如果仅有“小”,没有“小”中见“大”——大感觉、大体验、大眼界、大胸怀,小说便走不远,也留不下来。看看以下这些在面对人类精神问题上拥有胆识和胆量的出色小说吧:比如德国作家伦茨和他的《德语课》,是对责任感的反思,小说探讨了恪尽职守给人带来快乐、悲哀与灾难;比如日本作家石黑一雄和他的《长日留痕》,探讨的是人生的尊严,以及平凡个体与大的罪恶事件之间的痛苦关系;比如前面提到的拉什迪和他的《羞耻》,他对人类的羞耻感作了彻底的阐释;再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展示了人间苦难的极致;再比如奈保尔和他的《自由国度》,讲述异族文化间的冲突以及扭曲的殖民关系,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对人类精神和人生“大问题”的深刻探讨,将这些小说推上了世界经典的位子上。小说在精神上的胆量的大小,决定了小说能否走远的命运。
三
初步厘清了写作胆量的三种内涵之后,再来反观我们的小说,尤其新世纪以来十多年的小说,我们确实很难找到几部真正意义上的胆大之作。
与写作胆量的三种内涵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小说家有很多东西不敢写,也不敢写得深入,怕碰体制、政治的“红线”,尽管时代已经宽容了很多,但是在小说家的内心里,总存在一片写作禁忌区,有一片写作恐惧地带,不敢闯过去。我们小说家的这种写作禁忌区和写作恐惧地带是无形之阵,它的形成与中国解放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我们国民“中庸”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文化心态有关,它导致的后果是,我们的小说写作避重就轻、避大就小、避难就易。再者,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浪潮之后,我们的小说对表达上的突破和艺术上的实验的热情衰减到了极点,每个人都写得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致于我们读当前一些小说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写得千篇一律,内容上大同小异,形式上一模一样,难有给人的阅读带来挑战或者让人两眼放光的小说。难道是小说的表达边界已经无法逾越了吗,还是我们的小说家丧失了艺术上突破的胆量?另外,当我们历数近三十年来那些还不错的小说时,究竟有多少部具有了传之久远的潜力呢?大部分小说因为精神上的胆量的缺失,只能风流三五年便不再有人问津了。
举两个就在我们眼前的实在例子,来说明我们当前的小说有野心没胆量的现实。一个是贾平凹的《带灯》,一个是韩东的《中国情人》。贾平凹的《带灯》被认为是一部“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深刻且犀利”的小说。但我以为,《带灯》在即将出色的最后一两步止住了,作者没有勇气真正地去创造人物,去升华题旨,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是谁把带灯逼疯了?是谁应该受到指责甚至审判?如果要让《带灯》在当下现实面前成为一部真正的批判现实的巨作的话,小说不能在带灯疯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应该继续往前走,应该让带灯把一切打碎之后,闯出一条可能改变现实的希望之路。其实这条路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一条“淋漓的鲜血”的路。这是小说真正的价值,是读者对小说有效性的一种需求。老实说,这是我对包括《带灯》在内的,关注中国当下现实的小说的一种期许,我知道这样的小说很难出现。一些当着各级作协主席副主席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在触及社会深层次问题时,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在乎现在拥有的一切,在表达的夹缝间安逸生存即可。他们的写作没有胆量,不敢去真正碰触中国现实,但是,要写出真正的现实,没有一副硬骨头,又怎能写出来呢?作家,尤其一个标榜着写着直面当下现实小说的作家,是应该有些担当、冒些风险的。
贾平凹的《带灯》是没有敢写得更深入的胆量,而韩东的《中国情人》则是没有了在表达的突破和精神的开掘上的胆量。《中国情人》好读,吸引力十足,是那种能吸引你读下去并且中途不会因为无趣而放弃的小说,这得力于作者颇见功力的表达,也得力于小说在故事上的妥当安排。我觉得,《中国情人》最大的亮点在于,小说家韩东在小说中寄寓了自己巨大的写作野心:他要为我们的时代“画像”;他要写下与这个伟大或悲哀的时代相匹配的作品。但是,他的野心因为丧失了在精神开掘上的胆量而没有实现。在《中国情人》中韩东将当代中国现实简化为情欲和物欲的现实,建立在情欲和物欲基础之上的文化错位,成为小说叙述的推动力,但是作为一部“野心之作”,仅仅止步于用欲望来概括和描述一个时代,无疑是偏颇和不深刻的,而且欲望——情欲和物欲只是一种表面的现实,只有剖析了欲望席卷现实中国的深层次原因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小说是真正把握了现实中国,遗憾的是小说并没有带领读者进入到那个深层次的现实里,而流于浮光掠影的欲望的“展览”了。所以整个小说读下来,并没有带给我们精神上“大”的体验和眼界。《带灯》和《中国情人》均是今年出版的众多不忍卒读的小说中还过得去的作品,如果用更高的标准来谈论它们,它们不能令我满意,但这两部小说的作者仍然是我十分喜爱的小说家,他们让美妙的汉语在小说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只是写作胆量上的缺失,让这两部小说无法进入优秀的行列。
我们的写作曾经也有过“胆大包天”的时候,那是1980年代,社会思想大解放的浪潮席卷一切,文学艺术思潮波涛汹涌,那时冲突大、尝试大,包容的力度也大,一切处于不确定性当中,有一种探索、开放的力量贯穿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其实这力量就是一种写作激情,一种写作胆量,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尝试。由此也诞生了先锋文学运动,诞生了一批有胆量的小说家和小说。莫言的老师徐怀中在谈到莫言获诺奖时说的话佐证了1980年代中国小说家拥有的写作胆量,他说,“他要感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打破禁锢,迎来世界文学的八面来风,各种文学信息、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让莫言等一批作家开阔了视野、激发了灵感”,“莫言赶上了中国文学最火热的那个年代。他的文学热情喷涌而出”。我以为徐先生的这种说法是中肯且到位的。
但是经历了1980年代的激情、1990年代的余热之后,文学进入了新世纪十年的平静期,所谓的平静期也是一个平庸期,思想冲突没那么激越了,经济地位取代了一切,人的精神问题似乎也没人在乎了,人仿佛除了钱的问题外,不再存在什么问题了,小说里的世界也越来越物质化,人物也越来越冷淡,小说家的写作胆量也在自我满足、自我欣赏、自我安慰中,越来越小了。
我不禁想问:当今的中国小说家,在你们拿起笔的那一刻,你们的内心,有写作的恐惧感吗?有一条放肆、自由、任性和宽广的文学道路吗?是否在你们的身体里,已经无法体验自己民族的盛怒和激情了?还是因为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让你们和你们的写作失去了与这个时代较劲的能力和胆量?
2013年6月11日 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