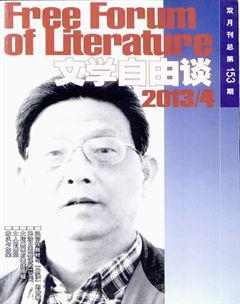新式阿Q令人无话可说
高深
我认识一位半新不老的写作朋友,他写了一篇超现实却又很现实的小说,题目叫《好一个阿Q》。他大概受了某些人的某些影响,把小说写得很离奇也很直陈,很滑稽又有些哲理,看似易懂又不容易读懂。
小说一开头就写阿Q被押赴刑场。他站在那个像大鸟笼子似的刑车上,边看着沿途风景边想:砍头,会不会比吃耗子药痛快一些?好受一些?他仍然为刚才那个圈儿画得不圆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叫了一辈子‘阿Q,临终却没有画圆那个圈圈,真对不起列祖列宗!”
不料在他赴刑场的途中,时局突发变数,原来是又闹起了一场革命,阿Q得到大赦。他丢下刑具,兴高采烈地回到未庄。阿Q为了搞清楚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救了他,也就忘记了自己还不曾从“死而复生”的惊喜中缓过神儿来,便东奔西走,四处打探,终于问出个子午卯酉来,原是一场“比剪辫子还剪辫子”的革命。
阿Q是未庄第一个学会说“古杜白”和“桑Q”的先进分子,随后就把“剪辫子运动”踩在了脚下,与夹着黑色真皮皮包的假洋鬼子握手、进餐、碰杯……终于成为一桩倒买倒卖生意的甲方或乙方。
摘掉了“流氓无产者”帽子的阿Q,拍拍身上的尘土和草叶,从此跟潮湿而又脏兮兮的土谷祠“古杜白”了,害得村扫盲委员会到处寻阿Q回去参加扫盲班。
阿Q在城里租了一间挺体面的门脸儿,挂出一个“未庄魔幻土特产无限公司”的牌子,交易范围广泛得几乎无所不包,一句话,除了军火、毒品以外(有人私下里嘀咕,阿Q偶尔也与别人合伙倒卖过一两次军火和毒品),其余什么都买,什么都卖。阿Q名正言顺、大摇大摆而又顺理成章地欣然做起了“Q老板”。
哇——塞!未庄人对阿Q刮目相看,都说他“爆发”了,因为他曾是判了死刑的革命者,如今在各项经济活动中都受到某些优待,据说在账面以外他还隐形持有百分之二十的干股,年终公司给他分了一笔可观的红利。难怪阿Q的腰粗了,气大了,脖子上拴着一条“金利来”,手指头上箍着两个“金圈圈”,在几个大城市置下了数套别墅式的花园洋房。他经常出入高级宾馆、酒店和娱乐场所,身后往往跟随一位女秘书和一个彪型大汉的保镖……看到了这些情景,吴妈都有些后悔,后悔当初太小瞧了阿Q。小说的后半部分还写了阿Q与赵太爷的儿子合伙开超市,干了一些卖地沟油、注水肉、抛光米、毒奶粉等违法的勾当;还写了有关衙门根据消费者的举报,罚了阿Q一百多两银子的罚款。阿Q寻个凉快地方偷着乐:罚款比请两桌酒席的钱差不多。心想:人家真给咱面子,咱可不能忘恩呀!
我读了这篇小说,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难过和尴尬,虽然他写的这个阿Q生活中屡见不鲜,可我不知道出于某种心理,还是坚决反对了文友的新作:世界文学画廊里本来就没有几个世人公认的中国文学的典型人物,有些所谓典型,大多是被不同历史时尚穿凿的男人或女人,有些虽在国内文坛也“轰动一时”过,但总是时过情迁,待张老忠浮出水面时,王老忠则沉入海底。鲁先生总算给中国创造了一个令世人较为认可的文学典型阿Q,你却把他颠覆了。这怎么可以!这怎么能令文坛容忍!
文友不无嘲笑地讥讽我:“看来您真是老了,难怪你现在写的诗小说没处发表,您太不会与时俱进了。”他摆出一副现实主义的冷峻面孔,并用逻辑推理的姿态给我的看法下了一个判断:“世界没有永远一成不变的事物,阿Q也不例外。他不可能吊死在‘精神胜利法这一棵树上,如今他信仰的是‘金钱胜利法,比从前高明多了。我今天塑造的这个阿Q,虽说颠覆了老阿Q,却是刻画出今天生活的本质真实。”
我悲哀地看着文友,最终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