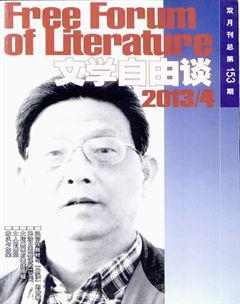迫切性题材与《崩溃》的命意
李建军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就受到片面的强调。后来,这种文学“工具论”主张渐趋狭隘和极端,直至形成一种“写谁”和“写什么”高于一切的理论,即“题材决定论”。这种文学政策所关注的,只是一时的政治需要,对作家写作行为的规约,也是随时变化的,要求作家一忽儿“大写”这个,一忽儿“大写”那个,例如大写“工农兵”、大写“十七年”、大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洎乎八十年代,又来了一种与旧的“题材决定论”拧着说的新潮理论,似可名之曰“形式决定论”或“技巧决定论”。在这种时髦理论看来,题材之间,价值相同,并无等差,所以,“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写”。
如果说,“题材决定论”压抑了作家的个性,限制了他们选择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的自由,从而催生了许多“假、大、空”的作品,那么,后来的“新潮文学”的时髦理论,则给了作家太多消极的自由,助长了写作领域的任性妄为、玩世不恭的坏习气,催生了许多“俗、小、薄”的作品。
其实,做为文学作品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题材与技巧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排斥谁或者谁比谁更重要的问题。道理很简单,若无重要的有意义的题材,任你把技巧玩出花儿来,也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反倒有可能让人看到一种精致的无聊;同样,若无高超的技巧和完美的形式,那么,任你的题材多么重要,也不可能使之成为优美的文学作品。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题材之间虽然没有“地位”上的等差,但不等于没有“价值”和“意义”上的等差。例如,写一只猎狗如何咬死一只兔子,肯定不如叙写暴君如何虐杀人民重要;津津有味地叙写一个变态狂的充满恋物癖和窥阴癖细节的无聊故事,无论如何不如写一个时代人们的不幸和痛苦更有意义。所以,从意义的角度看,伟大的作品总是关注和叙写充满意义感的题材;从与时代的关系看,伟大的作家总是关注自己时代的最重大的问题,总是选择那些对时代生活来讲更具迫切性的题材。
对一个时代来说,总是存在一些让人们最为焦虑和痛苦的问题,总是存在着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叙事内容,——这种包含着时代重大问题的题材,我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借助这个自拟的“临时性概念”,我想表达这样一些理念: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作家们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开掘和叙写的题材;因为,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难以泯灭的记忆,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前行方向。对文学来讲,这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和事件,就是“时代的迫切性题材”。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或者由于无知,或者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傲慢,而无视或者逃避这样的题材,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是缺钙和贫血的,就是失职和失败的,就很难产生真正伟大的文学。
《史记》之所以不朽,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题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是构成它的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司马迁写了一个又一个暴君的罪孽,写了一个又一个酷吏的凶暴;写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建立,写了一个又一个政权的覆灭;写了一个又一个义士的壮举,写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落难;写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血腥,写了一次又一次屠杀的无情,尤其着力于从日常生活细节方面,叙写刘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人格状况和行为模式,——他试图通过“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解决那些迫切的问题,为在战乱杀伐中建立的刘汉政权,提供以“仁义”为基础的“百世大法”。杜甫之所以伟大,他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诗史”,这固然因为他是登峰造极的“艺术家”诗人,更因为他是精神高尚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具体地说,是因为他“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下悯万民疮”(《壮游》)、“不眠忧战伐”(《宿江边阁》),“感时花溅泪”(《春望》),将“安史之乱”当做迫切的、值得叙写的大题材,在“三吏”、“三别”等大量的诗歌里,细致而深入地记录了人民在这场战乱中的境遇,抒发了对家国命运的关怀,对受到战争荼毒的普通人的同情。
对19世纪的欧洲作家来讲,法国大革命就是具有“迫切性”的叙事内容。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历史进程和法国人的精神生活,而且还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难怪十九世纪的多位作家,都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写过与它有关的小说,——雨果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都直接或间接写到了它;狄更斯的《双城记》也是写这场革命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则是延伸性地叙写了这场革命,叙写了它对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后革命时代”的青年一代的巨大影响,——正是这场革命点燃了他们的“梦想”和“激情”,也正是这场革命造成了他们的失落和幻灭。这些伟大的作家没有回避自己时代的“迫切性的题材”。
俄罗斯作家对自己时代的精神痛苦和生活困境更为敏感。他们敏锐地提出并及时地回答时代的问题,特别善于围绕那些重大的事件来展开叙事。在俄罗斯文学的叙事世界,假如没有对1812的年卫国战争、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漫长的“俄土战争”、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等“迫切性题材”的关注和叙写,那么,就不会有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战争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伟大的史诗性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巨著,就不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和《群魔》,就不会有屠格涅夫的《罗亭》、《前夜》、《父与子》和《贵族之家》。同样,假如没有对“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大清洗”、“卫国战争”、“个人崇拜”等“迫切性题材”的叙写,也不会有《第四十一》、《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日瓦戈医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辽娜的家》、《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第一圈》、《活着,并且记住》、《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不落的明月》、《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优秀的作品问世,甚至不会有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和曼德尔施塔姆的《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等伟大的诗篇诞生。
显然,所谓“时代的迫切性题材”,通常与毁灭性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迫害、天崩地解的大变革、改变历史前行方向的大转折、可怕的大饥饿、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问题关联在一起,它更感兴趣的不是胜利、花环和欢呼声,而是挫折、绝望和哭泣声,是生活的有待重整的脱序状态和混乱状态。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总是倾向于关注那些沉重的苦难和巨大的浩劫,总是倾向于叙写人们在可怕境遇中的命运和感受。
苦难与浩劫,固然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但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题材”。每一个民族都曾经历过挫折和磨难,都有属于自己的苦难和不幸。面对民族的灾难和浩劫,需要一种严肃而认真的态度,不能视之为“财富”,唱什么“无悔”的高调,更不能选择“遮蔽”和“遗忘”,而是,一定要将它当做巨大的“不幸”,进而当做值得反复解剖的认知对象,因为,一个民族的性格图谱和未来命运,通常就埋藏在它所经历的浩劫和苦难里;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意志,往往也就表现在它对苦难的态度里,表现在它反思和超越灾难的能力方面。深入而彻底地反思那些可怕的浩劫,也许并不能保证一个民族从此告别苦难,但至少能帮助人们避免重蹈覆辙,能使陷入绝境的人们感受到希望的存在,能鼓励他们仆而复起、不折不挠的勇气,正像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的最后一段文字中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任务都是新的和个别的。深刻的信念和焦灼的关切,都必定使我们完成解决这一任务的努力。那么就让我们仰望着永恒而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境遇吧,从那里向我们荡漾着这样的声音:‘我们嘱咐你们要满怀希望。”
如果说,沾沾自喜、夸夸其谈地渲染成功和荣耀,会使一个民族变得傲慢和自大,甚至浅薄和虚浮,那么,讳莫如深地为研究和叙写“失败”和“灾难”设置禁区,则会使一个民族变得愚昧和孱弱。以种种类似“往前看”等目光短浅的借口,压抑人们的反思诉求,甚至用完全站不住脚的话语遮蔽和美化浩劫,必将造成人们的健忘和无知、麻木和冷漠,必将导致巨大灾难的再次发生。一个民族,如果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摔跟头,总是因为人谋不臧而遭受同一种苦难的折磨,——这,固然让人同情,但更让人瞧不起。
中国是一个特别强调历史记忆的民族,也曾是一个反思历史的智慧很高、能力很强的民族,这一点,从伟大的《史记》里,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后来,随着“官修正史”模式的形成,司马迁式的“成一家之言”的个性化著史,就成了“史家之绝唱”,而为尊者讳的文过饰非,就成了一种强固的文化习惯,而这种文化习惯,则养成了中国人的普遍而严重的健忘症,——这一点,尤其严重地见之于我们对“文革”的失忆上。
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最迫切的叙事题材,非“文革”莫属。这不仅因为“文革”是一场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史无前例的“浩劫”,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丰富的象征意味的“事象”。也就是说,作为“胡风集团事件”、“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四清运动”、“社教运动”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惯性延伸和最终后果,“文革”不仅是我们读解“极左”政治的一把钥匙,还是我们读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的“密码”;不仅是我们进入幽暗、深邃的中国历史隧洞的入口,而且还是展望未来中国前行路途的塔台。如果没有“文革”这个背景和参照物,我们就不仅无法理解“前三十年”的中国,也无法理解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和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例如,当今时代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普遍存在的人格扭曲,诸如自命不凡、舍我其谁的自大狂倾向,蛮不讲理、污言秽语的话语习惯等等,追根溯源,都与“文革”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文革”是横扫一切的大风暴,也是全民参与的狂欢节;它造成巨大的毁灭和噩梦般的恐惧,也造成关于自由与幸福的虚幻想象;作为一场“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它颠覆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秩序和中国人的精神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改变了他们的心情态度和人格状况。它将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继续影响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忽略或者遗忘“文革”,等于遮蔽我们的历史,等于无视我们的现实,等于放弃我们的未来。
然而,在信息获取极为便捷的当下,人们对这场浩劫的记忆和了解,却很成问题。有笑话说,有的中学生在回答谁是“四人帮”的时候,答案非常“奇葩”:或者答曰“马恩列斯”,或者答曰“毛刘周朱”。我很希望这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笑料,但又很怕它的确就是真实的“新闻”。就我的观察来看,事情还有比这更加令人担忧的,也就是说,关于“文革”,还有更加可怕的无知——对“文革”的起源和本质的无知,对“个人崇拜”的真相和危害的无知,对这场浩劫的破坏程度和“影响深远”的无知。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幼稚的浪漫主义者,竟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通过不着边际的想象,将“文革”理想化和诗意化,并通过歪曲事实甚至虚构事实,来为自己的想象出来的“文革”辩护。对他们来讲,“文革”意味着普遍的平等和彻底的解放,意味着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克服。这简直像“痴人说梦”一样不着边际。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小说家的张忠富是清醒的。也许是因为在当下的现实生活里,他看到了太多“文革”的“孑遗”,也许是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里,他看到了太多“文革”的影子,所以,张忠富对“文革”始终念兹在兹,放心不下。他的长篇小说《崩溃》(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所处理的,便是关于“文革”的“迫切性题材”。在张忠富的意识里,“文革”与“改革”的“互文”关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他试图通过对“文革”的叙写,来阐释“改革”,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对“文革”教训的总结,来探索“改革”的出路。如此严肃而深入地叙写“文革”的小说,吾人之不见也,久矣夫!张忠富的这部泣血之作,写得很沉重,读来也很不轻松,但却含着内在的光芒和深刻的启示。掩卷之后,读者的心里难免会有五味杂陈之感,难免会有欲说还休的怅惘,正是:如梦往事来眼底,满腹思绪乱纷纷。
悬疑性和传奇色彩无疑是这部小说的极为明显的叙事特点。邱剑与苏曼丽到底是什么关系?苏曼丽到底是不是邱剑用枪射杀的?他为何要杀死自己的恋人?在死亡的背后,人们最终看到的,到底是“阴谋”,还是“爱情”?这种充满悬念的叙事,极大地强化了这部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但是,张忠富的这部长篇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者说,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的“智慧的痛苦”,或者说,在于它对“文革”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张忠富的理解里,做为一次巨大的“崩溃”,“文革”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将在长久的时段里引发别样形式的“崩溃”。他希望人们牢牢记住“文革”,好好研究“文革”,永远告别“文革”。小说中的老学者庞驼说:“如果人的信仰、人生意义等更高层次的价值问题没解决,而一辈子深陷于个人的专业中,就往往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失落感和不道德感。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对道德伦理,终极关怀最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作了合理的回答时,包括专业精神、民主、自由在内的其他精神规范才可能是明确的。”(《崩溃》,第239页)某种程度上,这段话可以看作张忠富对自己的《崩溃》的“命意”的说明:他试图通过对“文革”的叙写,回答那些“最深层次的价值问题”。
深入开掘“文革”题材所包含的意义空间,是张忠富的小说写作自觉追求的一个目标。为了更好反思“文革”,更深入地揭示“文革”的“根本教训”,张忠富在小说中引入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观念。小说中的华人学者史福威,一位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又从西半球飞回东半球的学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中国的维护“皇权”的儒家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将它的延续视为“中国的奇迹”和“中国的不幸”;在他看来,“国家的安危系于一人”的制度,是“现代社会最落后的制度”,“改变这种落后制度,这就是中国大战略研究的任务之一”。他试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阐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来解决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大战略”问题。围绕“周期性崩溃”、“儒家文明第三次繁荣期”等一系列“宏大”的问题,小说中的学者们唇枪舌剑,相互辩难。在《崩溃》所提供的认知判断里,现代制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当的制约”与“科学的释放”;倘若没有这种现代制度的建构,就不会有“人的解放”,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就很难避免最终“崩溃”的命运。在当代小说的患有严重的思想性贫乏症的语境里,这样的思想交锋,这样的理念建构,无疑会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人在巨大浩劫中的不幸命运和悲惨境遇,也是张忠富特别关注的问题。在《崩溃》里,我们可以读到令人触目惊心且恍然有隔世之感的细节描写。在细节呈现的真实感和惨烈性方面,张忠富的笔力,直逼萧红的《生死场》。借助“日记文体”的亲历性和直接性,张忠富将无辜的苏曼丽所遭受的非人迫害的大量细节,不加伪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更有好心人,在关心我的名义下,十多天不为我松绑,拉屎拉尿在炕上,幸好我没吃东西,只向我强行输液,因而没有屎,只有尿,但尿更比屎臭,我拉了睡干,睡干了又拉,坑上臭不可闻,连屁股、大腿也卤烂了。……渐渐,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可怜渺小。我想以死抗议,谁管你?这儿几乎每周都在死人,死一个罪犯不如死一条狗!我想一死了之,谁知他不让你轻易的死,要让你在痛苦中屈服。我也太把自己估计过高,并不是什么硬骨头,几天折磨下来,我几乎要跪在地上求饶了。”(《崩溃》,第212页)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时代,发生在女性“政治犯”身上的如此悲惨的事情,绝非偶或一见,而是普遍发生的,甚至更为酷虐的施暴,也并不鲜见,例如,对张志新、李九莲和陆兰秀的虐杀,就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令人发指。
从文体上来看,张忠富的这部小说,有着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无论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小说里人物的书面表达,都具有很浓的书卷气,都具有浓墨重彩的特点。苏曼丽的日记里充满诗情画意:“仲夏的果园是最美丽的季节,金色的阳光越过高高的雷岩照在茂密的枝叶上,漏下无数的绿色光斑。清风徐来,摇曳着果树,摇曳着被果子压弯了腰的果树,像摇响了无数的铃铛,让美妙的铃声激越悠扬。我手摘苹果陶醉在仙乐之中。”(《崩溃》,第349页)在小说里,类似的文字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语言,某种程度上,固然有助于显示人物的独特气质和文化修养,但是,如果我们从整部作品里所看到的,大都是这种非常文雅精致的语言,那么,我们就难免会有这样的感觉——作者把自己的语言的风格“分延”到了人物的话语里。是的,《崩溃》在文体特点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风格的单一化和唯美化,就是让自己的话语不加节制地侵入人物的话语。这无论怎么讲,都是《崩溃》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说到文学上的消极的“唯美化”倾向,这里无妨多说几句,因为,这种倾向现在仍然存在,所谓“美文”观念,依然眩惑着很多初涉文学和初习写作的文学青年。
我对当代文学至今仍然流行的“美文”主张,一直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那些装腔作势、自得其乐的“美文”作家,误导了当代读者的文学观念,助长了一种华而不实、伪而不诚的写作风气。在我看来,过度地追求形式上的“以藻丽为胜”的、“雕绘满目”的“美文”,过度地强调无视规范的“形式探索”与故作高深的“陌生化”,乃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文学观念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们将那些格调不高、忸怩作态的作品,当做学习的典范,将那些胡编乱造、毫无规矩的作家,当做崇拜的大师。我们不知道朴素和朴实的价值,也不理解真诚和真实的意义。那些将“先锋”和“魔幻”挂在嘴上的作家和批评家,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常识,那就是,对于文学尤其是小说来讲,朴实和朴素、真实和真诚,乃是决定美学的感染力和伦理上感召力的最内在、最重要的因素。俄国天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谈到俄国文学的伟大成就的时候说,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总的主要特征”,就是“艺术上的简洁,它不懈地试图让其风格尽量地不显山不露水。现实主义者们回避美文。他们心目中的优秀散文是与其描写对象等同的,是呼应其所再现之现实的散文,是不会引起读者关注的透明的散文”(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234页)。事实上,这种低调、内敛的写作态度和简洁的、朴实的写作方式,这种“回避美文”的、不事张扬的文学品质,乃是一切优秀文学的共同的精神特点。
是的,我的结论很明确:尽管从“题材”意义的角度看,张忠富的《崩溃》无疑是一部很有深度、很有分量的作品,但是,从文体角度看,他似乎也未能“免俗”,写得实在太唯美了一些。如此严肃的命题,如此沉痛的叙事,天然地要求一种朴实的文体,呼唤一种内敛的风格。
既然人世间不存在无可挑剔的杰作,那么,就让我们因为《崩溃》在叙事上的深刻与庄严,而向它的作者致敬吧,而文学上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耐心而认真的阅读——《崩溃》是一部值得怀着敬意阅读的忧患之作。
2013年6月30日,北京北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