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囚徒困境”?
| 文 · 朱敏

中国改革开放卅载以降,民企总利润增加17.4%,增幅超逾国企。就此数据来看,民企独立完成了一次新飞跃,若从体制机制创新层面解读,不啻是市场经济一场大胜利。
然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政策主导,结构升级迫不可待,贴牌出口的经济模式沦作落日黄花,做传统生意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已然不是昔日人们追捧的创业英雄。
那么,民企锐气是否真的大不如前?国企改革如何走出“囚徒困境”?“民有”与“国资”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辩证法?作为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王忠明的跨界研究与管理经历,无疑能更好地为人们解答与此相关的诸多疑题。
【对话选登】
朱敏:鉴于中国制造业存在的较大危机,不少学者认为急需“升级换代”,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不过,你却强调中国工业化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宜过早地或者单一地强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是要以就业优先为发展策略。原因何在?
王忠明: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如何更均衡发展,我们都不要忘记中国的一些实际。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就业的前提,事实上就要付出代价,高速增长也不可能持续,产业优势也很难形成。就业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回头就要被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的调整也要从现实出发,应该把内伸的需求作为动力,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政府应该引导金融以及采用其他的杠杆,来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
朱敏:但同样要看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适应的。
王忠明:重要的是,那些一时还没有条件进行调整的,是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就没有地位、没有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大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当然它的附加值要比劳动密集型高,但劳动密集型独特的就业价值是不可偏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力,甚至是国际竞争力。我们那么多产品出口,不是同样具有国际竞争力吗?
当然,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停留在这么一个产业层级上,因此必须形成必要的产业结构,努力地让那些有条件的企业做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品创新和生产制造,而同时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稳定的政策,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区要有必要的政策扶持,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恰当的分布。
朱敏: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一味地往高端走,而是要寻求一种结构均衡的布局?
王忠明:的确如你所言,低端制造业不宜过早转型。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升值,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正逐步提高,与周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再具有人力资源上的成本优势,中国自身就承担着巨大的产业转移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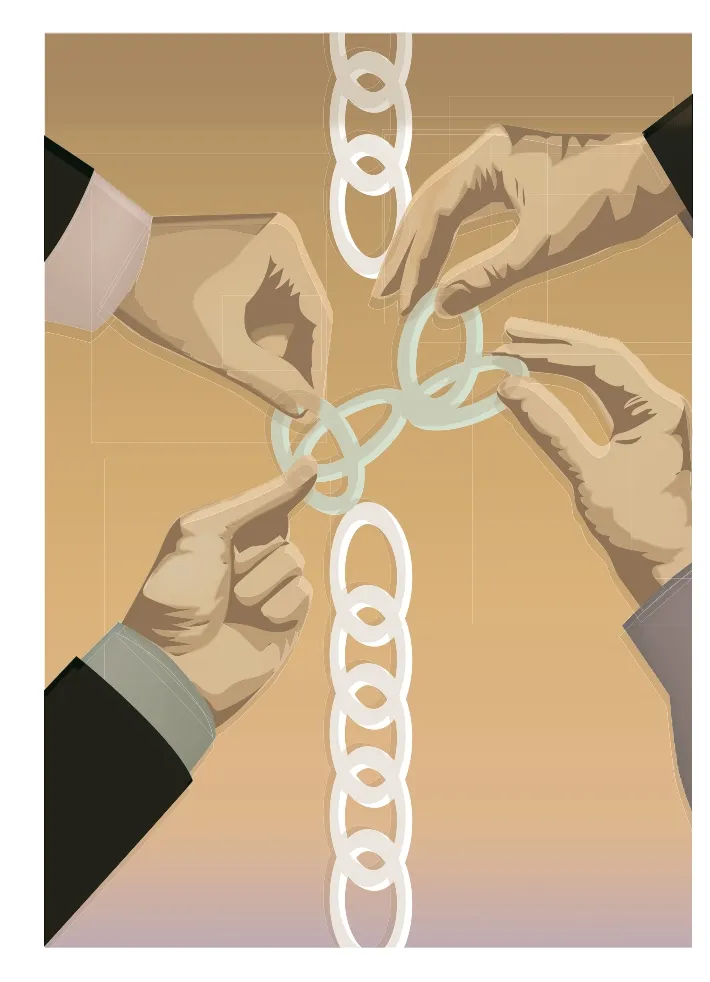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我们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把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留给自己很大的就业窟窿。我们始终要把就业优先作为重要的国策。同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一种低端的产业结构上,由低端向高端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
国企改革关键是把激励搞对
关于国有企业的下一步,王忠明坦言“不能以做大做强为目标”。
“国有资产不能以保值增值为目标。因为它们的诞生不是为竞争而诞生,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为市场而诞生,它们是为市场的修补而诞生的,是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诞生的。它们的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因此,但凡国有企业存在的领域,非国有资本都不会愿意进入,对于投资回报周期太长、风险太大,应该都由国有企业去担当。
循此逻辑,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理应不存在竞争关系,而当遇到竞争时,国有企业应该学着退出;只有在非国有企业想干不能干、不愿干的领域才应留住国企。但是,在真的要降低民资准入门槛上,有没有切实的具体路线和办法?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设计,王忠明概括为四个字:“战略退出”。他强调,这和一般市场的优胜劣汰的退出并非一个概念。战略退出明显具有战略意识,也就是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并非一种“溃败”,而是基于一种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有这种价值框架。”
据此,在观察国有企业改革、评价国资监管工作时,他谨防过于机械,“不要极端化、绝对化。”比如,一提起国有企业改革,就以为国有资产必须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当中退出。尽管从长远看会这样,但近期来讲,非要在一个时段里全部退出,恐怕也不现实。他建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当中,让国有资产或强势国企在竞争性领域中发挥一定的带动作用、一定的影响力。“过渡一段时间以后再退出,也未尝不可”。
这是否意味着,国企不但要在竞争领域内退出,即使在关系国家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当中,也并不应当一味地保值增值、一味地做大做强?
王忠明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表示,当遇到国企与非国企竞争时,国有企业应该学着退出,“不要说国有企业就最光荣,在这里我们不应说国企和非国企哪个最光荣,而是哪个作用最大。原始创造的动力国企不如非国企,经过长期战略性改组,国企应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
对国企改革而言,如何把激励搞对,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个至为关键的难题。在他眼里,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惟一正确的方向。“我想,我们的国有企业,除了极少的国家特别需要的,保留国有独资的形态之外,绝大多数国企都要进行现代产权制度改造。而现代产权制度意味着除了国有产权,还需要其他产权,比如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个人资本,以及引进战略投资家,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产权形态。”
不过,如此一来,一旦走到那一步,还会有国有企业吗?王忠明笑言:即便没了国有企业,依然有国有资产、国有资本。他一再强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这三者概念不能同日而语。国有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少,但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等比例减少,更不意味着国有资本毫无价值。
“现在我们离国有资产运营的市场经济行为还相去甚远,在市场运营方面,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一定要以民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如果经济真正实现了以民营为主体,国有企业减少到不能减的地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各有合适的地位,就能进行正常、有序地竞争。
看得见的流失与看不见的消耗
由于国企出资人是国家,进而可以说是全民,导致国企没有真正意义上自然人形态的产权所有者,因此也无法追溯到一个最终责任人。“尽管说民营企业发展最后也可能以委托代理的方式寻找职业代理人,但在这个高级经理人的背后,永远站着一个产权终极自然人,它会始终为企业负责。而国有企业如今尽管加强了监管,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但无法根本解决动力问题。”
对国企这一近乎“原罪”般的症结,王忠明的看法是如此地一针见血。的确,国有企业在顺利的时候大家都跟着走,在不顺利的时候,纷纷都会弃甲而逃,而且还真的找不到责任人;等到规避责任的时候,同时也规避了机会,做多做少,激励很难到位。
“由于产权制度是这么设定的,所以董事长、总经理很难说国企的业绩,都是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获得的,因为产权不是你的,你不是出资者,你不是投资人。比如年终增长12%,你说是你的业绩,老百姓不干啊,12%属于你不用去筹资啊,国家已经用投资的成本,承担了投资的风险。”他声情并茂地说道。看来,国企的一个永远的困惑是,无法界定各个职业经理人、员工的业绩边界。这就可能出现两个问题:

朱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现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关心中国政经改革与新经济转轨,出版了《中国经济缺什么》、《转型的逻辑》、《通向彼岸之路》等著作。
第一,国企的员工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民营企业一样干却达不到那么高的薪酬水平,我宁可不这么干。”所以有人说央企高管平均年薪60万,还嫌少,招来网上一顿痛骂。业绩薪酬难以界定,毫无疑问随之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界定。“你都不能说这个业绩是你做的,我怎么给你激励?所以永远无法科学。”
第二,约束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约束是世界上最苛刻的,除了基本结构之外,还有党委会、工会、纪检,要素特别多,但是忽略了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原理:给足激励,才是最好的约束。提高违纪、犯罪的成本,使之珍惜现在的岗位,拼命地诚实致富。偏重约束,使得自己谋财就是铤而走险。再者,磨洋工、耗、不好好干,人力资本严重流失。最后,耗不起,走人。
“只要是国有企业,我们看到的肯定是这个结果,使得它严重短缺竞争力。”对此,国家会有一个平衡:究竟是用这种代价来保证公共品的供给,还是完全不用国有企业提供公共品,将尽可能多的环节让渡给私营企业?美国选择的是后者,连军工产品相当一部分产品都外包给了民营企业。这就需要一种均衡。
实际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不应该存在竞争关系。用王忠明的原话来讲,“如果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和非公经济竞争的话,就没有必要叫国有企业,它们的属性应该叫垄断。进而说,凡是没有垄断性质的国企,应该尽早退出竞争。”因此,深化改革是获得经济秩序的一个根本杠杆。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王忠明认为,最大的流失不是货币损失,而是一种隐性的消耗:“多少人在里面青春年华付之东流,而且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部分进了国企,它们反而丧失创新的原动力,沦为平庸的人才。聪明才智流失,创新能力流失,青春年华流失……有效生命的流失才是最大的流失。而现在大家都不考虑这些因素。”
民营企业理应“当仁不让”
对改革与发展而言,危机无疑具有倒逼价值。王忠明告诫民营企业“要珍惜机会,勇于负重拼搏,善于在宏观经济出现不同变局的背景下有所作为,力求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前重点扶持国企、央企等大企业尽管是个可以理解的现象,但它们承担保增长的任务,却无法承担起保就业、保民生,甚至保稳定的重任,而这些更多地应该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非公经济来承载。“民营企业要当仁不让。”王忠明说。
在融资难、创新难等一系列困惑之下,民营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在他看来,需要利用好全社会的普遍觉醒,更好地把内功炼好,把自己的角度定位好。所以,中小企业外部要给与一定的环境支持,更重要的是要突破自身现有瓶颈,比如创新难、接续难等问题。
“我们搞市场经济毕竟时间不长,大家都有一个适应、锤炼、提高的过程。”到全国工商联之后,王忠明接触民营企业更多了,在这个万花筒里,最有出息的、最不好好干的同时并存,看上去也存在一些锐气上的问题。
但他并不这么认为,“你到印度看看,华为的境外公司,你会为民营企业的力量而震撼,当地有出息的大学生统统选择华为。还有,世界500强,沙钢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你说它有锐气没锐气?它并没有受到国家的什么优惠,宝钢进什么设备,它进什么设备,宝钢买什么技术,它买什么技术,但是它的体制优势就决定了它的成本比你低!就决定了市场竞争力。”
中国当前处在结构调整阶段,产业升级需要一个长远过程,有些民营企业陷入一种困惑和迷茫:暂时的升级转变实现不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出路。王忠明认为,“这是必然的。这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谁摊上了这个成本谁得自认倒霉。”因为,当大量国企退出竞争后,竞争主题一定会更多地展现在民企之间。国企以后回归垄断,不参与竞争了,可以想象,有一部分民营企业是要垮掉的。
然而“只有在血与火的拼争当中,才能诞生伟大的民营企业。一个强势民企的诞生,一定以相当一批落后民企的垮掉为代价”,因而对于一些企业短寿、三年死一批的现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的。“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百年老店,都是长寿企业,那是体现了我们人类的贪婪啊,要尊重规律。”正所谓“大浪淘沙”,这个过程恰恰折射出社会进步的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在王忠明的字典里,所谓的企业家,一定是具有深邃眼光的管理思想者,甚至是管理思想家;所谓的企业家,往往都是深刻的人道主义者。深刻的人道主义者体现在永远心存感激,对于这个社会,哪怕还有不公正,还有不尽如意之处,都应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一方面用做好企业的方式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期待着时间的发酵。
谈起企业家的财富观,他则诗意般地表示:“有了钱之后,不能够文明地去处理财富,这个财富是会把自己给淹没掉的。财富并不会无条件地给你带来幸福,连隋炀帝都说,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春兰很美丽,秋菊很美丽,但是仅仅是一时之秀,它确实比野草丛生更有价值、更美观,能够奉献给社会美,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生命周期,要看得到终点,才能使我们的步履稳健。”
因而,诸如资金短缺这样的问题,在王忠明看来并不是根本性的,重要的是“人格精神不能短缺,企业家自己的经营理念、自己的文化和境界不能短缺”。因此,“平和心态、平常心”是至关重要的。
“民营企业最艰难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呢!当国企改革基本到位之后,将是民营企业最艰难的日子。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现在可以埋怨国企垄断,埋怨政策没有倾斜到自己;到那时还做不好,埋怨谁去?”这位从研究国有企业再到研究民营企业的学者诘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