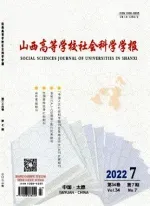娱乐文化与大众心理研究——以“选秀”为视角
秦秀清,王安萍
(江西理工大学,江西 赣州 341000)
近些年来,娱乐文化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选秀节目(以下简称“选秀”)这一类娱乐节目的盛行,充分体现了大众平等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话语权的追逐。《超级女声》(以下简称“超女”)的一炮而红,开启了真正全民娱乐时代,随后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选秀”。然而,过度的娱乐化却导致大众逐步丧失了对文化的批判能力与反思能力,导致大众对生存环境的麻木以及对生存意义思考的缺失。全民娱乐的兴起像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大众表现机会、给大众心理满足的同时,也给大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一、娱乐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娱乐生活相对匮乏。改革开放以后,电视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娱乐节目不断创新求变。发展至今,中国的娱乐文化主要呈现出两大趋势:从审美情趣上看,由艺术欣赏发展为对“快乐”的片面追求;从传播形式上看,大众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娱乐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早期的娱乐节目以晚会形式为主,其内容包含小品、相声、歌曲、杂技等。文艺作品大部分是对美好事物的歌颂以及对不良现象的抨击,体现的是审美诉求。但晚会的参与者基本都是专业演员,这种纯粹的明星表演模式,往往让大众处在被动之中,只能以一种看客的身份去观赏,对娱乐节目产生了“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感受。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娱乐节目逐渐向互动式的游戏模式转变,但仍处于相对幼稚阶段。如早期的《开心辞典》《快乐大本营》等电视节目,大众虽然参与其中,但依然无法实现自我个性化的展示和真实情感的流露。直到“超女”的举办,“选秀”这种新型的娱乐节目才真正地发展起来。第三阶段,全民娱乐时代的到来,“娱乐成分不断被强化是电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载体贴近生活、贴近观众的必然结果”[1]。“选秀”暗含了大众追求“去艺术化”娱乐方式的心理特征,致使大众对“选秀”乐此不疲地追逐,“享乐”成为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大众开始成为被愚弄和消费的对象,“选秀”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低级趣味暴露无遗。第四阶段,“限娱令”颁布之后,“选秀”步入了冬季。然而《中国好声音》重新点燃了大众“选秀”热情。重整后的”选秀”摒弃往日媚俗成分,节目内容从“秀”往“表演”方向转变。同时,节目参赛人群也不再仅限于大众,例如《我是歌手》《谢天谢地你来啦》等,明星被重新加入到节目当中,成了被选择的对象。这种节目方式的转换,重新定位了明星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让早期的“选秀”模式产生了分化。
二、娱乐文化的特点
(一)时代性凸显
市场经济导致娱乐被产业化,“选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一方面,“选秀”是现代人凸显个性、挑战自我、实现梦想的方式,其内部价值体系是基于当今主流价值观念而产生。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选秀”也深刻反映出社会价值内核的弊端。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混为一谈。例如,一些“选秀”通过公开选手隐私、制造绯闻来提高收视,这是典型的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体现出当下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双重危机。而大众往往带着看热闹的心态进行关注,这又体现出当今时代的第二个特征——“去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对自我生存困境的麻木和政治责任感的缺失,致使大众当下普遍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这就产生了对纯粹娱乐的需求。而商家为求利益最大化,不断地创造出符合大众需求的娱乐文化,无形中又加大了大众对于“娱乐”的依赖性。
(二)娱乐泛化
中国的电视业发展曾经历过三个阶段:教化年代、去教化年代及泛娱乐年代。从2004年开始,湖南电视台全面铺开了“快乐中国”的理念,曾备受好评的《晚间新闻》《新青年》等新闻类节目统统被娱乐节目所替换,各类新闻纪实类节目被动地处在一个尴尬的境遇之中。“以‘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为代表的那种审美——道德主义的批判话语和批判范式明显表现出激情过后的颓废气象。”[2]大众娱乐门槛的降低,却并没有让公共领域的政治质量有所提高;相反,公共责任变成了别人的事情,许多人表现出对现实无法改变只能被动接受的态度。“想唱就唱”变成了流行的口号,“选秀”成为了狂欢的重要途径。大众用过度娱乐来填补空虚感,逃避现实,享受着娱乐所带来的虚幻式自由。
(三)平民“显”化
信息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而娱乐文化的盛行,使大众的话语权获得了释放。电视媒体一改往日单项传播模式,通过“选秀”实现了娱乐的平民化。从选手参赛零门槛,到选手的去留由大众决定,“选秀”让登台表演变成了普通人都能参加的大众活动。“选秀”对明星专利的颠覆成为一种必然,各大电视台的“选秀”暂不必说,甚至连“春晚”的节目设置上,都加入了平民参与的环节。《我要上春晚》就是一档央视级别“选秀”,一方面可以为春节晚会输送受观众喜爱的作品,一方面也满足了大众的诉求。然而,娱乐的平民化却并不意味着娱乐就能反映出生活;“选秀”赋予大众娱乐自由权的同时,也并没有传递给大众娱乐的意义。
(四)娱乐模式化
中国的“选秀”大都是沿袭国外的创意稍加改动之后产生的。而节目模式一旦获得成功,接踵而来的是各大电视台的模仿和抄袭,以至于同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相似度很高的“选秀”。同时,由于商家对利益的片面追求,仅仅以市场份额决定节目类型,普遍以唱歌为主,导致“选秀”失去了冲突性与差异性。模仿“超女”而制作的《莱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等等,这些都是模式化的典型。“选秀”的模式化创作让节目失去了创造力,表现出趋同性,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节目创作的艺术性被逐步消解。
娱乐文化的盛行,正是由于契合了大众某些潜在的意识形态,宣泄了大众隐秘的欲望。媒体一步步将大众的欲望激发出来的同时,又力求迎合大众的需求;而大众的需求又决定着娱乐文化的定位和走向。中国的娱乐文化,正是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发展前进的。
三、娱乐文化对大众心理的满足
(一)平等意识的体现
我国自古便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可见,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中就体现出了大众与精英之间因权利的分化而产生的不平等。时至今日,精英与大众间对权利的争夺从未停歇过,而“选秀”的到来,将沉淀已久的“精英主义”彻底打破。明星不再是绝对权威,他们暴露于公众的视线下,任何的言语,任何的表情都会被放大,他们必须直面大众的质疑和批判。而“想唱就唱”的娱乐方式,彻底让大众颠覆了看客身份,体现了一个高参与度的娱乐模式。甚至有人把“选秀”看作是一场象征性的民主运动,挑战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无疑,对平等意识的渴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中国好声音》,采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评判方式,选手与嘉宾采取双向性的选择模式,大众与明星共同成为节目中的演员。“选秀”重新诠释了大众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其中除了参与娱乐的平等外,更重要的是大众所获得的心灵上的平等。
(二)自我需求的满足
首先,“选秀”满足了大众自我实现的需求。获得他人认可,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最为隐秘的驱动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诸多因素阻碍了人们的自我实现。面对生活的无奈,“选秀”似乎如“雪中送炭”般地拯救了大众的梦想,其所营造的让人心动的虚拟场景,激发并扩张了大众的“明星梦”。英雄不问出处,只要站在选秀舞台上,任何人都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选秀”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普通大众从默默无闻走上舞台这一过程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其次,作为观众,大众从选手身上发现与自身相似的方面,让大众产生“替代性满足”,选手的成功与自身的成就之间产生了联系,从而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同时,粉丝团所形成的拟态人际关系,让人实现了社会互动性和群体认同性。大众在参与“选秀”过程中,实现了对自我的定位。
(三)生活化审美心理的满足
中国的娱乐文化历来走的是明星路线,其艺术创作虽然受到现实社会的影响和限制,但表现的内容往往与大众的生活存在一定距离。如今,“选秀”打破了艺术的神秘性,在大众看腻了全明星式的娱乐时,“选秀”的草根性让大众产生了浓厚兴趣。正如街头广告、流行音乐、流行服饰一样,它与世俗文化相互交融,反映的是最根本最质朴的民间文化。“选秀”的草根性蔓延至中国传统娱乐文化的代表——春节晚会之中,兔年春节晚会“西单女孩”、“旭日阳刚”这些来自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崭露头角,与当今“反偶像”潮流相映成趣。传统偶像因太完美、太模式化而遥不可及,使人产生审美疲劳;而草根明星们来源于生活并贴近于生活,满足了大众对生活化审美情趣的需求。
四、娱乐文化对大众心理的消极影响
“选秀”因其自身的特点满足了大众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同时,它作为一个娱乐节目,所宣扬的负面价值观念,也对大众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易渲染功利化价值观
当年《非诚勿扰》中流传出的经典台词“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让事件女主角红极一时,也遭来一片骂声。功利主义正是当下主流文化的部分缩影,大部分角色以丰厚的物质回报以及一夜成名作为筹码;在节目设置中也体现出利己主义倾向和“厚黑学”的处事逻辑。功利文化的盛行,反映出娱乐文化已经彻底跌入了市井的泥潭中。娱乐文化的卖点从反映社会转向对一夜成名的追逐;大众从对商品经济的不信任转向对拜金主义的赞同和鼓吹。媒体为了迎合大众、吸引眼球,将焦点从社会民生转向了犯罪、灾难、花边新闻上,放弃了媒体应负有的价值导向责任。当文化的艺术性让位给了经济性,其生产、传播的主要目的是占有市场份额,获得利润,节目本身的意义也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二)易滋生自由主义倾向
“选秀”所标榜的追求个性、张扬自我的生活方式,实际反应的是大众对于“自由”的追求。随着“选秀”的发展,大众在与精英的博弈中,逐渐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与价值。“选秀”为大众制造了一个脱离于社会之外的幻象,让大众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当年“超女”红极一时,粉丝团失去理性的崇拜,天南地北的追星,疯狂的短信投票,将节目推至高潮。然而,娱乐的自由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自由。一方面是对娱乐的过度热情;另一方面是对于政治参与的冷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于各类社会问题,大众就像是个置身事外的看客,而不是一个实际参加者,“快乐依赖使得人们只能消费现实而不能面对现实;只能为了现实问题发出种种噪音,而不能面对现实;只能在快乐的时候哈哈大笑,不能在快乐之后表现出对社会的倍加关心。”[3]此类现象深刻反映出大众对自我的迷失,对沉重生活的逃避,对现实问题的漠不关心。其结果将导致集体的无意识状态。
(三)易使娱乐文化贬值
湖南电视台前台长魏文彬曾说过:“早期的电视节目是说教,我们改革失去说教,去说教的手段是娱乐,娱乐过度是导致泛娱乐,泛娱乐必然使娱乐低俗化。”快节奏的生活导致浮躁情绪滋生,大众已经无法静下心来读一读书,做一做研究,这正是泛娱乐所产生的根源。泛娱乐将艺术变为失去政治含义的商品,也就让艺术失去了反应现实的能力。同时,审美情趣的下降导致艺术创作流于形式,内容空洞无力。曾经拍摄的国庆献礼大片《建党伟业》就是一个典型。该部电影摒弃了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描述,转而将电影设计成一个精巧的明星走秀,历史事件被描述成为片段式的拼贴,历史感的遗失导致了文艺作品的内涵被扁平化。相比之下,早期的艺术作品就显得更具深刻的内涵。例如,早期小品《扯蛋》,运用滑稽搞笑的方式反应出农民对村干部霸权主义的讽刺和不满。又如小品《打工奇遇》,通过对某酒楼的物价虚高现象的描述,体现出当时大众对商品经济的不信任,以及对传统社会风气的怀念。显然,如今的大众对严肃的东西缺乏兴趣,热衷于“去政治化”的简单娱乐。然而,这样一种肤浅的艺术形式又进一步让观众失去了鉴赏的能力。
五、大众心理期待与娱乐文化的走向
当年,湖南卫视率先将节目重心转向娱乐阵地,随后各大卫视纷纷效仿。“选秀”作为娱乐的重点节目,凭借参与性和平民化特征,已经深深走入了大众的生活中,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节目品质方面来看,其改进空间仍然很大。
(一)娱乐化与品位并存
曾经泛滥的各类“选秀”因过度娱乐而被“限娱”,《非诚勿扰》也因传播不良文化而被停播整顿。但仅仅是限制,并不能真正让大众去欣赏有价值的东西,如何进行引导才是关键。大众对选手的认同更多的是放在外形、性格、舞台表现力等因素之上,节目显得过于表面化。媒体应当充分考虑到娱乐节目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坚持娱乐化路线的同时,力求提升节目的品位。在“选秀”过程中,应当削弱对选手外在包装的关注,突出选手的真实力、真感情;在嘉宾选择上,要注重嘉宾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对选手点评时,应更加侧重从专业角度引导大众对艺术进行欣赏。“选秀”应当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在保留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元素的同时,将良好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融入到节目当中去。例如,央视的《谢天谢地你来了》,即兴表演变成了主要的表演形式,通过设置情景,让嘉宾发挥个人才智处理突发状况,体现了娱乐节目在“智育”上的定位。由此可见,“选秀”只有在表演艺术支撑下,通过提高节目的文化内涵,才能坚守住娱乐文化的道德底线,彰显出娱乐文化的品位。
(二)现实性与德育功能并重
物质的极大丰富导致当下人精神的极度空虚,盛行的娱乐文化缺乏人文关怀、缺乏教育意义、缺乏真情实感。德育功能的体现不仅仅是单纯的说教,若要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应当通过传播一种具有引导性或者启发性的文化来实现。参赛选手通过个人努力走出逆境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励志教科书。它们因为真实而让人感动,对每一个人都能产生深刻影响。“选秀”应当充分研究大众心理,直面现实问题,反映出大众的诉求。在节目中穿插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环节,帮助大众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如《中国梦想秀》,以圆梦为选秀主题,旨在展现人性的美好,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为小人物实现梦想提供舞台。这种对百姓生活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是很值得引起共鸣的。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娱乐节目应当提高社会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并呼吁社会大众做出切实的行动。通过将公益理念融入娱乐的方式,并结合人文关怀和心灵感动等元素,将优良文化和审美情趣传递给大众,引导大众树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念,力求走出一条“以主流价值为导向,以受众需求为导向,以社会责任为使命,以公益诉求为己任”[4]的娱乐文化道路。
(三)层次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早期“选秀”的目标人群为青少年,并且以唱歌为“秀”的主要形式,节目形式过于单调,也无法满足其他年龄层的需求。面临娱乐文化不断成熟的趋势,节目形式应当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并对节目内容进行细分。从“选秀”层次性来看,主要从年龄层次、教育层次等方面进行纵向划分;多样性则主要针对“秀”的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所进行的横向扩展。“选秀”的创新通常是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实现的。如央视的《绝对挑战》,从层次性来说针对的是白领,节目形式是以现场面试为主的选拔类节目;央视的《开门大吉》中对选手的身份限制较低,节目是以听铃声猜歌名为主要形式的闯关类节目,融入了“脱口秀”“音乐秀”“模仿秀”等表现形式。另外,如《中国达人秀》是涵盖任何职业、任何年龄、任何才艺的高参与度“选秀”,最大程度提高了节目的受众群。层次性让“选秀”的定位更加具体和精准,多样性让“秀”的内容更加丰富,两者的结合让“选秀”赢得了更大的市场,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但是,在走层次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路线时,还应注意不要因过度泛化而导致节目失去了精致性和专业性。
(四)文化外交与本土创新相融合
“这是一个马车的时代,两个轮子的马车改成四个轮子的马车,长马车改成方马车,红马车改成黑马车,而不是改成汽车。”湖南电视台前台长魏文彬曾这样说道。从“超女”发展至今,虽然“选秀”内容在表面上产生了分化,但从本质来看,仍反映出“选秀”已经走进了一个瓶颈之中。“选秀”的创意源自国外,由于节目本身定位并不符合中国特色而很难获得突破性发展,本土化是“选秀”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因此,中国的娱乐文化应在不断吸收国外优秀创意的同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改进,通过节目弘扬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首先,在节目设置上要淡化竞争式的节目氛围,改变以PK为主的晋级模式,摒弃通过暴露隐私获得收视率的运作模式。其次,节目组成上嘉宾要取代评委,嘉宾身份可以从单纯的歌手扩展到演员、曲作家、甚至幕后人员。主持人要跳出“脱口秀”式的角色,以朋友拉家常的方式来实现串联节目目的。再次,将“秀”转化为表演,扩充节目表演种类,可以在节目中融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最后,在节目中倾注更多人文关怀,将社会公益穿插其中,是提高“选秀”德育功能的主要途径,也是进行本土化创新的重要途径。
纵观娱乐文化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整合的功利性和表面性,但也说明了娱乐文化对大众生活的重要性。中国的娱乐文化在借鉴外来创意的背后,包含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相容,中国的娱乐文化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不断摸索规律,以求获得自身长足的发展。
[1]王 普.艺术欣赏 娱乐体验 心里参与——对中国电视节目的几点思考[J].中国电视,2008(12):50-52.
[2]陶东风.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J].学术月刊,2009(5):21-28.
[3]周志强.从“娱乐”到“傻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4):36-43.
[4]王同元.彰显综艺娱乐节目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内涵——浙江广电集团打造公益性综艺娱乐节目的实践探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10):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