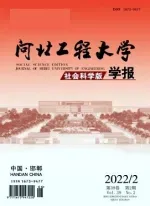“在而不属于”——施蛰存创作中的建构与解构
鹿义霞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200)
施蛰存曾在晚年时自喻一生打开了四扇窗子:“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1]其审美心理的组成非常多元——古今兼修的学养和中外兼及的趣味共同作用于他的内心深处,城乡二元的游走和新旧夹缝的身份浸润着他的笔端。多重因素交相辉映,促成他不一样的文化眼光和文学实验。他的笔下没有英雄或者完人,也没有荡气回肠或者大喜大悲。内倾如他,为海派小说家中最接近京派风格者,也是新感觉派小说家中最不够“上海”的这一个。因此有论者评曰:施蛰存的小说,宛如身着华丽的中式旗袍,在传统民乐的伴奏下跳着异国的华尔兹。这种特殊的光与色使他不但能在当时的文坛独步,也使其作品禁得住岁月的淘洗,显示出耐人寻味的丰富和驳杂。
一、城与乡——无处是家园
施蛰存是从江南水乡的书香气息和恬静风光中跨入上海这个喧哗摩登的大都市的。他的小说中有两个重要的文学地景,一个是逐渐破落的江浙乡镇,一个是五光十色的都市上海。
都市书写方面,施蛰存似乎有意地疏离喧嚣的市声,没有在灯红酒绿的世界放纵自己的感官,而是试图寻找一条窥视都市人隐秘心理的幽暗通道,挖掘人的本真生命形态。他不追逐都市的风景线,也不迷恋上海的狐步舞,热衷的却是探测摩天大楼背后的都市陋巷以及人性的复杂斑驳。在弥漫着薄暮情调的小说中,情景亦真亦幻,错觉、幻觉、梦境、臆想纷纷登场,精神分裂症和神经衰弱症、恐惧症、孤独症等“都市病”风行如潮。故事的主人公疑神疑鬼,看到的是一个草木皆兵的世界。这些人物多是“城乡边际人”,或是城市小市民,或是从郊区“进城”的过客,或是蛰居的候鸟。他们站在城市物象的边缘,有着紧张压抑的生存境遇,怀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隐痛,揣着不可言说的病态欲望,灵魂孤独而寂寞。紧张、恐惧、焦虑成为他们的情感主色调。《夜叉》、《魔道》、《旅舍》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样一种精神病态。他们都害着妄想症,经常性地陷入一种幻视、幻听和迫害狂的怪式思维中,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施蛰存渲染了都市人强烈的孤独感、软弱感和恐惧感等“创伤的执着”(弗洛伊德语),开创了一条在30年代堪称独步的心理分析之路,在咂摸人性的暗流涌动层面上作出了深入的探索。在都市的快节奏生活中,都市人时常处于一种紧张而焦灼的状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冷漠。于是,他们“在而不属于”,无依、无措、“无根”,心灵找不到归属,灵魂无处安放。
施蛰存的作品中,出现乡镇背景的小说为数不少。他笔下的乡镇大多以苏州、杭州和松江等地的农村和小镇为摹本,“江南”不仅是其出生和成长的地域空间,更是充满着丰富的文化指涉意义的意象空间,成为他文学上的“后院”。施蛰存的这些小说温婉、细腻,是带着忧郁的回味,是掺着惆怅的怀旧,是时光难追的喟叹,像傍晚的阳光撒在书页上,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怀。《扇》、《上元灯》、《渔人何长庆》等小说充盈着往昔难再的怅惘。施蛰存对于现代都市文化负面性的因素并不讳疾忌医,也无比清醒地看到现实的乡土不过尔尔,也不能起到真正的疗救作用。对于施蛰存来说,虽然“在被忘却故乡的山脚下,有我的铅皮小屋。”但是,乡村毕竟不是桃花源,在纯朴乡土伦理的背后也暗藏着它的愚昧和无知,比如生活艰辛、思想封闭、麻木迷信。乡村生活的阴暗面时时提醒他,现实的乡村不是净土,依然无法消解烦闷、安放灵魂,旧的精神家园已不足以排解现代人的孤独、寂寞。像《夜叉》、《旅舍》、《闵行秋日纪事》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喧嚣的都市患上精神病症之后,希望在宁静的乡野舒缓紧张的情绪,得到心理上的疗救,但他们回到梦魂萦绕的故乡,却发现一切皆是枉然,恐怖的幻觉依然来袭,感觉的阴霾依然浓郁。
城市的难题,乡村无法给予诗意的答复;乡村的幻梦,在时代的巨流中也逐渐飘零。在施蛰存眼里,水泥森林的城市与茂林修竹的乡镇都不是伊甸园,“城”与“乡”都无法成为真正的精神家园。作为精神流浪者、城市边际人,他笔下没有乌托邦,只有无法自主的社会人,其创作呼应了尼采诗中所吟咏的那种绝望感和荒原感。
二、古与今——你我皆凡人
施蛰存创作上勇于独辟蹊径,列入其小说名单中的既有历史小说《水浒》中的草莽英雄,又有《高僧传》里的伟大和尚。他重新演绎古人古事,不是像郭沫若那样“古为今用”、把“当代意识”和政治理念强加给古人,而是像鲁迅那样进行“故事新编”,并与心理分析手法结合,挖掘人的内在现实,铺展开古典题材下的“原欲”书写。郁达夫曾盛赞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做到了把“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人的脑里去”。
施蛰存笔下没有完人,没有英雄,有的只是复杂的人性和斑驳的心理。《石秀》、《将军的头》、《鸠摩罗什》、《黄心大师》等小说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人类心灵黑箱的窗户,揭示出世人在社会规范和个人欲望之间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和抉择困境。施蛰存好似潜入铁扇公主内脏中的孙悟空,揭示着古人隐秘的心灵世界。他通过合理的想象和心理分析,消解了高僧形象的伟岸和舍利子的神秘,剥离了佛教涂抹在他们身上的油彩, 用艺术的手法使他们“还俗”。 在施蛰存笔下,历史和种族在个体这里,不是引领行动方向的灯塔,情欲才是主导个体选择的罗盘;神圣和崇高在现实这里,不是约定俗成的传奇,“自我”才是主导个体走向的指针。鸠摩罗什、花惊定、石秀、段平章及黄心大师被奉为传统文明下的偶像,其传奇人生和高洁的品行曾被无限放大,但施蛰存却掸去了附着在他们身上的金粉,还他们以肉身的沉重。在《鸠摩罗什》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圣僧的光环,而是心神摇曳的术士。《高僧传》对大家的传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恶搞”和解构。在《石秀》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而是“因为爱她,所以想杀她”、被情欲捆绑的变态狂。在《李师师》和《黄心大师》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大写的“名女人”,而是恋爱幻灭的苦闷者。作者手中好似有一把寒光四射的解构之刀,他“将古人现代化,将古人弗洛伊德主义化”,以对高僧、名将、侠客等的颠覆性叙事来亵渎神圣,消解英雄,还原世俗,带有后现代的解构色彩。施蛰存的这类“故事新编”对历史进行了另一种解释,展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他告诉我们: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被弥天的雾障所扰,也许距离曾经深以为然、颠簸不破的“事实与真相”依然十分迢遥。
施蛰存努力经营的不是情节,而是心理、情绪和氛围,其小说具有鲜明的解故事性、解典型化特征,因而与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拉开了距离,呈现出现代小说意识的积极突破与现代小说创作的崭新探索。他打破呆板的线性模式,以回忆、联想、幻觉等心理活动为主导,将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无限放大。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和性格外部特征的模糊,是施蛰存刻画人物的主要路径。正如谭桂林所言,施蛰存的小说揭示了隐藏在“那枯寂入定的得道身躯里依然有着像地火一般运行的人性力量”[2]。
三、中与西——脚踏两条河
施蛰存曾经反刍过古典诗词,研习过苏俄文学,体味过欧美的现代派作家,又咂摸过日本的自然派作品,其接受资源是多向的。他曾说自己一生开了四扇窗子,其中有一扇开向外国文学翻译,一扇开向中国古典文学。开向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窗口使其在吸纳外国文化思想时有着东方的根基,使他的作品能够运笔流利,即使是精神分析一类的作品,以弗洛伊德的眼光透视人物的深层心理,也能做到杨义所说的“怪而不乱,玄而不晦”,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品味与解读习惯。东方温柔敦厚的诗教和西方人性探索的旨趣在施蛰存这里实现了巧妙的融合,他十分自然地从西方拿来现代精神分析的种子种植在中国的园地里,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技巧与民族传统的结合中找到了自己的契合点。
施蛰存从小就一直浸润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氛围之屮,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在对意象的运用上更倾向于“中国结”、民族风,表现出一种民族性的心理元素。在其早期创作中,传统文学的韵味是非常明显的,古诗词的神韵笼罩在现代小说中,现代观念与现代技巧如盐着水不留痕迹。小说集《上元灯》中的某些作品,就带有晚唐诗的意境,洋溢着感伤之美。当年叶圣陶评价施蛰存的文字时曾说:“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经文”[3]。《扇》中写两小无猜的一双少男少女,其中女性的倩影、手握茜色轻纱团扇追逐流萤的情态使人联想到杜牧的“轻罗小扇扑流萤”;《魔道》中的黑衣老妇、竹林,玻璃窗上的黑点、大黑猫、黑啤酒等意象营造出类似鬼才李贺诗的那种阴森险怪的意境。《上元灯》、《桃园》、《诗人》都有着细腻婉约、温柔伤感的底色,闪烁着某些东方诗的光影。《梅雨之夕》淡化故事情节,淡化人物性格,强化内心独白,既饱蘸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又几似抒情写意小说。《将军的头》将东方风土文化、民间传说与西方现代技巧相结合,既刻画出人物隐秘、复杂的心理,又形成了一种情景交融、含蓄深远的意境。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显尼志勒的内心独白、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中国小说的诗化结构共同碰撞,丰厚的文化准备与艺术积累使他的作品一贯地呈现出鲜明的特性——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式的意识流。《春阳》、《狮子座流星》、《雾》注重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的独特风格。《黄心大师》等创作实验将古典的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融合,拓出文学新路。施蛰存的另外一些作品,如《魔道》、《夜叉》、《凶宅》、《旅舍》,既具有“哥特式小说”的魔幻意境,又带有明显的“聊斋风”,是典型的中西结合式。这些小说虽怪诞、神秘,却自始至终渗透着东方特有的情调。在开放的世界眼光和现代性主体意识烛照之下,施蛰存在中国的土壤上培育出文学的混血儿。
从小所受的古典教育以及温婉内倾的性格决定了施蛰存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西化的现代派,他的行文是米线麻辣烫式的两掺,是中与西的交响与融汇。“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是施蛰存对自己创作的阐释。复杂心理的展现、性爱主题的表达、潜隐情绪的揭示,在文字创作中难以拿捏好分寸。过于细致则类似一种宣泄,容易落入俗套;过于含蓄则失于笼统,难以展现人性的本真。施蛰存综合中西文学表达的优长,在碰撞中解构,在解构中建构,正如杨义所言“站在现代大都会的边缘,窥视着分裂的人格,怪诞中不失安详,在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4]
四、左与右——游离大潮外
对于自己所秉持的“既不敢左,亦不甘右,又不欲取咎于左右”的中间派路线,施蛰存曾经这样咏怀:“左右逢源无适莫,衡文吾道一中之。”他的创作一直都是与中心话语体系相疏离的。这一点,他和沈从文很像。新感觉派的天地涵盖不了他的所有创作,海派铺张扬厉的文风诠释不了他的基本风格;左翼的政治气候太高压,他不具备参与轰轰烈烈社会政治变革的社会勇气;国民党的右翼圈子与他的创作风格很不搭——他渴望独立的文人姿态和自由意志,为人和为文上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施蛰存曾表示,在文学上他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所以坚持要“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 他创作中不站队,不跟风,在普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的三十年代,他疏于政治、沉潜艺术,专注于刻画人性的复杂斑驳,向灵魂和意识边际突进,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文学选择。他关注人的世界的复杂与生动,将焦点投射到“人”身上(不仅是社会的“人”,而且是个体的“人”),文字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功利色彩。因为非左亦非右,他的创作虽然显得不合时宜,却使一直追求宏大意义的中国文学开出了别样的花朵。
不但是创作,他参与编辑或主编的《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都呈现出“列车无轨任横行”的风貌。走中间路线的《现代》编辑理念更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于是便呈现出多元的风貌,以至被人称为“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混血儿。《现代》杂志的同一栏目下,往往可以读出针锋相对的观点的交锋。在“第三种人”论争中,施蛰存同样为双方开放战场。可以说,无论是势头迅猛的左翼文学,还是前卫先锋的现代主义文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园地;无论是新老作家,都可以在这里听到“同人”的声音。正如施蛰存所言,要《现代》成为现代中国作家的大集合、大本营。当时文坛上的大家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盛名正旺的如沈从文、沉樱、臧克家、李金发,甚至梁实秋、苏雪林、季羡林、钱歌川、赵家璧等都在《现代》一露身手,奉献出风格迥异的文学盛宴。
不愿意为任何派别所束缚,不愿意跟随时代潮流选择政治站位,施蛰存“我只能写我的”其实就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创作气质的确认和坚守。正是因为秉承这样的原则,年轻的施蛰存面对丰之余(鲁迅)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甚至茅盾、洛夫、陈子展、周木斋、曹聚仁等人的批驳,仍然在《庄子》与《文选》之争中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争一份表达的自由,争一个话语的空间,走一条行知合一的知识分子“中间派”道路,是施蛰存的创作姿态和为人为文之道。
也许正是因为坚持文艺创作的自由,施蛰存才没有观念先行,而是自由挥洒,拥抱真实,更多地将笔端对准“人”字做文章——关注“饮食男女”,聚焦“人间烟火”,不管是对现代城镇中的芸芸众生,还是对尘封历史中的名人,作者的笔都会探入到人物的内心,触摸人性的奥秘、状写内在的真实,展示其对人性独特的思考和阐释。
[1]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981.
[2]谭桂林.佛教文化的现代心理学透视[J].上海文论,1992(5):62.
[3]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53.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64.
[5]施蛰存.施蛰存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6]吴福辉.施蛰存对“新感觉派”身份的有限认同[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3):52-55.
[7][英]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8][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9]赵凌河.论施蛰存文学思想的现代性[J].当代作家评论,2005(1):42-45.
[10]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11]王艳凤.从新感觉派到新心理主义[J].外国文学研究,2003(6):36-39.
[12]周宁.《现代》和三十年代文学思潮[D].山东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