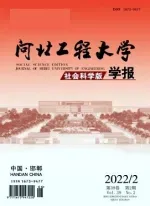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宋文坛,吴晓雪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新时期之初(1970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是一个颇为尴尬的历史时期:“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旧时代的伤痕还未痊愈而新时期的规划与蓝图还未及充分展开。在这样一个“将生未死”的特殊历史阶段,文学还无法编织诱人的理想远景,如何叙述当代历史尤其是不堪回首的“文革”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严峻话题。此时诞生的“伤痕文学”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说出真相、反思历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规范的压力。显然,后者是更为强大的。虽然“文革”历史已经被彻底否定,但当代的革命历史却不容置疑,这是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当代历史叙述的“底线”。因此,如何在小说叙述中进行有限度的“历史否定”同时对革命历史和意识形态进行“继承”就成为意识形态压力下文学叙述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正是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形象化的诠释和解答,从而,文学的历史叙述也便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一、“忠奸对立”:文革历史的“空白化”
在大量表现历史伤痕的作品中,“忠奸对立”模式几乎成为小说叙述的固定套路,在忠奸两派的对立叙述中,忠义之士往往受到奸佞小人的迫害,而在抗争之后,却无不取得最后的胜利,奸佞小人则无一逃离历史的惩罚。我们看到,许多伤痕小说正是这一“规范”的典范执行者。《神圣的使命》、《小镇上的将军》、《剪辑错了的故事》、《蓝蓝的木兰溪》、《罗浮山血泪祭》、《芙蓉镇》、《天云山传奇》、《许茂和他的儿女们》等等一大批经典作品,都惯于在伦理化的叙述中塑造“封建群小”形象,在“坏人猖狂,好人遭殃”的模式里控诉“文革”;同时,又以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拯救历史,其叙述思路显然在“忠奸对立”的二元模式中盘旋。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具体作品。以《芙蓉镇》为例,小说除了表现胡玉音等主人公的“苦难”遭遇之外,还着力塑造了李国香、王秋赦等“群小”形象。在作家笔下,这两个反面人物的形象基本上可以用“道德败坏”四个字加以概括。贪图享乐,奸淫成性、陷害他人、不择手段、自私冷酷、唯利是图、媚上欺下……几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人性丑恶的特征都在这两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显然,作者在竭尽全力地塑造道德上彻底败坏,人性上彻底堕落,政治上彻底流氓化的人物形象,他们集中了多重丑恶性格,成为“伤痕”小说中“奸邪”形象的典型。于是,主人公的苦难根源,乃至芙蓉镇苦难的所有根源,都指向了这两个人,指向了这两个人的道德沦丧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解释那一段灾难历史的唯一答案。与这部作品相似的是,许多“伤痕”小说也都致力于塑造这样的奸佞之徒的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积聚着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的人性的所有丑恶:嫉妒、权欲熏心(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好色(如《将军吟》中的江醉章);贪婪(如《三生石》中的施庆平);凶残(如《罗浮山血泪祭》中的刘永泰、《神圣的使命》中的徐润成);背叛(如《将军吟》中的邬中)等等。政治阴谋家与道德败坏者的身份重合往往是这一类小说反面人物塑造的常规写法。
这样的写法包含着重要的意义指向,那就是将“文革”“空白化”。在“新时期”之初对“文革”性质的争论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矛盾的观点,其一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它倾向于反思“文革”历史与当代中国历史整体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的连续性,对“文革”历史罪因的思考,既从政治的层面,又从文化与人性的层面深入挖掘,从而暴露出“左”的历史灾难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思考方向的特点是将“文革”“连续化”、“逻辑化”。另一种观点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在它的叙述中,“文革”是一场“内乱”,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次历史的失误。而那一小撮政治小丑,是历史浩劫的肇事者,他们被指控为是品行卑劣、道德败坏、无恶不作、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因此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简单化的道德控诉使“文革”的复杂历史成因被简化成了个人道德问题,这一结论有效地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了,这段历史不再成为可追究探讨的、在连续的历史实践中显示出复杂因果关系与逻辑意义的历史,而成为时间链条中的一段无意义的偏离,一段虽则痛苦却似乎与此前此后历史毫无瓜葛的,可以轻易告别、盖棺论定的时间。在“文革”与“十七年”和“新时期”的历史关系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都倾向于以“断裂”的方式加以叙述,从而,“文革”就成为尴尬的前后不着的一段空白,脱出历史的链条,沉落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放眼未来,沉重的历史问题似乎都在浅薄的道德义愤和悲喜中化解掉,这单纯得令人惊讶的历史叙述逻辑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新时期以来,许多论者都对伤痕小说的“忠奸对立”模式予以批评,认为这是新时期现实主义创作不能摆脱“十七年”文学公式化倾向的证据。实际上,这一看似文艺领域内的问题却体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要求,它并不单纯是文艺理论问题。
二、时间切分:“回归十七年”的历史逻辑
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一个如何保持历史“连续性”叙述的问题。在否定“文革”之后,主流历史叙述还要捍卫、肯定革命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还必须延续“十七年”以来已成定论的经典历史叙述,保持其连续性。如果不能明确这一根本性质问题,就不能明确历史的继承性和合法性,历史叙述的“断裂”将以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为代价。这样的历史认知体现在有关新时期的文学性质认定上,“新时期”被定位在“回归十七年”的历史关系中,“新时期文学”则是重新开始的一段“新社会主义文学”,于是,“回归十七年”便成为新时期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另一个逻辑。
邓小平在《祝辞》中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1]这一“定性”的提法,表明了“主流”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因为否定“文革”而否定整个革命文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正”就在“十七年”文学之中。因此,邓小平对新时期文学创作所提出的要求,基本上是对“十七年”文艺的重申。我们所熟悉的“描写新人形象”,“反映时代本质,历史发展”,“反映中外,借鉴古今”,“百花齐放”等等“十七年”文艺的纲领性原则,都在《祝辞》中出现。在其后周扬的报告中,这一重申更进一步具体化了。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时代“精神本质”的创作理念,“塑造革命典型”的主题要求,坚持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原则立场等等“十七年”文艺的基本主张,被周扬详加阐发,并被确定为新时期应继承的历史遗产[2]。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这些叙述表明了这样的历史姿态:在新时期与“文革”、“十七年”与“文革”关系上,强调其断裂性;而在新时期与“十七年”的关系上,强调其连续性,这样的用意很明显:新时期是对“十七年”的回归与重建。
“回归十七年”的历史叙述法则,在新时期之初的伤痕作品中多表现为“时间切分”的叙述方式。“时间切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今昔对比”的时间切分方式。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伤痕”小说中对50年代甚至对60年代初的社会描写都有一种美化的倾向:那是合作化热火朝天的时光(《许茂和他的儿女们》);那是田园牧歌的年代(《芙蓉镇》);那也是青春飞扬的时代(《布礼》);和经济起飞、社会和谐、年轻人抱负得以舒展的时期(《天云山传奇》)。而与之对比,“文革”时代就显现出荒谬和不合理来。在《许茂和他的儿女们》中,小说以许茂老汉的眼光表达了对“合作化”与“文革”两个不同时期的对比。在许茂看来,“文革”是一次巨大的破坏,而“合作化”时人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才是让人顺心顺气的。“过去”是美好的,“现在”则是令人气馁的,甚至老汉本人的性格都有明显的不同:“合作化”时他积极肯干,大公无私;而如今,为生计奔波,不得不自私、算计起来。许茂对过去的深情回忆蕴含着厚古薄今的意味。“十七年”,“解放初”,因为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成为一段辉煌的记忆和黄金年代,而“文革”现实在对比之下就立刻显现出其不可理解和“偏离”性来。
“时间切分”法的第二种方式,是小说的叙述者总是不会忘记给读者提供一个当下时间内的“幸福场景”以此体现与“文革”时代的截然不同并平衡小说中过于沉重的历史叙述。当下的场景可能是浩劫后的重逢(《天云山传奇》),也可能是与奸邪力量斗争的胜利(《神圣的使命》),更多的则是幸福生活的重新开始(《伤痕》、《芙蓉镇》、《小镇上的将军》);不论怎样,这些“重见光明”的幸福生活场景都预示着一段荒诞历史的结束和历史对原初“正确路线”的回归。
“时间切分”的时间修辞是有益的。首先,它以“光明”的方式有效平衡、冲淡了文革历史叙述中的苦难色调和悲剧色彩,暗示着“历史正义”的最终胜出,从而巩固了本已动摇的历史信念。其次,它将时间的整体切分成三个段落:十七年或建国初的美好——历史的徘徊与“偏离”——历史的“回归”。在一头一尾,小说明显暗示了历史的连续和呼应关系,这是革命理想的呼应,是牢不可破的革命历史的连续。伤痕小说的这一时间修辞正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回归十七年”策略的呼应和最好的文学表达。
三、“忠诚”叙述:革命“原点”的回归
伤痕小说中有着大量“表忠心”的描写,它往往与小说中对混乱政治时局的描写和伤痛书写形成对比、平衡关系。如果说“文革”的动乱和大量灭绝人性的残酷事实构成“变”的因素的话,那么“忠诚”叙述就构成历史中“不变”的因素。它昭示着这样的叙述动机和目的:尽管党、国家和民族遭受了最不堪忍受的劫难,曾经一度陷入混乱无序之中,但坚定的忠诚信念是抗衡以至反拨这一劫难与混乱的核心力量。对党与国家的忠诚将最终完成拨乱反正、解民于倒悬的历史使命。
在具体创作中,“忠诚”叙述的主体既包括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也包括广大农民。可以说,“忠诚”成为最广大群体的共同心声。《灵与肉》中,许灵钧甘愿放弃去国外继承丰厚遗产的机会,回到他梦寐不忘的西北草原,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的“根”,在他的理解中,“只有依恋自己的根才是爱国。”在《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为此,他甘愿赴汤蹈火,献出生命。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忠诚伦理”以李铜钟这个道德人格化的正面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在“大跃进”中,无论“浮夸风”如何盛行,李铜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当春荒蔓延,村民们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他又能挺身而出,不惜冒着犯死罪的风险,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在《剪辑错了的故事》中,小说通过对“寻找甘书记”一节想象化的描写,表达了“人民忠诚于革命,人民寻找真正的革命者”这一主题。在“反侵略战争”这一幻想性情节中,老寿出发去寻找真正的老甘,希望他能回到人民群众中来,领导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情节与其说表达了人民对党恢复群众路线的渴盼,不如说是曲折表露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忠诚信仰:即使党曾经有过历史失误,人民也仍然与她站在一起。这样,“寻找”就转变为类似母亲对儿子的亲情的召唤,“人民”与“党”之间相互忠诚的复合关系在此又一次得到表达。
在“伤痕、反思”小说的“忠诚”叙述中,主人公或是被奸人构陷获罪;或是受到政治风云突变的影响,而使自己的抱负不得舒展、事业横遭打击、人身受到伤害;或是家庭离散,亲情、爱情遭遇毁灭。但是主人公无不奋起抗争,或坚持真理与理想,与邪恶势力不惜殊死相拼;或坚信历史的正义必然能够实现,寄望于“党”与“人民”。小说往往以主人公的壮烈牺牲为结局,从而将“忠诚”叙述推向悲剧的高潮。如在《大墙下的红玉兰》中,葛翎为了表达对周总理逝世的哀思,不顾自己身陷牢狱的困境,冒着生命危险去采摘白玉兰花,结果惨死在“四人帮”爪牙的枪下;《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为揭露“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冤案,殚精竭虑,上下奔走,最后同样在与“四人帮”爪牙的对抗中牺牲。“牺牲”成为确证主人公信仰程度的试金石,悲剧因信仰与忠诚笼罩而具有神圣的壮丽色彩。
如果把前面论述过的“时间叙事”与“忠诚主题”结合起来,我们会更加清晰地发现小说历史叙述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可表述为:历史对某一个“原点”的建立与回归。这个“原点”在小说叙述中被表述为或是党群之间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或是“十七年”正确的政治路线,或是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总之,它是曾经存在的正确的意识形态。然而,历史的运行发生了偏差,从“大跃进”到“文革”,历史运行似乎越来越远离这个正确的“原点”,走过一段混乱而无意义的“空白”时间,而直到“新时期”,当历史重回“原点”,“拨乱反正”之后,时间的裸露之点与断续之处才接上,从而历史的运行才又被重赋意义。在那段“空白”的历史中,奸佞小人曾经猖狂一时,然而,依靠着对历史真理的忠诚,“人民”还是将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现了“拨乱反正”。可以这样说,时间的切分性叙述最终的目的,还是指向“忠诚伦理”的表白,指向政治意识形态的回归。
综上所述,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总是在暴露之中又有遮蔽和掩饰,这使它的历史叙述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正是这样,伤痕小说的历史书写实际上为推诿历史责任、遮蔽历史反思提供了某种便利。孟悦曾尖锐地批评道:“叙事使‘过去’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有:正义与非正义的清晰分野,遭到冤屈的好人及其同情者,逆境和高压毁灭不了的信念和理想,以及应当为恶行承担责任的坏人形象(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因素真的在现实中占有小说给定的结构性位置,那么这场群众性的‘文化革命’怎么会‘进行到底’。”[2]伤痕小说的历史书写特征是新时期之初特定意识形态历史要求的反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文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特点。
[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C],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3.
[2]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C],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77.
[3]孟悦.历史与叙述[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