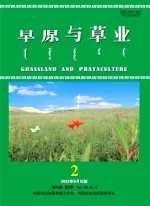我国草原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与未来
辛晓平,张保辉,陈宝瑞,杨桂霞*
(1.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000;2.农业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区划所,北京 100081)
1 我国草原分布及其自然、经济特征
1.1 草原涵义的界定
草原和草地的概念在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和定义。
根据《世界资源报告》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定义,“草地”包括天然放牧地、长久休闲地、五年以上生产草本饲料作物的耕地、疏林地、矮木林、疏灌丛、荒漠、冻原、沿海滩涂、湿地沼泽和草甸。
“草原”在地理学范畴被认为温带和热带干旱区中的一种特定的自然地理景观,在植物学范畴被认为是以多年生旱生草本为主组成的群落类型,在农学范畴,贾慎修(1963)认为“草原是畜牧业的组成部分,具有生产意义,植被表现了直接的、最重要的部分”。任继周院士(1990)认为“草原是以生长草本植物为主,或兼有灌丛或稀疏树木,可为家畜和野生动物提供生存场所的大面积土地。是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粗略的认为,“草原”一词泛指草及其着生的土地构成的综合自然体,包括我国北方的天然草原、南方草山草坡、草甸、沼泽、荒漠、灌丛、冻原等。其涵义包含了草原自然属性、植被类型和利用方式等三大内涵。
草原法第二条第二款中规定,天然草原包括草地、草山和草坡,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地,不包括城镇草地。本文取用此定义。
1.2 我国草原分布及特征
草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分布最广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世界草地总面积32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0%。我国是世界上草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草地面积占世界草地总面积的12.4%,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398万平方公里(可利用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2%,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位。我国草地大部分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和高原寒带地区,气候干旱少雨,土壤沙漠化严重,生态系统非常脆弱,承载能力低。按其所处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可分为北方温带草原、高寒草地、西部荒漠草地、南方草山草坡等四类〔1〕。
北方温带草原分布在北温带半干旱区,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与松辽平原,106.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北方主要牧区之一,从东往西受水分条件限制依次出现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荒漠,以饲养绵羊、肉牛为主;高寒草地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一般海拔四千米以上,面积126.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一类草地,由东南部的高寒草甸向西北逐步演变为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荒漠等草地类型,主要饲养牦牛与藏羊;西部荒漠草地分布于新疆的天山和阿尔泰山、柴达木与阿拉善,以山地草原、荒漠和绿洲为主,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多生细毛羊与骆驼;南方草山草坡分布于东南季风区,总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以次生灌草丛为主,水热条件好,但由于地形破碎、草质低劣,改造利用需要大量投入,开发利用很不充分,具有发展草食畜牧业的巨大潜力〔2,3〕。
2 草原的功能
天然草原是在数百万年到上千万年的进化过程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完整而美妙的生态系统,它不仅是家畜的放牧场,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和生产材料,也是主要的陆地生态屏障,对人类环境和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且不可代替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
草地是覆盖面积最大、更新速度最快、生产力较高的再生性陆地自然资源,占陆地绿色植物总生物量的36-64%,是发展草食家畜和草食动物的主要饲料来源。草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如蒙古、澳大利亚家畜饲料中有50%以上来自草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粮食生产不足,发展以精饲料为主的畜牧业受粮食生产所制约,根据全国草地资源调查研究成果分析和评估,我国草地的生物量每年约为22.29亿吨,进行草地改良后生产力能够进一步提高,是我国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4〕。
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碳汇之一,尤其是草地土壤腐殖质层富含有机碳,是地球陆地北方的重要碳汇。据测算,我国天然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总价值约为8697.7亿元,是其所生产畜产品价值的10余倍。同时草地植被是陆地最大面积的“皮肤”,防风固沙、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作用十分显著,尤其在具有很强荒漠化潜势的半干旱地带、地势陡峭与地球重力作用强烈的山地,草地植被的屏障功能就格外重要,例如草原退化引发的沙尘灾害近年来成为一个跨地区、跨国界的环境问题〔5〕。
草地上拥有非常丰富的生物资源,是许多有价值的大型野生有蹄类食草动物与猛禽类的栖息地,也是大量优良野生牧草、药草、观赏植物与经济植物的家园,可提供发展我国食品、纺织、制革、造纸、制药、化工等轻工业以及对外出口贸易等多种经济的原材料;芦苇、象草、甘蔗等C4植物有望成为新的绿色能源和生物质能材料;许多草原植物具有特殊的抗旱、耐寒、耐盐碱、高光合效率的生态生理特性,对农作物、牧草、饲料和林木的改良和育种具有很高的价值,其特殊基因资源是人类未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珍贵基因宝库。
3 草原利用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2000年TM卫片遥感快查,全国25公顷以上的成片草地为330.01万平方公里,比1980年代中期草地调查时减少26.23万平方公里,减少7.36%,大致相当于全国每年0.5%的草地消失,转化为裸地、沙地或盐碱地。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全国平均单位面积产草量由900公斤/公顷降低到目前的700公斤/公顷左右,其中优质牧草产量仅约380公斤/公顷。在草原退化与气候变化双重影响下,草原地区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沙尘灾害肆虐,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草地生态系统变得非常不稳定〔6-9〕。
草原区域出现的诸多问题,一方面是受到气候变化(增暖、干旱、气候不稳定性等)影响,更重要原因的是长期的超载过牧、不合理利用、粗放管理制度下的过度掠夺等。
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草地畜牧业几乎完全是原始游牧业,完全受制于自然条件。1949年以后,牧业生产水平逐年稳步提高,1980年代初实施草场承包制使草地由集体经营转入牧户分散经营,草地畜牧业短暂经历了“人畜两旺”的美好时期。同时,受人口过快增长、草地无偿使用制度的影响,草地家畜头数大幅度增长,造成草原长期持续的超载放牧。20世纪80年代至2002年,草原牧区人口增加33%,草地承载的牲畜头数增加了46%,畜均占有的可利用草地面积有20年前的30亩减少到21亩。全国120个纯牧业县和146个半农半牧县合计可承养1.5亿羊单位,实际承养了2.3亿羊单位,超载48%。巨大的家畜压力、原始的管理模式导致草原生产严重受损,草原区产肉量占全国产肉量的比例由解放初期的20%左右降低至目前的 5%左右〔10-13〕。
另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满足粮食生产需求,以及农业指导思想的重农轻牧倾向,导致大量开垦草地种粮的现象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全国有近19.30多万平方公里草原被开垦,占目前全国草原总面积的近5%,即全国现有耕地的18.2%源于草原,开垦草地中50%被撂荒成为裸地和沙地。20世纪90初开始,受经济利益驱使,来自非草原区的农民和单位滥挖、滥割、滥搂,屡禁不止,大面积草地植被遭到彻底破坏,仅内蒙古自治区因滥挖甘草、滥搂发菜破坏的草原面积已达1267万公顷,其中400万公顷完全沙化。近年来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公路、铁路、居民点扩建,以及工矿企业发展建设,由于缺乏环保政策约束,只管利用不管保护,也对局部草原造成毁灭性破坏〔14〕。
我国草原生产以资源消耗型放牧畜牧业为主,粗放经营的观念促使人类通过低投入方式不断向天然草原索取廉价粗饲料,在增加了本已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压力的同时,导致人类忽视和放松了加工饲料、畜牧业生产技术的合理改进和升级。在生产能力方面,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通过建立人工草地提高草地生产力,例如新西兰、英国、法国、加拿大草地总面积中的人工草地面积比例高达65.5%、64.5%,31%、20%,而我国不到3%;在管理方面,国外畜牧业已经进入到数字化管理的时代,我国长期以来重技术轻管理,草地畜牧业还基本没有定量管理的概念,没有考虑草、饲、畜的配置,忽视肉、毛、奶的质量管理,现有单项技术没有有效集成和利用,生产效率低下,事倍功半,资源浪费;在产业结构发展方面,我国草地畜牧业过分单一地依赖草地资源的直接产出,忽视了创建生产、加工与市场经营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的甚至循环的产业体系,起于草、止于畜的低附加值生产体系下,草地区域家畜数量在增加,但产值没有以相应的比例增加〔1,5〕。
虽然目前国内大部分专家和官员认识到了草地在生产和生态上的双重重要意义,但是有必要强调在现代生产环境下,正确评估草地作为资源的价值和地位。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看,占41%国土面积的草地没有得到相应的生产建设投入,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也没有被正确评估,而草原生态问题只有在发生沙尘暴等灾害时才偶然被关注一下。仅把草地资源当做生产对象,没有当做资本来看待,只要求其产出而不进行投入,因而对草地的建设和维护力度十分薄弱。
4 主要国家开发利用草原的经验教训与措施
国外草原利用也出现过很多的失误与教训。20世纪30年代美国半干旱草原植被开垦,造成2次横扫美国的2/3领土的黑风暴,使冬小麦减产51亿公斤,刮起了约3亿土表土。原苏联在草原区开荒0.6亿公顷,其中风蚀面积0.45亿公顷,20世纪50年代也引起了黑风的灾难。这些国家草原利用出现问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草原植被〔15-19〕。
许多国家制定了各种保护和管理草原的法律条例,如美国于1936年和1950年先后制定了保护草原和草原改良制度,明确规定根据不同草原的自然状况核定载畜量,租用属于国家的牧场放牧过度政府即将土地收回;英国经常进行草原调查和登记工作,将永久性草原划分类型,分别制定利用和改良方案,国家拨给补助金鼓励和推动草原改良。
世界草原面积多数在干旱地区,许多国家通过改善水利条件提高草原生产力。蒙古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平均每年打机井100多眼,大口井420多眼,使60%以上的放牧草场得到了水源保证;澳大利亚干旱威胁经常给畜牧业带来重大损失,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管理水利的专门机构,负责各地水利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全澳灌溉地中有60%用于牧场,20%用于饲料作物生产。
通过人工清除原有自然植被、播种优良牧草改良草场或建立人工草地,提高天然草原的生产力和家畜承载力。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改良草场为470万公顷,新西兰每年补播改良草场12万公顷,改良草场现已超过800万公顷,天然草场的面积仅余460万公顷。美国西部约有0.25亿公顷天然草场已改良为人工植被。西澳大利亚近30年来已有超过80%的草地引种优良牧草进行改良。人工草地普遍采用产量高、营养成分好、利用期长的栽培牧草,同时投入精细的管理、先进的灌溉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的饲草供给能力,为其草食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5 我国草地利用的几点建议
比较中国与畜牧业发达国家,主要差距在于:一是投入和建设,二是科学管理,三是经营意识〔20-25〕。
自上一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已先后完成了从原始的天然草地放牧到人工饲草地为主支持的现代化畜牧业的转变,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草地畜牧业的生产力,形成先进的产业链与发达的畜牧业经济,而且使天然草地得到充分的恢复和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
而我国到目前为止“靠天养畜”的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为放牧被认为是“投入最少”、“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事实上,所谓“成本最低”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本的损失,超载过牧所造成的草地退化、土地荒漠化具有极其高昂的生态代价,甚至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中国大部分天然草地已经不堪重负,传统的草地畜牧业已经难以持续,草原区环境安全和生态保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980年代以后,农区畜牧业、城郊畜牧业迅速崛起,特别是近十年来集约化、工厂化家畜生产兴起,使畜牧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农区家畜数量逐渐超过了牧区。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国草地畜牧业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有一个大的转型。
首先,我国应该完善草原开发保护相关法律与政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颁布、修订和实施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建立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农业部发布了《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退牧还草工程实施管理的意见》,这些管理办法不同侧面制定了草原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框架。在现有基础上,通过立法和强制性措施,落实草畜平衡、提高出栏率和商品率;通过国家政策性投入,改善草原建设、维护和管理的基础条件和能力,提高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将绿色GDP核算纳入到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并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通过政策性和行政措施,建立草地保护区,保护生态脆弱区域、水源地、珍贵的动植物种质资源分布区草地和重要的景观草地。
其次,建立南北方两个人工草地带,开辟和拓宽饲料渠道,提高全国草地总体生产力,减轻天然草地的压力。北方草甸草原和暖温性灌丛草原是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界限,也是农业区、林业区与纯牧区的过渡地带,气候湿润,河网较密,土壤肥沃,是草原上改造条件最好的地带。美国在相应地带建立了高产的玉米带,澳大利亚建立了人工草地带,对国家畜牧业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我国草甸-灌丛草原带长江以北地区也具备建立人工饲料的条件,实现畜牧业的集约经营,建成我国最大的商品畜基地。南方草山草坡水热条件好,单位生产力高,牧草生长期长,经改造可形成终年不枯的常绿草地带,一般可全年放牧。天然草场亩产量可达500-800kg,改良草场单产提高3-4倍,人工草地提高5-7倍。加之基本无雪灾、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发展畜牧业的风险小,投资回报率高,其有极大的开发潜力。建成人工饲草饲料带,堪与新西兰草地媲美。应像抓三北防护林那样,把南北两片人工草地建设起来,开辟我国草地畜牧业的新局面。
再次,加强天然草地改良与适度利用,尽快提高草原利用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引进优良草种,改良草地质量;引进优良畜种,提高畜产转化率;利用生态经济、空间信息技术方法,定量监测与评价草原生态经济效益与状况;发展因地制宜的草地-畜牧业系统管理模式,注意区域农业生产的最佳组合和整体效益,如旱作农业区粮草轮作,实行农牧互补、种养结合和林木结合;半干旱草原适于放牧,但要严格控制载畜量,实行季节畜牧业;南方低海拔次生草坡须林、果、农、草综合发展,不宜于单搞牧业;在气候适宜地区,开辟牧草良种繁育基地。
最后,促进草地畜牧业和饲料业的产业化,建立现代化草食畜牧业产业体系。通过调整畜牧业结构,发展强大的饲料业和舍饲畜牧业,扩大饲养能力。结合牧区、农区、城郊草地牧业,建成一体化的草地畜牧业系统。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加强政府对草畜业产业体系的宏观调控;扶强龙头,壮大基地,大力推行产业化经营。
〔1〕曹晔,杨玉东.论中国草地资源的现状,原因与持续利用对策〔J〕.草业科学,1999,16(4):1-6.
〔2〕张新时,李博,史培军.南方草地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1998,13(1):1-7.
〔3〕姜恕.中国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草地学报,1997,5(2):73-79.
〔4〕谢高地,张钇锂,鲁春霞,郑度,成升魁.中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J〕.自然资源学报,2001,(01).
〔5〕周旭英,罗其友,姜文来.中国草原资源综合生产能力研究〔J〕.2006中国草业发展论坛论文集,2006.
〔6〕李博.中国北方草地退化及其防治对策〔J〕.中国农业科学,1997,30(6):1-9.
〔7〕苏大学,我国草地资源快速消失与保护对策,中国草学会第六届二次会议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章力建.关于加强我国草原资源保护的思考〔J〕.中国草地学报,2009(11).
〔9〕吴精华.中国草原退化的分析及其防治对策〔J〕.生态经济,1995(5):1-6.
〔10〕王庆锁,李梦先,李春和.我国草地退化及治理对策〔J〕.中国农业气象,2004,25(3):41-44.
〔11〕谢双红.北方牧区草畜平衡与草原管理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5.
〔12〕杨理,杨持.草地资源退化与生态系统管理〔J〕.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5(2):205-208.
〔13〕于秀波.我国生态退化,生态恢复及政策保障研究〔J〕. 资源科学,2002,24(1):72-76.
〔14〕樊江文,钟华平,员旭疆.50年来我国草地开垦状况及其生态影响〔J〕.中国草地,2002,(05).
〔15〕刘政.国外草原开发利用的措施和政策〔J〕.世界农业,1992,10:38-42.
〔16〕苏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草地及管理,草原与草坪,1987,5:5-8.
〔17〕缪建明,李维薇.美国草地资源管理与借鉴〔J〕.草业科学,2006,2:5-8.
〔18〕李志强.美国草地资源合理利用与信息化管理的启示〔J〕.中国畜牧业,2012(21):56-59.
〔19〕陈洁.典型国家的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经验〔J〕.世界农业,2007(005):48-51.
〔20〕修长柏.试论牧区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2,7:31235.
〔21〕王利民,姜怀志,姚纪元,等.我国北方草地的现状和可持续发展对策〔J〕. 家畜生态,2004,25(2):4-7.
〔22〕姚春玲,刘瑞萍.内蒙古草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7,2:009.
〔23〕任继周.现代草业科学进展〔J〕.草业科学(增刊)国际草业发展大会论文集,2002.
〔24〕曹晔,王钟建.中国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9(7):19-22.
〔25〕张连义.对草地的科学开发与利用的几点想法〔J〕.科学管理研究,1999,17(4):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