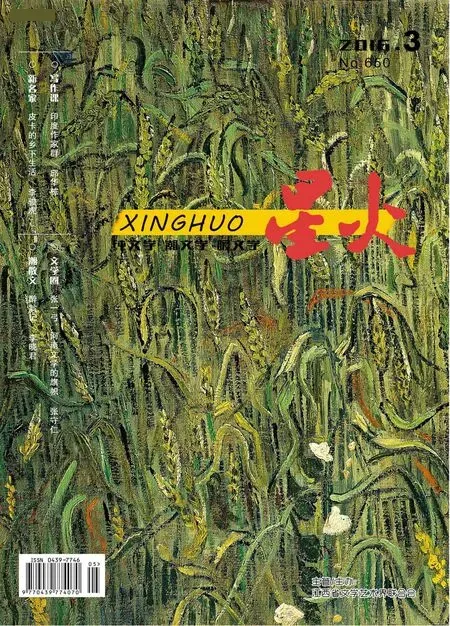在渣山
□许 侃
一
小莫看见妹妹从草窠里走出来的样子,就知道出事了。
黑暗正在四处逃散,晨风像小偷似的掠过薄薄的衣衫。妹妹拨开齐腰深的茅草,走到小莫面前来。这时太阳还没冒头,那一道长堤状的渣山还是青黝黝的。这边坡上,茅草已能辨清一支支茎叶,只是还没有镀上颜色。坡上有一座裸砖的旧库房,房头有一株阔叶无花果树。房后是大片茅草地,一直蔓延到西边灰色的围墙下。
小莫并没有想到妹妹会从茅草地里钻出来。他惊讶地看见妹妹拨开茅草,从那灰蛇般的围墙边上朝小路这边游走。天色微明,妹妹的眉眼已能看清,只是颜色未显。小莫看见妹妹走路的姿势有些特别,双腿不敢并拢,像踩高跷那样往外撇着,与平常迥然不一样了。小莫突然意识到什么,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惊慌,嗓子眼好像要冒出烟来,而这烟瞬间变成魔鬼。
“小娜。”小莫叫了一声。
小娜的头发并未见得零乱,而是被汗水濡湿了,很顺服地贴在头皮上,刘海抹得光光的,有些刻意了。小娜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形象,这么刻意把自己收拾整齐,让小莫感觉奇怪。小娜看见哥哥小莫,眼睛里闪过委屈、羞愧和慌乱,她像吞咽口水那样把眼眶里冒上来的泪水憋了回去,变成头上更多的汗下来了。
“你怎么会在草窠里?”小莫问。
小娜的喉头向上提了一下,说:“我把王八铁藏起来了。”她回头指了一下茅草深处,又说,“你把它驮起走吧。”
小莫趟开半人深的茅草,三步并作两步窜到那堵围墙前,果然在一片被压倒的茅草间看见一条熟悉的王八铁。王八铁三块一条,像巧克力那样连着,每块鼓起一个王八壳似的脊背,故名王八铁。小莫打量了一下那片被压倒的茅草,正好是一个大人躺下的长度。他想问问妹妹这是怎么回事,小娜已经走出茅草地,独自沿着那条灰白的小径往前走了。
小莫解开腰间的布带,把王八铁拴在后腰上,又用宽大得耷到膝弯处的工作服盖好,抬起脚来去追小娜。从背后看,小娜走路的姿势更不对了。小莫从没有见过小娜走路的样子这么难看。小莫脚下一紧,挨近小娜,压低声音问:“瘸子把你怎么样啦?”
“没怎么样。”小娜说,她低着头往前走,小莫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平淡空洞,力图掩饰什么,却掩不住喉头有点堵。
“我以为他要把你交到经警值班室去咧。”小莫说。
“去了不是又得罚钱呀。”小娜瘦弱的肩头缩了一下,两只手像小耗子洗脸那样举到脸上去了。小莫揣测她是不是哭了。
一个小时前,他俩在厂区偷了王八铁经过此地,被一个值夜班的工人发现了。工人是个瘸子,追不上小莫,却把小娜逮住了。小莫跑到棚户区放下赃物,回头来找妹妹,这才发现天已经亮了。
现在,他们要回到棚户区去,必须越过长堤般的渣山。渣山上铺着铁轨,人们又叫它渣线。兄妹俩相跟着爬上一个陡坎,踩得路基石块哗哗地往下淌。上了渣山铁道线,兄妹俩看见东方一抹鱼肚白浮在烟灰色的地平线上渐渐泛红,突然被冒出头来的一轮旭日撕裂了,刚才还是青白色的天幕迅速地渗出血来,再看周围景物,一下子全都焕发了颜色。最突出的是渣线值班房顶上那面旗,不知什么时候完全变红了,红得不能再红,像浸了血似的,无精打采地耷拉着。
“瘸子这回怎么开恩……?”小莫还是绕不开那个疑团。
“别问啦!”小娜忽然大喊一声,在前面跑开了。
她一跑,小莫就在她的裤裆里瞥见一抹非同寻常的深红,像太阳从云缝里迸射出来一样,刺得小莫眼睛发花。豆大的泪珠一下子从心底里冒出来,好像涌泉跃出水面,令小莫两眼发花什么都看不见了。
二
渣山是钢厂倾倒炉渣的地方。从钢厂开出的小火车牵引着盛满废渣的渣罐沿铁道开上渣山,把废渣倾倒在铁道两侧。渣罐形似两三米深的大锅,架在槽车上,旁边有齿轮令其倾翻。日久天长,倒出的钢渣形成一条带状的凸起,好像伸进海里的长堤一般。
长堤的尽头蹲着一节报废的客车箱,永恒地固定在铁轨上。它是渣线工人值班休息的场所。客车箱经过改造,非常像一座房子,门开在直头,焊了一个宽敞而又平缓的铁梯子供人上下,情形有点像影剧院门前的阶梯一样了。车厢内的情景可以想象一下美国西部影片中的拓荒者要塞的样子。值班工人大概也是这样想的,跟西部片经常见到的情景一样,他们在车厢顶上竖了一面旗。
落日的余晖格外红亮,把渣山镀上了一层金色。值班车厢像一幅风景画的焦点,以黑色剪影方式突出自身存在。一个人走出车厢,在阶梯的顶端做了一个扩胸运动,这个人胸肌发达面露凶相以示强悍,脚下却不争气,走出时上身幅度很大地往前一栽,让人看出他是个瘸子。瘸子应老拐三十多岁就已经秃顶,为了掩饰头发稀疏,干脆理了个光头。此时他刚把头伸在水龙头下冲过凉,站直了身体手往后一抹,把水沫子撸得乱飞。忽然,应老拐的目光定住了,好像一只豹子发现了猎物。在前方,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正在玩弄他操作的机械设备。
如果说渣线上只有一个值班车厢突兀于天幕背景下,那是不对的。除了车厢之外还有一座可以移动的铁架子,中间吊着一只笆斗大的圆铁坨子。因为它是以线条形式呈现的,便不如值班车厢更占体积更抢眼。此时,小莫爬在这个铁架子上面,像一只猴子那样好奇地打量那个硕大的圆铁坨子,心里想,那么细的钢丝绳牵着它,怎么就不断裂呢?瞧它被拽得高高的,蓄满向前冲下来的势能,仅仅是因为有一根钢丝绳牵着,就像一只被吊死的野狗那样乖乖地停在半空中。它要是掉下来该多好呀,它为什么不掉下来?为什么不掉呢?
“喂,你,干什么的?”应老拐站在值班车厢前怒气冲冲地说。
小莫轻蔑地抬眼一看,并不怕他:老子又没有偷废铁,怕他个卵!
应老拐看见威胁没有奏效,一拐一拐地亲自走过来了。走到近前,他感觉曾经在哪儿见过这个黑巴干瘦满身污渍的小子。
“是你呀,小兔崽子……”应老拐说,口气缓和下来,因为他记起曾经向这小子勒索过香烟。
小莫横了应老拐一眼,嗓子一吸,一口浓痰含在嘴里,准备射到应老拐的脸上。这是事先计划好的,可是事到临头,小莫有片刻犹豫。
“小兔崽子,身上可揣着好烟?”应老拐的脸上绽开笑容。
应老拐这一笑实属意外,令小莫惊慌起来。小莫没有想到瘸子还会笑,这太奇怪了,他那满脸的横肉在小莫眼里都笑得抖了起来。小莫的那口浓痰一时失去了方向,他含混地说:“没有。”
“没有。你下来,抽我的。”应老拐难得高兴地说。
从小莫的方向看去,应老拐正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小莫的心头忽然哆嗦了一下,好像一道闪电裂过乌云翻滚的天空。他脖子一伸,将那口浓痰悄悄地咽了回去。小莫跳下架子来,说:“抽就抽。”
“抽老子一根,下回还一包!”应老拐露出流氓本色。
一个月前,应老拐值夜班曾经逮住过偷铁的小莫。小莫掏出一包红塔山香烟来,应老拐的态度就缓和了,他同意不把小莫送到经警队。但是一包香烟太便宜了,他在小莫身上搜身,最后内行地让小莫脱下鞋子,从鞋垫下搜出皱皱巴巴的十块钱来,应老拐并不嫌臭,拿上那包烟和十块钱,就把小莫连同偷盗的废铁一同放了。小莫失去了香烟和钱,最终没能把废铁带回棚户区,因为十块钱是为下一个捉住他的人准备的,没有了钱,当他又被人追赶时,小莫只好扔下废铁逃命了。
“你怎么就抽龙泉啊。”小莫下了铁架子,凑着应老拐的打火机点了火,吐出一口烟,装着老练的样子说。
“他妈逼的小工人一个,不抽龙泉抽啥。”应老拐骂道。
“这么说,你这几晚上没有好好逮人嘛。”小莫说。
应老拐笑道:“你小子门坎蛮精的嘛,知道逮了铁耗子就有阿诗玛、红塔山抽。”
“这谁不知道。我自己就送过你……”小莫说着话,怕应老拐看出他心中的愤怒,脸扭着不敢正面相向。
“前几天逮了一个小铁耗子,女的。嘿嘿嘿……”应老拐淫荡地干笑几声,下面的话突然收住了。
小莫的拳头在袖管里攥得铁紧,若不是应老拐及时打住的话,他无论如何也管束不住自己,就要跳起来一拳砸在他的脸上。这是在心里预谋策划了无数遍的事。但是刚才,他从铁架子上跳下来前的一瞬间,他忽然有了别的主意。为了实现这个主意,他要把自己的愤怒藏好。
“你要是下回给我一整条阿诗玛,以后我看见你偷铁就当没看见。”应老拐说。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小莫说,做出巴结的样子,“我只能买得起一包。”
“一包就一包,你要带来啊。”应老拐威胁地在小莫的头上抹了一把。
“那我要看看你怎么打渣锅,让我跟着你干活玩儿。”小莫提出了条件。
“这有什么好看的。”应老拐不介意地说,“我马上下班了。要看下回带着香烟来看吧。”
“那好。”小莫点头同意,怀揣着一个梦想走了。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好像一下子长高了许多,有点像一个凝结着心思的老头了。
三
小莫这条命,是靠那笆斗大的圆铁坨子砸出的哐哐声唤回来的。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冬夜,小莫独自来到钢城找寻在此地打工的叔叔。叔叔找不到,晚上没处栖身,小莫四处游荡,又饥又累,走到渣山脚下,发现这里的钢渣坨子暖哄哄的,就在几个渣坨子之间坐下来休息。身上一暖和,小莫睡着了。那年小莫才十二三岁,并不知道这些钢渣坨子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散发出让人愉快的温暖。睡到半夜,小莫突然听见头上传来哐哐的撞击声,声音大到几乎震破耳膜。小莫抬头一看,渣线顶端出现了一只血盆大口,正滴滴拉拉地往下淌着红色的哈拉子,大口中央被封闭了,半冷凝的炉渣青红相间,正隐隐地透着凶险。有一粒蹦溅的火星子飞进了小莫的脖颈,烫得小莫一下子蹦了起来,再也顾不得发呆,一个箭步向前窜去。
小莫的窜出把渣线上操作的工人吓了一大跳,他完全没有想到渣山下还有人躲在那里睡觉。当盛满钢渣的大锅倾倒后,因为渣锅表面已经冷却,钢渣倒不出来,工人正开机提起沉重的圆铁坨子去砸渣锅的底部。忽然看见一个小鬼模样的人影从死亡的红光中奔出来,让他惊骇地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花了。随着又一声圆铁坨子撞击锅底的巨响,凝结的红渣轰然倒塌,一只红钢坨伴着如雨的渣液,像一只怪兽从山顶上滚下来,一直滚到小莫的脚下,仅有数步之遥。灼烈的热幅射立即烤得小莫脸上发烧,却一滴汗也没有。
真是千钧一发,若不是打渣锅的声音唤醒了小莫,迟上半步,小莫必死无疑。事后想来,也是小莫命大。一般来说,渣锅并不是每次都凝结,需用大铁坨来砸的。如果耽搁得时间不长,钢渣还呈液态,渣锅一倾,兜头而下,顷刻之间小莫就葬身火海,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是渣锅表面的冷凝救了他,是咚咚的大铁坨撞击锅底的声音救了他。小莫对那个吊着圆铁坨子的龙门架有感情是很自然的,小莫对那个圆铁坨子有感情更是无保留的。
小莫没有找到自己的叔叔,却在钢城留了下来。因为经过一次死里逃生,小莫觉得这是自己的福地。俗话怎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莫虽然只读过小学,但是这句话还知道的。当然,光有这句话小莫也留不下来,关键是小莫在渣山后面的那片棚户区找到了落脚的地方。这里汇聚了外地来的各种各样的吃钢铁饭的人,三教九流都有。有的人你别看他穿得像土鳖,赌起钱来钞票多得吓人一跟头。当然,绝大多数还是穷人,是穷得叮当响的以偷废铁为生的人,俗称“铁耗子”。
小莫当了一名铁耗子。春节回老家才知道,叔叔转到别的城市打工去了。母亲让叔叔再出门时带上小莫,免得小莫跟母亲吵了架,一个人瞎跑。小莫不跟叔叔走,他铁了心还要回到钢城去。就这样,小莫在钢城扎下根来。过了一年,母亲改嫁。小莫再回去发现妹妹在别人家里日子过得凄惶,甚至连母亲也嫌恶妹妹。小莫索性把妹妹小娜带到钢城来了,兄妹俩在棚户区租了一间八平米的小屋,日子过得竟然像河水流淌那么无喜亦无忧。
小娜十三岁了,是个知道好歹的女孩,对哥哥知疼知热的。不仅给哥哥做饭,还帮着哥哥“做生活”。十三岁的小娜能做什么生活呢?无非是跟着哥哥一道去偷铁。自从小娜来了,小莫就感到肩上多了一份责任。他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送小娜去读书什么的,他知道那只是电影里的故事而已,而他要做的就是把小娜好好地带大,看到好人就帮她寻一个自己的家。他记得父亲临死前摸着他的头说,你是小子我不担心,我就是担心你妹……
应老拐打破了小莫的梦想。虽然小娜什么也没有对哥哥说,但是小莫知道那件事肯定发生了。小莫对男女之事并不太懂,他从大人们冬令时节的闲聊中得知,一个人要是娶媳妇,新婚之夜是要试红的。在乡下发生过许许多多新婚之夜试红的惨烈故事,在这一关上出丑的新媳妇下半辈子就算掉进火坑了。小莫不停地想,既然那天妹妹的裤子已经红了,今后还怎么试红呢?这件事压在小莫的心上,像一页磨盘重。
小莫后悔当时只顾了自己跑,没有留下来断后。
四
小莫拿着一包“阿诗玛”走进值班车厢的时候,应老拐正擎着一张报纸,双腿架在桌子上读报。应老拐既不是装积极,也不是爱学习,他是关心报上的一则社会新闻。
新闻说钢厂揪出了一个大蛀虫。这蛀虫是个多大的官呢?屁大的官都不是,只是小工人一个。小工人凭什么贪污腐败呢?原来他是管合金的,监守自盗,每天把厂里的贵重合金用饭盒子盛了,带出厂去私卖。据说用这个方法发了横财。应老拐看到这里愤愤不平,倒不是因为有正义感,而是觉得自己亏了。他喃喃自语道:领导拿年薪,工人偷合金。他妈的!老子既拿不到年薪,也偷不到合金……
正想到这里,小莫进来了。应老拐忽然产生了一点幽默感,心里说,来得正好,看来老子只有逮逮铁耗子,从他们身上榨点油水了。
小莫对应老拐很巴结,递上香烟的同时说:“外面来车了,又送来几大锅钢渣。”
应老拐笑骂道:“那叫钢渣罐,还几大锅!你当是你妈在家煮稀饭哪。”
“是,是钢渣罐。”小莫点头道,“咱们去倒钢渣罐吧。”
“急什么!你小子比我都积极似的。”应老拐说着,拆开小莫的香烟,叼上一支,乜斜着眼睛说,“你小子也来一支?”
小莫说:“我还是算了吧。”
应老拐就不客气地把那包“阿诗玛”装进衣兜,带着小莫到出渣现场去了。
“你小子!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呢。”应老拐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
“小莫。”小莫心想,我行不改姓坐不更名。
“家里都有什么人啦?”应老拐又问,跨过一根废枕木。
小莫差点被那根枕木绊了一跤。他想,这个可不能跟他说实话,如果暴露出他有一个妹妹,说不定就会引起应老拐的怀疑。小莫说:“就我一个。来找叔叔,叔叔没找到。”
“哦,老家是哪儿的?”应老拐有点聊天的意思了。
“北边的。”小莫含混地答道。
听见这话,应老拐心里有一根敏感的弦莫名其妙地震颤了一下,仿佛嗅见异味的猎狗,伸长鼻子立定,露出一丝警觉的神情。小莫的口音让他想起一个人,谁呢?一时间应老拐想不起来,或者说不愿想起来,下意识地屏蔽掉了。无论应老拐品性多么差,罪恶感还是有的。那件事干过了,就一风吹了,他不愿老是去想。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他想起来,他宁愿装出一副记不起来的痴相。
牵引机车送来渣罐,脱卸挂钩就开走了。一溜三只大锅状的钢渣罐架在槽车上,边上有齿轮可以把它们倾倒过来。小莫饶有兴致地观看应老拐作业。钢渣坨倒不出来,应老拐就摁着电板,把另一股道上的打渣锤开过来,那个吊在半空中的笆斗大小的圆铁坨子就哐当哐当地砸钢渣罐底,直到把半凝结的钢渣坨子打掉下来。
这一次作业非常完美,不到十分钟,倾倒钢渣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老拐瘸着腿一拐一拐地往值班车厢走去。小莫跟着他,在后面用阴暗的眼神打量他。应老拐身材高大结实,小莫瘦小灵活,两人厮跟着,好像一只大蝎子拖着一根带毒戟的尾巴。小莫就是那根毒戟,他那阴歹歹的眼神不是一个十五六岁孩子应有的。
天空乌云密布,就像小莫脑海里翻滚着的粘稠的沥青状泡沫。
五
时间一晃过去小半年。小莫跟应老拐已经混得很熟了,都可以代替应老拐操作打渣锅作业了。
这期间,应老拐曾经提出到小莫的住地去看看。小莫说我们棚户区近来闹鬼,都说鬼是一个没有头的瘸子,半夜三更在人家的房沿上一拐一拐地走。你去了不要被人当做鬼暴打一顿。应老拐忽然想起自已造的孽,就再也不提到小莫住的棚户区去了。
这期间,小莫经常从那个吊着笆斗大圆铁坨的铁架子下面走过。每次走过,总是在心里试想吊着它的钢丝绳突然断裂,大铁坨子打在头上会是什么感觉。也许一下子就飞出去了吧,像一只鸟儿一样嗖地一声,就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呢?要是像鸟儿一样不见踪影就好了,可是八成还会剩下一个身子,就跟僵尸似的留在人间。
这期间,小娜还是每天洗衣做饭,只是再也不去偷废铁了。哥哥小莫不让她去,她自己也不想去了。她跟哥哥之间过去无话不谈,现在彼此的眼睛都躲避着,绝少相碰。同在一个屋檐底下,两人的眼光要不接触还是挺难的,这样的日子不好过。小娜也想过跟哥哥把那事说出来,可是说出来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叫哥哥为难!
小莫有时会心血来潮,买一大堆好吃的回来,让妹妹小娜做。搁在过去,小娜一定会说:“买这么多做甚,明天不过啦!”可是现在小娜一言不发,只是做,买多少做多少,好像吃过这顿就再也没有下顿一样。兄妹俩吃着饭,一声不吭,过去有说有笑的情景再也不见了。吃完饭,小莫说:“娜娜,拿人家的手短。哥有一天不在了,你记着——咱不拿人家的,咱就谁的欺负也不受!”
小娜转身伏在自己的小床上,呜呜地哭了半天。她知道哥哥说的“欺负”是什么意思,但她想不通哥哥为什么要说 “有一天不在了”,“不在了”上哪儿去呢?你上哪儿去妹妹也要跟着啊!
小莫已经等了很久,他盼望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就在他几乎失去耐心,打算另想办法的时候,一连三天大雨,让机会意外地降临了。
那天又是应老拐值班,小莫穿着雨衣到渣山上去了。他打算实在不凑巧就找个简单办法,把应老拐做掉算了。小莫穿了一件胶布长雨衣,套上帽兜连身形都别想看清楚。他的袖管里藏了一支铁路工人检查道轨用的尖榔头,他曾用它砸通了好几个钢渣坨。
小莫来到渣山上,看见应老拐正在烦躁地对付那个吊起铁坨子的设备。因为是露天装置,雨天使什么地方生锈了,一向自由升降的铁坨子卡住了,既不能升又不能降。应老拐恶狠狠地咒骂天气,说小莫来的正好,你猴儿似的,爬上去看看什么地方卡住了?
小莫听话地爬到了架子上,并且很快找到了卡壳的地方,经过简单的处理,大铁坨子又顺利地升降了。小莫并没有马上下来,而是指挥应老拐再试一次,将铁坨子吊了起来,然后对应老拐说,你看铁坨子是不是吊得有点歪啊?
应老拐控制着电门说,不歪。小莫说,你过来看看嘛,吊吊线看歪不歪。铁坨子的控制按钮在应老拐手里掌握着,他想放,一按机关,铁坨子脱了挂钩就砸下来了。他见小莫坚持,以为他在上面看得准一些,就移了两步,站在正中央说,我说不歪嘛,就你罗嗦。
话音未落,那个笆斗大的铁坨子像一只复仇的猛兽,呼地一下扑面而来,应老拐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下,就被砸飞了。原来,由机械操作的当然也可以由手动操作,电门控制着的那个机关就在小莫的手边上。
应老拐残余的意识闪回到一片茂密的茅草地里。他看见那个细嫩的黑妹子挣扎着,反抗着,如一尾咬钩的小鱼儿挣脱不掉那样。应老拐凶狠地说:“你不听话就把你送到经警队去,罚款,还要关你的禁闭。”最后她服贴了,顺从了,牙齿咬着他的膀子说:“疼,疼,大爷你轻点,大爷,你轻点……”唔,对了,她也是北边的口音,与小莫的口音一模活脱。
应老拐恍然大悟:这个小莫与那个黑妹子是一对兄妹。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来不及了,人生的大幕已经拉上。应老拐最后的意识停留在那个口音上,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