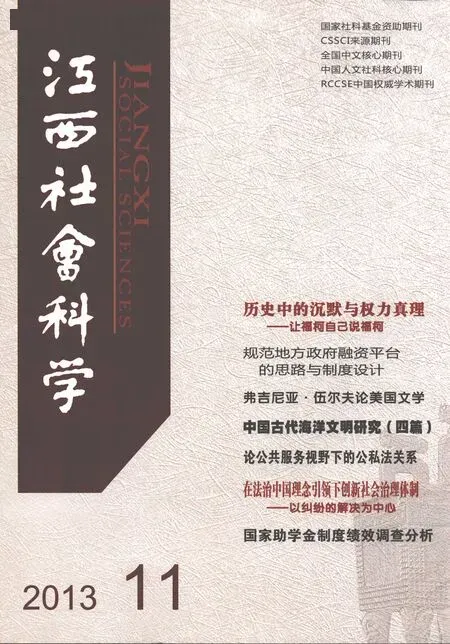海防地理视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内迁
王日根 黄友泉
海防地理视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内迁
王日根 黄友泉
明代水寨内迁是古代海防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明清以来,水寨内迁举措遭到了广泛的非议,甚至被视为明代海防衰弱的主要标志,这种简单的推论不仅没能发现水寨内迁的真正原因,更无法揭示水寨内迁背后的海防寓意。透过海防地理视角考察明初福建水寨选址问题,并通过烽火门水寨内迁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到,明初海防经略者忽视海防地理对军事驻防的制约,错误地将水寨设置于战线前沿、易攻难守的小岛之上,导致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处于无法自存、防御不足、易遭突袭的险境,其后水寨的内迁是对明初水寨选址不当的修正,值得肯定,而水寨内迁所反映出的明代在军港选址与岛屿驻防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与总结。
海防地理;军港选址;海岛防御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友泉,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福建厦门 361005)
明清史料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明代海防建设的信息,这其中不乏准确揭示海防规律的经验总结,但是也存在着大量人云亦云的偏颇观点。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在于当时“谈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①在形形色色的讨论者中,不少人并未实身涉海,而是以陆地经验畅谈海事,难免“水土不服”,观点偏颇。然而,在陆地思维浓重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观点往往更易引发读者共鸣,而被反复引述和转载,明代福建水寨内迁的探讨便是其中典型的个案。近年来,海防地理学被引入海防史研究之中,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研究海岸、海岛、海洋等地理环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为海防建设、军事驻防、海军作战提供依据与指导的专门学科,海防地理学的引入不仅拓展了海防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我们辨析海防史料,纠正认识上的偏差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本文即从海防地理的视角出发,着重从海防地理对军事驻防的影响,重新审视明代颇具争议的福建水寨内迁问题,力求揭示明代福建水寨内迁的真正动因,总结明代在军港选址与岛屿驻防上的得失。
一、明初福建水寨的选址问题
明初,为贯彻“倭从海上来则海上御之”的思想,以期达到“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1](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P3754)的目的,明朝统治者在沿海建置水寨,作为战区水军母港及其指挥枢纽。明代水寨在海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尤以福建水寨最为时人所推崇,“闽之五水门寨尤硕画”[2](卷五十七《沿海御寇要地》,P508)。其建置情况参见表1。
明代福建水寨中烽火门、南日、浯屿水寨最初轫建于海岛,而井尾澳和小埕水寨则设立于陆上。明初水寨选址十分重视其宏观战略环境,表现如下:

表1 明代福建五水寨设立情况表
首先,福建水寨守卫着海上要冲,起着陆地藩篱的作用。如,浯屿水寨一直被认为是漳泉两郡的海上门户,“盖其地突起海中,为同安、漳州接壤要区,而隔峙于大小嶝,大小担,烈屿之间,最称险要”[3](P40)。而南日水寨则被视为闽省中部的海上屏障,“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冲,南可以阻湄洲、岱衴之阨,亦要区也”。同样,铜山水寨被视为闽南海上锁钥,“北自金石以接浯屿,南自梅岭以达广东,险阨所系匪浅浅也”。[4](卷四《福建事宜》,P277)
其次,福建水寨扼守海上交通要道,发挥着控制海道的职能。如,浯屿水寨控制着闽南海上的交通要道,“大小担之间门狭而浅,惟浯屿与小担其间洋阔而水深,商船出入恒必由之……而江、浙、台、粤之船,皆可绕屿而入厦港”[5](P118)。同样,烽火门水寨控制着闽东战略要地烽火门水道,明清之际,该水道一直是进出闽浙的主航道,“由烽火门过大小仑山、秦屿、水澳,至南镇、沙埕,直抵南、北二关,闽浙交界”[6](卷一《建置沿革·水道》,P24)。而南日水寨则控制着南日水道,该水道亦为闽海中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
最后,福建水寨据守着江河的出海口,起着防范敌寇溯流内侵的作用。如,小埕水寨控制着闽江的出海口,由此溯江而上可直逼会城,小埕水寨的设置即为守护会城的海上门户。“(小埕)北连界于烽火,南接壤于南日,连江为福郡之门户,而小埕为连江之藩翰也。”[4](卷四《福建事宜》,P277)又如,浯屿水寨位于九龙江出海口的南端,控制着九龙江的出海口,“外有以控大、小岨屿之险,内可以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4](卷四《福建事宜》,P275)。
明初对水寨选址宏观环境的偏重,很大程度上是受陆上关隘镇戍经验的影响,这使得明初海防经略者无视海陆驻防的重大差异,忽略海防地理对军事驻防的制约,导致明初水寨出现了选址不当的问题。例如,明初设立于陆上的井尾澳水寨即存在着通航条件恶劣的问题。井尾澳位于漳浦县井尾半岛,该地处于鸿江的出海口,为江海交汇之所,确系防海要地。“(井尾澳)在青山北,南距鸿江四十里,可泊船百余,内通白石、赤湖、佛昙桥,萑苻所出没。”[7](卷四,P1046)然而,此地恶劣的通航条件决定其不宜建置水寨。对此,清初曾实地踏勘的工部尚书杜臻就指出:“(井尾)澳口多礁,巡船避之,非潮至八、九分不可入……惟浅船可入,又不利南风,夏至后,巡船辄弃井尾去。”[7](卷四,P1046)可见,井尾澳口水浅礁多,战船需待潮进出,由此制约了战船的机动。而每年夏至后,在强劲的西南风季风作用下,战船触礁的风险大为增加,迫使战船不得不改泊他处,水寨战船的四散停泊导致水寨呈现出“星散势弱”的状态。可见,明初忽视海防地理对军事驻防的制约作用,导致水寨出现选址不当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明初设立于海岛的水寨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且与岛屿驻防问题搅和在了一起,显得更加复杂。
明清海防实践中,人们即已发现海岛地理环境对军事驻防的制约,并总结出不同类型海岛在防御方式上的“守”、“哨”之别。如,清代著名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就说:“海中岛屿,东南错列以百十计,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8](卷九十五《福建一》,P4377)那些适宜“守”的海岛往往是岛幅面积大,开发条件好,适宜大规模驻军,且具备优良港口的大型海岛。对此,《海防志》即以金、厦二岛为例指出,“闽地之濒海者虽多,而金、厦为最著,盖其间有平原广陆,可以牧马、屯兵,有曲港深洲,可以围舟结砦,有豪门巨贾,可以助饷资粮”[9](卷四十二《旧志小引·乾隆丁亥志小引》,P6)。相反,小型海岛因不具备上述条件,在防御上不能“守”而仅能“哨”。而明初恰恰将水寨设置在这些不宜“守”的小岛上,这不仅给水寨的驻防带来困难,更是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危,表现如下:
首先,保障困难,难以固守。
明初福建水寨驻防的海岛均为基岩小岛,多红壤土,水源缺乏,不适垦殖。[10](P245)即便是岛幅较大、条件稍好的南日岛亦被认为是“土质硗确,耕田稀少”。这使得明初水寨驻军补给依赖海运,战时后勤无法保障。对此,倭乱期间,曾为名将戚继光幕僚的福清人林章就指出:“航海远戍,兵食有弗继之忧。”[11](P679)而后勤保障的困境极易转化为海岛攻防上的劣势,如,杜臻在总结清、郑反复争夺福建海岛时就称:“盖以四面阻水,运道易绝,而贼驾舟薄城则甚便。”[7](卷四,P1048)而强行驻防此类岛屿存在着不攻自破的风险,对此,被誉为“筹台宗匠”的蓝鼎元即以澎湖为例指出,“澎湖不过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长树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捍御,形势不足依据,一草一木需台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则不待战自毙矣”②。对于此类海岛驻防的险境,我们不妨举个战例。嘉靖二十七年(1548),双屿为明军攻灭后,葡萄牙人移驻明初曾设水寨的福建浯屿岛,明军随即对该岛进行了封锁,“以致葡人既得不到货物,又得不到粮食”。饥饿的葡萄牙人被迫登陆觅食,“一支舰队焚毁了他们的船只,500多名葡人,仅有30余人得以逃脱”[12](P77)。由于粮道断绝,葡人无法在岛上立足,最终主动放弃了浯屿。可见,小型海岛在军事驻防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决定了其在战时难以固守,所谓“弗能自保,乌能保人”?明初在这些小岛上创设水寨,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其次,防御不足,难以应援。
海岛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军事驻防上呈现出相对孤立的特点。而明代的水寨既是战区水军的母港,又是其指挥枢纽,本身就是重要的战略目标,有着相对较高的防护要求,这决定了强化岛屿防御与完善应援机制的重要性。如上所述,明初水寨驻防的小岛并不具备长期大规模驻军的条件,而强行大规模驻军又潜藏着很大的风险,这也就是顾祖禹所说的“可哨而不可守”的道理所在。自身防御的不足使得海岛应援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然而海岛应援并非易事。我们知道,海岛应援需要经历跨海登陆的过程,在帆船时代要受到风向、潮汐等因素的制约,这与陆上应援完全是两回事。“舟行全藉天风与潮,人力能几,风顺而重则不问潮候逆顺,皆可行,若风轻而潮逆,甚艰。”[2](卷五十《海中泊舟》,P208)正因为海岛难以应援,所以尽管明初水寨与大陆的绝对距离并不远,明人却仍以“孤远”称之。对此,林章就说过:“海洋浩渺,观望易生,卒遇警报,果能联络相卫欤?”[11](P679)而实际上,明初并不重视海岛应援,表现在水寨设立之后,卫所战船便渐次消乏。明初,每“十百户所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及置水寨,前船改移、存殁,今不能复矣”③。卫所战船的消乏便意味着水寨无法获得有效的应援,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水寨的防御形势。可见,明初水寨自身无法构筑足够的防御,又难以建立有效的应援机制,这些弊端的存在与明初水寨选址不当有直接的关系。
再次,目标暴露,易遭突袭。
为达到由海上屏障陆地的目的,明初水寨被设立于战线最前沿的小岛上,由此不仅带来了保障困难、防御不足的问题,更使得明初水寨目标暴露,易遭海上突袭。我们知道,帆船时代,风潮是影响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海战)至要莫如辨风色潮期,取上风上潮以战,失此虽十万不能以敌千余”[13](《闽中兵食议》,P425)。而明初水寨突出前沿,目标暴露,极易在风潮上处于劣势,面对海上突袭,“会有孤危掩袭之失”[3](《议水寨不宜移入厦门》,P40)。同时,古代预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瞭望,受气象条件的影响甚大,加之水寨突出前沿,缺乏必要的预警和防御缓冲,由此增加了水寨遭受突袭的风险。对此,明代著名军事学家王在晋即指出:“倘乘昏雾,假风涛之顺,袭至……岂能御之?”[14](卷一《浙江事宜》,P673)此外,明代水寨特殊的驻防体制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形势,明初水寨采用特殊的人船分离体制,水寨有船无兵,卫所有兵无船。汛期,水寨兵船才与卫所出海军结合。汛毕,“把总指挥以下皆解去”④,这使得水寨在非汛期有船无兵,处境险恶。对此,名将俞大猷就曾警告说:“闽广海洋之盗,不时生发,忽然而至,有船无兵,必致疏虞。”[15](P487)而明人章潢进一步指出:“倘贼觇我无备,批吭捣虚,不亦危乎?”[2](卷五十七《海防》,P482)可见,明初水寨选址目标过于暴露,易招致海上突袭的威胁,这一弊端的存在同样与明初水寨选址不当有直接的关系。
最后,缺乏优良港澳。
在火炮技术引入港区防护之前,军港对战船的防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形的屏障,这也正是《海防志》所说的“有曲港、深洲可以围舟结砦”的道理所在。对此,杜臻亦指出:“盖海之险,在水有澳曲可以藏舟。”[7](卷四,P1048)相反,缺乏地形屏障的保护,将船队直接裸露于敌方是相当危险的。对此,我们不妨举个战例,天启六年(1626)秋,新任福建巡抚朱一冯遣把总许心素、陈文廉率大支船队进击铜山,征剿郑芝龙。陈文廉所率百余艘战船不收泊铜山母港,而“尽行收入小港,先自立于死地”⑤。郑芝龙闻讯后,先派两只小船伪装成渔船潜入明军泊地进行侦查,随即率领大支船队乘着顺风、顺潮,突至明军泊地。由于明军船队缺乏地形屏障的保护,郑军假风潮之便施放火船,以极微弱的代价,轻易地烧毁明军各类船只70余艘。可见,有地形屏障的纵深港澳对船队的防护有着重要意义。而明初福建水寨驻防的小岛,不仅地势突出,而且岛幅面积小,岛澳平直浅出,缺乏有地形屏障的优良港澳以庇护军船,这使得聚泊水寨的大支船队随时面临海上突袭的威胁,这不能不说是明初水寨选址的另外一个重要不足。
综上所述,明初海防经略者忽视海防地理对军事驻防的制约,错误地将水寨设置于战线最前沿小岛上,导致明初水寨出现了无法自存、防御不足、易为袭破的问题。对此,长期在闽海征战的督府中军都司戴冲霄进行了总结,并明确地肯定了水寨的内迁。“福建五澳水寨乃江夏侯所设,俱在海外,今迁三寨于海边,曰浯屿、烽火门、南日是已。其旧寨一一可考,孤悬海中,既鲜有村落,又无生理,一时倭寇攻劫,内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设无益也。故后人建议移入内地,移之诚是也。”[4](卷四《福建事宜》,P280)
二、烽火门水寨内迁的个案分析
明代在水寨选址问题上几经变易,多数水寨都经历了复杂的迁移历程,以福建为例,除较晚设立的小埕水寨外,其余水寨均经历了复杂的迁移历程,其大体过程如下:
井尾澳水寨,于景泰三年(1452)内迁至铜山所城西门外,改称铜山水寨,今其地在东山县铜陵镇西北面的九仙山下,后玄钟所边设立玄钟水寨,隶于铜山水寨。
浯屿水寨,最迟在弘治二年(1489)之前,就被内迁至中左所(今厦门)⑥,万历三十年(1602),水寨改移至晋江石湖。⑦
南日水寨,亦于景泰三年(1452)被内迁至“府城东南新安里吉了巡检司之东滨海”[16](卷四十三《公署》,P906),今地在莆田忠门半岛南端的东埔镇梯吴附近。万历六年(1578),在福建巡抚刘尧诲的奏请下,南日寨被移至平海卫南哨澳。⑧万历四十一年(1613),水寨改移至三江口刘澳⑨,今地在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镇附近。
烽火门水寨,永乐年间(1403—1424)由烽火岛内迁至海岸边上的三沙,正统七年(1442),水寨再次内迁至福宁湾腹里的松山。嘉靖二十七年(1548),水寨改移流江,同时三都澳口的大箬头设立官井洋水寨,隶于烽火门水寨。⑩不久,烽火门水寨回迁松山。
可见,明代福建水寨的迁移历程相当复杂,相关的研究仍有不小的拓展空间。本文集中于水寨内迁问题的探讨,对于水寨因战区重要性升降而做的改移运动暂不涉及。明代福建水寨的内迁历程中,烽火门水寨是最早被内迁,内迁次数最多的水寨,因而最具代表性,以下便以烽火门水寨为例,考察水寨如何通过内迁以克服明初选址的弊端。
关于烽火门水寨的迁移历程,嘉庆 《福鼎县志》载:“于外洋设烽火门水寨,永乐间设游把总一员,后徙三沙,正统徙松山,嘉靖徙箬头,旋徙松山。”可见,自永乐以后,烽火门水寨便经历了复杂的迁移历程。永乐年间(1403—1424),卫所规制尚称完整,卫军战力尚强。因而有学者认为水寨内迁是卫所制度衰败所致的观点便很难成立,水寨内迁与明初选址不当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明代倭患呈现出由北向南的发展态势,紧邻浙江的烽火门水寨最先感受到倭患的压力,亦最早暴露出选址的问题。永乐八年(1410)十一月,一股驾船23艘,人数多达2000余人的倭寇由浙江突入福建,直接攻陷了汛期向烽火门水寨派遣出海军的大金、定海二千户所,并乘势攻围平海卫城。此时,大金、定海二所已是自身难保,而“孤悬海中”的烽火门水寨的危急状况便可想而知。为此,福建方面曾试图通过增兵以保护水寨,然而,增兵的效果仅限于增强对岛上的公署、校场、营房等设施的防护,并不能克服水寨在选址方面的劣势,特别是对战船的防护效果甚微,为防水寨为倭寇所袭破,福建方面将水寨内迁至陆上的三沙。
然而,三沙的驻防条件仍不甚优越,迫使水寨不得不再迁松山。关于水寨再迁的原因,著名福建史专家朱维幹就认为:所谓地点孤远,风涛汹涌,是迁移水寨的一种借口,并非事实。[17](P184)如果从地理环境考察的话,朱先生的这种推论略显武断,三沙海域确实存在风浪问题。史载:“(三沙)每年七、八、九月,常有大潮,飓风更甚,如钱塘之怒涛。”[18](卷一《山川》,P35)如此大的风浪势必会对泊船产生影响。对此,宁波生员陈可愿在考察相同地理环境对泊船影响时就指出:“但水震荡不宁,舟泊于此,久则易坏。”[4](卷十二上《经略三·御海洋》,P771)可见,风浪问题确是水寨再迁的重要原因。然而问题是,三沙附近有着众多的避风良港,如果是因风浪,完全可以在附近找到合适的港口,何必舍近求远,远徙松山?可见,风浪问题又不完全是水寨再迁的原因。
永乐年间(1403—1424),烽火门水寨内迁三沙解决了水寨后勤难以保障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水寨的应援条件,而福建方面亦特地调大金所官军协防水寨,“永乐间,倭寇犯境,议拨福宁卫大金所官军防守”[4](卷四《福建事宜》,P276)。然而,从地理上看,三沙位于福宁湾口的北端,而大金所却位于福宁湾口南端,两者道里相去甚远,这势必会影响大金所应援职能。而大金所拔出的守寨官兵亦少得可怜,仅“官四名,旗军三百”。这与水寨所承受的防守压力完全不相匹配,此外三沙附近再无卫所建置,水寨安全仍无法得到保障。对此,顾祖禹在分析广东柘林水寨先后为海寇李魁奇、刘香袭破的原因时就指出:“海寇扬帆直指,瞬息可至,且四面孤悬,无附近卫所可以缓急应援。”[8](卷一百○三《广东四》,P4725)三沙的地理环境与柘林十分相似,三沙紧邻烽火门水道,地势突出,水寨独处三沙很可能像柘林水寨那样,为敌寇所袭破。而再迁后的烽火门水寨位于今霞浦县州洋乡松山村,该地紧邻福宁卫,水寨由此被置于福宁卫的保护下。福建水寨向卫所周边迁移并非仅限于烽火门水寨,内迁后的井尾澳水寨位于铜山所城西门外,内迁后的南日水寨紧邻莆禧所,内迁后的浯屿水寨则靠近中左所,而较晚设立的小埕水寨直接就设在定海所旁。可见,福建水寨并非随意地向腹里迁移,而是通过有意识地向卫所周边迁移,以达到借助卫所力量增强自身防御的目的。
而就地理环境而言,内迁后的水寨均被置于具有地形屏障的纵深港澳,以此改善港区的预警与防护条件。如再迁后的烽火门水寨位于福宁湾腹里的松山,松山港地势深入,具备较好的防御缓冲,而且港区周边遍布着福宁卫、大金所的众多烽堠,有力地改善了港区的预警条件。同时,松山航道沿线分布着诸多岛屿,“港口有大、小门二山,北有小岛筋山,南有长泰山,其东即烽火门也,门南又北桑山,南桑山、火焰山”[19](P657-658)。这些岛屿对松山港形成有效的屏障作用。同样,内迁后的铜山水寨位于铜山港内,铜山港位于东山岛东北端,港口由东山岛与古雷半岛夹峙而成,港区较为隐蔽。同时,港区水域宽而深,港口进出便利,“东山港口之形势至为扼要,口之中央有塔屿,海拔五百公尺,砥柱中流,分港口为东、西二门户,东口小,通潮汕,曰小门;西口大,通漳、厦,曰大门”。此外,港区内外分布着铜山所的诸多烽堠,有力地改善了港区预警条件。可见,水寨内迁除了寻求卫所的庇护外,亦在寻求有地形屏障的优良港区,以克服明初水寨选址目标暴露、易遭突袭的弊病。
三、围绕福建水寨内迁的争议
明代水寨的内迁在历史上即遭到广泛的非议,特别是倭乱爆发后,时人更将海防的废弛归咎于水寨的内迁,主张恢复旧址。“识者谓,沿海设烽火五寨皆在海洋之中,如处弓弦之上,故声势联络,可以互相应援。承平弊滋,正统间,倡为孤岛无援之说,移各寨内港,今寨名虽是,寨地则非。内港山澳崎岖,每被贼舟径趋浅水,而吾大船为无用之器。故迎则不支,追则不及,由失势所致也。”[18](卷一《山川》,P31)又如,“国初海岛便近去处,皆设水寨,以据险伺敌,后来将士惮于过海,水寨之名虽在,而皆自海岛移置海岸。闻老将言,双屿、烈港、浯屿诸岛,近时海贼据以为巢者,皆是国初水寨故处,向使我常据之,贼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国初水寨所在,一一修复”[20](P2746)。此类的言论在史籍中可谓俯拾皆是,其批评的着眼点大体有三:其一,水寨的内迁导致防线的内缩;其二,水寨的内迁造成大型兵船无法发挥作用;其三,水寨的内迁导致海岛为敌寇所占据。然而,几乎与批评声鹊起同时,部分久历海战的将领及长期居住边海的士人对上述看法提出了质疑。
首先,关于水寨内迁造成防线内缩的问题。
水寨职能的发挥取决于战船的机动与作战,而非水寨的驻地,这与陆上关隘的据险镇戍有着本质的区别,亦即水寨的驻地与汛地关系问题。对此,游击王有麟就指出:“论闽事者往往以复江夏侯旧寨为说,又有言其不当复者。不知今之寨游,虽设在旧寨之内,而其哨守常在旧寨之外,其言当复与不必复者,皆剿纸上之谈,而未亲历海上者也。”[21](卷四《福建事宜》,P78)在此,王有麟对不谙水军特点,空谈复寨的看法提出批评,同时指出水寨的驻地与汛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水寨驻守内港,军船仍能出哨外海。对此,同安人蔡献臣以浯屿水寨为例指出,“如厦门防守官军果能以湄洲、深沪、料罗、大担为汛地,络绎巡警,而于料罗澳及大担屿最切要处,常扼守之,则又不论旧浯屿与厦门矣”。在蔡氏看来,浯屿水寨驻守浯屿或厦门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战船出哨汛地。同时,他也对固持复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强调战船出哨的重要性,“夫寇飘忽靡常,刻舟于旧所从入者,固为拘挛之见。第将士以船为家,时戒严于波浪要害之冲,则弭盗之上策也”。同样,莆田士人朱蒘在论及南日复寨问题时亦认为水军的出哨远比复寨更为重要,“诚使海滨诸镇舟舰整具,军士在营,戍将得人,奋励威武,日以舟师巡逻海上,一闻寇盗,首尾邀击,自足以弹压弭服,南日之移姑俟他日随机应变计未晚”[22](卷二《海上赠言》,P447)。可见,水寨职能的发挥并不取决于水寨驻守内港或外港,而取决于军船是否出海巡哨。而“自升平久,而额军、额船,渐失旧制,指挥、千百户等官,足不逾城,会哨之法杳然矣”,军政的废弛,巡哨的不行才是明代中叶水寨职能丧失的关键因素,亦是海上防线内缩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关于大型兵船在内港失势的问题。
事实上,大型兵船设计本来就不是为了内海及港区的作战,而是用之于外洋的冲犁。“按福船势力雄大,最便冲犁,所以扼贼于外洋……港中山澳崎岖,贼船窄小,反易趋避,而大船转动多碍。”[13](《福建》,P457)如上所述,大型兵船不出外洋,并非水寨内迁的结果,而是明代军政废弛,巡哨不行的结果。而即便是大型兵船出外海巡守,亦不能尽阻贼船于外洋,总是会有敌船透过稀疏的防线突入内港。因此,对于一支健全的水军而言,发展大、中、小各号船型,以适应内外海及港区作战的需要是水军发展的必然。“故寨中有福船,又有次号哨船、冬船以便攻战,小号鸟船、快船以便哨探,或助力袭击。如福船出洋犁贼,贼船势将内逼,哨、冬船与鸟、快船急抢上风,又出贼船之内,向外逐打,务逼使出洋,内外夹击收功,如一概从外追打,逼贼登岸具有军法。”[13](《福建》,P457)可见,内海及港区作战主要是由中、小号的哨船、冬船、鸟船向外驱逐,而大型的福船由外向内助战,征战的主力是中、小号的战船。而明代福建水寨亦配有各号战船,如:浯屿水寨“管福、哨、冬、鸟等船四十八只”;铜山水寨,“原设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共四十六只”,等等。水寨配备大、中、小各号战船就是为了适应不同海域作战的需求,苛求大福船在内海及港区作战,其本身就是不太合理的想法。
最后,关于水寨内迁致使敌寇占据海岛的问题。
明初实行迁岛政策将沿海大量岛民内迁陆地,对海岛采取部分弃守的政策。该政策的制订与执行说明明初并未真正重视海岛,亦未真正将海岛防御纳入海防经略视野。这种轻视海岛的思想和行动使得明人对海岛驻防规律认识不足,成为明初水寨选址失误的思想根源之一,亦构成海岛为敌寇占据的现实基础。而从战术层面而言,岛屿拉锯是岛屿攻防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只要配备足够的海上力量,建立动态的海岛防御机制,部分军事价值较差的海岛暂时为敌寇所占据,并非什么可怕的事情。明代海寇活动的游移不定,历来是官军征讨的一个难题。对此,兵部尚书聂豹就说:“海贼与山贼异,山贼有巢穴可以力攻;海贼乘风飘忽,瞬息千里,难以力取。”[23](P10)相反,如果海寇专驻某澳、某岛,便相对有利于官军的征剿。对此,名将俞大猷就指出:“窃意海贼之所以难与者,为其一闻官兵追捕,即驾出洋,不得接战收功,为可虑耳。若夫专泊澳分,轻视官兵,驱之不去,此则脆兵之所忌,强兵之所喜也。”[15](P164)而明代成功清剿海岛的战例并不鲜见,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遣都司卢镗围困并攻灭双屿,一举捣毁中外海盗盘踞多年的双屿巢穴,“斩俘、溺死数百人,贼首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
十四等,皆就擒”[4](卷五《浙江倭变记》,P322)。而且,在“四面阻水”的海岛,一旦将敌人包围,往往可以全歼。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月,有倭船飘至兴化府南日山旧寨,登岸流劫,“把总指挥张栋督舟师冲击,倭走据山。知府董士弘纠民兵、猎户与栋等围而歼之”。可见,在总结明代海岛防御问题时,不应简单地归咎于水寨的内迁,而更应该反思当时消极的海岛政策,探讨切实可行的岛屿防御机制。
四、结语
明代水寨内迁集中反映了明代海防经略者由最初无视海防地理,到重视与累积海防地理知识,并主动将之运用于指导海防实践的转变历程,体现了明人克服陆地思维,形成海洋意识的过程。同时,水寨内迁亦折射出了明代在军港选址与岛屿防御问题上的探索,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下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关于军港的选址。舰队作为夺取制海权的海上攻击力量,其本身亦是敌方搜寻和攻击的主要目标。因此,军港的选址不仅事关舰队攻击职能的发挥,更关系到舰队自身的安危,选址时除了关注宏观战略位置外,还必须重视军港自身的微观驻防环境。具体而言,在考虑港区水深、航道、风浪等停泊与通航条件的同时,应当重视地形屏障和防御纵深对舰船的保护,避免将舰船直接裸露于敌方的火力之下。同时,应配置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保护港区。此外,应充分重视港区预警的重要性,努力构筑和拓展预警体系,为舰船的机动与防护提供必要的时空缓冲。其次,关于岛屿的驻防。在关注岛屿的宏观战略价值的同时,应对各类岛屿的实际驻防条件有准确的认识,从而对海岛驻防的价值和目标做出客观的评估,并综合岛屿的驻防条件、驻防价值、驻防目标选择对应的防御方式,避免将重要的战略目标构筑于防护条件较差的海岛之上。同时,应充分重视岛屿驻防与陆上驻防在补给、预警和应援等方面的差异,拓展岛屿预警和防护空间,形成完善的保障与应援机制,构建动态的岛屿防御机制。此外,应重视岛屿开发与军事驻防的相互关系,充分重视民间力量在岛屿开发与军事防御中的作用,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海岛驻防与建设。
注释:
①赵园:《谈兵——关于明清之际的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上)、(下),分别见《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1、2期。
②蓝鼎元:《东征集》卷4《论台镇不可移澎湖书》,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26册,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47页。
③朱肜纂,陈敬法增补:《崇武所城志·战船》,第25页。
④周瑛:《烽火门海道分司记》,载殷之辂:(万历)《福宁州志》卷14《艺文志下》,《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47页。
⑤曹履泰:《靖海纪略》卷1《答朱明景抚台》,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台湾大通书局,第4页。
⑥何孟兴:《明嘉靖年间闽海贼巢浯屿岛》,载《兴大人文学报》总第32期,下册,2002年。
⑦叶向高:《石湖浯屿水寨题名碑》,载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4页。
⑧项独寿:《小司马奏草》卷6《题为严禁下海奸人勾引接济逋贼贻害地方事》,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
⑨《明神宗实录》卷505,万历四十一年二月丁未条,第9598页。
⑩《明代宗实录》卷212,景泰三年正月壬寅条,第4559-4560页。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2](明)章潢.图书编[A].四库类书丛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明)洪受.沧海纪遗·建制之纪第二[M].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
[4](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李致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清)许松年.浯屿新筑营房墩台记[A].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6](清)周玺纂.彰化县志[A].台湾文献丛刊(第156种)[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7](清)杜臻.巡视粤闽纪略[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9]林学增.(民国)同安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10]福建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福建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报告[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5.
[11](明)林章.林初文诗文全集·第五问[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2]J.M.Braga.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Macau.London,1949.
[13](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2册)[M].合肥:齐鲁书社,1996.
[14](明)王在晋.海防纂要[A].续修四库全书(第73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5](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M].廖渊泉,张吉昌,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16](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17]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18](明)殷之辂.(万历)福宁州志[A].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19](清)齐召南.水道提纲[A].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地学卷(第五册)[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20](明)唐顺之.条陈海防经略事疏[A].明经世文编(卷260)[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明)郑若曾.筹海重编[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227册)[M].合肥:齐鲁书社,1996.
[22](明)朱蒘.天马山房遗稿[A].景印四库全书(第1273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3]嘉靖平倭通录[A].倭寇事略[M].上海:上海书店,1982.
【责任编辑:俞 晖】
K248
A
1004-518X(2013)11-01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