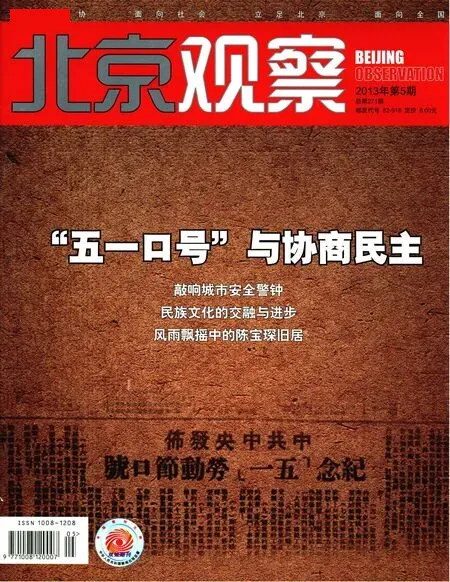房山石经与历代王朝
文/郑永华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延续千年的云居寺刻经,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珍贵而稀有的奇葩,有“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等美誉。云居寺现已成为佛教经籍的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
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经,是世界上规模巨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佛教文化珍品,在佛教传承、社会历史、书法艺术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文化价值。总计达一万四千余块经碑的房山石经,自隋唐肇始以来,经辽、金、元、明诸代僧俗的持续努力,绵延千年。而其兴起与发展,则与历代王朝的关注与资助密切相关。
高僧静琬刻石经
房山石经创始于隋唐高僧静琬。静琬(?~639),是北齐名僧慧思的弟子。慧思鉴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产生的严重后果,为了防止佛法在今后大规模的灾难中遭到毁灭,有意刻石藏经,却始终未能实现夙愿。静琬秉承师意,立下宏志,决定将镌刻石经的重任付于行动。隋大业年间(605~617),他来到涿州白带山,开始开凿石室,刻造石经。此事一开始就受到隋代皇室的支持。白带山智泉寺以隋文帝谕命修建的舍利塔著名。静琬来此镌石藏经后,又得到隋炀帝皇后萧氏的支持。当时因东征高丽,隋炀帝举驾来到涿州,随行的有内弟萧等人。萧平生即笃信佛法,听到静琬刻经的非凡举动与远大志向后,很受感动,并告知于其姐萧皇后。萧皇后即施绢千匹以嘉其志,萧也随同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由于隋室皇廷亲贵的显赫身份,萧氏姐弟的捐施之举,大大增加了静琬的声望,刻经也逐渐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静琬刻石一直持续到唐初贞观年间。经过三十来年的努力,到唐贞观十三年(639)静琬辞世之前,完成了《维摩经》《、胜经》以及《华严经》、《涅经》等经石146块,计佛经12部。静琬在《贞观八年题记》中嘱咐后人:“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表明刻经目的旨在法难佛经无存后,能再次发掘出来作为底本,使佛法重传于世。为了妥善保存,静琬将刻好的石版均密藏在开凿的石室之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同时又在其地构建云居寺,既便于刻经持续相传,亦利于随时弘扬佛法。
后世流传续不穷
静琬圆寂之后,其徒玄导、僧仪、惠逻、玄法等人依次相承,在云居寺继续石经刻造,“凡五代焉,不绝其志”。这也得到唐代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唐代中期,唐玄宗之妹金仙长公主嘉叹于静琬师徒的事迹,再次予房山刻经以大力资助。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奏请赐给云居寺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僧俗刻造石经的蓝本,又将寺旁的麦田、果园、林木等,皆赐给云居寺作为寺产。随后,金仙长公主又捐资重修、扩建云居寺。由于受到皇亲贵戚的重视,唐代云居寺的影响随之增大。唐末幽州节度使刘济,也捐出自己的俸禄,助刻了《大般若经》等佛经。燕地百姓则结为邑社,常年集资刻石。据粗略统计,隋、唐两代云居寺共完成经碑4978块,分藏于9个洞窟中,占到房山全部石经的三分之一。
五代战乱时代,云居寺多有损毁,刻经工作也陷于停顿。辽统一北方后,刻经又渐有起色。辽穆宗应历年间(951~968),僧人谦讽立志重兴。他一方面努力吸纳宗教信众的捐助,更重要的是,他又设法争取到当朝契丹贵族的参与,包括“前燕主侍中兰陵公”以及“某公主”等权贵。在官宦信众的支持下,谦讽修葺破败,“见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请以经金,遂有次序”,又增建大量佛寺建筑,其中由兰陵公化助建讲堂一座五间七架,公主则化助建造碑楼五间六架等。寺庙的整修复建、信众的聚集,为恢复刻经做了很好的准备。
辽代石经的正式续造,始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前后。辽中后期,统治者奉佛之风日盛,石经刻造也在皇室的支持下复兴,并很快达到新的高潮。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持续资助下,云居寺续刻了《般若经》后80卷和《大宝积经》等大量佛典。先是辽圣宗“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继由辽兴宗赐钱造经,随后又有相国杨遵、梁颖等经辽道宗奏准续刻,共完成刻石187帙。其中辽道宗尤“好佛法”,有“菩萨国王”之称。他曾撰《御制华严经赞》(即《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鼓吹“圆融无碍”之道,于咸雍四年(1068)颁行天下,后还刻入《契丹藏》中。辽道宗推崇佛经,撰有《发菩提心戒本》2卷,云居寺辽刻石经中的《发菩提心戒》可能就是其节本。由此一例,即可见辽道宗与房山石经的密切关系。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云居寺僧人通理“见今大藏仍未及半”,与雕刻全藏的宏愿相距甚远,于是发起大规模的石经续刻活动。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正月初一日,通理在云居寺内大放戒坛,前来受戒者“叵以数知”,一直持续到暮春时节,共募集银钱万余镪,交其弟子僧录善定主持石经续刻。经一年多的努力,共刻“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通理另一弟子善伏,又与善定募捐善款,将辽代所刻石碑,全部妥善秘藏于寺内地穴。至此,辽代石经刻造告一段落,取得了巨大成绩。总计辽代官方与僧俗续刻石经,数量多,内容丰富,总量几乎占云居寺全部石经的三分之一。这与辽历代帝王尤其是辽道宗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金代以后,房山石经续刻数量不多,但仍在持续。金代僧俗四众在云居寺刻造佛经多种,如张企徵与其妻萧张氏出资助刻的《妙色王因缘经》、《八部佛名经》等佛经十余种,又有皇伯赵王、汉王所刻《增一阿含经》与《杂阿含经》等。尤其是僧人玄英与俗家弟子史君庆、刘庆余,自天会十五年(1137)至皇统九年(1149)间,共刻造《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等密宗经典39帙。玄英又刻造《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为后人了解金天眷三年(1140)之前辽、金二代云居寺续刻佛经的总体情况,提供了可靠资料。
明清之际更尊崇
明清时期房山石经刻造基本停止,但云居寺仍得到统治高层的关注,有利于石经的保存与传承。明朝建立后,行童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听闻石经之事迹,特命人前去视察。洪武二十一(1388)年正月二十一日,随侍燕王朱棣的高僧道衍禅师(即姚广孝)奉旨前去观瞻。道衍向朱元璋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撰诗纪事,称:“竺坟五千卷,华言百师译。琬公惧变灭,铁笔写苍石……功非一代就,用籍万人力……不畏野火燎,讵愁藓苔蚀。兹山既无尽,是法宁有极。”并对静琬表达了崇敬与景慕之情:“如何大业间,得此至人出。幽明获尔利,乾坤配其德。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高度推崇静琬法师的护法盛举。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又有高僧德清与达观发掘出云居寺秘藏一千余年的佛舍利,经皇太后虔心斋供后回藏,成为轰动一时的佛教界盛事。德清(1546~1623),全椒(今属安徽省)人,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达观(1543~1603),祖籍江苏句容,幼年迁至吴县,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为真可,号紫柏老人。憨山德清、紫柏真可分别有《憨山老人梦游全集》、《紫柏尊者全集》等传世,位列明末四大师,是明代德重一时的著名高僧。两人发现云居寺舍利,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当时德清访达观真可于房山上方山,久闻石经山盛名,遂邀结同游,巡礼静琬所刻佛经。他们在清理雷音洞时,发现了秘藏多年的石穴,其中藏有隋大业十二年(616)静琬大师所置石函。请出细观,发现石函内套银函,银函内再套金函,金函中又有小金瓶,“中安佛舍利三颗,如黍米,颜红色,如金刚”。德清、真可请人奏于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受到内廷高度重视,“太后欣然喜,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佛宝出世,轰动一时。太后“仍于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复加小金函……仍造大石函,总包藏之”,归还云居寺,回藏于雷音洞,“愿住持永劫,生生世世,缘会再睹”。又嘱德清撰文刻石,以纪其事。德清在文中,赞称:“至我圣祖、神宗尊崇敬事,超越百代。”佛舍利是重要的佛教法物,云居寺在北方佛教界的名声,随之大振。时静琬塔院为寺僧所卖,德清、真可等以皇太后所施斋供赎回,还得到中贵杨廷及其弟子法灯等人的鼎力相助。明末万历、天启、崇祯年间(1573~1644),南方籍官员、居士集资刻经,由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书额“宝藏”,藏于雷音洞新开洞窟中,最终结束了石经刻造事业。明亡清兴之后,房山石经仍得到朝廷的关注与重视。清初经超古、僧广二位大师的住持修复,继续保持香火鼎盛的繁荣局面。广大信众施舍钱粮,买山置地。乾隆二十一年(1756),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博明撰文,书于碑石,为寺庙的传承与石经的保护提供稳定可靠保障。后来嘉庆帝又两次游幸云居寺,御题《云居寺瞻礼二十韵》和《再游云居寺》两诗,立碑于寺内弥陀殿院。
延续千年的云居寺刻经,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珍贵而稀有的奇葩,有“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等美誉。云居寺现已成为佛教经籍的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经历代王朝支持刻造而成的云居寺石经,迄今得到妥善保护和珍藏,焕发新的生机,展示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