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
文/孟昭旺 [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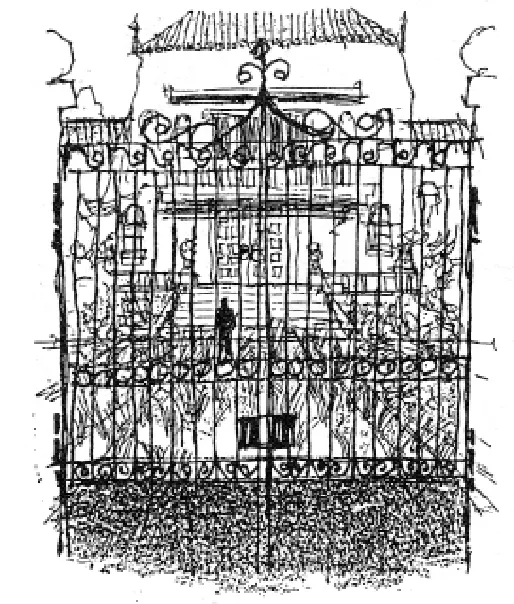
1
我敢断定,隔壁的男人一定是个烤栗子的好手。
黄昏时分,我常见他披着军大衣,端坐在蜂窝煤炉旁,不苟言笑。我站在他旁边,抽着烟,看他用一把军工刀,在栗子壳上划着口子,再把它们撒进锅里。男人的脸被炉火割成两半,一半鲜红,另一半隐藏在房间的黑暗中。他就那么独自坐着,一言不发,直到我彻底失去耐性,打着呵欠从他身边走开,去逗房东那只绿鹦鹉或者拿火腿肠喂趴在窗台上的猫崽。大约十几分钟,栗子的香味儿从废旧炒锅里钻出来。唯有这时,男人才会在变得轻松起来,如不出意外,他准会嘟起嘴唇,吹几首曲子。不过,吹口哨这件事他并不拿手,翻来覆去地,他只能吹出那么几首老掉牙的歌:《蜗牛与黄鹂鸟》《我爱北京天安门》,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烤栗子的男人是在一个月前搬到十里尹村的。十里尹村,这可真是个奇怪的名字。不过你们可别被它的名字欺骗,它其实跟“十里”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就在市郊,到位于二环以里的师大附中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至于这个村子的人是不是都姓尹,我曾专门问过房东。房东只淡淡地问了我一句:石家庄的人都姓石吗?烤栗子的男人搬来之前,这间石膏板搭成的简易房间里,依次住过有点儿娘娘腔的保险推销员,住过衣服上沾满墙漆的粉刷工,住过酒气冲天的三流艺术家。当然,住得最多的还是师大附中的学生情侣。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顶多十六岁,也许他们的打扮和嗓音使他们看上去更大一些,但是他们顶多十六岁,他们有着十六岁的眼神。遇到这些租客,房东通常会趁机敲一把竹杠,把房租提高两到三倍,并不忘暗示他们,出门之后朝西拐有一家诊所,诊所往前是离此处最近的保健品商店。
烤栗子的男人——哦,对了,在他搬来之前,有段时间,这里还住过一名操外地口音的按摩女。我必须隆重介绍她,因为,不瞒你说,我对那个长着兜齿的大胸女人颇有兴趣。我承认,自打她搬来的第一天,邪恶的念头就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很多个夜晚,在稀疏的星光和清脆的蛐蛐叫声中,我悄悄醒来,成了一只敏感的蝙蝠,小心翼翼地细嗅着隔壁房间的动静。那个名叫秀秀的女人长得不算难看,我想,假如我的女朋友李亚红不介意,我会毫不客气地推开隔壁的房门,投入这个陌生女人宽广的怀抱。遗憾的是,直到她搬出十里尹村,我都没弄清她的底细。我细嗅到的,只有一些细枝末节,一些鸡毛和一些蒜皮。比如,她叫秀秀,据我推测,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假的。凌晨两点左右,她房间里会有灯光。她平时饭量很小,对吃的东西总会精挑细选。她喜欢穿着粉色的棉鞋,到朱老三的熟食店买久久鸭脖。她门口的垃圾桶里,经常见到废弃的避孕套和嚼碎的鸭骨。她说话声音很大,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大嗓门的女人。有一天半夜,她被床底下窸窸窣窣的老鼠吓得半死。她的乳房,啧啧……我对拥有健壮乳房的女人充满热爱,原因是,我从小营养不良,体质虚弱,几乎每年冬天,都要生一场大病。直到现在,我还能准确说出十种以上治疗咳嗽的方子,还有十种以上治疗发烧的、治疗牙疼的和治疗腹泻的。呃,关于秀秀,我只能说到这里。事实上,我与她的交往时间很短,自打那天晚上在按摩店认出我之后,她很快就搬到别处去了。她说,她受不了房间里的老鼠,那些犄角旮旯发出的声响,会让她浑身不自在。她时常感觉,那些老鼠正在偷偷啮噬她的身体,从脚趾到小腿、膝盖,她的皮肤碎成一块年久的塑料,她的骨骼成了一根脆弱的玻璃管儿。她还提到了她的继父,那个有着老鼠一样小胡子的男人。她说,他比那些老鼠要可恨一千倍,一万倍,迟早有一天,她会把一包鼠药投进他的饭碗里,毒死那个畜生。秀秀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身上正压着一百五十斤,这个重量让她有些吃不消,她的叙述因此变得断断续续。很快,她便放弃了倾诉,化悲痛为力量,她的仇恨也随之被声嘶力竭的叫声取代。我说过,她是一个大嗓门的女人,她和李亚红简直是两个星球上的人。秀秀搬走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她。不过,有那么几次,和李亚红做爱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在她圆润的下巴上想象出一副好看的兜齿。
2
烤栗子的男人搬到这里不久,我知道他有一个晦涩的名字:索尊池。也许是苏知晨、隋自臣或者孙志春吧。谁知道呢。这个沉默木讷的男人,口齿永远都含混不清。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的舌头其实已经锈住,或者,他的口腔里根本没有舌头,只有一块硕大的富有弹力的牛皮糖。还有,索尊池的嘴角有道伤疤,只要开口说话,口水准会顺着疤痕淌出来,这更给他的表达增加了困难……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管他呢!他究竟叫张三还是李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上去,这个索尊池对我也没什么好感。他从不肯邀请我尝一尝他的栗子,即便我一再暗示栗子是我最爱吃的零食之一、栗子放久了就会霉掉也不行。真的,他很少跟我说话,跟房东也是一样。冬天的冰把他的嘴巴封得严严实实。
“喂!伙计,你老家是唐山的吗?”有一次我穷极无聊,这么问他。
索尊池摆弄着手里的刀子,没有回答。
“我知道唐山那边有个叫迁西的地方,那里盛产板栗。有一年,我去那儿出差……”我说。
“那年我刚二十出头,去迁西是为了推销一种假睫毛。呵呵,说实话,那种假睫毛完全是劣质产品,打开包装就有一股刺鼻的塑化剂味道。我向当地人撒了谎,我告诉他们,那是纳米的香味儿。纳米,你知道吗?可真是个好东西,我轻而易举地骗过了当地人。家家户户爱美的女人都戴上了我推销的假睫毛,我因此而赚了一笔。那时候,我真是想钱想疯了。唉!不说这个了。”
“在乡下,我遇到一个穿着米色裙子的姑娘。当时,她只有十六七岁,在县城读高中。在一座石桥下,她请我吃了一包栗子。然后,她提出想要入伙,跟我一起去卖假睫毛的想法。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她还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并且慷慨地撩起自己的裙子。她说,她不是跟我闹着玩儿的。浪迹天涯,一直以来都是她最大的梦想。后来,她的哥哥闻讯赶来,在石桥下发现了我们。那个浑身腱子肉的男人,挥舞着拳头让我赶紧从他们眼前消失,于是这场闹剧草草收场。为了表达我对姑娘的感激,临别之前,我免费送了她一副假睫毛。”
“哦,对了,接着说栗子。那个姑娘告诉我,她们迁西人都特别爱吃栗子,老人小孩都爱吃。也难怪,这么好的东西,有谁不爱吃呢?”
“你是不是迁西人?要是哪天你见到那个姑娘……”
“索尊池?伙计?”
“喂!你听见了吗?”
“真该死!”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闷头闷脑的邻居。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怀念以前住在隔壁的那些人,保险推销员、农民工、画家、无业游民,还有远遁他乡的秀秀。虽然他们跟我没有过多交往,至少,他们会喝酒、聊天、上网、画画儿,会光着膀子大声说话,或者当着女人的面儿讲一些荤段子。至少,有他们在,这个冗长的冬天显得不那么死气沉沉。而这个名叫索尊池的男人,简直是只冬眠的棕熊。出来进去,他都悄无声息,像个刺客那样尽量把头低下去,再低下去。这个沉默寡言的家伙,已经和整个世界彻底划清了界限。我敢保证,假如没人打扰,他会一直沉默着,整整一个冬天不说一句话。他全部的生活,除了烤栗子,还是烤栗子。
3
让我想想,让我仔细想想。好吧,我承认,上面的说法不够准确,有失公允。我承认,有一些坏情绪,埋藏在我心底,就像枯枝败叶淤积在河水深处。坏情绪带来了敌意,敌意产生了偏见,偏见让我对索尊池的评价失去了准星。我承认,索尊池,除了擅长烤栗子之外,还有许多本领。这些本领包括:用废弃的木料做板凳(他刨出的板凳面光滑如镜),天气晴朗的时候,义务为房东砌灶台(我则躲在墙角吊儿郎当地用牙签剔牙),修理一台破烂不堪的收音机(我敢保证,那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破的收音机),扎风筝和糊纸人(他的手指简直可以用来绣花)。当然,他还有那么一点点艺术细胞,偶尔,他会将一把脏兮兮的口琴塞进嘴巴里……
事实上,索尊池搬来没多久,他的才华便显露出来。在我面前,李亚红曾不止一次提起索尊池。她说,索尊池的手指真细啊,像女人的手指。她说,索尊池在后房檐上掏了三只麻雀,竟然把它们养活了,麻雀是最难养的,它们的脾气大得很。她说,索尊池用木头削了一把手枪,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她说,索尊池,索尊池,索尊池……
我不喜欢她在我面前评价别的男人。那些评价,好的或者坏的,都会成为一层新的枯枝败叶,落到水底,落到那些腐败的淤泥上。
我说:“我的烟,只剩下半盒了,如果你手头宽裕……”
李亚红说:“别看人家表面一声不吭,他可是个聪明人呢。”
我说:“亲爱的,也许我需要一个加湿器。房间太干燥了,每到半夜,我总会被自己的咳嗽声弄醒。再这么下去,我的肺迟早会爆掉。你觉得呢?”
李亚红说:“他房间里的东西——衣架,窗帘,板凳,菜板——都是自己弄的呢,还有,他烤的栗子可真香啊!”
我说:“你……能不能,再借我两百块钱?”
李亚红说:“我敢打赌,索尊池上辈子一定是个女人,他比女人心更灵,手更巧。”李亚红说完,捂着嘴巴“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真想象不到,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男子,就像……就像……接生婆。”她说。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我又不是傻瓜。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换工作,说明什么呢?二十六岁,仍然这么晃荡着,谁愿意跟这样的男人混在一起呢?
李亚红止住了笑声,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可而止。她说:“过两天吧,孟毛,过两天,等我发了工资,等我……”说到这儿,她就忍不住抽泣起来。不过,她的抽泣只持续了一瞬间,十秒钟,甚至更短,便戛然而止。我说过,李亚红是个聪明的女人,聪明的女人懂得收敛自己的野心,懂得得寸不进尺。然后呢?她缩进我怀里,用触须般的睫毛拱着我的下巴,她的泪水便蹭在我的嘴角,咸咸的,并且凉。我抱着她,紧紧地,把她抱进我的身体里,骨骼里,血液里。李亚红天生是个瘦姑娘,她让我时常感觉到一片虚无。也许我根本没有抱住她,我只抱住了一团空气。
“你放心,等过完年,我就去重新找份工作。”我抚了抚她的头发。我知道,这多少会让她开心点儿。
李亚红就笑了,露出两颗好看的虎牙。
“你别说了,什么也别说。”李亚红说,“孟毛,我这辈子就毁在你张嘴巴上了。”
李亚红说得对,她这辈子,从认识我开始,就毁了。生气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地表示,假如手上有一把剪刀,她会毫不客气地把它塞进我的嘴巴,“咔嚓”一声,剪掉我的半条舌头。
“你这只聒噪的乌鸦。”她愤愤地说。
我闭嘴,用小指在她的头发上缠来缠去。李亚红对自己的一头秀发充满自信,和我做爱的时候,她喜欢埋着头,把窄小的脸颊遮掩在黑发中。我的脸被她扫得痒痒的,让我怀疑,正在和我疯狂做爱的,其实是一只发情的水獭。
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李亚红就把多才多艺的索尊池抛在脑后,趴在我身上睡着了。同往常的喋喋不休相比,我更喜欢李亚红睡着的样子。说实话,除去脸上的几粒雀斑,李亚红基本属于好看的姑娘。我的那群狐朋狗友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小子摊上李亚红这么个好姑娘,真是修了八辈子福分。现在,这个皮肤干净的姑娘霸占了我的胳膊,把它当作枕头垫在脖颈下面,她的身子成了一把曲尺,佝偻着,蜷在被子里面。这是一个艰难的姿势,如果不是我尽量用力向上撑着,她的腰一定会从中间折断。她现在睡得正香,鼻翼像蛤蜊般一张一翕,脸蛋儿上微微起了褶皱。算起来,我们好了整整十年了,从……十六岁开始。
十六岁,那是多么遥远的年龄啊!
4
李亚红在市区烧伤医院做护士。她很忙,只有周末才有空乘车来找我。我真纳闷儿,为什么这个偏僻的小城天天都有火灾,为什么那些烧伤的家伙全被送到她们医院。有时候,我觉得李亚红之所以这么忙,是因为她太好欺负,人善被人欺。我曾亲眼见过,在病房,一个满脸油光的胖子,把手掌贴在李亚红的屁股上。李亚红看样子对自己屁股上游弋的手掌并不讨厌,她什么都没有说,甚至还对手的主人报以微笑。本质上,李亚红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或许,在她看来,那只是一个需要照顾的普通胖子。
李亚红是个好姑娘。每次来找我,都主动把我的脏衣服洗掉,旧报纸、啤酒瓶、烟蒂和碎头发也被她清理干净。李亚红有轻微的洁癖,她不允许任何脏东西出现在我的房间,一点儿也不行。干完活儿,我们会一起做顿午餐。李亚红的厨艺不错,她做的水煮鱼堪称一绝。我不止跟一个人说过,李亚红做的水煮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水煮鱼。我对李亚红说,干脆你别当护士了,你去当厨师吧。要是你当了厨师,一定是很牛的那种。
吃完饭,她会麻利地脱掉衣服,钻进我的被窝。李亚红的身体光滑,冰凉,让我感觉,我正把一条蛇压在身下。于是,我又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用身体把蛇焐热,然后……下午三点左右,李亚红会悄悄穿好衣服,起床,步行到一公里外的路口,赶返程的最后一班车。如果不出意外,我会在李亚红走后的半小时内醒来。我的枕头下面,总能发现她留下的一些钱,一两百,或者三五百。
李亚红已经很久没来了,她太忙。这个城市每天都有火灾。
5
真想不到,索尊池这样的人,在这个偏僻的小城竟然有朋友。
起初是一个男子。他和索尊池一样,都有着乱糟糟的头发和青蛙般鼓嘟嘟的下颚。他肯定和索尊池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两位同乡仿佛出自同一个模子,就连他们的表情也如出一辙,一个阴沉,另一个同样阴沉。他拎了瓶“牛二”,看样子,他是专程来找索尊池喝酒的。除了酒,他还拿了几个小菜,他是个慷慨的男人,这一点和索尊池不大一样。遗憾的是,索尊池恰好不在,大概他又去邮局给贞贞寄包裹了。贞贞是他的宝贝女儿,按照索尊池的描述,她可是个机灵鬼儿,是个人见人爱的丫头。真的,索尊池说,我敢保证,从没有一个女孩儿像她那么好。除了是个机灵鬼儿,贞贞还是个贪吃的孩子。索尊池说,栗子是她的最爱。每周,索尊池都要去镇上的邮局给贞贞寄一包栗子。我看了看手机,今天是周五,果然。阴沉的男人只在门口停留了片刻,就下楼去了。他有些阴暗的背影在我瞳孔里忽高忽低,他的身子于是轻轻地左右摇摆。这让我更加确信自己刚才的判断——他是个跛子。
索尊池回来,我把有人找他喝酒的消息告诉他。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只淡淡地“哦”了一声,看样子,他对那个陌生的访客没什么兴趣。
也不是完全没有兴趣。当天晚上,他就主动跑来找我,让我把白天那人的情况跟他详细描述一下。索尊池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或许他打算抽空去拜访一下那位朋友。很遗憾,我没能给索尊池提供更多的信息。事实上,每到冬天,我的记性都会变得很差,许多过去的事情,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糨糊,张三的帽子常常被戴在李四头上,驴唇和马嘴也经常被我弄混。
我没能给索尊池提供更多信息,这让他有些失望,失落和沮丧迅速爬到他的脸上。
除了失望,还有害怕。是的,索尊池害怕极了。他甚至紧张地抓住我的衣领:“你再想想,那人有什么特征,拜托你,好好想想,一个细节也不要错过。他是不是有些秃顶,是不是有着鹰一样的眼睛,是不是问过你什么。你想想,好好想想!”他的声音开始不住地颤抖,他成了秋风中飘摇的叶子。他简直就要崩溃了。
“对不起,老兄,我真的记不得了。他没什么特别,他只是个普通人。他拎了瓶酒,还有一些下酒菜。他是专门来找你喝酒的。”
“不是!”索尊池说,“他绝对不是来找我喝酒的,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我谁也不认识!”索尊池浑身是力气,他快把我拎到半空中了。
我挣扎着,大叫:“喂!你最好对我客气点儿,这样对你有好处!”
索尊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办。我的话,被他当作了耳旁风。一双钳子继续夹在我的胸前。
“把你可恶的爪子拿开!快点儿!”我踮着脚尖,用力一甩,挣脱了他的手掌。我恨恨地推了他一把,索尊池就被推到沙发上。有时候,我可是个有脾气的人。
摔倒之后的索尊池看上去有些自暴自弃,他似乎没有再次站起来的意思。他就侧在沙发上,倚在那里,像只斗败的公鸡,有气无力地,把头埋进身体里。
“你最好把她看紧点儿。”索尊池的声音从沙发里头传出来,“你的女朋友,最好看紧点儿,要是有时间,就多到医院陪陪她,反正,反正你也是闲着。她有好久没来找你了,这不是什么好兆头……”索尊池不再说话,房间里静得出奇。一潭死水里两条绝望的黑鲤。
良久,索尊池从沉默中醒来。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叮嘱我说:“伙计,要是再有人找我,你别说见过我,跟谁也别说,一个字也别提,求求你。”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贞贞病了,病得很厉害。大夫说她恐怕活不过年底,她这么好的女孩儿。你不知道,她好的时候有多好。”
索尊池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走出房间的脚步仓促而踉跄,喝多的醉汉一般。
“他似乎是个跛子。”我说,“今天找你喝酒的那个人。”
索尊池飞快地跑起来,健步如飞。
6
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一个冬天像现在这样漫长而无趣。除了看索尊池烤栗子,我几乎无事可做。不,好像也并非完全无事可做。我有一台电视机,没事的时候,就窝在房间的沙发上看电视打发时间。我喜欢看体育频道,篮球、排球、跳水、F1赛车我都爱看。不瞒你说,我打小就热爱体育,有段时间,我还经常到附近的一所中学打篮球。有个三十多岁的退伍兵也经常去打球,他是沧州人,和我算是半个老乡。不过,自打那次他说似乎在哪儿见过我之后,我就再没去打球了。他的话提醒了我,我们的确见过,不在别处,就在秀秀的按摩店里。
七点整,我会准时把电视调到本地法治生活频道,看一档名叫“法治进行时”的栏目。这个栏目总能带给人一些惊奇——如果你不看,根本想象不到,一座火灾多发的小城,竟然隐藏着这么多犯罪嫌疑人。
李亚红决定搬走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时,我正拿一根谷穗站在阳台上。笼子里那只牡丹鹦鹉鬼得厉害,手里的稻草好几次都被它啄个正着。很快,手里的谷穗就变得光秃秃的。真奇怪,每次我都躲不开它的啄击。这让我有些恼火,这次,我换了一支竹签,准备给它点颜色瞧瞧。李亚红就是在这时候进来的。一段日子不见,她有点儿胖了。她穿了一双红色的高筒皮靴,很鲜艳,跟她往日的风格大不相同,我都有点儿认不出她了。
“太好了,李亚红,你终于来了!这些天你忙坏了吧,最近总是有火灾。”我说,“你来了就好了,快来,看这只鬼家伙,简直太难对付了。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根铁丝,最好细一点儿的,我要缠在它的爪子上,让它吃点苦头。”
“李亚红?”
“你怎么了?你要出远门吗?干吗要收拾行李呢?”
“李亚红,你怎么哭了?”
“他是谁?”
一个男人站在李亚红背后,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对男人的这双手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它曾经在医院的病房里,在李亚红的屁股上游走。
自始至终,李亚红什么都没说。她只默默地收拾东西,鞋、围巾、闹钟、梳子、相册、毛绒熊……她低着头蹲在地上,她的头发就从两边垂下来。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在犹豫该不该上去帮帮忙,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收拾好东西,李亚红站起身来,她长出了一口气。她张了张嘴巴,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可是她终于什么也没说,只把一沓钱塞到我手里。我相信,在下楼的一刹那,她一定泪流满面。跟我一样。
7
李亚红搬走后,房东家里倒显得热闹了不少,接二连三地总有一些陌生人找上门来。那些人都是为索尊池而来。他们找索尊池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找他要账,有人找他定做家具,有人找他打听消息。还有一个穿着皮靴的大胡子自称是个生意人,他要跟索尊池谈笔生意。大胡子转而又说,他其实是索尊池的远房亲戚,他来找索尊池除了谈生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有些伤感的大胡子提到了贞贞。他说,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在几天前去世了。他让我转告索尊池,他寄的那些栗子她都收到了,味道很好,香,而且甜。贞贞还说,她总是梦见母亲,梦见母亲浑身是血,梦见她哭喊着找索尊池算账,梦见她跪在贞贞面前求她原谅……可是,索尊池去了哪儿呢?
索尊池去了哪儿?几天来,房东已经被这个倒霉的问题折磨疯了。几乎每个找上门的人,都用同样的语气向他发问。为了应付这些不速之客,房东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话。“索尊池不在,你们不用等了,等也是白等。”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要是你们见到他,一定把他找回来。”
“没见过这样子的租客,欠了我一个月的房租就跑路了。”
“不知道,你们什么也别问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已经说过一百遍了。”
“什么也没做,他在这儿住的时候什么也没做。他只是在烤栗子,白天烤,晚上也烤。他很少出门,跟谁也不交往,这一点他的邻居可以做证。对吧,孟毛?”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在乎索尊池。他是死是活跟我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他去了哪里跟我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他的宝贝女儿,那个叫贞贞的女孩,跟我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我可不想为他们操心。那段时间,我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我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不瞒你说,这个计划跟李亚红有关。我要尽快找到她,这个计划,我想亲口告诉她,只是,我不知道她对此还感不感兴趣。
我的这个计划,在执行中遇到了那么一点困难。那就是,李亚红已经辞职了。是的,她其实早就辞职了,她已经离开了那家医院。一直以来,她就在躲着我。其实,她原本没必要躲我的,她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去找她呢?我其实早该想到这个结果。女人,需要男人的一张嘴,但更需要一个男人做靠山。在这个不大的城市,找到那个叫魏青山的男人并不难,真正有钱的胖子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有时候我想,是不是该和他坐下来好好谈谈,他应当不至于像李亚红那样躲着我吧?我们又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当然,说朋友吧,也算不上。
8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下午,我又见到了索尊池。不是我去找他,而是他主动来找我。这些日子,他吃了不少苦头,这是肯定的,从他的乱糟糟的头发和身上臭烘烘的味道就能看出来。他瘦了,眼窝深陷,无精打采的样子。他跑到我屋里来,是想跟我借点钱。他说,他想回家看看,回山东德州的乡下,看看贞贞。他说,哪怕回去被他们抓住他也认了,总这么东躲西藏也不是个办法。
“唉!总有一天,我会被他们抓回去的。”索尊池叹了口气说,“看一眼贞贞,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有钱,李亚红给我的一沓钱足够厚,她向来是个慷慨大方的姑娘。
“好吧,”我掏出几百块给了索尊池,“赶紧坐最早的火车回去吧,贞贞一定很想你,或许都该急哭了。”
索尊池很高兴,他笑了,嘴巴咧成一只熟透的石榴。
“等等!这里还有二百,你最好给她买件像样的礼物。要是你那么做的话,她一定非常高兴,她会为拥有你这么优秀的父亲而骄傲。”
索尊池回到自己的房间,没多久他又返回来。他拎了两箱栗子,满满两箱,放在我的床下。他说:“伙计,栗子可是好东西。要是有机会就到德州去做客,我好好招待招待你。”
我收下了索尊池的栗子。我向来不善于拒绝别人的好意。我心里一阵一阵的疼,我又想起了李亚红。
“谢谢你。”我说。
“还有,你最好少抽点儿烟,这对你的肺有好处。”索尊池迟疑了一下,嚅嚅地说,“迟早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迟早。”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拉回到现实。那个男人,那个曾经拎着酒菜来找索尊池的跛子,再次出现在我的门口。他穿了一身警服,看上去神采奕奕。他的身后跟着另外几名警察。他们无一例外地有着鹰的眼睛。
“别问我,”我说,“我有些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9
第二年的春天,我的生活有了一点儿变化。原因是,我顺利谋得一份差事。我的老板就是那个跟我一起打球的老乡。我们在一次同乡聚会中再次重逢,因为有点儿他乡遇故知的味道,便一起多喝了几杯。期间,他一再重申,他之前说的在按摩店见过我的话,其实是跟我开个玩笑。然后,我们一起为这个可爱的玩笑干了一杯。我甚至借着酒劲问了他一句,认不认识一个叫秀秀的姑娘。
我一直觉得,总体来讲,我是个不乏运气的人。因为那次聚会,我顺利地谋得了这份工作。我的任务是往各地推销一种新型消防设备。这不算什么难事,之前我有过推销产品的经历,这次算是做回了老本行。况且,我对火灾有些特殊的敏感。
有那么几回,路过德州,我曾经专门打听过索尊池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有点儿想念这个擅长烤栗子的男人。当然,寻找的结果令人失望。几乎所有人都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了我。他们说,不知道谁叫索尊池,更没有人见过索尊池。
我的工作还算顺利,一个月下来能有三五千块的收入。除了必要的花销,我把那些钱统统存进银行。每周,我都跟我的老板一起去打球。然后,跟一帮朋友在路边吃烧烤、喝啤酒。除此之外,我还经常看《法治进行时》,偶尔还会想起李亚红。没什么别的想法,仅仅是一种习惯。
七月的一天,我竟然在电视里意外地见到了索尊池。没错,颧骨突起,鼻梁高挑,嘴角一道长长的疤痕。索尊池,我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他,没想到,我们竟然在电视上重逢。电视里的索尊池看上去有些沮丧。在屏幕上,这位昔日的邻居弓着身子,把自己佝偻成一只大虾。他举着双手指向前方,远处是市郊一处新建的小区。索尊池用手指着一幢装修高档的别墅,讲述他用汽油点燃建筑材料,然后引起一场火灾的过程。手铐影响了索尊池的动作,也影响了他的舌头,使得他在叙述时断断续续,显得十分吃力。隐隐约约地,我听见他提到李亚红和魏青山的名字。看样子,索尊池在被捕之前,一定吃了不少苦头。节目最后,我的邻居索尊池,这个有着一米七八身高的大个子,竟然坐在地上“呜呜呜呜”地哭起来……索尊池随后被警察拖走了。
那段节目到此为止,接下来插播了一条广告。利用这个间隙,我赶紧去了趟楼下厕所。我重新回到沙发上,广告还没有结束,于是我又想起了索尊池。我总觉得,他在被拖走之前,似乎发现了我。有那么一瞬间,我和他四目相对,我甚至想和他打一声招呼:“嘿!伙计,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当然,这句话显然是废话。难道警察会允许他随便跟我聊天吗?况且,当时索尊池的眼睛布满泪水,就算他能认出我,隔着屏幕,我在他眼里的形象也一定是混沌不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