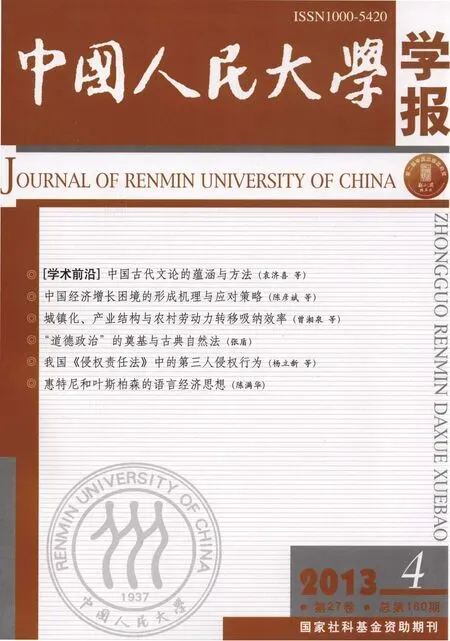否定词的实质与汉语否定词的演变*
张新华 张和友
一、否定词无实质
关于否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柏拉图以来的看法,认为否定表示 “别的、其他、相异”,即处于矛盾、对立关系中的另一个。 《智者篇》指出:“非”这个前缀表示与后续词不同的某事物,如“不高”可能表示“矮”或 “一样高”[1](P65)。另一种观点由叶斯柏森所提出,认为否定表示“少于、低于”[2](P325),其阐释更为细致。具体而言,肯定范畴指一定量幅的内涵,否定范畴则指少于该内涵的其他值项。但概括地讲,“少于”无非是一种“别的”,即另一种肯定项。
我们认为,否定范畴根本上是无实质的。肯定范畴是认识及语言表达的基本方式,功能在于编码人们关于外部世界所已把握的具体内容,所以,只有肯定成分才能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例如,“走”指一种具体样式的动作,“大”指事物绵延的一定幅度。相比较而言,虚词所表意义虽较抽象,但仍有确定的内涵,如 “着”表示一种特定的动作进行貌。这种语义内容就构成肯定成分间相互组合的根据。但对否定词却不能在常规的意义上说它指什么,因为它根本不编码任何关于事物的认知内容。虽然我们可以且只能用“空、去除”之类肯定式语词对其进行描述,但这仅是帮助语义解读,否定词自身并不指这些。概言之,否定词的功能只在于对具体肯定项所指内涵做绝对超离,但并不另外指向任何一个别的肯定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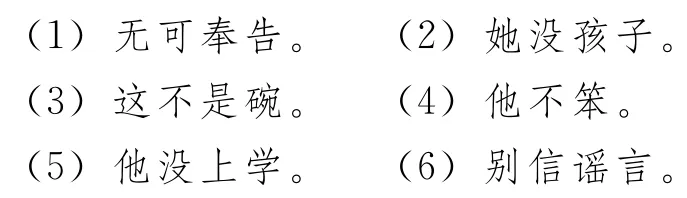
(1)只是指没任何话可讲,但并不同时暗示还有些别的言说内容。(2)是排除她有孩子的事实,并不表示她有其他什么。一个专家对某考古发现的文物,可用 (3)陈述,他只排除了该物“是碗”这个事实,但完全没有确定它是什么。(4)-(5)排除他 “笨、上学”的真实性,并不另外肯定他聪明、他在做什么。因此, (4)的后续句可以是“而是愚蠢”,或别的相关项,但否定自身并不指其任一项。同样, (6)只禁止对 “信谣言”这件事的执行,也并不指出另外怎么做。
从最概括的意义看,肯定范畴的语法特征可归纳为两点:“累积性”、“归一性”。肯定成分总是表示一定范围的实质内涵,这些内涵又总是关联累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例如, “书”指一定范围的具体物质内容,但这些内容并不被视为多,而是视为一,即一个关联的整体。同样,“笑”指一定幅度、具体样式的统一性的动作。一般而言,否定词的作用对象主要是名、动、形等实义范畴,不直接用于虚词。这并非因虚词无内涵可去,只是因其太虚,本不易把捉,去除操作就更难感知了。
否定词确实在不少语境下可解读为 “别的、少于”,但这只是一种日常语用推理,并非否定词的本来功能,其动因有两方面。首先,肯定成分具有外部相关性的特征,即对一个特定的存在领域,语言系统总是会分割编码为不同的语词,它们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松散量域。其次,肯定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否定只是去除而并不另外指向哪里,这就使思维空无所依。这样,对否定式的语词组合,人们往往就会退而求其次,即努力基于所否定项的相关语义域就近寻找一个肯定项作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关于否定指“少于”的解读容易用于形容词、数量词,因为二者表连续量,自然与外面的其他词语构成一个相关语义域,方便就近寻找。但由于这并非否定词自身的功能要求,所以这种推理并不可靠。而对 “这不是碗、别信谣言”这样相关量域不明确的语词,“少于”的解读就很困难了。另外, “少于”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它只适合否定词用于程度高的词语,如“他不高”,可理解为 “较矮”,但对程度低的词语就不适用了,如“他不矮”也是普通的说法,但“不矮”显然不表示“更矮”。
二、汉语否定词的分类与演变
(一)否定词的分类系统
否定词功能分化的根据只在于对不同类型肯定范畴进行去除,所以,理论上说,一种语言的肯定范畴分化为多少种,其否定词就可形成多少种。因此,虽然语言系统中的否定词数量很少,却构成了与整个肯定成分相对的另一极。当然,具体语言既可用一个否定词对多种肯定范畴做统一否定,也可在不同范畴上分别编码。绍兴话、上海话、广西北海话及英语等属于前者,汉语普通话属于后者。英语一般谓词、完成体、祈使句都用not。汉语则分别编码为 “不、没、别”。历史上,汉语否定词的分化更复杂,形成更为严整的系统,并直接平行于其演化的过程,如 (7)。

需指出的是,这个系统是一种泛时的逻辑归纳,并非共时层面的现象,每个具体时代或特定方言都只从整个否定词系统中选取了不同的成分。下面分别说明。
“无”只是作为否定名词的代表,并非指其为历史上的最早形式。否定名词是否定范畴的初始形式,直接指称一种绝无物质的事物状态,对应于普通名词所指之 “物”。在初始阶段,并非“有、无”相对,而是 “物、无”相对。否定名词与普通名词的差别在于,前者指有特定实质内涵的事物形式,后者则指相对应的纯无内涵的空形式。学界多称 “无指代词”,本文称为 “否定名词”,因其编码方式是指称,并非替代。这一点跟回指性的 “否”加以比较就更清楚。也有将“无”称为 “否定性无定代词”的,并不确切,因为这种否定词所指全空,也就无所谓 “无定”,甚至可以说,因为它是遍指性的,倒更接近类指、定指。
否定动词的功能原理是:原本存在着一种肯定事物,然后再对之进行去除,具体机制后文详述。
否定副词是对述谓范畴的去除操作。汉语否定副词与述谓范畴的分化层级形成更为细致的对应关系,这与汉语体貌系统发达是一致的。“不”是对事物一般存在情形的否定,编码为光杆或未经体貌 (Aspect)操作的形容词、动词组。学界多用意志性、可能性之类说明 “不”的语法特征,概括性都不够理想。例如,意志性不能统一说明 “树不大、他不笨、他不动、石头不动”的“不”,其实意志性只是存在展开的一般性在具有[+属人]特性事物上的表现,这并未编码为一个专门的否定词。 “不”所否定成分的语义一般性还表现在:它可把殊指化的事件强制改变为类事件,如“他不星期天工作”, “星期天”是对“工作”的殊指化,但加 “不”后又反过来指一种一般性的行为模式。比较, “*他不这个星期天工作”不成立,因为指示词 “这个”就把所指事件个别化了,不符合“不”的否定要求。
“未/没”是对事物特殊存在方式的否定,即体貌操作的动词组。语义上, “没”大致相当于“不+曾/了”。体的功能是指出动作的具体进行样式,逻辑上,每种体貌类型都可分化形成一种特定的否定词。但是,实际上汉语否定词主要只是针对完成体作出分化,对其他体貌并未各自专门编码,如对 “V 起来、在V、V 着、VV、V啊V”等就缺乏合适的否定词, “不、没”都不大好。如,“*外面不下起来雨”、 “?外面没下起来雨”,“*不看着电视”、“*没看着电视”都不是好的形式。比较而言,对它们进行否定时用“没”要比 “不”好些,但一般要去掉体标记,如 “没看电视”。“起来、在、着”等虽具体所指动作样式不同,却都指动作的实际进行,都有现实性的特征,因此大致可用 “没”来否定。但因为“没”对诸体貌次范畴作了概括处理,所以就难以推知其相应的肯定范畴。如, “外面没下雨”,不能明确其相应的肯定形式是 “外面下着雨、外面下起雨”,还是 “外面下了雨、外面下过雨”。
“不、没”所饰的都是现实事态,区别只在于现实性的具体化程度,二者都与 “莫/别”不相同。“别”是对虚拟态的否定,包括命令 (“别去那里”)、意愿 (“别没钱”)等。“别”相当于“不+要/用”。
“否”是指代性的,且有独立述谓功能。“否”有两种用法,一是以否定的形式回指前面的述谓部分,如 “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周易》)。二是单独回答问题,如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孟子》)。这个 “否”自成小句,故表述性更强。这两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但在连词 “否则”中仍保留。来源上,“否”是从独立回答问题的否定词发展而来的,甲骨文中就有很多省略前句主动宾部分而仅用“不”或 “弜”的用例,它们在这种环境中很易固化为回指性的述谓功能。
上述系统没提到“非”,它特别用于否定判断句,一种很专门的肯定范畴环境。编码判断关系的典型形式是系词“是”,因此可认为“非”相当于“不+是”。来源上, “非”是其他否定词与某种表示肯定的语气词(如“唯”之类)的合音。
否定词与特定肯定范畴有确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可视为一种功能范畴的标记。形式上,“不”、“没”、“别”都可单独回答问题,代表对应的肯定范畴。从这个意义看,具体否定词的功能内涵可分为两方面:A.纯否定性,B.与具体肯定范畴的对应性。如 “没、别”的B是完成体及道义情态,这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范畴类别,因此“没”、 “别”的虚化程度相当高。而动词 “没”、“非”的B 是肯定性谓词 “有”、 “是”, “有”、“是”指事物的一般性本体存在,其概括程度比普通谓词高,但比指范畴类别的完成体及道义情态低,因此,“没”、 “非”的虚化程度也就相应降低。
以上正是否定词很易发生更替的根本原因,而具体否定词功能成熟的过程,也就是其与特定肯定范畴形成稳定选择关系的过程。起初,否定词往往需借助某种肯定范畴的形式标记的提示,才能实现其功能。如 “未”早期常要与 “尝、曾”等时间副词连用以提示其后谓词的完成义,而后出的 “没”就无需如此。又如, “别”在成熟前也常接 “要”,如 “你别要说嘴” (《金瓶梅》)。 “非”显示了相反的情形。它本专用于等同判断,但后来其中的功能要素 “是”被离析出去,出现 “非是”的分析形式,如 “及见他鬼非是所素知者”(《论衡》)。这也就是把 “非”用为“不”了,因而 “非”被淘汰。
(二)否定词演变的一般情形
词形上看,古今汉语否定词数量众多。杨伯峻、何乐士所列单语素否定词就有20个之多:不、非、弗、否、棐、匪、毋、勿、无、罔、亡、蔑、靡、莫、未、末、曼、没、休、别。[3](P320-330)这 显然只是一种历史的汇集,并非一个共时逻辑系统。但即便只基于特定文献,如果只作现象上的排列,也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系统,因为其中多有功能交叉。据已有研究,甲骨文否定词有“不、弗、亡、勿、毋、弜、非”等,其中就有大量的重叠现象[4][5]。下面以 《尚书》“罔、无”为例对古汉语否定词的功能不稳定现象略作观察。 “罔”在 《尚书》中很常用,有否定名词、动词、副词三种功能,且副词功能又可进一步分为一般副词、完成体副词、禁戒副词三种,如:
(8)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名词)
(9)今其有今罔后。(动词)
(10)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一般副词)
(11)羲和尸厥官,罔闻知。(完成体副词)
(12)吁!戒哉……罔游于逸。(禁戒副词)
类似地,“无”在 《尚书》也几乎具有 “罔”的全部否定功能,如:
(13)我无以告我先王。(名词)
(14)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动词)
(15)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一般副词)
(16)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禁戒副词)。
可以看出, “罔、无”首先都有名词功能,而副词功能与名词是有联系的。另一方面,同书又用其他否定词表示诸功能,如 “不、弗、未、非、匪、棐、莫、勿、毋、靡、蔑”等。实际上,否定词功能重叠的现象并不只在古汉语中存在,而是贯穿整个汉语史,如晚清 《儿女英雄传》禁戒副词还用 “别、莫、休”三个: “你别着急”、“你可莫怪我鲁莽”、“快休如此说”。直到现代汉语,否定词的个体选择才基本稳定下来。
历史上,汉语否定词的演变现象相当复杂,但主要是围绕 “亡”类否定名词进行的。 “亡”自身作为否定词消失很早,但后来出现的同类否定名词数量却很多,如 “罔、无、莫、蔑、靡、末”等,而其中每一个都可演变出整个否定词系统。杨伯峻认为, “亡、罔”古音完全相同,“莫”与两者则为阴阳对转关系,说明它们是同源的[6](P473-474)。徐丹指出, “亡”的否定词用法在战国后期为 “无”所取代,自身则转而指 “死亡”义[7](P64-72)。 《尔雅》指出, “靡、罔,无也”,《小尔雅》则指出,“未、没,无也”。后沿用的主要是 “莫”,它从古到今分化形成了否定系统的所有功能,是 “不”之外另一个生命力最强的否定词。另外,综观汉语史,否定词演变又显示了轮回的特征,即很早就有一套大致完善的否定词系统,但后来又不断地重复演化、选择。例如,禁戒副词很早就采用 “勿、毋”,二者后来被 “莫、休”取代,进一步又为 “别”所替换。又如否定动词 “无”、副词 “未”后来替换为 “没”。演变到最后,所有否定词中基本没变的只有一个 “不”。在特定时期内,演变又具有很强的单向性:否定名词不断向动词、副词演变,却无反过来的现象。
克罗夫特对否定词的演变现象做了跨语言考察,分出三类语言。A 类,无专门的 “存在性否定成分”,存在否定用肯定性存在谓词加上否定副词来表示。B类,仅有一个专门的存在性否定成分。C类,存在性否定成分与否定副词相同。克氏指出,三种语言间形成循环演化的现象。[8]可以看出,专门的存在否定成分 (如汉语的否定动词“无”)在该演化过程中占有枢纽地位,但克氏未指出否定名词,实际上,这种否定词才更为初始。另外,克氏所述否定词演变只有三个环节,而涉及的实际成分则只有两个:一个动词性否定成分 (“无”类)和一个否定副词 (“不”类),语言事实过于简单。显然,汉语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这就更便于我们深入了解否定词功能分化的细微之处。
汉语学界也已论及否定词的分化现象。吕叔湘认为, “弗”合为 “不”,周秦的 “不”变为“否”,“没”出于 “勿”,禁戒之 “毋”由有无之义引申而出。[9](P73-102)王力指出, “不、否、弗”实同一源。[10](P102)不过,学者们并未对其分化的具体机制做深入分析,下面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三、否定名词的动词化及遍指操作
否定动词由主语位置否定名词演变而来,有两种情形:一是小句引入一个指论域的词,二是引入另外一个回指成分。其中,否定名词都与论域形成一种遍指的操作关系。
(一)论域词的引入
从现存文献看,否定名词主要出现在两种位置:主语、介词宾语。先看主语位置。
(17)王孙亡弗褱井(型),亡克竞厥烈。(《班簋》)[11](P67-71)
(18)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尚书》)
(19)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
(20)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
(21)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
(22)夫二国士之所图,无不遂也。(《国语》)
(23)罪莫大焉。(《左传》)
句中否定名词都是单个语素,即以综合的方式直接指称一种纯粹的空无物质,并不另外替代什么。现代汉语缺乏编码这种观念的词汇形式,所以无法直译,理解为 “无人、没有谁、没有什么东西”之类都是用分析式的句法手段解读,接近英语nobody、nothing,并不符合当时的语言心理。(23)“罪”为话题,“莫”为主语,形容词“大”充当谓语,句子表比较,意为 “在罪这方面,无任何别的大于它”。这种用法在先秦很普遍,如果把 “莫”解作 “不”,即 “罪不大于它”,句子意思就完全改变了。
语义上,主语位置否定名词的论旨角色多是施事,这与普通名词并无不同,差别在于所指事物的具体性。普通名词指一种具体事物,故与谓语动词有语义上的选择关系,而否定名词指纯无,因此与动词无搭配限制,其具体语义只是由特定谓语动词临时赋予的:上文 “无”后所加“人、谁、东西”之类就是通过与动词的关联而推理得到的。从现存文献看,未见否定名词充当动词宾语的实例,原因可能是后来汉语否定名词的功能确实退化了,而与宾语相比,主语是名词更典型的句法位置,所以还有保留。有些否定名词虽句法上是主语,但语义角色为受事,似乎是其本可做宾语的痕迹,如 (21)。成语 “无可奉告”也是如此。
否定词作介词的前置宾语,该介词词组修饰其后动词。如:
(24)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尚书》)
(25)善哉,蔑以加焉。(《国语》)
(26)不善蔑由至矣。(《国语》)
(24)两个 “罔”都是名词,前句 “罔”作主语,后一小句 “罔”做 “以”的宾语。 (25)的 “蔑”是答话时凭空提出的,很难说 “以”后承前省略了别的宾语。语义上, “蔑以加”大致相当于英语的 “with/have nothing to add”,(26)的 “蔑”做“由”的宾语。
有学者对否定名词功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认为应视为副词。我们认为,至少以上两种句法位置的否定词应确定为名词。更重要的,这种小句在语义上都有强烈的遍指义,持副词观点的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但副词说是难以解释遍指义的来源的,而否定词并无自身实质,硬性规定其内在包含遍指义,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否定名词的处理策略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
否定名词独立做主语是一种绝对用法,但观念上,人们往往会把 “无”理解为相对于某种具体事物的 “无”。如果将这个所无的参照事物指出来,在否定词之前就会引入一个表论域的词,后续含否定词的小句针对该论域进行说明。这种用法很普遍,下面略举几例:
(27)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尚书》)
(28)允若茲,嘉言罔攸伏。(《尚书》)
(29)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
(30)周馀黎民,靡有孑遗。(《诗经》)
(31)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国语》)
(32)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
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
否定名词本指一种空泛的纯无,其前面的词语指出了一个特定的事物范围,即论域,因此这种语义关系一般可理解为 “…中/方面”,或 “对于…”、“就…而言”。(27)论域词“人”是泛指,其后“莫己若者”对 “人”进行限制。 (28)中“罔攸伏”对“嘉言”进行说明。(29)-(30)结构相同,“莫非王土”是论域“普天之下”的说明,“靡有孑遗”用来说明“周馀黎民”。(31)中“小大”名物化作为“莫不怀爱”的论域,(32) “天下”是大主语,指天下所有的东西、人,“莫”为小主语,句子形成话题链结构。
上述各句中否定词都有遍指义,其根据就在于肯定范畴的基本语义特征及否定词的功能方式。如前述,肯定成分必指一定范围的内涵,刻画为X {a,b,c…}。否定名词指相对于X 而全无其 “a,b,c…”的空无状态,这就表现为一种穷尽性去除的操作关系,故形成遍指义。在“论域+否定名词小句”结构中,论域与否定名词间的遍指操作是隐性的,小句也可用显性形式予以标明。这有宏观和微观两种方式,前者是自外而内的操作,即直接从外面对论域事物整体作遍指运算,形式上用 “凡”、 “普”等修饰,如:“凡厥庶民,无有淫朋”(《尚书》),“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普”、“率”、“凡”的着眼点是全体,否定名词则向内对其成员做彻底去除。另一种宏观式操作是用否定词,如 “无野人莫养君子” (《孟子》), “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无”、“非”用于排除论域所指事物,后面的 “莫”、“无”则指其外为全无,所以表现为强调唯一性。下面集中讨论微观式,其与否定名词动词化的关系更密切。
微观式是自内而外的操作,就是先指出构成论域的一个内部单元,然后再用否定词去除,从而达到取消全体的目的。微观单元是累积为宏观整体的起点,无前者即无后者。微观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其中不少与否定词后来都形成固定搭配。
1.数词 “一”或“一+名”
(33)死生利若,一无择也。(《墨子》)(34)一民莫非其臣也。(《孟子》)
“一”指极限小量,是构成事物的起点,去除这个起点,整个事物也就不存在了。
2.无定代词“或”
(35)夙夜罔或不勤。(《尚书》)
(36)图厥政,莫或不艰。(《尚书》)
(37)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尚书》)
(38)何斯违斯?莫或遑处。(《诗经》)
(35) “或”指论域所表事物中的任一成员,(36)解释为 “治理政事,没有一件不是艰难的”。“否定名词+或”是一种较典型的格式,这种搭配具有语言化石的性质,一些名词用法保留不多的否定词如 (37) “未”出现在其中,也可处理为否定名词,小句解释为 “没有什么人不亡国”,这提示了其名词源。有人把 (38)“莫或遑处”直接读为 “不敢稍住”,这是一种意译,按结构关系应为 “无任一地方可作驻留”。
3.指示代词“之”
(39)及殷、周,莫之发也。(《国语》)(40)楚君之惠,未之敢忘。(《左传》)(41)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荀子》)
“之”的功能与前述 “或”相同,二者可互换。也有 “之”、“或”一起出现的,如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周易》)。这显示了用一个显性形式指出论域内部成员的强烈动因,但用两个成分其实冗余。“否定名词+之”后来也成为固定搭配。
4.疑问代词
(42)封疆之削,何国蔑有?(《左传》)
(43)何莫由斯道也?(《论语》)
“蔑”回指句首 “封疆之削”,但指其空无方面, “何国”指论域的一个下位事物。疑问代词是在一定项目范围内做逐一搜索,最终却不落在任一成员身上,因而形成遍指义。
上古各种否定名词都可用表示肯定性存在的动词“有”陈述,这个事实也表明,否定词自身并不指任何存在方式的实质性内涵,而只指一种纯粹的空无。有学者把近代汉语 “没有”组合视为 “没”发展为完成体标记的重要证据,看来不足为凭:上古 “罔、靡、蔑、无”等都常与“有”组合,这与其跟其他普通动词组合在句法性质上没什么不同,据此显然不能得出 “罔”等都成为完成体否定词。
(二)否定动词的形成
在论域 (NP1)、否定词、回指成分 (NP2)间,后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直接决定对否定词的定性,而NP1总是居于句首,是一种话题性成分,与否定词的关系较疏远。逻辑上说,对否定词和NP2间的关系,语言系统可有两种处理策略:一是把否定词解释为一种纯算子成分,NP2是一种待量化的成分。这就把二者纳入一般偏正结构,英语的no-one、no-thing 选此策略。二是把否定词解释为一种笼统的表取消作用的实义动作,NP2指有待取消的事物对象。这就把二者纳入一般动宾结构关系,汉语做此选择。 “no one”与 “无一”所指观念全同,但语法属性不同,可见,否定词的语法功能并非根据自身的概念内涵,而是基于肯定成分的反向类推。
否定名词在无回指成分的小句也可动词化,途径是:论域词充当全句主语,否定名词直接动词化,原来的谓语部分名词化,并充当前面否定动词的宾语,小句形成普通的主动宾结构。这有两种情形,一是自指,即指一种名词性的事态,二是转指,即指该事态的参与者。如:
(44)天难谌,命靡常。(《尚书》)
(45)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尚书》)
(46)故五行无常胜。(《孙子》)
(47)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左传》)
(44) “常”是自指,小句解释为 “天命无常”,(45) “常怀”是转指,小句解释为 “民众无常怀的人”。(46) “常胜”是比较典型的指称性的事件。实际上,由于缺乏明确的形式标记,这种否定词有歧义。如, (47) “无”可看做名词,指“无任何人”;作动词, “相渎”指称化,表示一种事情;作副词,解释为 “不”, “相渎”保留谓词身份。谓词指称化也常用 “者”加以标明。如:
(48)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
(49)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管子》)
“无”、 “毋”为动词,其后部分为其宾语。不用 “者”, “无”、 “毋”就更倾向于作否定名词,后面的动词组做其谓语。但用 “者”并不能肯定 “无”、“毋”为动词,因为 “者”也可视为与 “无如寡人之用心”、 “毋敢立私议自贵”组合,这样,“无”、 “毋”仍可作名词解。要完全确定否定词的功能分化情况,须跟当时整个语言系统的发展联系起来看。
吕叔湘讨论了 “毋”在祈使句用作否定动词的情况,与上述情形同理。吕先生认为 “毋”后动词皆可视作名词,换言之,即 “毋”可看做动词。语义上, “无有如此之事”,也可说成“勿为如此之事”。形式上,禁戒及悬拟之辞亦有作 “毋有”者: “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尚书·洪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礼记·月令》)。[12](P73-102)先用 “有”提示肯定性的存在义,再用 “毋”进行取消,因为 “毋”自身只指一种纯粹的否定性。
不管宾语指事态还是事物,否定名词动词化后在语义上都有一个重要改变:作为名词,与前面的论域词构成回指关系,小句有明显的遍指义;作为动词,直接与其后指称短语组合,而失去回指关系,小句无遍指义。
以上小句环境显示了否定动词形成的初始状态。同时,这种否定动词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否定词。这表现在其所述名词的指称特征上:主语指一种集合或类义性的东西,个体性程度低,如“民、命、邻国之政”。宾语指一种自身独立的个体,或一种抽象的事态、属性,并非典型的构件性成分,如 “敢立私议自贵者、常”。这样,主语对宾语的具体控制关系就不显著,即否定动词不具有太多实质性的语义内涵,因为这种实质性内涵会使否定词改变为肯定成分。
否定动词的进一步发展是主语指处所、个体事物,宾语指存在物、构件、财产、亲属等,小句表示普通的所有关系。如: “川无舟梁、道无列树”, “谁谓雀无角、谁谓女无家、之子无裳、人无兄弟”(《诗经》)。在各种否定词中,主要只是 “无”发展出这种用法。 “莫”在整个古代汉语都未见普通名词做宾语的用例,但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却有,如“莫啥子关系哟”(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再如河北邢台方言无否定词“没”(mei),否定副词、动词都读mó,如 “他mó去美国”,“他mó好车”。
到了指 “整体—构件”及 “处所—存现物”事件的阶段,否定动词也就走到自己的反面,逐渐转变为肯定成分了,因为它获得 “缺乏”、 “丢失”之类的实质内涵。上古的 “亡”和现代的“没”都发生了这样的改变。如“没”可带完成体标记并单独做谓语:“他的车,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骆驼祥子》);后带补语“不了”:“成绩不讲没不了”;用于把字句:“傻根儿把钱没了”。与普通动词一样,这个“没”还可虚化为准体标记,如“他的钱用没了”。
因此,像 “雀无角”、 “他没钱”的说法,“无”、“没”都非地道的否定词,而是一种指消极义的存在动词,其概念结构可刻画为:“不”+“有”。可比较英语:英语缺乏汉语 “无”、 “没”这样的否定动词,而采取have not或don't have这样的形式,have 指肯定性存在,类似汉语“有”,not是副词,表纯否定,类似汉语 “不”。历史上,汉语也采取过 “不有”的说法,如 “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尚书》), “无国而不有治法” (《荀子》)。 《玉篇》释:“无,不有也。”在假设复句中, “不有”形式沿用很久,如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世说新语》)。吕叔湘指出,直到今天,云南方言仍使用 “不有”的形式。
跟否定动词的概念结构为 “不+有”一样,“非”等于 “不+是”,所以 “非”也不是纯粹的否定词,而有普通动词的特征,如可带宾语:“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这种用法是对 “非”中的实义要素“是”做了凸显,显示了 “非”向肯定成分的靠拢。
最后谈谈否定名词的副词化。动词短语(VP)前名词副词化是一种常见的语法化现象,否定名词也是如此。这种演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其前名词由表复数、集体、类义事物改为指个体,或者论域不明确,在此情况下,否定词就不能回指,这就迫使它向后面的动词方面寻求解释。至于该副词是表一般否定、完成否定、禁戒否定,则根据其后VP 而定,而并非由否定自身决定。如:
(50)朕德罔克,民不依。(《尚书》)
(51)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诗经》)
(52)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庄子》)
(53)死吾君而杀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国语》)
(54)自此其父之死,吾蔑与比而事君矣!(《国语》)
(55)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史记》)
(56)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史记》)
(50)主语 “朕德”是抽象名词,一般理解为单数,因此 “罔”不能读为回指用法,这就迫使它向后解读为动词 “克”的修饰成分,又因语句为完成义,故可解释为 “我的德行还不能胜任”。但是,我们也可认为德行包括很多方面,那么“罔”就可理解为否定名词 “无一”了。同样, (51)的 “他人”如作复数,那么 “莫”就可作名词,如为单数,则 “莫”解释为 “不”。(52)“莫”与前句 “不”对举,可看做副词,但观察全篇,发现 “莫”在 《庄子》出现一百余例,绝大多数是名词,少数近似禁戒副词,基本无一般副词用法,因此该句 “莫”仍是名词。(53)“蔑”前是 “吾”,单数,这样 “蔑”就不能回指,而只能向后看做动词部分的修饰语,功能相当于 “不”。 (54)虽其前也出现 “吾”,但“蔑”并不回指它,而是指一般性的无人,因此仍是名词。(55)否定词前有论域,“莫”读为名词很自然。而 (56)论域不明确, “莫”就无所回指,因此作一般副词。
语义上,在 “否定名词+VP”组合,由于否定名词是遍指性的,所以句子指一种一般性的事实,而在 “否定副词+VP”组合,否定副词指谓语动词的进行情况,所以句子指当下存在的特殊事实。
英语not也由no 演化而来,大致途径为:初始形式是I have no word,后出现I have no one word,no one本是对名词word的遍指操作,类似前述古汉语的 “无一/或”,后来,“no one”合为一个词形not,并向前解释为动词have的修饰成分,因此成为副词。语义上,no否定句表一般情况,not否定句则表特殊行为,这跟汉语否定名词、副词的区别也相平行。
四、方法论的总结
否定词无自身语义实质,其功能分化只在于所组合肯定范畴的不同。方法论上,用 “少于、别的”说明否定词都是将其改变成了肯定成分。本文第一部分探讨否定词的功能实质,这是一种共时逻辑的视角,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接着,则以否定名词为基点,以所在的句法环境为根据,探索汉语否定词功能分化的机制,这表面上看是一种历时演化的视角,根本上仍是共时实质的推导。原理在于,就单一语言而言,其不同时期演变形成的众多否定词,也就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实质系统,因此,这也是一种类型学的思路,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概言之,共时是对历时的静态汇聚,历时是对共时的动态展开。共时看,虽然整个否定词系统不一定出现在现代汉语某单一方言中,但如着眼于众方言,可发现它们仍被不同地选择使用着,而这种选择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更大视野看,世界上不同民族语言系统否定词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本文是严格在否定词系统内部讨论其分化情况。逻辑上说,否定词不编码任何实质内涵,这在认知上显然是很难处理的,那么,在最原初阶段,是不是否定词由肯定成分演化而来,确实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这在中古出现而后淘汰的“休”上略见端倪。“休”本是肯定成分,如 “按甲休兵”,后因失去实义内涵而成为否定词。可进一步比较 “少”,它更微妙些:尚处于去内涵未彻底的中间阶段,故接近 “别”但不成熟,如“少管闲事”。这种演化比较自然,但语言系统是相当古老的,并非所有否定词都是这样直接形成,更多的情况应是系统内部的分化。
[1] 柏拉图:《智者篇》,载 《柏拉图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 O.Jespersen.ThePhilosophyofGrammar.Chicago &London: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4.
[3]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4] 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
[5] 朱歧祥:《殷墟卜辞句法论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6] 杨伯峻:《上古无指代词 “亡”“罔”“莫”》,载 《中国语文》,1963 (6)。
[7] 徐丹:《上古汉语后期否定词 “無”代替 “亡”》,载 《汉语史学报》,2005。
[8] W.Croft.“The Evolution of Negation”.JournalofLinguistics,1991,1(27):1-27.
[9][12] 吕叔湘:《论毋与勿》,载 《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1999。
[10]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武振玉:《两周金文中的无指代词》,载 《长江学术》,2006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