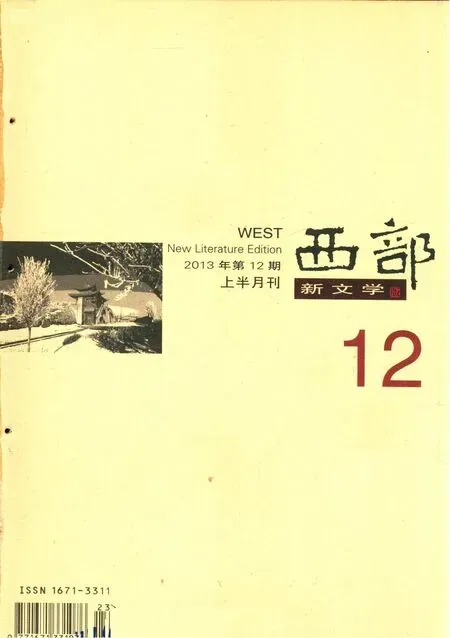木桶(外二篇)
李成林
偶尔逛市场,商品琳琅满目。一家店铺经营的木桶,竟让我如获至宝,挪不开脚步。
那本色天然的木纹,经过加工打磨细腻如脂,即或是桶底桶壁瑕疵的各色木节疤,也浑然一体,成为天然的图画。无需打磨,都让人感到那是树木闪烁灵性的眼睛!
店主是个精明的四川人,我的老乡。一百元钱,就请回了一只大大的实木桶。人有人缘,物有物缘。回到家一想,这木桶与我缘深,我买的何止是一只木桶,还结识了一位四川乡下来疆的老乡。

这只木桶,实在是非常实用,泡泡脚上的老茧最是相宜,即或是不用作泡脚,放在我的书房一角,也是谐和的工艺品,朴素而又华美,简洁而又庄重。夜里看书写作累了,四野的风灌将进来,空空的木桶与之相应和,传出隐隐的松涛声,尤其是在暗夜里,由木桶散发出的木香,让人深深迷醉。一只木桶,复活了我多少乡间生活的往事!
我生活的乡村有个习俗,叫“洗三”。百度一下,这个习俗就更不得了,原来,“洗三”是中国古代诞生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婴儿出生后第三日,要举行沐浴仪式,会集亲友为婴儿祝吉,这就是“洗三”,也叫做“三朝洗儿”。其用意,一是洗涤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祥求福,图个吉利。母亲生下我后的第三日,就用一只大木桶为我行了“洗三”。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艰难人世,我之所以每每能逢凶化吉遇呈祥,是不是也是拜这木桶所赐呢?
能做木桶的一棵大树,一般是选树身至根部一段木料。树材选料也较考究,主要选树质密实的香柏木。别看木桶工艺并不复杂,考量乡间一个木工的水平,就是看他能否打造出一挑不漏水的木桶。若能,便可以出师,为乡亲们服务了。
在乡间,谁家没有木桶呢?贮粮的米桶,挑水的水桶,送肥的粪桶,农业生产离不开桶,木桶与乡民的生活紧密相依,连村姑的陪嫁也有一对木桶。在村里,一个小伙是否长大成人,木桶也是极为重要的考察工具,如果那个小伙子能挑一对木桶从村头的那个古井里打上水来并能挑满家里的水缸,基本上算是过关了,此后就可以挑起粪桶送肥上山,成为一个合格的壮劳力,并能在乡村的农事耕作中训练成为一个出色的庄稼汉。如果说,大地是五谷生长的母体,木桶则是五谷的摇篮,也是最终的衣胞。
在乡间,老农们教训一些败家子也常拿木桶作譬,“有了一顿充,没得敲米桶”。木桶常常作为乡下老人教育子女的“传统”。
说起木桶理论,更是众所周知。盛水的木桶是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盛水量也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若要使此木桶盛水量增加,只有换掉短板或将短板加长才成。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或“木桶定律”,又称“短板理论”。 这是来自生活中的经验,但朴素的道理却是人类运用木桶的智慧的结晶。这个理论由谁提出,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了,但是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却十分广泛,从经济学、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到个人发展。生活中,木桶现象比比皆是,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深谙木桶效应并注意指导人们的工作,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然而,有的人并不懂得“短板效应”,不加长短板,而是锯短长板。这样木桶只有越锯越短,最终不成“体桶”。
我最喜爱的一位特立独行的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据说出生于一个银行家家庭,可他却喜欢住在一个木桶里。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去访问他,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兑现他的愿望,第欧根尼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一阵惊愕的沉默让时间静止下来,亚历山大慢慢地转过身。那些穿戴优雅的希腊人发出一阵小声的窃笑,马其顿的官兵们判定第欧根尼不值一提,也互相用肘轻推着哄笑起来。亚历山大仍然沉默不语,最后他对着身边的随从平静地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愿是第欧根尼。”住在破木桶里的哲学家赢得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敬意,也赢得了我的景仰和崇敬。他住过的木桶与我使用的木桶的形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木桶,不只是一种器物,可以盛水、装物,木桶也是一种兵器,在山地作战中,滚木桶的杀伤力是所向无敌的。木桶无言,胜过雄兵百万。
一只只普普通通的乡间木桶有如此显赫的身世,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然而随着时代的脚步,乡间的木匠渐渐流失了,木桶也慢慢地被化工塑料桶取而代之,淡出了乡村的视野以至难觅踪迹。城里没有多少文物的博物馆里,乡间的木桶也摆进了那里任人观瞻、惊讶、评说。木桶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本色与价值。一个来城里寻亲的乡间老农,在城市的洗脚屋里找到了自己辛苦养大的闺女,他发现那些乡间来的年轻女子一排排蹲坐在地上,用自己柔软的双手在一只只木桶里费力地搓洗着那些不沾泥土害了脚气长了鸡眼的肉脚,老农捶胸顿足,双泪直落。
木桶装天下,木桶见人生。木桶沦落的背后,是农村风物风俗凋敝的缩影,是当今物质精神双重沦落的真实写照。这个木桶买得值,不只在实用,还满载着人生的哲理,时时警醒着我这个住在城里的乡下人。
水缸
乡村老百姓有句俗语“穷灶门,富水缸”。再穷不能没灶,再懒不能没缸。那时,我们家虽然极穷,但却有一口祖传的大缸,而且水缸的水确实非常富有。灶门要穷,是怕失火酿灾;水缸要富,不仅是一日三餐所必需的,而且发生意外时也是救火息灾的水源。不仅居家农户是这样,就连名胜古迹殿前都置放硕大的水缸,就是备消防应急之需吧。
朱子治家格言中第一句乃“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一点在我们家是非常到位和形象的,东方天空才刚刚露出鱼肚白,妈妈便已经起床升起了第一缕炊烟。三哥早挑起一担水桶踩着沾衣的晨露来到村头的古井边,单膝跪地,倾身扶桶,并用扁担钩用力将水桶倾灌入井底,起身提上一挑水挑回来,倒进了水缸。
那口石水缸摆在灶房一侧,占去了大半个灶房。它高及腰胯,一个成年男性伸开双臂也围不住那口石缸。这是全村里最大的一块整石凿成的水缸,十挑水都装不满它。每次挑水,三哥至少要往返七八趟。
从我记事记,这口缸就稳稳当当地摆放在瓦房院子的厅房左侧,如卫士般稳重庄严。它将我从一个个头不及它一半的孩童养到个头高过它一半的半大小伙时,我也能到井边去挑回一担清凉甘甜的井水,倒进这口巨缸里,显示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和力量:我也可以养家活口了!
水缸的石壁厚实,黑油油的,森森的,凛凛的,用手摸一下,只一下就让人深刻地记住了石性的冷凉。这样的石器,盛水却最为相宜,缸中之水涉寒暑不腐不变质。盛夏里,一身热汗地从庄稼地里回到家来,抄起一把木勺或铁瓢从缸里舀起一瓢水灌下肚去,既解暑又消渴,人也不拉肚子,甘甜清凉的水浆胜过矿泉水多矣。缸中之水不见底就要挑水回来,因此缸中水永远都富足得汪洋恣肆。只有到了腊月中下旬的隆重除尘日时,那口水缸的水方才叫它见底,挑一两担净水倒进缸中,里里外外地洗刷干净,一年时光就像缸里的水一样消逝了。
小时候,学过一篇《司马光砸缸》的课文,回家便也学着司马光砸缸,只听咣咣响,缸却完好无损。那口石缸的石质密实,砸它就像鸡蛋碰石头。我砸不动的石缸,在文革中遇到一劫,红卫兵以破四旧之名来搬石缸,缸的巨大沉重,让红卫兵也退兵了,石缸安然无恙。偶尔,我从河溪中捉回红尾鲤鱼,把它放进缸中放养,几尾鱼儿在缸中游弋嬉戏,即或它们静卧缸底、伏于缸壁,也给这古拙的石缸增添许多意趣、生气和灵气。
石缸养水养人,装尽东海水,装满世代情。它滋养了我所有的远祖,也把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养大成人。大哥长到能挑满一缸水的时候,被一个窑场主相中,成了窑场的一名砖工;大姐长到能挑一担水的时候,嫁到了远方他乡;我长大后,还没有尽到给家里挑水服务的职责,便被部队征召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口水缸养几代人,我们都被那口水缸的水养大,即使我们到了远方,饮水思源,也忘不了那口水缸。
前不久,远在克拉玛依的二嫂打来电话,询问那口水缸的下落,我才忽然想起自己已然忽视了那口养育我们成长的石缸。多方打问,方才得知那口遗落在乡村一角的石缸被收购古物的人给收走了,当作宝贝收藏。
石课桌
在乡村,石头上虽然种不出庄稼,但它还是非常有用的,比如铺路的青石板、建造房屋的地基非坚实的石头不可;还有乡里人家的好多器具也非石料不可,比如贮水的水缸、磨刀石、石菜案、猪食槽、洗衣槽等等。在我所使用过的石头器具中,最难忘的却是石课桌。
石课桌只有村小学里才有。我们村小学叫碧龙庵小学,是由一个尼姑庙改造过来的。那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和坐上石课桌的,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村小学离我们小队有一里路,割草、捡柴、放牛时,我们这些还不够学龄的孩子便会偷偷地跑到学校后窗去听和偷窥,看到那些和我们差不多的孩子整整齐齐地坐在石课桌前,跟着老师朗声地念:山石土田、日月水火……那朗朗的读书声比山野里的歌声还要好听,我们又是新奇又是羡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进学堂,坐在石课桌前像唱歌一样地念书呢?
每年暑假期间,学校的老师都要到各小队去招收一批学生。老师招生的办法很简单,到了有孩子的人家,老师拿出一把玉米粒或是石子,若是这家人的孩子能数清楚十粒玉米粒,便被顺利地录取了,数不清的则要等到下一年。
招生的老师到我家让我数玉米粒时,我已经八岁多了,我一气数了二十粒还要往下数时,老师就高兴地把我收下了。我终于坐到了石头做的课桌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学生。
从坐到石课桌前的那一天起,我以为天下所有的课桌都是石头做的。我心里那美滋滋的感受,是不为人知的。这些石课桌虽简陋却结实耐用,两张石板竖立埋入地下,上面架上一张石面光崭的石板,一张课桌便告成功了。我们那所小学有四间教室,每间教室可排下约三十张石课桌,能坐下五十多个娃娃。
石课桌的石材据说来自西河滨,在我们村也只有西河滨的石材是好的了,石质坚硬、耐用。石课桌虽然笨重、粗糙、简陋,但于我们这些顽皮的毛孩子却很相宜。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在教室里打出闹进,课桌就不会像木凳子那样被弄得东倒西歪了。它显示了石头的本色,沉静而安稳。这些用来读书的石课桌用处很多,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和黄泥做哨子吹,用小刀或石子在桌面上划分三八线;用各种软硬笔乃至用旧电池里的黑碳笔芯、石灰石、小碎石在上面写字演算画图,还可以在桌面上画格子下棋、做游戏等等。石课桌对我们宽容、厚爱,它任由我们在它身上撒野,充分发挥山里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和石课桌只朝夕相处了五年,小学毕业后进入乡镇中学,我才发现还有不是石头做的课桌。
如今,那所乡村小学早已废弃不用了,不知那些石课桌又流失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