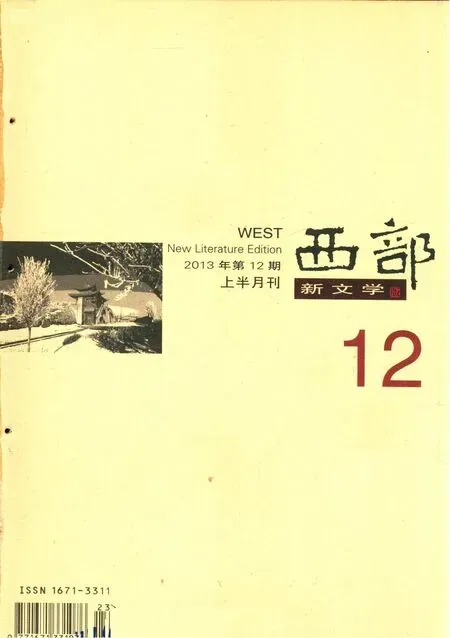七月·湖畔之思
赵荔红
光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湖上的每一日,重复着世界从混沌到光亮、又重归于暗黑。神的光运行湖面,一切便闪闪发亮。神的光运行在我们暗黑内心,一切就会闪闪发亮。
夏日早晨,白雾满湖。山,树,堤,岸,全笼罩在雾气中,混沌,朦胧,事物没有形态,天地灰白一片。静止中,悄然酝酿变化。世界的界分,从一条墨线开始。墨色漶漫,白色渐褪,事物慢慢显露出来。此时若从高处俯视,喀纳斯湖如同一个敞开巨盆,盛着奶泡。突然,光降下,湖面上一块月牙形亮光如镜片。光在扩展、蔓延;雾气散溢、稀薄,世界缓慢地裸露、清晰、起伏、多彩起来。
上午的湖泊是块凝重墨绿的碧玉。背光一面黯淡、哑默、隐忍;面光处,有莹润光泽。光如同微笑,忽隐忽现。湖水并不通透,你的眼睛触碰不到湖心。湖的秘密深藏在醇厚碧血中。清凉的碧血。神的一滴。你翻越多少山脉,度过灼烫沙漠、了无人烟的戈壁,前途茫茫,焦渴万分,马已经跪倒,你就要跌下来,被沙土埋葬。突然,那神的一滴,那清凉的碧血,呈现眼前,如同白色吗哪从以色列天空降下。上帝化为火、为光、为水,显现给世人。人心在苦痛中灼烤,瞬间的美好,犹如甘泉,如这泓清凉碧血,浇灌着它,慰藉着,温润着,让它不至于变得如石头般坚硬,如枯木般焦黑。你宁可是一株易受伤的柔嫩小树,或是如湖中水草柔软地摇摆。
下午六七点钟,阳光依旧猛烈。湖水墨蓝,远山近树都是墨绿色。涌动的蓝光,随风改变,有时向中心汇聚,有时向外层层扩散,有时打乱了节奏如丝线缠绕。躺在堤上,随光波动。趁着你还年轻、完整、美好,就这样被光运走吧!却又慢慢渡回来,还在原处徘徊。太阳从云层露出,万千细密银线,从天降下,在湖面,转变为无数短短的银箭镞,向湖心扎去。假如你眯缝起眼睛,那些银线就连结成一整排银色瀑布,哗哗哗倾泻下来,湖面如同蓝黑绸缎上嵌着无数亮银片,富有节奏地起伏。下面包裹着谜,是你无可抵达的世界。你可以潜到湖底,了解水下暗黑的转折、礁石的粗砺、水草的斑斓;你可以叫出鱼虾名字,分门别类,依旧无法了解湖泊之谜。只有神知道。神的光,可穿透一切暗黑,抵达一切想象。时间越深,湖水反越透明起来,湖岸,山树,晚霞,雪顶,全都明晰倒映水中,湖水将眼睛看到的裸露世界,以倒影、相反的姿态呈现出来。你以为所见的湖,就是真实的湖。在最隐深处,依旧潜藏着你所不知的。只有神的光知道。只要你的心贴近神,就能够感觉到一点点。
这一天就要结束,黑暗又笼罩湖面。但你知道,神的光,凝结为星星、月亮。星星密密闪烁在湖上天空,月光从天降下,又从湖面延展到天空。即使湖被完全的暗黑控制,你也知道,死去的时间会重新开始,明天,光会重新降临。
我们必须有信心,等待,神的光。
林中
这是午后的泰加林小道。如此寂静而活跃!
沿湖畔,密植云杉、冷杉、侧柏、花楸,以及小叶白桦树、扎根在湖中的五针松。高大针叶林和阔叶林混合,将栈道遮蔽得异常阴凉、幽静。那些云杉冷杉的尖顶拼命向上,似要越过阿尔泰山直抵云霄。秋天尚远,白桦叶尚未黄,向湖倾着绿身子,赤脚站在薄薄滑润苔藓上,大张着惊讶而忧郁的眼睛。那些深褐泪水垂挂下来,一直滴落到湖中。喀纳斯湖,盛满白桦的泪。
高树下错杂生长着各种灌木、野草杂花。上千种植物,野芍药、野罂粟、火球花、金银花、低头葱、野蔷薇、龙胆、萤花、紫花苜蓿……随季节、光线变化着色彩,像湖中的鱼变化游泳的姿态,像翻动的日历、人的心情、流变的境遇。我们遇见最多的是黄色柴胡、聚伞形白花独活。蜜蜂忙碌地起降,穿梭在这花那花之间。隐藏在密集草丛中,还有多少我的眼睛没有看见的生命:蚯蚓、金龟子、蚂蚁、天牛、滚粪球的屎壳郎?坐在林中,面向湖泊,湖面泛着碧光;一只鸥鸟俯冲下来,贴着湖面滑翔,又振翅而起,嘴里多了条挣扎的小鱼;风将湖水推到岸边,白浪轻舔着树根、沙粒、苔藓、断枝,发出汩汩啧啧的轻响,水流在树脚打了个转,爬过苔藓,又转回湖中。
并没听见什么鸟鸣。不时间,枝桠颤动,那是一只松鸡、榛鸡?会变羽色的雷鸟、有白斑的星鸦?或仅仅是只乌鸦、最不起眼的两只麻雀,他们震动翅膀,穿越林枝。听说有种黑琴鸡,被称作林中诗人,我很想遇见他——他会像俄耳甫斯,在林中徘徊,弹着琴、到处找寻妻子的魂影吗?也没有正面遇见什么野兽。只是我们行过时,会听见一阵响动,草丛或厚厚树叶下传送着一道起伏的波动,恍惚见到黑暗树荫下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是一只土拨鼠或松鼠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越跳而过?听说在密林深处,友谊峰那一带,能遇见狐狸、驼鹿,身上有梅花的马鹿,甚至还会碰见哈熊(棕熊,饿了一口吞下一只猪仔)。但在这浅近靠湖的泰加林内,只如歌里唱的,“长尾跳鼠轻轻穿过阴凉幽静的森林……”
不时有松果掉落地上,扑扑响。到处躺着松果,圆柱或圆锥形,青中带紫的,是未成熟就落下的。想想看,在春天,雄球果张开鳞片,将黄色或红色花粉随风播撒,一些粉尘被雌果吸附,开始孕育种子。未及孕育便陨落的松果,满怀着伤感,躺卧在松针枯草中。成熟的松果是咖啡色或浅赭色的,鲮片张开,种子已经播种,完成了使命,安静怡然地回归大地。只有成熟的松果,不会腐烂,我捡了几颗,预备带回家。在我的书橱里,还藏着天山、阿尔卑斯山的松果,维也纳一个小教堂边上也捡了几颗。
到处躺着枯木、断根、残枝。在西伯利亚泰加林里,这些浅根性树木种植在疏松土壤上,根无法扎到深处,只是横向伸展。湖水侵蚀,大风摇动,土壤又松,就极易倾倒。在这条小道上,有一块巨大的泰加林木根部,侧卧着,令人惊骇地呈现横向伸展密集的根部世界。当年,那里站立着怎样高大的一棵树啊!你在这样的死亡中看见了他蓬勃的生长,他倾倒时,该发出多么巨大的轰响啊!又有一棵十几米高的云杉,不知何故(雷电?人为?),拦腰折断,裸露着巨大、新鲜、黄亮的伤口。那些躺在草丛中、沙石上的形状各异的陈年块木、根茎,风和鱼也不去顾盼他们,湖水茫然舔过他们裸露的体表,似乎忘记了疼痛,忘记了时间,散发着闷热、陈腐、潮湿的气味。

毡房水草边的马 赵荔红摄
不必伤感!在腐败与死亡中,新的生命正在酝酿。那些断枝枯叶、松果落花,疏松柔软的部分,化为肥料,被大地吸收,滋养别的树木花草。甚至在腐败断枝上,又生长出新绿枝叶;腐木上还冒出各种菌菇,正突突生长着,散发着香气。即便是一时无法腐烂的残骸,一棵折断大树的根部或空心树洞,也成为亿万蚂蚁的家。他们繁忙地进出、劳作、繁殖、死亡。在林中,绝无任何无用之物,飞鸟甲虫的尸体,动物粪便,凋谢的枝叶落花,腐烂树木,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新生命的养分。一边死亡,一边生长。生生不息,无限循环。
沿湖畔小道,在阴翳林中走了一个多小时,尽头是一面山岩。爬上岩石,豁然开朗,潮湿阴翳一扫而光,炙热阳光让人眯缝起眼睛。整个喀纳斯湖在脚下展开,四面山势柔和起伏,包裹着一块翡翠(早上是碧玉),若非游艇划出白亮航迹,她几乎凝滞不动。如此寂静!游艇如鸭,阳光下拢着柔软的钢铁翅膀。远离人众。听不见汽笛声、车声。一只飞鸟也无。湖怪或大鱼,似乎从不存在。只有五针松,士兵般密集站立湖中岩上,青绿草丛乱开着野花。一只山鹰飞得很高,如蓝布上一点墨。喀纳斯以其随季节、辰光改变颜色闻名。但现在,时间消失了,你盯着她看一小时二小时,或是离开好几年,回过头再来看,她似乎依旧如此。只是高阔蓝天,几朵白云,一泓碧水。
好几日傍晚,我们依旧在泰加林小道散步。此地十点才天黑,八点左右,夕阳最好。夕光温暖、淳厚地照进林中,将杉树粗大枝干、草花椅子,染成橘红色,枝叶杂草的影子散乱投在上面,图案奇妙。我最爱坐在木椅上,看湖水黝黑涌荡,水纹银亮波动,白桦枝叶墨黑凝滞的剪影。我们这样坐着,森林一点点暗下,直至漆黑……明早,湖上白雾会溢进林中、填充虚空,鲜嫩的朝阳又会最先照亮哪一株树木?
味
在新鲜的松木香气中醒来,仰望木屋顶,有瞬间迷惑:这个夏日,我身在何处?
穿行门前小径,两边草坡开满野花,野气的芬芳,顺着风,一阵一阵将我迷惑。我能辨识的几种花香,不过是玫瑰、蔷薇、桃花、丁香之类,这里几百种、上千种野花开放,陌生香气让我丧失了分辨能力。好香!贫瘠而抽象的词语如何传达我的感觉?我的全部知觉远不如一只蜜蜂。他们能分辨出每一种花的香味,知晓她们何时开放,循着花香,从数百里地飞聚过来。奇异的是,假如我身上洒了香水,那是由十几种花提炼、蒸馏、调和出来的香氛,蜜蜂是绝不会将我当作一朵花——偶尔一只比较呆气的蜜蜂判断失误,跟着我飞了一会儿,也会断然返身离开,说不定因为气恼蛰我一下——可见蜜蜂是能分辨“人为”或“天然”花香的。也许一朵花,散发的不仅仅是香气,还有蜜、花粉或其他什么?你必须变成一朵花,或一只蜜蜂,才能弄清楚。
何止是蜜蜂。自然里到处是气味大师:卵生在松树上的松毛虫,忙碌地啃吃松针,边啃边吐丝,无论走多远、天多黑,嗅着自己吐出丝线的气味,总能找回家。离散了的蚂蚁,闻到同伴留下的气味,能将食物或同伴尸体,老远地弄回家,分门别类存储。吃草的母马,突然不安地嘶叫,她嗅到了一头狼或哈熊靠近的气味,威胁的气味。我们朝水草边的白毡房走去,几百米远一只大狗,大声吠叫着朝我们奔过来,却不扑上身。他是嗅到了我们身上的陌生气味,同时又明白,并没多大威胁,不过是吓唬吓唬我们罢了!毡房边一棵树,系匹马,我试图抚摸他,他就歪着身子斜着眼打着响鼻,不停地踢腾蹄子、想挣脱绳子。主人说,马不熟悉我的气味……人原本如昆虫动物般具有敏锐嗅觉。“嗅闻”等同于“亲吻”,恋人们搂在一起嗅嗅闻闻,就足以诱发情欲。可是我们闻惯了汽油、香精、化工产品的气味后,就丧失了对自然之味的分辨和体会能力,剩下香水师、品酒师之类,将它当作一种特殊技艺。
在这森林草坡中,我的嗅觉慢慢醒转。除了野花香气,还有松针、松果的青涩香味,蔓生杂草的气味不算明显,但我很喜欢闻除草机新割过的草坪那种短簇尖新的草香味。草坡上翻飞着赭黄底子白黑斑点的蝴蝶,她们的翅膀扇动起粉尘之味,嗅了会咳嗽不停。走在栈道草丛,不小心就踩到马羊牛粪便,气味并不如圈养牲畜那般恶臭,那些散养的马羊牛,日日啃吃的是新鲜杂草野花,粪便也散发着甜甜的草腥气。越挨近毡房或木屋,粪便的草腥味越浓,混杂着牲畜身上暖烘烘的膻气。哈萨克族的白色毡房往往临溪搭建,蘑菇般独立在一片青绿草坡中,四面环绕着云杉或冷杉树。挨近毡房,各种气味扑面而来,马羊身上的膻气,木桶中盛放的羊奶、牛奶的奶味,风干的羊肉味,放置在木架子上晾晒的奶酪的酸味,燃烧的干粪便有干燥、烧焦的香味。若是走进一间新盖的图瓦人木屋,红松木的浓郁芳香沁入心肺,木栅栏前摆设着巨大的烤馕炉子,燃烧的松木兹兹地冒着松脂油,散发出焦香,烤馕的麦香味弥漫到大路上,几百米远都能闻到。在这里,人的味道,与动物气味、植物气息混合。人的味道,即是自然之味,就像毡房木屋,与森林草坡河流牛羊,如此协调而充满生命力地安置在一起,都是神的作品。
每天,我在松木香气中醒来,顺着野花香气的小径走到喀纳斯湖边。早晨的喀纳斯湖,白雾从湖面缓缓漫溢到林中,送来清凉而空旷的味道。朝霞的,白云的,湖水的,树木和草坡的味道,我深深呼吸,似要将山水之味努力吸收、蕴藏在身体里。但我嗅闻不到湖中大鱼的味道。是汹涌的密集的腥气吗?是火红熔浆般的味道吗?他们下潜到了哪里?在这白雾之下,湖水之下,平滑暗黑之下,在最深最僻隐处,裹在淤泥、湖藻、枯木之中,那种味道一定是深沉的、久远的、浓烈的。弥散亿万年的谜怪之味,或是神灵之味,岂是生命不过百岁的世人可分辨的?
午后,被阳光熏蒸了一上午的湖畔,弥漫着湖水热热的潮气,湖沼淤泥的土腥味,湖边枯木的陈腐味,闷热的泥土枯叶相杂的气味,同时混合着晒软的野花草叶的沉醉香气,树叶树脂的甜香,以及腐木上生长的菌菇香气。三个采蘑菇的十几岁少女,挎着篮子笑着说着从我们身边行过,她们的汗味和篮子里的菌菇香味轻柔袭来。遇见陌生的我们,少女们羞涩而好奇地朝我们看,如同歌里唱的:“哦,我的黑眼睛,一遍遍望你望你……”我也看她们。少女的黑眼睛,纯净又茫然,空无一物,又似蕴含千言万语。那摆动自然、小而结实的身体,成长着我所不知的未来,如同这山川、草坡、湖泊,散发着陌生芳香,我嗅闻不到她们秘密的忧伤或喜悦之味。盘旋空中的山鹰却知道。
这里所有的,生命之味,时间之味,自喀纳斯湖存在就有了,自它未形成之日就有了。
木屋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边上,德国的黑森林里,有个小木屋,他背着手,在那里散步、沉思,写下《林中路》,他是在阳光折叠进檀木林、嗅着龙脑树的香气写下那些文字吧?梭罗有一日,提了一柄斧头,去瓦尔登湖畔,造一个木屋子。他种豆子、钓鱼、任风拂面一上午,听鸟鸣叫,独自微笑。
我终于在七月,也住进喀纳斯湖畔的一个木屋子。
喀纳斯木屋,有三种。一种是供旅客“家访”的,以展示图瓦人的历史、生活、风俗、歌舞等等。在那里,我听到,湖怪之谜、捕捉大红鱼、狩猎哈熊……我听说匈奴人呼这片蓝色湖泊作“斋桑淖尔”,意思是“大海上的铃声”,那是马背上的民族穿越戈壁、沙漠,蓦然见到清凉湖泊的惊喜。我还听了楚吾尔,吹奏者将嘴角贴近一种轻薄草管,按捏三个洞,发出颤动的呜呜乐音,或低沉悲凉,或高亢尖锐,模拟种种自然之声,让我想起希腊传说中的芦苇牧笛……的确,我在木屋中听到了许多动心的事。这样的木屋,铺了绣花地毯,墙壁挂各种动物皮毛、猎枪、雪橇,几上摆着油果子,客人席地而坐,表演或讲解者穿民族服装站在中心。热闹的木屋,崭新,却已是一种商品仓库、种族标本。当一种文化被展示,被游客猎奇地匆促一瞥时,文化中鲜活的部分已不存在了。这样的木屋,我只进去一次。

早晨雾中的喀纳斯湖 赵荔红摄
一种是当地图瓦人住的木楞屋。禾木、白哈巴一带较多,喀纳斯河边也有。禾木我没去。白哈巴那儿,有的单独尖着顶站在山坡上、蓝天下,在青绿草场、墨绿杉林之中,简洁漂亮;有时它们排排站在一大片平整草毯上,远远俯视,如同青灰瓦片或鱼鳞排列在阳光下。挨近了看,上部是等腰三角形屋顶,灰黑木板架立,下部为正方形,四面墙壁皆以原松木垒就、苔藓抹缝,冬暖夏凉;往往保留松木的树皮、结疤、松黄色,质朴而扎实;有些墙壁用的是松木板,精细些。一幢木屋,往往有两个木窗,一扇木门敞开,如人安静蹲坐,睁着眼、张着口,又有木栅栏在门前围出空地,散落走动些自家马牛羊狗。这些木屋,如同杉树草场,是自然的一部分。你看见了它,却对它一无所知,因为木屋中图瓦人的生活,你是无法触及的。即便作一次所谓深度访问,甚至与主人度过数日,以外来者口吻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你依旧是个旁观者,与那些木屋隔膜。因为你不是牛羊的主,不是木屋的主。你只是远远看着,有时它们在烟气中发蓝,有时候被阳光染成金黄色,有时白雪牢牢覆盖只露出黑洞洞窗门。湖怪于图瓦人是神灵、护佑者,亲近而敬畏,对外来者言,不过是雨后彩虹,添加些神秘,引动些口沫。假如我们对他者文化、对湖怪,仅仅有些浮皮了解,又过度阐释,这种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对我们的生命、对图瓦人,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确是很羡慕拥有那样一幢独立于草坡的木屋,但图瓦人的日子,又如何嫁接到我这样一株植物身上?
我们住的木屋,是管委会提供给客人住的木屋别墅。一套两间,主体材料是混凝土,辅以带树皮的松木贴面,外观与图瓦木楞屋一样,质朴、本色,又避免了松木易腐烂、蛀蚀的缺点。内部装潢是上了亮漆的松木板,散发着好闻的松木香气;陈设雅洁,有最现代、最舒适的一应生活设施。让客人既能体味湖畔生活的自然,又不离开习惯的干净舒适。对于我这类来度假的城市人,也许是适宜木屋生活的。我自视自己,并不能够如梭罗,操一柄斧头,一无所有,到森林中,造一个木屋住下来。梭罗的木屋只有一床,一椅,一桌,以及满足生活的最基本用品。他主张去除一切多余的装饰、华美、享受,只要能遮雨保暖维持生命必需即可。他以为人为了积累财富而忙碌的生活是绝望的,一切为了交易的劳动是无必要的。他甚至让他的木屋与所有邻居保持一英里距离,认为与人交际,远不如与花鸟树木湖鱼交往自在。
我承认,我缺乏梭罗的勇气、毅力、智慧,更因为我不信奉他那犬儒派哲学的一些极端主张、清教徒式的严苛。假如造一个木屋,仅仅为了遮蔽风雨,他为什么不学他所说的爱斯基摩人或印第安人一般,裹着衣服在雪地里睡着,或挖一个洞穴钻进去?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同样可以享受阳光、让风自由吹拂的牛羊,是因为人会创造,创造美、劳动、交易,文明的每一步,伴随着人性的美善与丑恶,这才是人类社会。我从不厌倦、并热爱在自然中感悟美善,但远离人,只与鸟兽虫鱼为伍,不是我的追求。
何况,简朴就能杜绝邪恶?克制欲望,就会产生美德?
但梭罗说:简单而诚恳地生活,让风自由拂过面庞,这才不是虚度光阴。简单。诚恳。自由。他的“消极抵抗”式生活,无疑是给予我们异化的加速度的消费时代一记棒喝。他提醒我们,去反思自己,怎样去过一种有品质的、宁静的、沉思的、德行的生活;他提醒我们,缓慢、自处、静观、远离喧嚣;他提醒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中恢复我们日渐散失的对美善的知觉。他以一种生活,提醒另一种生活,以一个世界,反思另一个世界。
在七月,我住进喀纳斯湖畔木屋,读梭罗,在他的文字中,在湖畔森林草坡中,慢慢让生活的渣滓沉淀下来,沉到心湖之底。
我们的木屋掩在几棵云杉下,边上有个四面敞开的木亭子。开门是野花盛开的草坡。穿过木栈道,顺台阶下到湖边,只三分钟。那几日,我们经常在湖畔,看雾中的湖,正午的湖,霞光映照的透明湖泊;看山顶积雪,看白云飞渡,顺泰加林小道一直走到原始人画过的岩石那边。傍晚浓烈的阳光,将木屋染成橙红,黑色针叶影子晃动在木墙上。
哪里也不去时,我们就呆在木屋里,闲话,坐在窗前读书。窗外草坡延展到高高路边,各色野花一直流淌到窗下。草坡之外是倾斜的云杉林,林外不高的一片山,早晨帽子云笼着时,显得神秘,山下木屋黄墙异常新鲜;正午阳光垂直,白云移去,山与草坡一览无余,只是那些圆锥形杉树伴着自己的影子,一只山鹰缓缓绕着树尖顶盘旋,一圈,又一圈。午后,四下暗将起来,以为暴雨将至,等半天,压低的云却被风吹跑了,阳光复又炙烈明亮地倾泻下来。到傍晚,山转蓝,阳光忽闪忽灭,我们守着窗,等待天黑,看一个图瓦童子骑在马背上,小小的黑色身影,几只羊,缓缓地穿过草坡、云杉、红松,走过了窗框外的世界……
我们木屋的访客是:一只停在西瓜上不停以手抹脸的苍蝇,一支搬运粮食的蚂蚁小分队,一只误把我当花、发现错误后慌乱地嗡嗡撞窗的蜜蜂,还有一条蹑手蹑脚顺墙爬的千足马陆,一只拱着背在松木屋顶逡巡的长脚蜘蛛……我甚至担心从草坡爬进一条蛇……一只蝴蝶,橘黄粉底、黑白斑纹,我们从卧龙湾向神仙湾走时,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蝴蝶,在风中翻飞着各样美丽姿态,有时停在一株黄花柴胡上,有时落在颤动的柔茎野罂粟花上……它突然向窗户撞过来,趴在玻璃上,挥手赶它也不走,只是一动不动趴着。他就说,是从卧龙湾就跟着我们的那只蝴蝶。
半夜开门出去,我们小屋的灯光,将纯黑世界圈亮了一小块,草虫的鸣叫告诉我,到处潜藏着生命,世界在呼吸。宝蓝天空,满布星星,看见我,就扑簌簌跳下来,我都来不及接,他们就跳下来了……跳到路边的,变成石子,跳到森林里,化作松果,跳到湖中的是鱼,那落在草坡上的,都变成各种各样野花了……
此也一世界,彼也一世界。假如身在湖畔,心神却漂浮在尘埃,思想下降到泥沼,木屋于我,形同虚设。而假如,我的心存有一份对百汇万物的新奇,对渺小之物的关注,对自我的警醒,对他人的怜悯,对美善的热爱,对德行的偏好……不苛求自己的完善,却能时时反省,且不沉溺,那么,即使身在最闹热的街市,我也同样拥有一个木屋。我在心中造了一个木屋了。
在湖畔的日子,天气异常好。我很渴望下一场暴雨,听凭大风穿过山谷、激动湖泊,热烈晃动木屋门窗;雨打在木屋顶像豆子落了一地,该多么动听?我渴望秋天再来木屋,金黄的白桦叶漂浮在湖上碧光中,五针松的赭红针叶铺满了山坡。冬天,我们在木屋听雪块压断了云杉枝桠;到春天,湖上融冰的巨响,惊落了瞌睡的鸟……飞鸟穿过林枝,大鱼跳出水面,光线行走在草坡,云翻过了山岫。在木屋,我谛听着百汇万物的声响,谛听着自己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