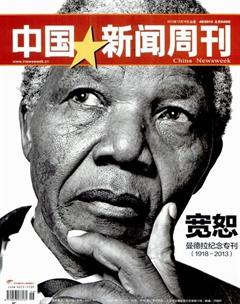谭利华:一个交响乐团团长的“年关”
陈涛

“以前年底是我们收成的季节,现在都没了。”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近的困难是意想不到的。”
办公桌上没有电脑,只有文件和乐谱,有些凌乱。身为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谭利华考虑的显然不仅仅是艺术。“现在满脑子都是事,一个是文化走出去,一个是乐团的建设,还有乐团现在面临的困难。”谭利华点了根烟,有些犯愁,“乱七八糟的,忙忙碌碌,一天到晚都在为生存去想各种办法,还要参加各种学习,路线教育等。”说这话前,团里的书记探头进来,示意谭利华要开会了。
“困难”已经迫在眉睫,因为今年年底的商业演出目前只定了一场。而以往,北京交响乐团在新年和春节期间,商演得有二十来场。今年,中央下达了“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其中的“厉行勤俭节约”“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等规定已经改变了年底热闹的演出市场。
“严控各种大型晚会或演出,难免会有些一刀切的现象。大型豪华的晚会制作,没人来听了,因为领导不来听,就没人敢来办了。”谭利华有些无奈,“我们就等死,这市场现在就成这样了。”
前段时间有人想把谭利华的日常生活拍成纪录片,“不想拍光鲜的,就想拍这个”。谭利华说,还是不要了,已经够烦了。外界或许想不到,高雅的交响乐以及它背后的指挥家与团长,此时正在努力渡过“年关”。
“谁还去听古典音乐?”
每年年底,一些大公司或财团都会办一些庆典或晚会,其中包括银行业、房地产业,甚至地方政府。“现在政府不办了,也不让办了,而地方的企业以前是希望领导来看晚会,现在的领导都不出现这样的场合了,所以就不办了。”谭利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总结今年的状况。甚至一些办晚会的企业已经跟乐团事先签约,但他们宁愿毁约。“我们靠什么?以前年底的这些商演。”谭利华自问自答,还一边翻着办公桌上的资料。
文化体制改革,全国2700多个团,最后剩下130多个团还是属于事业单位,北京只有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以及北京交响乐团保留事业编制。“不改体制,但要改机制,要面对市场,要企业化管理和运作。”这就是他作为团长必须考虑的事情,“就是相当一部分工资要靠我们自己去挣。”
这样的困难与北京交响乐团刚刚结束的欧洲、北美、南美以及国内十余个城市的成功巡演是不对称的。北京交响乐团也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全部演出都卖票的乐团。
今年9月北京交响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谭利华给记者拿出的照片上,鼓掌的观众均是国外面孔。而9月份,“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国人的卡拉OK厅”的争议也见于媒体。原因是,金色大厅这个被看作是“艺术的神圣殿堂”,从2月份到9月份,中国有130多个团体来到这里走马灯式的演出,台下甚至没有多少观众,或者是赠票请来的华人观众。相比而言,“北交”的反响还算不错。
而走下灯光和鲜花点缀的舞台,这支交响乐团的生计却一直是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要卖票,又不像欧洲有固定的观众群,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周或者每个月都会去听古典音乐。”谭利华说,“中国人现在浮躁得很呢,油盐酱醋,怎么想办法还房贷,怎样多挣钱,谁还去听古典音乐?”
“干着行政的事,搞着艺术的职业”
事实上,谭利华作为国内活跃的指挥家,也曾先后指挥过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美国法都威交响乐团、瑞士苏黎世交响乐团等国外名团。
谭利华一直认为交响乐或者芭蕾能代表国家的主流文化。给他印象深刻的是,普京担任上一任总统期间,中国文化年的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普京带了俄罗斯的歌剧团、交响乐团、芭蕾舞团过来演出,“展现他们的文化沉淀”。
“我们要出国去,都是一个大晚会,热火朝天,琳琅满目,人山人海,给人家什么印象都没有,就暴发户。”谭利华直言不讳。作为一名指挥家,他喜欢谈这些,可能跟他的社会职务相关,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兼任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干着行政的事,搞着艺术的职业”,他说自己是“多重角色”,或者戏称自己是“复合型人才”。
“给你看个东西,你就知道了。”谭利华去隔壁办公室取了一张纸,那是一张墨西哥酒店里的便签。
“你说我这脑子里,刚刚在国外演出完,还得操这些心。”谭利华用手指弹了几下这张纸。23天跑了8个国家,演了18场,这是北京交响乐团今年9月到10月在海外的演出数目,每天下了车,就得排练和演出。在墨西哥演出完,谭利华在酒店里写下了那张纸上的内容,相当于“自我反思”,这几百字还得扩写为2000字。
“我得花全部的时间去工作,这边给艺术,那边的时间给经营和管理。”谭利华抽完一支烟,又焦虑地点上第二支,“累是累点,但能够按照艺术规律去建设乐团。”他是学提琴出身,后来当了指挥和团长,按照他的说法,艺术家也做管理,才能让乐团按照艺术本身的规律去发展,虽然这其中难免也会遭遇比如当下的“经济困难”。
“得想办法要钱”
“我都说让我孩子不要学音乐。太苦,但长大之后的收入并不跟这些苦成正比。”谭利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出生在1950年代的江苏徐州,父母是干部,并非音乐世家。“是文革时候没事干,才这样。”谭利华说,“但音乐不是说刻苦了就行,还要有天生的条件,要有天生的乐感和节奏感,要不然只能成为工匠。”
1977年,谭利华面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专业,师从指挥家黄晓同。“这个专业很特殊,一年就招两个人,我那个时候拿了两个奖,我就免试了。”谭利华回忆说,自己15岁就开始上台指挥,那个时候在军队的文工团,不过经常是样板戏。
大学最后一年,黄晓同不慎把腰扭伤,无法上课,由另一位指挥家李德伦指导谭利华的两部毕业作品,即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和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毕业后,谭利华做了李德伦的助理,去山东、湖北、天津等交响乐团排练,随后开始独立担当交响乐的指挥。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谭利华就已经到过北京交响乐团的前身、北京歌舞团做指挥。之所以后来说摇滚歌手崔健是他的同事,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有过合作。彼时,崔健在北京歌舞团吹小号。这也促成了多年后,崔健的摇滚乐和北京交响乐团的合作。
2010年,崔健多次来到谭利华的办公室,谈摇滚和交响乐合作演出的事情,最后促成了摇滚交响乐的新年音乐会。
“这是崔健的一个心愿,他毕竟是交响乐团出身的。”谭利华回忆说,“但这样的制作成本很高。”那是国内摇滚乐第一次和交响乐结合,并没有赞助,最后的票房只和成本持平,其中崔健和他团队的出场费也是不低的成本。
其实,近年来,交响乐和通俗歌曲,以及黄梅戏、河北梆子、越剧、京剧、豫剧等戏剧的结合已不在少数,“为的就是拓宽市场,让更多人能够买票来看演出。”当下的交响乐市场已不是谭利华刚刚工作时的样子,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看场交响乐,人们通宵排队买票。
按照谭利华平时爱用的比喻,自己当指挥,就是统领,就像导演,但指挥还要直接参与一线的表演,而且带领一群人表演。而此时,他还得带领这群人走出经济上的困难,其实很多音乐演奏者的月薪也就几千元。
“当团长,不光是音乐家,得转换身份,得想办法要钱,得想办法维持乐团的生存和发展。”临近中午,谭利华拿笔在乐谱上做了标记,然后走出办公室,不是去吃饭,他需要去问问书记,过一会开展内部学习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