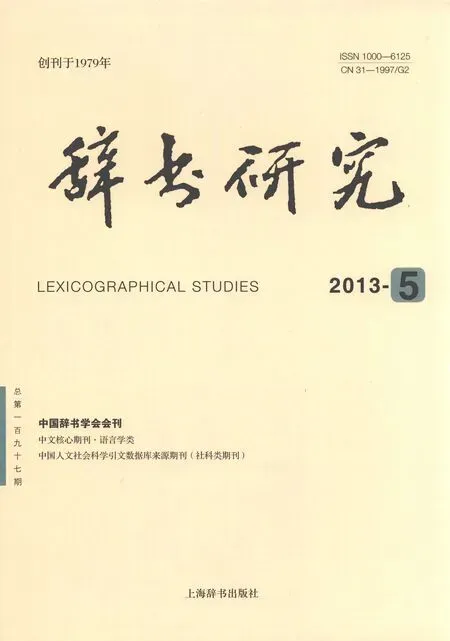《类篇》编排特色析论——基于“双轨制”辞书《集韵》《类篇》的对比分析*
杨小卫
《类篇》是宋代官修的字书,它以《集韵》为蓝本修撰而成,《集韵》《类篇》是宋代“相副施行”的“双轨制”“篇韵”辞书的重要代表。《类篇》在编排方面借鉴了《集韵》的优势,融字书与韵书于一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们借助计算机技术制作出高质量的《集韵》《类篇》电子文本,采用先进的XML技术构建两书语料库,在辞书学领域首次实现字书《类篇》按照韵书《集韵》的体例编排,韵书《集韵》按照字书《类篇》的体例编排。[1]在此基础上,重点对《集韵》《类篇》的编次进行比较,考察《类篇》的编排特色。
一、从《类篇》编排透视宋代“相副施行”的“双轨制”“姐妹篇”辞书的真实面貌
《类篇》作为《说文》一系字书的集大成者,它的部首编排严格遵循大徐本《说文》——以《说文》540部为经。同时,作为《集韵》的姐妹篇辞书,它又要实现其编纂意图,与当时刚编纂完的《集韵》相副施行,所以对部首中的字次以及每个字下的音义则按《集韵》的韵目编次——以《集韵》为纬。
为了贯彻“双轨制”“姐妹篇”辞书“相副施行”的编纂目的,《类篇》在内容材料上与《集韵》大同小异,彼此可以相互参稽;在编排方式上,《类篇》全书所收的3万多个字头,在按《说文》540部编排之后,同一部首内的字头以及字头下的音义依照《集韵》的音序设置了两个阶次的“以韵相从”。
1.按韵编次的第一阶次
按韵编次的第一阶次是把《类篇》同一部首内的字头依照《集韵》调、韵、纽的音序据音系联。下面以“谷”部下字头的排置为例。

表1 《类篇》“谷”部下字头的排列
《类篇》在部首之下对字头以始“东”终“乏”的《集韵》音序编次。
《集韵》分十卷,每一卷下分为若干大韵。在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我们对《集韵》文献特征的标识如下:
《集韵》音序的百位和千位数字代表它的卷数,个位和十位数字代表它所在大韵的次序。
《集韵》共十卷,平声一为《集韵》卷之一,用1表示;平声二为《集韵》卷之二,用2表示;平声3为《集韵》卷之三,用3表示;平声4为《集韵》卷之四,用4表示;上声上为《集韵》卷之五,用5表示;上声下为《集韵》卷之六,用6表示;去声上为《集韵》卷之七,用7表示;去声下为《集韵》卷之八,用8表示;入声上为《集韵》卷之九,用9表示;入声下为《集韵》卷之十,用10表示。
《集韵》是按韵排检的辞书,数字化处理时对韵目进行了区分,我们把韵目在卷中的次序用数字来表示,并且卷次与韵目紧密相连。如:东,《集韵》卷第一→韵目→一东,我们标注为“101”东,其中百位上1表示《集韵》卷第一,十位个位上数字01表示大韵东在《集韵》第一卷的次序。“谷”的《集韵》音序“901”屋代表“谷”在《集韵》第九卷即入声上的第一个大韵。
表1中,“谷”部所收全部字中除部首字“谷”外,部内32字头依照《集韵》206韵的次序排列如下:
《类篇》先排列《集韵》第一卷平声一东韵的“豅”“谾”“谼”诸字和江韵的“”;

如果同一大韵下存在多个字头,则再按照《集韵》声纽次序排列(依次是唇、齿、舌、牙、喉)。
如《集韵》第一卷平声一东韵下有三个字头:“豅”“谾”“谼”,《类篇》修撰者的处理是先排列半舌音“来”母字“豅”;再排列喉音“谾”“谼”;后两个的先后次序依照36字母次序先“晓”母字“谾”,后“匣”母字“谼”。
由上表可知,《类篇》按照《集韵》音序排定部首内的诸多字头,其排列有条不紊,极为整齐。
2.按韵编次的第二阶次
对于同一字头下众多音义,《类篇》不以形义编次,而改按《集韵》音序排定。对于第二阶次的据音系联,《类篇》的处理办法是分两个步骤来编排同一字头下的众多音义。下面以“示”字头为例进行说明。

表2 《类篇》“示”字头下众多音义的排列
步骤一:依形汇聚音义。如表2中《类篇》将《集韵》的4处音义中有关部首字“示”字及其出现在本义(《类篇》忠实于《说文》,部首字以《说文》所载意义为本义)后面的所有异体字的全部读音和意义,汇聚于字头“示”之下,完成了依形汇聚音义这个层面的工作。
步骤二:据音列义。《类篇》排列汇聚到字头“示”下面的4组音义组合时,先排列字头“示”的本义“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类皆从示。古文作。”紧跟着排列与本义对应的主音切“神至切”,其余的音义组合再按照《集韵》音序排列,依次是平声支韵“翘移切”、平声韵“市之切”、去声寘韵“支义切”下的音义组合。
《类篇》依照《集韵》的音序设置了两个阶次的“以韵相从”,克服了《说文》《玉篇》部中字次无规则可循的弊端,减少了使用者的翻查之苦。黄侃(1964:20)曾经这样评价这种编排法:“在未有编画字书以前,此法颇为简便;以视《玉篇》等书,列字先后毫无程准者,又远胜之矣。”
《类篇》这一创举,不仅增强了辞书的实用性——便于查检,而且对后世辞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金韩孝彦的《四声篇海》部首按三十六字母顺序排列,字母下再按平上去入四声为先后,部内字则按笔画多少安排。《四声篇海》部首的编次显然受到《类篇》的影响。
《类篇》为何设置两个阶次的“以韵相从”?究其深层动因,我们认为这是贯彻宋代“双轨制”“篇韵”辞书“相副施行”的修撰意图。正是这一修撰理念,最终催生了《类篇》独特的以部首为纲,以韵目为目的字书排检法。
二、《类篇》的编排反映了宋人进步的辞书修撰理念
1.《类篇》作为《集韵》的姐妹篇,反映了宋人自觉修撰“相副施行”的“双轨制”“篇韵”辞书的时代风尚
宋人对于字书、韵书的编纂,有着自己独特的理念,刻意追求字书、韵书在内容上能协和一致,以便相互参照。宝元二年十一月《集韵》成书后,翰林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2]
鲁国尧(2003:341—343)把字书和韵书的相配划分为三代“篇韵”。即顾野王《玉篇》、陆法言《切韵》是第一代“篇韵”;大中祥符元年(1008)重修的《广韵》、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的《大广益会玉篇》是第二代“篇韵”;宝元二年(1039)修成的《集韵》、英宗治平四年(1067)修成的《类篇》是第三代“篇韵”。
这些“双轨制”“篇韵”辞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后人的配置;如编写者在修撰《切韵》及《原本玉篇》,或者《广韵》及《大广益会玉篇》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做到字书与韵书相副施行,而是后世学者在对它们进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相配的。另一种是当时的编排,辞书修撰的目的就是刻意要求字书和韵书的内容协和一致,以便相互参稽。例如,与韵书《集韵》相对应的字书是《类篇》,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辞书的“双轨制”,或者字书、韵书“相副施行”的原则。这才是真正的“双轨制”。况且,在《集韵》《类篇》之后,辞书修撰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双轨制”现象。
2.《类篇·序》所载凡例反映辞书修撰遵循理论指导的理性精神
凡例亦称“发凡”“例言”,是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对于辞书“凡例”的源流问题,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就字书而言,《说文·叙》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学理论文献,《说文·叙》展示了字典发端期理论的端倪,但是理论见解的阐述大多隐含在对字形的分析之中,缺少提炼概括。
魏晋隋唐字典理论沿袭了两汉的传统,但是,理论研究仍旧远远落后于编纂实践,创造性的字典编纂实践,还没有来得及做必要的总结,未上升为理论或转化为编纂条例。如顾野王《玉篇》的修撰在语言史上具有许多方面的创新,在当时却缺少明确的理论阐述。
宋代是字典与字典理论的发展期,字典编纂纷纷提出理论纲要,如凡例、韵例等,从而宣告把字典编纂置于明确的理论指导下的新时期正式开始。《集韵》是最早明确提出“韵例”的韵书。《类篇》秉承《集韵》传统,成为最早明确提出“凡例”的字书。
《类篇》代表《说文》类字书在宋代的发展,领衔修撰《类篇》的司马光在序言中明确全书编排的原则为:“虽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无不各获其处也。多而至于失其处者,非多罪也。无以待之,则十百而乱;有以待之,则千万若一。今夫字书之于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
《类篇》凡例中明确规定把反切注音作为字头类别部居的依据,《类篇》序所载九条例中涉及字音的有两条。

宋代学者重视“义理”的阐发,把字典编纂置于明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如上述《类篇》序的九条例,就是辞书编纂史上的空前创举。《类篇》序所阐发的编次体例涉及字音、字形、字义,周密具体,完整系统。尽管这些条例在理论上还谈不上完美,但条例的制订表明修撰者已经自觉地遵循理论的指导,因此宋代辞书的编纂更加规范、科学。
3.《类篇》编排突破了《说文》“据形系联”的套路,创造了“据形系联”与“据音系联”相结合的全新编排路径
“据形系联”是许慎创造的字典部首编排法。“据形系联”基本符合汉字结构的特点与规律,因而它能起到“若网在纲,如裘掣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3]的规范作用。
《说文》成书于东汉,对字义的阐释大多局限于本义,不存在音义的排列问题;到了梁代,《玉篇》对一字多音义的处理是先排列所有读音,再列出所有义项,音义匹配关系模糊;《类篇》则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对于部首的排列,它秉承《说文》《玉篇》的传统——“据形系联”;对部首内字头和字头下音项和义项的排列改用“据音系联”——按《集韵》音序排置。《类篇》的修撰者对部首、部首下的字头及字头下的众多音义按照“据形系联”与“据音系联”相结合的原则来排列、编次,反映了《类篇》的修撰者具有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
三、《类篇》的编排折射出宋代语言学领域的革新和进步
1.《类篇》的编排吸收了姐妹篇辞书《集韵》在音韵史上革新的成果
《集韵》在音韵方面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按声类集中排列小韵;改类隔切为音和切;改进了反切上字在等呼、调类的不合状况;按照时音标准,合并“同音再出者”;新增了许多反映时音的切语等。《类篇》吸收《集韵》在音韵方面绝大部分的革新成果,这一点从《类篇》的编排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例如,《集韵》改变了《广韵》相同大韵下同音字排列杂乱无章的状况,按声类集中排列相同大韵下的同音字。各小韵按照声母的次序依次排列——先排列与韵目同声组的字头,然后再依照唇、齿、舌、牙、喉的次序排列其余字头。齿头与正齿,舌头与舌上,大体上分开排列。这些成果被《类篇》吸收过来,用于部首内的字头以及字头下音义的排列。这些编排方面的变化反映了随着宋代等韵学的勃兴,人们审音更加精细,《类篇》的这一革新措施方便了使用者查检。
2.《类篇》对多音多义字的处理吸收了当时语言学领域最新的成果
《类篇》对多音多义字的处理与它之前的字书不同。面对一个字头下的多音多义,《原本玉篇残卷》的处理是在字头下分音、义两个部分编排,先一次性全部排列这个字的所有音项,再排列它的所有义项。《类篇》则注重音和义的匹配。我们选取《类篇》和《原本玉篇残卷》三个字头下的音义排列进行对比,列表如下:

表3 《类篇》与《原本玉篇残卷》字头下音义排列的比较
通过表3《类篇》和《原本玉篇残卷》两书字头下音义排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原本玉篇残卷》的音义排列固然考虑到字音不同字义相同的情形,但是这些音和义的匹配关系是笼统模糊的,不如《类篇》音义关系那样准确、清晰。
第二,《类篇》对多音义字义项的处理特色之一是,对同一字头下的众多音义,《类篇》先排列本义和相应的主音切,再按照《集韵》音序来排列其他别音别义。
第三,《类篇》对多音义字义项的处理特色之二是,创造了反映字的多音义的义项模式,即按不同音切分列不同音义项,并用“又”作为划分的标志。《类篇》的修撰者已经触及到了多音义概括与区分这个字典编纂的重大问题,他们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体现于多音义字义项的据音列义——依照《集韵》音序来排列多音义项。这一举措不仅和《集韵》互相照应,而且把同一字头下的众多音义编排得井然有序。《字汇》在《类篇》的基础上进一步形式化,用“○”作为划分不同义项的标志。由此可见,现代字典的义项处理意识,在《类篇》中已初现端倪。
总之,《类篇》的编排展示了语言学领域进步和革新的成果。
在排检法方面:
《说文》首创部首检字法,对后世的字典编纂影响深远。《玉篇》对部首进行了改革,但并不成功,故《类篇》的分部仍依照《说文解字》,分部首列字。《类篇》虽从《说文》分部,始一终亥,但部内字的排列顺序则依从韵书《集韵》。这样,《类篇》就创造了以《说文》为纲,以《集韵》为目的字书排检法。
在字形方面:
《说文》采用小篆为字头形式,而《玉篇》则首次使用楷书,《类篇》顺应了这种文字演变潮流,也以楷书为字头。
在字音方面:
《说文》的注音是以“读若”为主要形式的譬况法,《玉篇》采用反切注音法,《类篇》是一部与《集韵》相副施行又有独立性的字书。它一方面充分吸收《集韵》反切注音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凡字有别音别义者,皆在本音本义之后一一注出,最后做一小结,注明重音的数量。
在字义方面:
《说文》通过分析小篆字形来探求本义,析形与释义相结合,偶有其他意义,则用“一曰”解说。《玉篇》不再依《说文》先释义,后分析字形,而是注音在前,释义在后。再列异体、异读别义,分别注音释义。《类篇》继承《玉篇》音义配合的释义模式,但是它克服了《玉篇》音义匹配关系笼统模糊的弊端,注重音和义的匹配,从而使音义匹配关系较为清晰、明确。
四、《类篇》的编排启示学者科学、合理地利用古代“双轨制”辞书
鲁国尧(2003:627)从辞书编纂史的角度评价三代“篇韵”,认为第三代“篇韵”中《集韵》和《类篇》都是语词性字典。鲁先生还进一步结合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和考古学等宋代学术大发展的背景考察《广韵》《集韵》,他认为“《广韵》是‘述’,抄缀旧文而成的内部矛盾纷杂的韵书;《集韵》是‘作’,义例谨严组织致密的字典。”
我们赞同鲁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作为与《集韵》“相副施行”字书的《类篇》也是“作”,它借鉴《集韵》的编排成果并把这种进步的编纂思想成功地运用到字书《类篇》的编纂实践中。
当然,《类篇》也决非毫无缺点。如在编排上,借鉴了《集韵》的编排成果,但是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这一编纂原则并没有彻底贯彻。例如,《类篇》反切标音吸收《集韵》在音韵史上革新的成果,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字本义下主音切的标注时,《类篇》反而由于严格遵循大徐本《说文》,导致某些音切并没有吸收《集韵》的革新成果去反映时音,反而有存古的意味。读音如是,释义亦如是,所以自身制订的编排原则没有一以贯之,因此编排优势也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但这些缺陷都是不难理解的,不能据以贬低乃至否定其历史贡献。
《集韵》《类篇》作为宋代“双轨制”辞书的重要代表被学术界喻为“姐妹篇”,它们关系密切﹑同中有异。分析《类篇》的编排特点,我们必须把《集韵》纳入考察视野,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获得全面而科学的结论,割裂二者关系进行孤立的观察,会产生偏误。所以我们制作出《集韵》《类篇》的电子文本,转换成数据库,并且建立两书的关联,比较两书的编排。我们认为,《类篇》的编排,不仅贯彻“双轨制”辞书“相副施行”的编纂原则,融字书和韵书的优势于一体,而且反映了辞书学和语言学领域的革新和发展,顺应了字典编纂定型化、通俗化的必然要求,方便读者查检。这些无不启示后来的学者科学、合理地利用古代“双轨制”辞书。
附 注
[1]我们利用计算机对《集韵》《类篇》进行数字化处理,对于《集韵》,我们以曹刻本为底本;对于《类篇》,我们以清姚觐元覆刊曹楝亭扬州诗局本为底本。《集韵》的电子文本制作出来后,我们参照长沙本《集韵》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述古堂影宋抄本进行校对,同时吸收方成珪、黄侃、白涤洲、邱棨鐊、邵荣芬等的校勘成果,对《集韵》进行校勘。《类篇》的电子文本制作出来后,我们参照四库本和清曹楝亭扬州诗局重刊本进行校对。此外,有了《集韵》《类篇》的电子文本和数据库,可方便地将两书按字头进行比勘。如果发现问题,又可返回《集韵》《类篇》进行校核,保证制作出来的《集韵》《类篇》电子文本的高质量。我们还采用XML标记语言来标注经过校勘后的电子文本,然后将标记好的电子文本转换成数据库。
[2] 司马光等(宋).类篇.北京:中华书局,1984:563—564.
[3]段玉裁(清).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
1.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
2.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