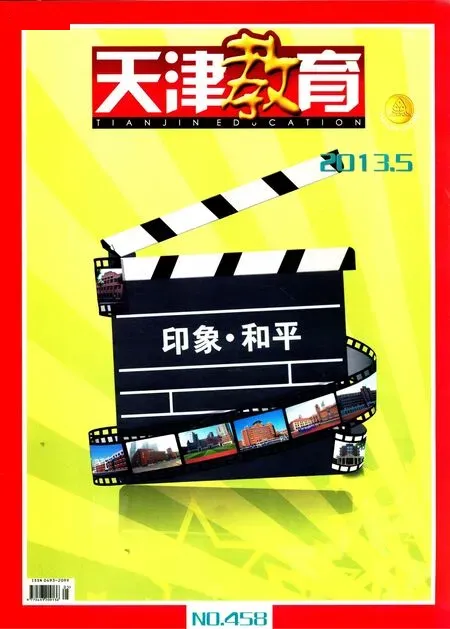我在《焦点访谈》栏目
■敬一丹
我在《焦点访谈》栏目
■敬一丹

敬一丹,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副会长,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生于哈尔滨,1976年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1979年起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1983年考取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入中央电视台任记者、节目主持人。现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曾经主持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建党80周年等一批大型直播节目。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
这个地方有一个“场”,一进校园感觉就不一样,让人说出这句话都特别由衷——我是爱南开的。
在座的同学们,16岁的举一下手,好,谢谢16岁的少男少女们。高一的同学都是16岁。《焦点访谈》和16岁的男生女生们同岁。就在你们出生的年份,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一个栏目,它叫《焦点访谈》。我想讲的是,在没有《焦点访谈》的时候,中国电视是什么样的。过去,像我们电台、电视台、报纸,等等,不叫媒体,叫宣传机构。那时候,人们不知道什么叫舆论监督,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播出的东西都是正面的。我们经常讲:“下面播送广播稿……”基层的广播站是这样,即使是在国家电视台、省级的广播电视台,大量的也都是宣传。
宣传和传播是不一样的。《焦点访谈》在创办之前,这个栏目的创办人孙玉胜,他也是《东方时空》的创办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现在要办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舆论监督的,它将每天出现在《新闻联播》之后,黄金时间播出。”那时,我已经做了四年经济记者,听到他的电话我非常吃惊——舆论监督在中国这个土壤里,能做到每天黄金时间播出这样的力度吗?我们有这样的土壤吗?我说这个栏目叫什么名字啊?他说:“还没有起名字呢?你帮我起个名字吧。”这个栏目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
于是在1994年的4月1号,《焦点访谈》开播。《焦点访谈》刚刚开办的时候,多数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舆论监督为何物,中国偶尔的一点舆论监督,被人看作是新闻,所以当时我们的栏目面前有很多禁区。什么是禁区呢?戴大盖帽的,不能进入我们的镜头。大盖帽就象征着某种权力。而舆论监督所要监督的,最重要的就是权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不平,没有秩序,不文明,阳光背后的阴影,这是《焦点访谈》所面对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寸一寸地开拓出舆论监督的空间。假如说中心城市做不了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做一个其他城市的,例如我们家乡哈尔滨一带的,河南、河北省的。所以,有段时间老百姓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是挺好的,但是你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我们说,能打苍蝇也是好的,中国的媒体过去连苍蝇还不打呢!
媒体应该是什么?我们《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共用一个LOGO,那是一只眼睛,眼睛就要看着这个社会,看到它不健全的地方,及时指出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我们的机体保持警觉。如果我们社会的机体,对这些不完美不健康的地方没有意识,直到它坏死,影响着机体的运行,那就是悲剧。所以社会需要这只眼睛,我们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眼睛的注视下,就会有所约束。《焦点访谈》就承担着舆论监督的使命。它像一只眼睛,是睁着的眼睛。后来当我们一寸一寸地开拓出舆论监督空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从一个一个的节目里,就认识到一个词,这个词就叫做“舆论监督”。
于是老百姓,遇到不平的时候,就会说:“我去找《焦点访谈》。”那个时候,《焦点访谈》变成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的是一个诉求的渠道,是除了行政和法律力量以外的另外一种力量,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这就是伴随着大家长大的,与大家几乎同龄的《焦点访谈》曾经起到的作用。
2010年4月1日,是《焦点访谈》开播16周年纪念日。尽管《焦点访谈》不像在十几年前那样具有锋芒,但是我们毕竟知道这个节目是为什么出发的,我们走到了这一天,我心里暗暗地在纪念这个日子。那天恰好是我主持《焦点访谈》,我很想在节目里跟观众们分享一下这种感觉,后来我们领导说:“算了吧,逢五逢十说一下就行了,平常就不说了。”但是我还想说,于是晚上我就在微博里说了一句,我说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节目里坚持这么久,但是让我欣慰的是,我和我的同事一起,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让《焦点访谈》这样一个生词,在中国的土壤里变成了熟词。我心里更想说的是,没有写在微博里,《焦点访谈》虽然不像当初那样醒目,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舆论监督遍地开花,这让我们享受到自己工作的成就感。
在《焦点访谈》创办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焦点访谈》最有战斗力的时候,我见到的观众见面都说:“我看了你们《焦点访谈》上星期播的什么什么节目。”真都是这么说的,类似于这样的话。现在我走进校园,看到年轻的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他们通常会这样说:“我妈妈特喜欢您,我妈妈就是从《焦点访谈》那时候开始喜欢的。”其实她不是说喜欢我,而是喜欢《焦点访谈》。然后再问,那你爸爸呢?那你呢?还非得让人家说出来全家都挺喜欢的。其实我知道,年轻人和电视越来越拉开距离,可能你们现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网络,所以我们电视现在经常被人家用来怀旧。那天我看见一些“80后”写的东西,他们在怀旧,连《实话实说》都算怀旧的材料了。我不知道崔永元看到这些文字以后怎么想,连《实话实说》都被他们用来怀旧了,哎呀,我们要提知青什么的,那简直是太遥远太遥远的过去了。
有一个年轻人,那是在1998年,他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个年轻人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经常觉得,茫茫人海中他还在注视着我们。他写这封信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到了《焦点访谈》工作以后,每天都收到几百封观众来信,过去我在主持经济节目的时候,也常收到观众来信,那时观众来信多半都是来问我一些致富经,如怎样养牛等问题的。到了《焦点访谈》以后,忽然间每天办公桌上几百封信,那时我最初的感觉是什么?这节目有这么多人在看,然后你拆开这些信来看他们说什么,说的全都是自己所经历的不平。你看到第一封信的时候,你会拍案而起;看到第二封信的时候,你想站起来,走到那个相关部门去;你看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心里开始郁闷;然后你天天,一年365天,每天都看这些,这些信能变成节目线索的微乎其微,但是它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认识国情、民情。我天天看这个节目所积聚起来的那种沉重,我是没法在镜头前说出来的,但是观众在镜头前看出来了,他们都说:“敬一丹怎么满脸凝重啊?你就不会笑一笑么?”我在开研讨会的时候,专家看着我在一起讨论问题,讨论半天以后他说:“哎,敬一丹,你还会笑啊?”可见大家在镜头上是没有机会看到我笑的。大家都觉得,你有必要那么凝重吗?我不是故意的,你要知道我每天看到的是什么,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总是紧锁眉头。我不想总是紧锁眉头,可这是常年的内心积聚。
有一天我又看着这些信的时候,我对面的同事,看着我唉声叹气,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做成一本书?”能把这些东西做成一本书么?我过去没有想过,从这个建议开始,我们就做着尝试,我们就在成千上万的给《焦点访谈》的来信中,挑出了150封信,覆盖了当时最热点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腐败、污染、贫困、教育,等等。这些信都是原生态,全都来自民间,你从信封的落款就可以看出,这些地方是角落。越不是角落的地方,那信封上的字越少。比如说,天津南开中学,就6个字,不用写邮政编码就能寄到,对吧?但是给我们来信的落款都是这样的,黑龙江省依兰县中和镇小民乡某某村第二村民小组,特别长特别长的落款。然后那信封皱巴得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粘邮票的浆糊是黑乎乎的,你就可以想象,他把这个信投到邮箱里后心里是怎样的期待。这些信到了我的桌上,如果它不能被做出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么这些人就白发出声音了。我是媒体人,我有传播的优势,我何不利用一下我传播的优势,把这些声音收集起来,传播开去呢?
于是,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观众的来信和我读观众来信的感受,这样就形成一个电视人和百姓之间声音的交汇。这本书里的内容都是原生态的,里面所说的事情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那个时候,信都是手写的,都是最传统的传递方式。在编这些信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在猜测,人们会怎么看待我的这种做法?我在家里摊了一桌子的信和稿子,我的公公很不安地跟我婆婆说:“一丹在干什么啊?她写那东西,要是在1957年就是右派。”1957年对大家来说太遥远了,1957年以后中国的变化,大家将来学历史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了。1957年之前,传播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民情、民怨,很有可能被看成是右派。当时我就想,我现在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90年代,1997年,1998年,不是1957年,我是赶上了可以说话的时代,这是一个媒体人的幸运。而这些人,发出声音的这些人,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这是一个进步,它就使得我更有欲望,我一定要做这件事。
这本书出了以后,起名叫《声音》,副题是《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为什么叫《声音》?就是我每次拆信的时候,都觉得一拆开信,就觉得里面都是声音,很喧哗,但是我觉得声音尽管有点嘈杂,也比万马齐喑好得多。它是一种真实的社会面貌,而我们听到了,我们共鸣了,我们反映了,就不枉这些人发出声音,所以做完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会有种安慰。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学生给我的信,他说:“我看了你的《声音》,你所听到的声音只是你能听到的,而我的乡亲们已经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只剩下呻吟了。”这封信出自一个学生之手,他的家在偏远的山村,所以他说我听到的只是我能听到的,而他的乡亲们只剩下呻吟了。这封信使我又一次进入了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我终于知道,我原来的那种满足,那种舒了一口气的感觉是很肤浅、很浅薄的满足,而这个学生给我的提醒,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同时背负着这样的托付。所以这么多年了,我还在《焦点访谈》坚持,我总是觉得中国只要有了这样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就会让那些呻吟的人看到一种希望。这个工作给我带来一种职业的特殊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体面,不是有个人成就感,而是让我感觉到我做这个工作,可以让世界好一点,哪怕一点点。如果说这个世界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力量,变得更有秩序、更文明,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这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学生的来信,经常在提醒,要听到声音,要看到角落,尤其是要关注那些不容易发出声音的草根发出的声音。
当时我想,如果过五年、十年,我再来做一次这样的工作,也许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比如说像下岗、腐败、污染这样的词可能会少起来,而那种有亮点的词可能会多起来。如果那时候我能继续收集这样的词,再做一本有关声音的书的话,它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记录,这种记录给后来的年轻人,他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百姓都说什么,这种原生态的声音,这样一种特殊文本,是其他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它不是通过作家的笔,不是通过作家的思索过滤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带着气息的声音。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搜集这样的声音,没出第二本《声音》,是因为那时候的声音现在还存在,有的甚至更严重。这让我觉得,有什么好的声音可以传达吗?
其实,如果有机会走到咱们16岁男生女生的家里,我想我会看到很多和《焦点访谈》有关的故事,你们的父辈,你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焦点访谈》和你们所看到的《焦点访谈》也许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知道《焦点访谈》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曾经在中国做了什么。今天,舆论监督成为你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成为你们生活中的常态,这就是幸福。《焦点访谈》时起时落,有时有锋芒,有时有温存,这件事比起各位的生长环境来,并不那么重要。如果现在对你们说,把这股力量抽走,让舆论监督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已经是不可能了,这就是进步。所以说,不管我所在的栏目如何起伏,我觉得自己还要在《焦点访谈》这样一个栏目里面坚守。我们把这颗种子种下来,总会在中国这个土壤里结出健康的果实。
现在更多的人遇到不平,遇到让自己愤怒的事情,可能不再说“我找《焦点访谈》去”。现在人怎么说呢?“我上网去,我直接在网上说。”短短的16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网络的出现,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传播者。原来电视台是传播者,观众是接受者,而现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网络完成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网民都自觉运用起自己这种传播的力量,进行着舆论监督。也许他们不用“舆论监督”这个词,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了当初。比如说在广州法院值班的一个公务员,在办公过程中,对市民发脾气、大呼小叫,服务态度极差,而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市民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把那个人大呼小叫的形象录了下来,回家就上网。人家不用找《焦点访谈》,人家自己就是“焦点访谈”,他上了网以后,这个公务员获得了一个名字,叫“咆哮哥”,也失去了饭碗。这就是力量。就这个网民,他有这样的自觉,用网络手段,而不用找《焦点访谈》,这事自己来做。
但是如果说,《焦点访谈》所代表的这种力量,曾经在大家的成长中有过一点作用,这就足以让我欣慰了。当然,你们有空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依然可以陪着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看《焦点访谈》这个节目,谢谢收看!
刚才我进南开校门口的时候,就看校门口有一个广场,走进学校还有那么多的细节很值得品味。我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学校,比如说南开大学,那时我也不认识咱们海麟市长,没进过南开中学。有一次我到天津出差,特意到南开大学转了一圈。在大学校园里,有一些新的感觉。兰州是水均益的故乡,兰州大学分校距离兰州市50公里,里面有个新闻传播学院,我和那里的同学有一个交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站在他们的校门,往右是兰州,那是在西北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往左是定西,那是中国最穷困的城市之一,它穷困到被人认为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兰州大学恰好在它们中间。我就问同学们,我说大家都是学新闻的,你们走出校门以后,习惯往哪边走?有没去过右边的定西?他们说没有,全都是出了门非常自然地奔向兰州;我又问有没有故意地、诚心地去趟定西?回答是“很少”。我面对的那些同学是学新闻的,他们将来是要做记者的,是要做西部的记者的,所以我就说,你们想没想过往西边走,也是50公里,去看看那个中国最穷的地方?你将会看到两个世界。向左走,向右走,就在你面前呈现出两个世界。
校园里面的同学,走出校门的时候往哪走,它就决定了你的视野。你只往光鲜的地方走,只往中心地带走,只往有鲜花的地方走,你只看到世界的一面;而没有去过定西,没有看到赤贫,没有看到过那种无望,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对于学新闻的同学来说。所以,我对他们说,你们将来在西部当记者,西部记者对西部有什么样的了解?如果说“从大学出来,你看我也没去过美国,也没去过深圳,也没去过上海,人家会不会说我孤陋寡闻呢?”我说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没去过定西,也会被认为是孤陋寡闻,这是另一种孤陋寡闻。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你只看到生活的一面,那就可以被认为是孤陋寡闻。我所强调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在西部求学的学子来说,你不知道鲍鱼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只,你不知道鱼翅长什么样,不丢人;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在定西那些孩子是怎么上学的,出去打工的人是怎么把钱挣回来的,你就要感到脸红。人是有天性的,向着那些光鲜的热闹的地方走不用引导;而向着那些角落、阳光后面的阴影、不被人关注的地方走,是需要自我提醒的。左右都看到了,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坐标。我们对上下左右都观察,对不同的人生活的状态都有所了解,我们才给自己有一个合适的定位。
各位是中学生,我们的生活半径有限,我们靠什么去认识校园外面的世界,除了自己有机会去直接接触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依靠媒体,借助媒体。当然媒体也有各种各样的,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像我少年时那样,相信一切印出来的字。我像大家这个年龄的时候,正处在“文革”中,我相信一切印出来的字,我觉得印出来的字都是真的,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才知道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家成长的环境已经告诉了你们,对媒体是要做选择的,但是媒体毕竟是一个渠道。而在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外部世界的时候,要自己辨别,要对外面的世界有了解。我们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时代?你们回家可以问问你们自己的父母,如果你们的父母还显得太年轻,你们可以问一问50岁到60岁的人,他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所经历的什么,都是一样的。想的都一样,做的都一样,穿衣服都一样,选择都一样,没有个人选择。老一代和你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你们的成长中,你们有多重的选择,从个人打扮到你求学的方向,到将来你们找男朋友女朋友,你们自己都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而过去没有选择,大家都一样。
而我们经历了从一样到不一样,但是不一样是走到了一个太不一样的境地了,就是我们社会出现了差别。这个差别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差别让人产生动力,但差别也会带来失衡。现在在相当多的地方差别是太大了,这种差别体现在,你向左走50公里和向右走50公里是两重天。这么巨大的差别在同一片国土上,它就会带来不平衡,它就会带来很多矛盾。你们将来上大学可能会接触到不同背景的同学,这会让大家更能感觉到差别。有的人从出生就和你不一样,起跑线就不一样,就在你身边,你天天走路看到卖油饼的、收废品的那些人,你停下来看一看他,你看看他身边的孩子。我们好像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我们能不能看到,会不会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将来我们能不能改变它?我今天会觉得上一代有上一代的使命,下一代有下一代的使命,那么上一代的使命,是让原来大家都一样的变得不一样,它生动了,活跃了,但是差别太大了,以至于失衡;而当你们长大以后,你们的使命也许就是减少这些差别。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让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什么叫体面、文明。所以现在,对校外生活的了解,就是未来完成这种使命的准备,这是校门口的故事。
我这还有最后一个故事,叫“第一次”的故事。你经历过很多“第一次”。刚升入高中,正在体验自己的“第一次”高中生活。一旦你走出校门,不再是学生身份的时候,你所经历的那些“第一次”,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美好。
大家知道陈虻吗?我们《东方时空》创办人之一,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他的创意。他英年早逝,影响了一代电视人,改变了电视的面貌。在他们那个“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之前,中国的电视里没有平民,只有要员、领导,要不就是敌人。让平民走进电视,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这个陈虻,他跟我谈过他的第一次。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专业毕业的,他分到电视台以后,电视台不知道这光学是干什么的,于是领导说:“那给你分到灯光科去吧。”后来他一再申明,这个专业跟灯光科不是一回事,然后把他分到了编辑部门,他就想当记者,就想做电视,于是被分到了编辑部门打杂。天天就是给老张弄个水,给老李转个带子什么的。这些事干了很多天,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零活都让他去做,他就很有耐心地积聚着自己的力量。他不知道机会在哪里,别人都觉得他是别的专业毕业的,他如果是北京广播学院采编专业的,早有机会了。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个学光学专业的人能干什么。所以没有人招呼他,他就一天一天在那做琐碎的工作。
有一天都快下班了,忽然间有一个老编辑打来电话,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老编辑说:“办公室里还有别的人吗?”“没有。”那老编辑实在没办法,就说:“那你现在能不能找一找关于哈默的资料?”哈默是美国石油大亨。当时中国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刚刚开始恢复,哈默来访华,能不能获得采访哈默的机会,这是中央电视台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获得了这个机会,但是那老编辑却抓不着人了,于是就和恰好在办公室的陈虻说:“你能不能找到关于哈默的资料,明天早晨采访,没有别的时间准备,我现在找不到别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于是陈虹放下电话直奔资料室,翻江倒海地找,终于找到了一本《哈默传》。通宵达旦,从那么厚一本书里,生发出50个问题。第二天早晨,交出了这个50多个问题的采访稿,那老编辑一看,用功了,真的是用功了。然后从那里抽出了一些问题,作为真实的采访问题,于是人们就认识了陈虻。哦,这小伙子是学光学的,但是他是有编辑头脑的,以后他的机会就慢慢多了起来,他就成了独立的一个编导,最后成了制片人,成为一个领军人物,成为在中国电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是南开中学的同学,南开中学的盛名之下,人家也会那样看你,比如上大学的时候,你说是南开中学来的,人家会对你寄有一份期望。将来你上了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等,毕业以后走出校门,你还一路带着那种走出南开的高贵、优越,你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求职场合,你将来从事的第一件工作、第二件工作里,遭遇到很多这样的“第一次”,而之前的光环、盛名、优越,这一切曾经影响你的东西,在那个时候都会归为零。你终有一天要走出这个校园,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对校园外面的世界,有一些了解,我们上路的时候,就会多一分从容。
(以上是敬一丹同志于2010年9月16日在南开公能讲坛上所作的报告,本刊登载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 隋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