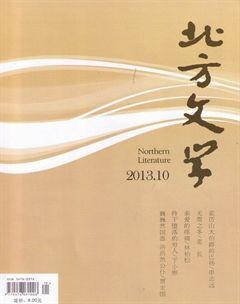螺蛳宴
陶群力
几颗星星在天空眨巴起眼睛,龙江化肥厂的家属区一矮房外围着好多人。“哇”地一声啼哭传来,人们雀跃:“生啦,生啦!”
罗四眼的婆娘一阵风般出来,“小子,是胖小子耶!”
“请客,请客。”人们嚷嚷着。嘻嘻,嘻嘻,赵麻子咧开嘴,两手不停地搓着。
“傻样,还不快进屋?!”有人捶了一拳头。赵麻子抬头,扫视了一圈,像个将军,手一挥:“上酒,开宴。”立马有人抬来三个酒坛、两个超大瓷盆,唤, 开宴喽……大家一看,傻眼了,整整两大盘螺蛳,掌声暴雨般响起,大伙高喊,乌拉,乌拉——
罗四眼知道咋回事的。眼睛就红了,想哭。
那年,赵麻子带着罗四眼他们来到了这千塘畈。同行的,共七人,六男一女。
下了车,赵麻子愣了:“我的个亲娘唉,这啥鬼地方,还说江南处处好风光哩!”眼前一片荒草艾艾,风呼啦啦地号。已是草长莺飞四月天了。
那个叫柳芳的女娃却故意这样唱:“如今的好江南,处处是南泥湾!”赵麻子瞪了她一眼。女孩调皮地伸了伸舌头。
赵麻子下令,吃完干粮,上山砍树。
山路弯弯,满目翠绿。上到山顶,到处是五针松、香樟、红豆杉。一袋烟工夫,木材备齐了。赵麻子发现山的背面有条江,他让大伙将木料放倒,自个儿溜下去。到了江边,江水清澈见底,有几只鸬鹚在江面扑腾,溅起水花朵朵。
“咦,快看,快看,这啥玩意儿。”柳芳一乍一惊的。大家一瞅,见水中有小东西嘴巴一翕一合,慢慢地“游动”。都摇头,不知何物。“捞上来,带回去再整,”赵麻子笑说,“这玩意儿指不定就是个宝呢。”
回来遇一老农,老人家说,这是“螺蛳”,很好吃的。
到了营地,赵麻子支起铁锅,点火烧饭;那帮秀才躺在地上,一个个喊累死了。赵麻子摇头,一群没用的蛋蛋。便动手整那螺蛳了。待螺蛳起锅后,罗四眼捞起就往嘴里咬,“嘎嘣——”罗四眼呸、呸,一颗牙就带了出来。嘴上挂着好多血。柳芳咯咯地笑说,真逗。
后来,人们才晓得,吃“螺蛳”这玩意儿,得剪掉屁股眼儿。当然,赵麻子做的“螺蛳宴”同样不能吃。赵麻子没搁盐、酒、酱油哩,那螺蛳还得放了辣椒才够有味儿。
勘测进展到一半,开来大队人马。千塘畈换了面貌。工地上,五彩的小旗迎风招展,高音喇叭传出女播音员甜润的声音。赵麻子站在太阳底下,草帽也不戴,两手打着拍子,很有节奏,扯起公鸭嗓儿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赵麻子觉得很威武,仿佛大军南下那会儿,他在指挥着部队。推小车、担土筐的人群里有人戏谑:赵厂长唉,你不怕变成黑泥鳅啊。
赵麻子的肚子闹革命了。咕噜咕噜地闹腾。他瘫坐下来。
“妈了个巴子。人马老子是多了起来。可这帮娃娃总不能跟着老子受苦,每天尽吃萝卜、青菜,面糊疙瘩啊。”
赵麻子盯着这群后生寻思。眼球一骨碌:有了——让女娃娃们抓螺蛳去!
于是,食堂的灶台上每天就有扑鼻、诱人的香气飘散出来……人们的干劲更足了,赵麻子也更威武了。
这赵麻子,平时粗嗓门喊人,说话呢,也常带个“屌”。别看赵麻子长得五大三粗的,还蛮懂讨好女孩的。
有人发现了秘密。原来这赵麻子每回去食堂,让炊事员开个小灶,叮嘱烧的螺蛳少放些辣椒;赵麻子也不在单位吃,装上小饭盒,带回去。
带回去的螺蛳是为了上柳芳姑娘寝室的。柳芳是苏州人,喜欢吃甜食。上哪弄白糖呢。这赵麻子,就跟在省军区当大官的老首长说,寄点白糖来,俺这有个“秀才”得病了,要白糖!
麻烦事来了。过些日子,柳姑娘的肚子一天天鼓胀起来。有嚼舌头的说,那一定是老赵干的好事。闲言碎语传到了老赵耳朵。老赵骂:“是哪个龟孙子干的!”
老赵找到罗四眼,一把拽过衣领,说:“你四眼儿要真对柳姑娘做了啥缺德事,看俺不砸扁你。”“狗屁。你……你,你侮辱人。”罗四眼梗着脖子,声音颤抖。“是哪个杂种呢?”赵麻子一脸迷惑。
厂子里许多人的肚子都大了起來,连老爷们儿也不例外。原来,柳姑娘闹的是一种“吸血虫”。风波过后,柳姑娘却整日不再言语了。也有人说,是柳姑娘的父亲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柳姑娘要走了。同天来到千塘畈的同志,不,是战友,来送她。
月高星疏,秋虫在秋风里哀婉地唧鸣。赵麻子说:“来,为未来,为友谊,干杯——”他的眼湿润润的。
红红的篝火上,一铁锅满满的“螺蛳宴”飘出浓烈的辣椒味,赵麻子的鼻子汗珠点点,闪烁着耀眼的红光。柳姑娘捂住嘴不停地颤抖着身子。罗四眼像个孩子,“哇”地跑开,哭得很凶。
柳姑娘走后,没人再见赵麻子吃过“螺蛳”了。直到他老婆生大胖小子那天,才让大伙备了一桌子“螺蛳宴”。
多年后,当我成为赵麻子的儿媳妇时,我的母亲——柳芳才得以与赵麻子相见;赵麻子摆了一桌子各式“螺蛳宴”,上面的那段故事是陪客的罗四眼叔叔讲给我听的。
责任编辑 付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