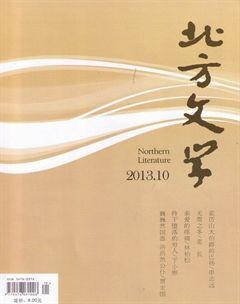油城春趣
满文斗
周六的下午,天气时晴时阴。从楼上望去,一面是忽明忽暗的云朵,一面是忽暗忽明的太阳。
“咱俩去挖苣荬菜?”我征求着妻的意见。
“好吧!”妻拿上一把雨伞。
“不用带雨伞。”我武断地说。
出得门来,竟有几滴雨点儿稀疏地飘来,雨点儿还挺大,有的落在地上竟有铜钱儿大小。
“回去吧?”妻撑起雨伞。
“我看没事儿。”我看看天,踅出小区大门。
我家附近有一潭湖水,相距楼区百儿八十米,名曰燕都湖。这个燕都湖有三十多万平方米的面积,一条创业大道把它分为两半。这个湖原本叫王连科东泡,一听就土得掉渣儿,不像燕都湖那么有诗意。不过,还是很有历史沉积感的,里边还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据说,上个世纪初期,随着清朝末年东北地区的开禁,就有一些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人们闯关东而来,落户于荒漠无际的让胡路一带,垦荒开地,割草熬碱,采药搭棚。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一锹一镐的辛勤劳作,使这里有了鸡鸣狗叫、炊烟袅袅,生机盎然。在这些开垦的人群中有一个叫王连科的人,落户于现在的明湖、燕都湖附近。由于他在这一带也算大户,有些名气,他所在的那个自然屯就叫王连科屯,附近的这两个泡子也就顺其自然地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个大的也就是如今的明湖叫作“王连科泡”,小一点儿的也就是现在的燕都湖叫作王连科东泡。这很像我的老家,现在还叫“满国芳屯”,那就是以我爷爷的名字命名的,我的祖辈也是闯关东来的。
我和妻顺着燕都湖的南沿儿向西走去,湖边修砌的汉白玉围栏还算整齐,偶尔也有些破损。平整的水泥小道,早已成为附近居民遛弯儿的好去处。虽然已是闰四月的下旬,水泥小道外侧的荒地之间,还是青草与枯草相间而生。就在荒草之中,偶尔看得见几棵深绿颜色的苣荬菜隐现其间,几许紫色染在叶片上,甚是好看。
此时,虽然乌云依旧,些许的雨点儿却已经不见了踪影,气温立即上升。我和妻依然在草丛中寻觅着苣荬菜。苣荬菜,菊科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野生于荒山坡地、海滩、路旁。东北多为蘸酱食用;西北一般做包子、饺子馅;华北则多为凉拌、和面蒸食。这种东西,早些年间我也曾挖过,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后期,当时不到五十岁的奶奶,踮着小脚,领着尚小的我路过田间地头儿或房山野地,剜上一把,洗净蘸酱吃,也算是充饥调味。至今,那种浓浓的苦味儿还萦绕在口中。近年来,也不时地吃上一口,有时是在高档的酒店,抑或也有在市场中买上几两,回家打上一碗鸡蛋酱,就着小葱,也能吃上一两碗香喷喷的米饭。不过,现在野生苣荬菜已经被人工种植的所取代,大棚经济代替了自然生长。不论是什么季节,不论是什么地界儿,人们都能够吃到新鲜的苣荬菜,然而,苣荬菜的味道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浓浓的苦味儿变得淡淡的不說,没了那种野味儿,倒叫人感到缺少了些什么。
“来来来,你看这几棵是不是?”我向妻挥挥手。
“嗯,是!”妻用小铲子铲下一棵,看看根茎,肯定地说。
当然,这种野生的一定比市场上卖的保真,是纯天然的。因为就长在我们的身边,就长在燕都湖畔。说起燕都湖畔,我还真的很欣慰。如果是傍晚,如果是夕阳西下,你若置身于燕都湖畔,隔湖眺望,在火红的夕阳映衬下,周围新兴的楼群,若剪纸一般,贴在火红的天际,又倒映在静静的湖面,并随着落日余晖的渐渐退去,五彩的灯光又替代了金辉一抹,使湖景更加绚烂多彩,让傍湖而居的人自然领略到东坡先生比喻西湖的那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似的人间胜景。
然而,当石油大军尚未进驻这片荒原以前,这里蛮荒的天地之间人烟稀少,荒滩遍布,野草萋萋,就连鸡鸣狗叫都显得格外的凄凉。当数万名头戴狗皮帽子、身穿杠杠服的会战大军,“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东西南北来会战的壮举发生以后,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阳出来了,回去吧,有这一把也够吃了。”妻说。
望望天空,云散雨停,暖暖的阳光洒在草地上,随风涌动着的燕都湖的水面,波光粼粼,甚是养眼。
随着近些年来城市建设脚步的加快,大庆油田绿色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早已不是过去“青天一顶,荒原一片”的旧印象。甚至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只能通过原始的图片和影像资料,才能一窥几十年前大庆油田艰苦状况。就说这燕都湖畔吧,百年的荒芜与今日相比,也已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了。周围数百栋外形各异、参差错落的楼群拔地而起,当你偶尔一瞥,颜色碧绿澄黄的树林间,相扶相搀的银发老人,缓步遛弯儿;汉白玉围栏边,亲密依偎的情侣,漫步徜徉;休闲广场里,天真烂漫的孩童,追逐嬉戏;湖畔亭台座椅周围,几家要好的友朋举杯野餐,品尝烧烤,真可谓是惬意安然。再加上湖中小岛矗立着的磕头机,成为这座城市固有的标志性建筑,既为我们身边平添一抹亮丽的风景,也用它那美妙的歌喉,轻声哼唱着一曲韵味悠长、永无止境的幸福圆舞曲,勾勒出一幅幅现代化油城恬静的景致。
噢,春的油城太美了!
责任编辑 刘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