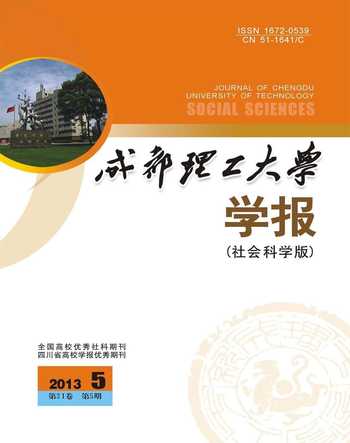东晋佛隐诗创作述略
高智
摘 要:东晋佛教蓬勃发展,佛教思想与隐逸文化的相通合流,助长了隐逸之风,在汉魏时期演变为成熟的隐逸诗,在东晋达到了繁荣。佛隐诗成为一种新的隐逸诗形式,东晋诗僧是佛隐诗的主要创作群体,庐山隐逸集团是其中重要流派,支遁、慧远等是佛隐诗创作代表。佛隐诗中多有镜、水、月等佛教意象,是艺术审美与宗教哲学的融合,佛教意象丰富了佛理隐逸诗的内涵,对后世佛教与诗学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东晋;佛隐诗;创作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5007407
随着佛教的传播,玄佛结合,东晋士人崇佛现象很普遍,文人多精通佛理,名士多以与僧人交往为荣,王导、谢安、许洵、孙绰等与名僧支道林、道安、法深、法汰等交往甚密,玄佛相互渗透,老庄之学与佛学并行不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隐逸文学的创作上,既没有阮籍、嵇康正始名士鄙薄功名,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清高,也没有太康之英畏灾避祸,“仕”与“隐”的极度矛盾。这一时期隐逸诗歌的创作,是和山水、诗酒和清谈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从容不迫的风度,与悠远达观的心态,借山水抒情,寓哲理于玄言[1]。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佛玄合流的趋势,使得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玄言诗开始盛行。支遁作为东晋玄言诗的开创者之一,不仅将佛理融入玄言诗中,更将其对般若学的认识和即色论的思想一并融入诗歌创作之中,催生了佛理隐逸诗的出现。
一、东晋诗僧与佛隐诗的创作
东晋僧人都有较高文学修养和创作才能,僧人多以隐逸高士自居,《高逸沙门传》即是两者融合的产物。以支遁为代表的佛教徒,以佛理入诗,写山水之乐,“妙唱发幽蒙,观化悟自然”(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皓然之气,犹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竺法崇《咏诗》),用佛教意象,吟咏佛境,抒发隐逸之情,形成独特的佛隐诗。以道安高徒慧远为中心的庐山诗僧集团,吸引了大批僧人名士隐士,诗酒唱和,亦佛亦隐,支遁、康僧渊、竺法崇等僧人,都创作有大量隐逸诗,诗风恬淡雅逸,在当时影响很大。
早期的佛理隐逸诗创作者有康僧渊、支遁、竺道壹、竺道潜、慧远、史宗、帛道猷、竺僧度、张翼等,这里主要列举帛道猷、竺道壹、支遁和康僧渊等人的部分作品。
支遁、帛道猷并举,开佛隐诗先风,清钱谦益《有学集》卷二十评曰:“静拱虚房,永怀支遁,陵峰采药,希风道猷。”支遁事迹颇详,道猷史载很少,且文献所载资料牴牾处较多。
《高僧传》载:“释道猷。吴人。初为生公弟子。随师之庐山。师亡后隐临川郡山。”第七卷(义解四三十二人)条:宋京师新安寺释道猷。道猷则变为刘宋时人。《诗品》评道猷见于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条,作齐人。
其实考道猷交游,可知道猷大约生活在晋末宋初。《高僧传》有“少以篇犊著称。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与道壹有讲筵之遇。后与壹书云。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
竺道壹为晋末吴人,俗姓陆,孝武时,会稽守王荟为起嘉祥寺。隆安中卒,葬虎丘山南。道壹性至简,广游历,喜隐逸,尝作《答丹阳尹》表达自己的隐逸志向,指明佛理与隐逸的关系,云“盖闻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夺其性。弘方由于有外,致远待而不践。大晋光熙,德被无外,崇礼佛法,弘长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远万里,被褐振锡,洋溢天邑,皆割爱弃欲,洗心清玄。遐期旷世,故道深长隐;志存慈救,故游不滞方。”(《高僧传》五),
道猷与道壹有“讲筵之遇”,又一起“优游山林”,其中,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便是两人交游之作。此诗为隐逸诗名作,清人吴之振《宋诗钞·石门诗钞》称此诗为“山阴帛道猷诗寄道壹,有相招之意。”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间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宋魏庆之以为后世名句多出于此,道猷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后秦少游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僧道潜云:隔林彷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于道猷(《诗人玉屑》卷八)。明杨慎于石刻读之后,在中连连称奇:“此四句(上接‘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千古绝唱也!”(《升庵诗话》卷六)。深山茂林,一片寂静,不实写人家,只借一声鸡鸣,引人想象,便道破所有天机,妙极!后世作家也多借鉴这一虚写手法,隔物闻声,借声写景。如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梅尧臣《鲁山山行》“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支遁为东晋第一大诗僧,买山而隐,交游甚广,作品繁富,影响深远。计有《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收录诗文,逾十卷之多。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支遁诗16首。
支遁事佛陀,为东晋著名隐士,“寻元存终古,洞往想逸民。”(《咏利城山居》),支遁承阮籍之风,作《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两首,多谈隐逸之志,抒遁世之情。“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 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中有寻代士,外身解世网”,“ 闲邪托静室,寂寥虚且真”……于孤独中静思宇宙人生的奥秘,彰显着诗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哲思的敏锐。“俯欣质文蔚”,支遁于东晋诗僧中,是倾向文质兼胜的。
支遁创作的佛理隐逸诗,多是以自述人生和对玄佛的理解为主,如: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中路高韵益,窈窕钦重玄。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咏怀诗》其一)
这首诗叙述的是诗人由老庄进入佛门的的思想历程。诗的前六句,简述了诗人早年的身世和经历,未入佛门前,不知人生真谛,尸位素餐,日复一日的无所事事。灰心丧气地困在人情风波里,随波逐流地追逐物欲。直到人生出现转折,高雅的韵致日益增加,美好的愿望化为对玄佛的钦佩和重视。诗的余下部分,皆是描写诗人探玄求道,研习佛理的过程。“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一问一答,质问玄佛意义何在,只有达到庄子“至人无己”的境界,才能寻得真理。紧接二句中的“苟简”、“逍遥”也是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苟简”一词,原意为草率简陋,这里引伸为老子“无为”的处世准则,“逍遥”则是庄子学说中追求的最为自由彻底的人生境界。“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这四句则是对之前追求的逍遥境界的描述,即心明神莹、清淡虚无、顺应自然的境界,孜孜不倦的情感已经退去,光彩明丽的玄佛思想令其倍感新鲜。诗末:“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徘徊不前来回观看物象,还未开始便已看见全部,这里用的是《庄子·养生主》里“庖丁解牛”的典故:不以目视而以神遇。毛、鳞虽然重要,但诗人心中已得见全牛,这些表面物象皆可忘却,最后用《庄子·外物》里“得鱼忘筌”: 毛、鳞珍贵,细部物象的呈现显然比达到的途径更为重要。
以上可见老庄思想对于支遁有着很深的影响,汤用彤评曰:“东晋名士崇奉林公(支遁),可谓空前,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 [2]。除了对玄学的深刻理解,支遁对般若学也有着独道体会,认为在佛教经典中,“《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大小品对比要钞》)。
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辔,领略综名书。涉老咍双玄,披庄玩太初。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匠徂。萧萧柱下迥,寂寂蒙邑虚。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途。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怅怏浊水际,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咏怀诗》其二)
此诗写诗人领悟般若学“空无”理论的途径及体会。首八句是诗人阅读老庄著作体悟玄理的过程,一个人独自静坐在孤影里,闭上眼睛苦苦思考玄理,在仰卧中缓缓收敛精神的辔头,领略各种名作,读到《老子》,领悟双玄而发出笑声,批阅《庄子》,玩味宇宙的起源,吟咏志向,抒发情怀,这种感觉如同清风吹拂,引起的思考全都感觉恬静愉悦。中间八句以浅显的自然现象来说明佛理。低头欣赏老庄质朴华丽文采的同时,抬头为两位文学巨匠的逝世感到悲伤。时光如白驹过隙,在悄无声息中走向虚无。寥廓深远的千载往事,都将归于空无。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感到伤感呢?世间万物都是殊途同归。最后十句,描述诗人经过思考、阅读、领悟透彻后达到的空无境界的体会。只有通过冥想才能体会到玄理,从无形无象中拾取玄学精华。在污浊的水边感到惆怅不快乐,几乎忘记自己是在映照着清澈泉水。心如明鉴地反观自己,才能回归到澄净的境界,从容地获得与玄理相符的意蕴。心灵与各种道理密合无间,形体与各种物欲渐渐疏离,所有的人和事都将荒凉、凄冷地逝去,唯独精神长存。
受东晋玄学影响,支遁的佛隐诗多掺杂玄理,“中路高韵益,窈窕钦重玄。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咏怀诗》其一),“感降非情想,恬泊无所营。玄根泯灵府,神条秀形名”(《四月八日赞佛》),“玄祗献万舞,般遮奏伶伦。”“缅哉玄古思,想托因事生。(《咏八日诗三首》,此外,支遁崇佛又重道,兼有佛僧、道士、隐士三重身份。《八关斋诗三首》载支遁集僧人与道士二十四人于吴县土山墓下,吃斋、作诗、采药,“清和肃穆,莫不静畅”。“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药。集严水之娱。”他的佛隐诗把“静斋”“坐禅”与“采药”结合起来,“令月肇清斋,德泽润无疆。”(《五月长斋诗》),“从容遐想逸,采药登祟阜。”(《八关斋诗三首》)),他的隐逸诗作兼容性佛道,“色空观”、“波若学”和“物物论”(《逍遥论》)“物物而不物于物”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
除了支遁外,西域僧人康僧渊也值得关注,他也是著名隐士,晋成帝时过江,于豫章山立寺讲说,“栖峙游方外,超世绝风尘。”(《又答张君祖诗》),后卒于寺中。《世说新语·栖逸》载其事:“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庚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起。后不堪,遂出。“闲居研讲,希心理味”,离群索居,隐于山野,研习佛理,遵循佛教教义,把隐逸和出家修行结合起来,有异于张君祖的“何必玩幽闲,青衿表离俗”,(《咏怀诗三首》),认为修行不必出家的观点,后者和竺法深、竺道生一起,倡导成佛不必出家,为佛教的中国化,禅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康僧渊的诗,“恬淡雅逸有晋风”(《诗纪》),在《代答张君祖诗》中将佛理与栖居的真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真朴运既判,万象森已形。精灵感冥会,变化靡不经。波浪生死徒,弥纶始无名。舍本而逐末,悔吝生有情。胡不绝可欲,反宗归无生。达观均有无,蝉蜕豁朗明。逍遥众妙津,栖凝於玄冥。大慈顺变通,化育曷常停。幽闲自有所,岂与菩萨并。摩诘风微指,权遒多所成。悠悠满天下,孰识秋露情。
“逍遥众妙津,栖凝於玄冥。”流露出诗人隐于物外之境的快乐,诗的前十四句,诗人举了“冥会”、“本末”、“有无”、“逍遥”等字眼,表达其对玄理的理解感悟。后八句则列了“大慈”、“菩萨”、“摩诘”等佛意词语,将佛理融入诗内,“表达了真心向往无生无灭涅槃之真理”,最终发出“悠悠满天下,孰识秋露情”的叹息,感慨世人大都无法真正领会佛旨。
张翼(君祖)善草隶,为东晋著名书法家,是东晋隐逸诗僧集团的重要人物,与康僧渊、竺法頵等唱和颇多,《答康僧渊诗》中“蔚蔚沙弥众,粲粲万心仰”,“三法虽成林,居士亦有党。”“冲心超远寄,浪怀邈独往。”《赠沙门竺法頵三首》“万物可逍遥,何必栖形影。”等表现了在隐逸中体味佛理带来的心境自由超迈之情。
二、庐山隐逸派与隐逸诗
东晋末年,政局混乱,社会动荡。378年,前秦围攻襄阳,道安分遣徒众,慧远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到荆州住上明寺。381年至浔阳,见庐山情景秀丽,足以息心,遂定居此地。慧远从此“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深居庐山30年,直至逝世。这期间他创建精舍,修筑寺庙,裁松种竹,别置禅林,尽览庐山之美。同时,以慧远为首的庐山僧人形成一派,以“隐逸遁世”为主体,吸引了许多文人,庐山也因此一度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
东晋佛教已经普遍流行,信徒众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教徒出家求佛隐居,士大夫避世不合作,自耕农的减少,对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教权和政权的较量成为东晋政治一大现象。元兴元年(402),桓玄当政,下令沙汰僧众,为出家设置门槛,意图缩减僧尼人数,增加国家收入,但对庐山隐逸派特别关照,把慧远等人,划入“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类,允许他们可以继续出家。
慧远作为庐山隐逸派的领军人物,多有诗文创作,可惜大都已经失传,现存诗歌只有《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写东林胜景:奇峰突起,山岚云蒸,恍然仙境。清净山水,涤却杂念,幽邃深谷,叮咚山泉。“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诗中之客指的便是诗人自己,独游山林,冥想佛理,在林中小径里流连忘返。“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诗人在山林中神游,借风景探索玄机,在挥手间感受心境,心安即可,不必疏辟求通。“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神思如流水,叩响心扃,触及玄理,心扃既开,便直接从山水感悟到佛理的存在。“孰是腾九霄,不奋冲一翮”,这是在问,怎样才能不展冲天之翅,却能奋飞于九霄云天之上呢?最后两句则是对其的回答,“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佛理之妙,山水神趣,两相交汇,互相渗透,在这之中领悟的佛理,远胜于儒家修身的“三益”之法。
东晋隆安四年(400)仲春,慧远与徒众三十余人游石门山,这是一次大规模吟咏活动,有兰亭集会遗风,“因咏山水”,“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写自然之美蕴,体悟山水之道,阐发佛理,旨在否定神仙道教,抒发隐居的幽情。《游石门诗并序》:
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端坐运虚论,转彼玄中经。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写隐居中的悠远之境,没来由的特别兴致,心中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了。忽然听闻要去石门一游,突发奇想地提倡要吟咏抒情。撩起衣裳,思绪似乎驾着云朵远去了,望着断崖想念昔日的曾城。快步登上山岩,不觉得体重有所减轻。回头一看,仿佛能踏入天上宫阙,天空也不觉得有多遥远。端正地坐好,旋转心中法轮,感悟高深玄妙的理论。既然神仙也和我们一样生老病死,那就任其含糊不清,无须过多深究。
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均作《奉和慧远游庐山诗》:
理神固超绝,涉粗罕不群。孰至消烟外,晓然与物分。冥冥玄谷里,响集自可闻。文峰无旷秀,交领有通云。悟深婉中思,在要开冥欣。中严拥微兴,□岫想幽闻。弱明反归鉴,暴怀傅灵薰。永陶津玄匠,落照俟虚斤。
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彻彼虚明域,暧然尘有封。众阜平寥廓,一岫独凌空。霄景凭严落,清气与时雍。有标造神极,有客越其峰。长河濯茂楚,险雨列秋松。危步临绝冥,灵壑映万重。风泉调远气,遥响多喈嗈。遐丽既悠然,馀盼觌九江。事属天人界,常闻清吹空。
觌岭混太象,望崖莫由检。器远蕴其天,超步不阶渐。朅来越重垠,一举拔尘染。辽朗中大盼,回豁遐瞻慊。乘此摅莹心,可以忘遗玷。旷风被幽宅,妖涂故死灭。
三首诗大都以谈玄理,阐发佛教义理为主,可见当时佛道释合流形象已经很普遍,佛道关系尤为密切,庐山隐逸派受慧远影响很深,慧远本人其实也是博采众家,先学世俗之学,再学道,最后才参习佛学的,“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高僧传》卷六本传)。
庐山隐逸派的出现,为当时的众多隐士所向往,如周续之、雷次宗、刘程之等人皆侍奉过慧远,宗炳还常常上庐山向慧远请教佛义。故其在佛教传播及隐逸文化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东晋佛隐诗中的意象
(一)佛教意象与诗歌意象的关系
意象,是抒情文学中特别是诗的主要构件之一,《周易·系辞上》“圣人以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老子》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东汉王充《论衡》将“意”与“象”合二为一“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士龙亦夫熊糜布侯之类。“(《论衡》十六卷《乱龙篇》),此“意象”指古代箭靶上所绘动物图案,传达当时的一种礼制,已经变成了一种象征手法。
魏晋之交,文学走向自觉,“缘情”、“体物”在诗学中涌动,诗人的关注“情”与“物”的关系,情思与物象交织,由此生出了诗学中的意象思维,“意象”的审美功能逐渐被揭示。西晋挚虞论及意象与赋体文学的关系云“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心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文章流别论》)。陆机则强调“意象”为作家构思时的特意追求“虽离方而遯圆,期穷形而尽相”(《文赋》)。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里提及的“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是意象在我国古典诗学中的首次运用,指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对象互相感发而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艺术形象。可见六朝时,意象作为一个艺术审美概念,在文学表达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重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学意象范畴的提出和完备建构与佛教思想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3]。六朝时期,佛教的兴盛,佛教思想也跟着活跃起来,东晋著名僧人僧肇在其代表作《不真空论》提到“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正因为“象非真象”,故不能执着于象[4]。这与《庄子》里提及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思想相似,玄佛合流后,强调了意象之主体的意,促进了诗学意象范畴的提出。
由上可知,意象理论的建立离不开佛教的影响,这便使得意象这一概念拥有了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是艺术的、审美的;一方面它又是宗教的、哲学的。这两种含义常常相互缠绕,难以区分,意象概念也在这种意义交织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而佛教意象与诗歌意象间的关系,则正体现了意象概念中双重意义的不同指向[5]。
(二)佛教意象在隐逸诗中的表现
东晋时期的佛教主要呈现般若学和涅槃学两大流派,受玄学思想里“无”的影响,般若学的主旨,同时也是六朝时期佛教镜意象的主要意蕴,即是“空”。佛教典籍中“空”的意蕴常常被用来阐明佛理、宣传佛法。佛教极重“空”,这一思想几乎成了佛教之象征,如出家被称为遁入空门,得道高僧被称为解空大师,大乘般若空宗的十八空,以及支遁的“色即是空”等论述,可见空无思想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般若学中特别提到了“万法皆空”,在解说这一佛理时还用了许多譬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金刚经》中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所有一切,都“如梦”、“如电”一般空幻,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其倾向是虚无的,但却启发了晋宋之际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宏大视野和全新的境界。
佛教宣扬的这种虚空,将一切视为无的思想,在当时背景下,与隐逸诗人的思想倾向是有一定契合的,“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张翼《赠沙门竺法頵三首》)。佛教思想的出现,代表的是一种出世思想,这与隐逸文化是相似的,只有将一切视为空,才能真正放下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这也是隐逸文化中注重的对世俗价值的疏离和扬弃[6]。东晋诗学正是因为吸收了佛教镜意象中空的意蕴和精神,才能展现出色空一如、虚实相生的独特审美气象。加之隐逸文化与佛教空无思想的种种契合,使得此时隐逸诗中描绘的虚空物象,超越了单纯的物象层次,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内涵,蕴含了众多的文化象征意味,凸显了这一时期佛教和诗学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以下略举数例:
以水为例,佛教常以水的流转不息、易逝难追喻指生死轮回、生命无常。佛教的《三法印》中提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个法印的意思是:“世界万有变化无常;一切现象皆因缘而合,没有独立的实体和主宰者;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佛教徒总是坚信自己已认识了人生实相,故对死无所畏惧,死亡对其而言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种解脱,摆脱了这身臭皮囊,才能完成超脱,神识就能前往西方极乐净土,即涅槃,这是每一个佛教徒都梦寐以求的境界。因此东晋以降,受佛教沾染,隐逸诗中“水”意象,既是隐士守虚处静的养生法,又受佛理的影响[7],董京“仰荫高林茂,俯临渌水流。恬淡养玄虚,沈精研圣猷。”(《赠挚仲治诗》)。孙统“期山期水”,“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兰亭诗二首》),江淹《访道经》:“澹深韵於白水,俨高意于浮云。”王籍《入若邪溪诗》“艅艎何汎汎,空水共悠悠”。东晋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把隐逸诗中“水”意象与佛教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
这个“神趣”即为“佛理”,“所以,以水流不止喻生死轮回是佛教水意象的典型意蕴。通过水喻,佛教将其对人的生死问题认识的严密体系展现出来,相对‘明确地解除了对人生苦短的焦虑[8]。”
佛教“月”意象中通常讲人生空幻的核心意蕴,月在佛教中常用来喻指人生的短暂、空幻。《摩诃般若经》初品:“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闼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缘、如化。”这里谈到的佛教著名般若十喻之一的水中月,就是用来说明诸法缘起无自性、人生虚妄不实的道理。
佛教中的月意象还用来喻指佛性圆满、本自清净的教义。如《佛说月喻经》曰:“皎月圆满,行于虚空,清净无碍。”还有《大般涅槃经》卷九《如来性品》云:“譬如有人见月不现,皆言月没而作没想,而此月性实无没也。转现他方彼处众生复谓月出,而此月性实无出也。何以故?……如是众生所见不同,或见半月,或见满月,或见月蚀。而此月性实无增减蚀啖之者,常是满月。如来之身亦复如是,是故名为常住不变。”众生看月有圆缺有无的变化,这是由于人自身所处的状态所致。月亮光照四方的,正如佛性本自清净无染,圆满自足。《大般涅槃经》卷二十《梵性品》:“大王,譬如月光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渐渐损减,月爱三昧亦复如是,光所照处所有烦恼能令渐减,是故复名月爱三昧。……能令众生除贪恼热。”这里是将月光比作佛教教义,能带领众生走出贪恼痴嗔等无明状态,突出了佛教对众生的重要意义。
六朝时期,随着佛教思想的全面渗透,佛教月意象所代表的“人生空幻”意蕴与诗歌中的月意象开始结合起来[9],演变出一种悲而不伤的新意识,成为隐逸诗中常用的意象。杨羲喜用“月珠”,“佩玲带月珠,薄入风尘中。”《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台昭灵李夫人作与许玉斧》,“龟阙郁巍巍,墉台落月珠”(《歌》)。支遁“穆穆升堂贤,皎皎清心修”(《八关斋诗三首》其一),用“皎皎”,“乐野室之寂”,写斋后“清和肃穆,莫不静畅”的心情。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南朝,如江总隐逸诗《游摄山栖霞寺诗》:
霡霂时雨霁,清和孟夏肇。栖宿绿野中,登顿丹霞杪。敬仰高人德,抗志尘物表。三空豁已悟,万有一何小。始从情所寄,冥期谅不少。荷衣步林泉,麦气凉昏晓。乘风面泠泠,候月临皎皎。烟崖憩古石,云路排征鸟。披迳怜森沈,攀条惜杳袅。平生忘是非,朽谢岂矜矫。五净自此涉,六尘庶无扰。
江总极善写景,常通过情景相融,寄情于景来表达自己的愁思,或抒发朋友离别的悲凉,或惋惜韶华易逝[10],此诗也不例外。这首诗是其在追忆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而作,颇有谢灵运山水诗的痕迹[11]。用“皎皎”明月,写栖宿绿野隐居山寺的高僧,赞扬其高洁的品德,“敬仰高人德,抗志尘物表”。“乘风面泠泠,候月临皎皎。”凄冷的风迎面扑来,让人不禁感到一丝悲凉,但抬头望见天上皎洁的明月,在皎皎月光的映照下,多少冲淡了这股悲凉感。这里的月意象,便是佛教意象融入诗歌后新的表现形式 [12]。
东晋佛隐诗中的月意象凸显了悲而不伤的意识,使诗歌月意象具有了和谐、安适、空灵的境界追求和深邃、悠远的宇宙意识和终极关怀。月意象意蕴看似不同,实则具有一致性:因人生空幻而要修道,修道在于领悟佛理,领悟佛理要有佛性,因人人有佛性而佛性本清净;佛性真如玄妙神奇,非语言所能把捉。即佛教月意象的核心意蕴是人生空幻。
四、结语
佛教思想与隐逸文化的种种契合,从两晋之交开始,佛教便对隐逸文化展开了渗透,直到南朝梁代二者合流的完成,隐士与僧人从此不分家。东晋中期,支遁开创玄言诗后,将佛理融入玄言诗中,促进了佛理隐逸诗的形成,而以慧远为首的庐山隐逸集团的创立,更是加速了佛隐合流的步伐。而佛教意象中镜空思想、水流不止的生死轮回观、月意象中悲而不伤的新意识等对诗学的融入,则进一步丰富了佛理隐逸诗的内涵。东晋是佛教的繁荣期,也是隐逸文化的兴盛期,二者的发展与交融,对后世佛教与诗学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汤用彤.两晋之名僧与名士[G]//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刘艳芬.佛教与六朝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陶文鹏,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林庚.中国文化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7]袁行霈.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脉络[M]//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8]任继愈.佛教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9]李文初.汉魏文学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10]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11]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吴小如.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