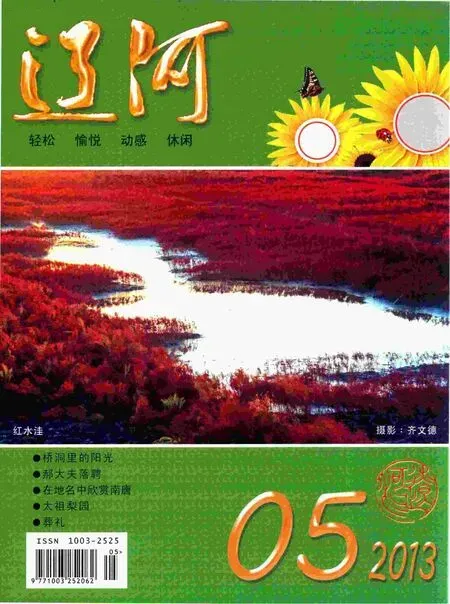1976年的年味
黄圣福
1976年秋天,我们家那只养到半大的猪,耐不住圈养的寂寞,一天,觑准机会,拱开没有栓牢的圈门,溜到生产队的庄稼地去大快朵颐,很不幸地遭遇了瘸子天福的儿子。瘸子天福专职看护庄稼,那天不知他病了还是什么的,由他儿子“代父从军”,他儿子是个有名的二愣子,还是个“飞毛腿”,那只笨猪不知死活地跟他赛跑,惹恼了他,结果挨了他几红缨枪,死了。这样,我们家赖以过年的种种打算就都泡了汤啦。
那时,每年出一头猪和冬季做贩卖海蛎生意,是我们家的两大经济支柱,随着那只猪的不幸夭折,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就一股脑儿斜压向做贩卖海蛎生意那根柱子上,要不是我们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尽力撑持,那我们家的经济怕要“天柱折”而“天倾西北”,那么,那年过年,我们恐怕就得喝西北风啦。
我们村地处海边,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次声势浩大的围海造田大举动前,村民们经营海蛎养殖。那时的海蛎养殖很简单,不过是把条石植于滩涂上,潮涨潮落,海蛎就附在条石上生长。那片海域被围后,海蛎养殖不能再进行,但经营海蛎的手段、什物都还在呀,村民们便都驾轻就熟地做起海蛎贩卖生意。
海蛎来自我们村东面的一座岛屿。那岛屿不小,当时的行政级别是公社。那岛屿与我们村相望的一面不怎么出产海蛎,挺奇怪的。起初,村民们都是坐渡船过那岛屿,再徒步翻山越岭到岛屿的那一边的最南端一些偏僻的村庄去,那儿的海蛎较便宜。后来,我们村东北方向筑了条跟那岛屿连接的海堤,村民们便通过那条海堤而去,来回行程七八十里,也是徒步,买了海蛎后都是挑着回来,虽然筑了海堤也通了公交车,但大家毕竟做的是小本生意,利润没几个子儿,不愿让公交车分一杯羹去。
贩卖海蛎生意,有的人家做带壳的,有的人家做不带壳的。做不带壳的会多挣些,其实多挣的也就是自家人剖海蛎的工钱。1976年以前,我们家做的都是不带壳的海蛎生意;1976年冬天我们家也做起带壳的海蛎生意。那生意脏,累,都是那条夭折的猪给招的。
那时买回海蛎的活由三姐出马,因为那年秋天二姐也出嫁了,又因为三姐跟二姐一样都没上过一天学,算术最头疼,而母亲那时总病怏怏的,所以她自愿揽下那粗活。那年她十六岁,每次能挑回七八十斤,甚至更多,真不简单。
母亲那时“专职”剖海蛎,父亲卖完海蛎回家,也参与。
父亲卖海蛎时总爱说“讲价不讲秤”,由于秤头足,回头客多,大多日头不到中天就回家。当然,海蛎卖得快,跟海蛎卖相好也有关系。
我们村里人经营海蛎生意很有一套,不是把剖好的海蛎直接泡在水里出售,而是把剖好的海蛎,先沥干了水,再匀在密箩里,夜渐深了才浸入注水的木桶或水缸里,用手轻轻抖散抱成团的海蛎,细心地拣干净碎壳,挑出大朵的海蛎均匀地铺在面上。第二天,连密箩从桶或缸里提出,水自然流干后,海蛎显得鲜鲜丽丽。那时,在集市常听我们村里卖海蛎的人跟客人讨价还价时说:“瞧仔细了,我的海蛎像猛糕(我们这儿的一种因发酵得厉害而又膨松的小吃)!”那绝不是“王婆卖瓜”,他们说得极有底气,极自豪。
剖海蛎的活绝不轻松,且不说手指叫咸腥的水给泡得死白死白、皱皱巴巴的,也不说手指常叫海蛎壳给划破而鲜血淋漓,单是长时间坐着就很让人吃不消。母亲那时年近五十,每每起身的时候,总佝偻着腰,手在腰眼好一阵子敲后,才能把腰伸直。
两个弟弟当时都还小,在村小学读书,一放学也帮着剖些。多数时候,他们是一放学,就帮着做饭,喂鸡喂鸭喂猪,到野地里牵回拴在那儿的羊。他们俩分工得挺好,配合得挺默契。
我那时在读初中,由于学校离家远,午饭在学校吃,傍晚放学回家,见母亲辛劳,也主动帮着剖海蛎。母亲见我毛手毛脚的,手指总被海蛎和扁而薄且锋利的剖海蛎的刀划伤、扎伤而不要我剖。不过,周末我却不愿袖手旁观,曾有几次主动请缨跟三姐去买海蛎,三姐挑带壳的,我挑不带壳的。
买带壳和不带壳的海蛎都有中间人,俗称“牙人”,他们领着我们到各家各户去收。各家各户把剖好的海蛎都养在水里,我们前去收的时候,照规矩要沥干水,他们不会拦住你。但怎样才能把水沥得最干,却是需要经验的。记得第一次,我挑回三十四斤不带壳的海蛎,由于沥水的经验不足,脱水得厉害,结果只挣了五角钱,被三姐和两个弟弟笑个半死。
做那海蛎生意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大队部冠之以“投机倒把”,每到冬季,总派干部到村里召集社员开会,三令五申地加以禁止,却总禁而不止。于是,他们便采取路口设伏行动,也不管用,村民以绕远道对付。一次,我们家的海蛎量比平常多,我便帮父亲挑了两小密箩海蛎参与绕道行动,我觉得那次“绕道”,起码多走了十里路。也正是那一天,大队部改变策略,组织民兵突击集市。那一天,多亏我在场,我眼尖,首先发现情况,帮助父亲逃避,让我们家的海蛎躲过一劫。而同村的阿朱嫂就没那么幸运,她正打点全副精神跟一个客人讨价还价间,一个民兵,像从天而落的神兵一样,提着她的海蛎就跑。阿朱嫂回过神来,举着扁担,像一个厉鬼嚎叫着追击,那个“神兵”一慌张,就把海蛎连同密箩甩向市场边上的一口臭水塘里。阿朱嫂哭天喊地,跟他玩命,高举扁担照着那“神兵”猛砸,把他给砸得头破血流。她那架势相当慑人,很有几分“玉猴奋起千钧棒”的气势。
从那天起,我因为要给父亲当护兵,上午总旷课,课旷多了便不好意思,后来干脆就辍学。辍学,当时算平常事,班主任并没有到我乡下的家做家访动员我回校。父亲因为我的不可或缺,也就由着我,我也就专心做父亲的护兵。
由于大队部组织的那次突击集市打击我们村的投机倒把活动,村里许多人家便有所收敛,这样集市上我们村的被称为“密箩蛎”的量就见少了,价钱便看涨,利润就可观多了。父亲很高兴,顺利卖完海蛎后,常常带我这个有功的护兵去吃碗馄炖(我们这叫“扁食”)以示犒劳,有时还另外赏我几分零花钱呢,我把它们都攒起来。
年近了,天气很冷,母亲抖抖索索地剖海蛎,因为冷,她胡乱穿衣,头上还总扎着一块花色模糊的旧头巾,冷风袭来,牙齿就咯咯打战,让她看上去像一只抱窝的母鸡。我和父亲和三姐风里来雨里去,但我们心里有希望,脸上有笑容。两个弟弟,那些家务活他们都做熟练了,配合得更默契。那时煮饭都烧柴火,柴火燃烧的时候有时会发出噼啪噼啪像放鞭炮的声音,母亲便会说是火笑了,预示家里有喜事,所以他们烧火做饭的时候,就特别渴望火笑的声音。第二天,如果父亲给他们买回新鞋子什么的,他们便欢呼雀跃,以为火笑的吉兆应验了。他们一高兴,进进出出便学鸡鸣学狗叫学鸭走路什么的,还瞎唱,特别是小弟,常唱样板戏歌曲,比如学《红灯记》里李奶奶唱:你的爹爹像松柏。他不理解歌词的意思,半方言半普通话地瞎哼成:你的爹爹反动派。我现在见着讨人嫌的人做令人厌恶的事时常学着小弟当初那样,把人家哼成“反动派”,哼完后眼前常会浮起小弟当初哼歌时歪着嘴梗着脖子的令人喷饭的样子,就常情不自禁地狂笑。
其实父亲是早计划早安排好了,临近年关,今天给这个买双新鞋,明天给那个扯回一块布。家里每个人过年穿的新衣的布都买齐了,便暂停两三天带壳的海蛎生意,改回做不带壳的,母亲腾出手,从叔公家借来那部印尼带回的手摇缝纫机给我们缝制过年的新衣服。母亲不识字,但手巧,当时一些潮流的服装样式她一看就会。母亲给我们量尺寸和让我们试穿新衣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那种开心是带点羞的,实在难于言表。
那两三天,嫁到附近村庄的大姐、二姐相约着回家来,她们帮着做年前大扫除,我们这儿称为“筅堂”。她们照传统,用新竹叶做成的接上长竹竿的专用扫帚,把屋顶上、角落里、墙壁上的蜘蛛网和灰尘扫去;把门窗擦得干净明亮;把床板、桌椅、箱橱都腾到池塘边去刷洗,放在太阳下晒。她们还合作拆洗被褥,晾在房前屋后,又编铺床的草垫。她们的努力,让杂乱无序的家显得干净整洁,充满冬日阳光的味道,喜得小弟晚上在床上蹦跳、打滚。
大姐、二姐手脚真是麻利,腊月廿五前就帮着把每个大年必做的红色米粿(一种糯米粉皮包上糯米饭馅或豇豆馅,再印龟或菊花模的甜点)给蒸好,又和三姐一起去买回足够大年那几天经营的带壳海蛎,然后顺手剖些带回去过年。
父亲按计划买回各种过年物品,父亲买回那些东西总是一样一样递给母亲,母亲也总是笑眯眯一样一样地接。父亲说香菇,母亲也跟着说香菇;父亲说扁肉皮,母亲也跟着说扁肉皮……那些日子家里便特别喜庆,特别温馨。
小村开始有鞭炮声,那是村里的孩子把鞭炮给拆了,一颗一颗地放以取乐;男人们扎堆说笑,在屋檐墙角;井栏那儿,妇女们洗洗涮涮,交流蒸年糕经验或说些家长里短的欢声笑语,被井壁给扩大了似的在小村上空回荡。
一切准备就绪,各家各户的烟囱,便起劲地冒烟,人们开始准备年夜饭了。
我们家的年夜饭,一向都是母亲烧火,父亲掌勺。灶膛是新通的,烧的又是平常舍不得烧的松枝以及树根树头,火特别旺,特别喧腾。因为温暖,因为高兴,母亲平常锅巴似的脸便神奇地焕成刚出笼屉的红色米粿,泛着喜气。父亲厨艺好,平常村里人家的红白喜事,都邀他操办酒席。年三十晚上,他更大显身手,每种菜式他都煮双份,一份留到正月吃。弟弟他们在外面瞎玩,肚子饿了敢随便用手抓已上桌的菜吃,因为他们都知道不会遭骂,过年的那几天,父亲母亲都会忌口的,他们不但不会骂,还会笑眯眯地说,傻孩子,要吃就随便吃,过大年还怕你们吃?
在他们准备年夜饭的时候,我写春联,贴春联,父亲便笑眯眯的,显出很欣赏的神情,虽然我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好看。他的欣赏是有原因的,他也目不识丁,总称自己是盲牛。记得有一年他把买回来的贴在我们老屋窗户上的春联贴倒了,我那时虽然已上学,但识字不多,只觉得那字怪怪的,不敢说,直到人家来拜年才说破,父亲臊得脸红红的,像关公……
吃年夜饭的时候,满桌子都是菜,弟弟说干嘛煮这么多,都吃不完。母亲说,辛苦做,欢喜吃,越吃越有。敢情他们就是冲这句话而把钱差不多尽数买吃的,那年年夜饭后分压岁钱,父亲的钱包里极寒酸,我得两角,两个弟弟各一角,三姐只得个两分。三姐嘀咕说两分就是两角,她的最高祈望也就是两角。她没有嫉妒我得两角,因为她是姐姐,因为她是女的。女孩子不读书,女孩子穿破衣,吃差点,做多点,村里的女孩都那样,她们好像也没感觉那是男尊女卑的思想作怪。可我却为自己得两角而不舒服,便悄悄地把平常积攒的零花钱往她口袋里塞了两角,往两个弟弟的口袋里也各塞了一角,当他们发现的时候,都嘻嘻地冲我心照不宣地笑,如今想起他们当初那从心底发出的笑,我的眼睛常会因泪水而模糊。
那天晚上守岁,母亲教我们唱民谣,最记得有一首是:正月正头放炮仗(鞭炮),走家串户拜年欢。初二禁忌走人家,亲朋戚友拜灵堂。初三新娘偕郎回,初四家神接回门。初九到十五上元节,舞龙耍狮闹昂昂。
父亲或许感到又熬过一年而快乐,竟高兴地给我们讲故事,讲了个民间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说,祝英台出嫁那天,要求轿子要打山伯的墓前经过,得允许她拜祭山伯。她哭得伤心,哭得天昏地暗,末了,就求告天地说,有神有鬼墓门开。刚一求告完,就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那当儿山伯的墓门就真的开了,她就一头撞进墓门。马文才一见,也撞进墓门去拉英台,墓突然塌了,他们就被活埋了。他们去到阴间,阎王觉得他俩和山伯都不该死,都阳寿未尽,就判他们借尸还魂,重返人间过日子,还允许梁山伯和马文才在包括英台在内的十八个美女中各挑一个女子为妻。马文才争着先挑,他见那些女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加上心里还气着山伯,就不给山伯留一个,就说十八个美女他全要。阎王见马文才贪色贪心就判说:马文才真骚哥,拨去凡间做猪哥(种猪)……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加上小弟说我们以后不养菜猪,就养猪哥,更让我们笑痛了肚子。那以后我一见着种猪,就想到那是马文才变的,呵呵……
父亲那晚因为高兴,多喝了点地瓜烧,困,还因为初一早上他要赶早市卖海蛎,赶在初一十二点前卖完海蛎以遵守民间初一至初二禁做事习俗而不守岁就睡了。半夜,迎新年的鞭炮声把他给吵醒了,他索性就坐起来,卷纸烟抽,做沉思状,冲我说:阿福,开春后,你还是回校读书。
我听了,也就无可无不可的。
不过,新年开学的时候,我还是背上书包,继续当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