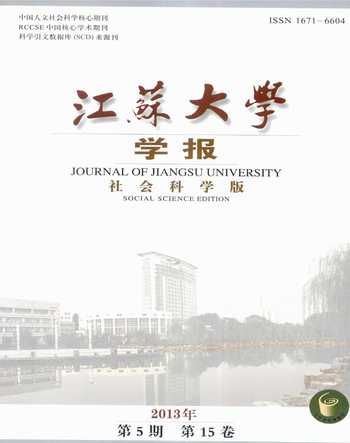分隔渐隐
史蒂芬·吕斯特 萨尔玛·莫娜尼 侯娇婴
摘要:生态电影研究不仅简单局限于直接传递环境意识信息的电影,而且也考量电影的维度。《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关注各种生态电影理论和不同体裁,并结合生态电影研究的历史发展实践,启发我们应当将视线转向该领域内理论创新动力的需求,同时模糊体裁关注中的历史划界。
关键词:生态电影;生态批评;环境保护关注;自然;实践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5-0042-08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说,环境不只是有机世界,或者是被康德施以人类理性的力量在自由的斗争中所对抗的自然法则,抑或是马克思认为我们为了生存而注定要去与之搏斗的大自然;环境其实就是围绕着我们的整个栖息地,是物理世界与文化世界的交融。它是各种关系的生态,我们在其中谈判妥协以获取意义,实现生存。在这个栖息地中,电影也是一种协商,一种调节,是一种自我生态的存在,因为它吞噬着周遭这个交融的世界,因而,也在自我消耗。
尽管电影和媒介学者始终致力于研究电影的文化调节作用,但直至近期,生态批评的视角都还在学界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多少被大家忽视的一个方面是,从制作到发行到消费到循环流通,一部影片的历程是不可避免地深深交织在生态网络之中的。电影文本加之音频一视频手段所体现的个体及其生活场所,影响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想象,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除此之外,各种电影技术,从灯光到相机到碟片甚至到看似无形的因特网,都涉及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因而也宣告电影在转变并影响我们生态系统过程中的直接作用。只是近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渐有部分学者开始批判性地审视电影的生态维度,以及它们对人类和比人类所居住的世界更广阔空间的影响。
《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便是有关此类生态批评审视的,汇集了该领域内领军人物的观点和思想,如肖恩·库比特,大卫·英格拉姆和斯考特·麦克唐纳;更收纳了时下的声音,如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和妮可·斯塔罗谢尔斯基等人,他们的文章体现着鼓舞人心的崭新的学术研究方向。该书萌芽于学术会议中的对话,在网上的密切交流和“生态媒介研究”等网站的博客中得以孕育,因此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对话的作用,《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一书致力于为日趋丰富的这一批评领域——生态电影研究——穿针引线。
一、对生态电影研究的定义和定位
《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在遴选文章时,要求投稿人思考当前电影研究和生态批评所关注的问题,并针对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撰文,这样就可以从整体上呈现生态电影批评所涵盖的大量电影和理论方法。结果证明,有的文章涉及我们通常认为属于环境的话题和体裁,例如关于企鹅的野生动物纪录片,但有的则属于我们最初不会归为环境范畴的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恐怖电影。总体来看,这些视角各异的文章限定了《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的目标,那就是要清楚表明生态电影研究不仅简单局限于那些直接传递环境意识信息的电影,而且也考量电影的维度,从好莱坞的公司制作到独立先锋电影直至制片人、消费者和文本进行互动的扩张中的传媒网站。
很多学者(和其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或许对于生态电影究竟是什么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些批评家,如宝拉·薇洛奎特一马里康迪在《构建世界:生态批评和电影探讨》一文中建议,某些独立抒情和激进的纪录片——而非商业(即好莱坞)电影——可以被视为生态电影,因为它们最能激发激进的生态政治探讨和观众的行动。虽然有人指出,对于个体是如何被激发的,什么样的电影可能激发他们,以及由此带来的到底什么是生态电影的问题还存有更大争议,但生态电影批评家们在几个关键概念上普遍持一致观点。首先,我们认同所有影片都毫无疑问有其文化和实质寓意。其次,无论我们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主流的、消费主义的处事方法通常体现着不仅是在人类交往中而且在非人类世界里事务的纷繁状态,电影提供的一扇窗则可以窥视我们对这种纷繁状态的设想,以及我们顺应或抵制这种状态的方式。再次,正如肖恩·库比特雄辩的论断所言,“尽管可以断定许多电影有关当下普遍的意识形态,包括自然的思想意识,但还有很多其实更富含矛盾对立,在伦理、情感和智力方面比大多被误认为是生态政治的影片更令人满意”。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有意赞同所有影片都呈现有效的生态批评探索,因此,细致的分析可以揭示看待电影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有趣视角。《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所展示的当前生态电影研究的维度即印证了对所有电影所持的这种关注。
为了给如此宽泛的学术研究以秩序,《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以期同时反映并模糊迄今该领域中存在的界限。第一章“生态电影理论”,指出了困扰该领域的某些理论困境并提出了对生态和电影现实本质的崭新见解,为全书设置了理论背景。第二章“生态电影实践:野生生物和记录影片”,聚焦大量生态电影论题,尽管这可能会与人们所划定的野生生物影片或纪录片界线有所冲突。在纪录片常常因其蕴含的环境意识而备受称赞的同时,第三章“生态电影实践:好莱坞和虚构叙事电影”,将视线转向主流影片,一方面对基于此类电影的大众噱头和商业意图而推断其无力推广生态意识的假定提出了质疑,一方面突出了曾经被生态电影批评家忽视的门类和体裁。第四章“超越电影”,通过对环境电影节的考察提出了扩展该领域的范本,也更近距离审视了被科学家和电影工作者用以记录、阐释并呈现科学数据的形象化、声像化手段的技术和审美属性。
《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四个章节的构架,及对生态电影理论和不同体裁的关注,强调实践,并体现生态电影研究的历史发展。这也正是一本试图侧重该领域学科基础的文集在认可其新兴发展方向的同时不可忽视的。在学术研究历史上,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就有零星文章出版(如堂娜·哈拉维1989年的著作《灵长目动物的视野: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中的某些章节,和芭芭拉·克劳瑟1994年的论文《走向对电视自然历史节目的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电影批评蓬勃发展开始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标志为五部长篇研究著作的发表,即詹·霍奇曼的《绿色文化研究:电影、小说和理论中的自然》(1998),格雷格·密特曼的《旋转胶片中的自然:电影中的美国与野生动物浪漫史》(1999),德里克·博赛的《野生动物电影》(2000),大卫·英格拉姆的《绿色荧屏:环境保护主义与好莱坞电影》(2000),及斯考特·麦克唐纳的《机械中的花园:独立制作处所电影的田野指南》(2001)。
其中,密特曼和博赛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首个对野生生物自然电影的全面考察,英格拉姆的《绿色荧屏》是对好莱坞环保影片的首次全面探索,而麦克唐纳将视线转向先锋电影。霍奇曼的《绿色文化研究》则是首批把文化研究的分析理论应用于电影的生态批评解读的长篇著作之一。虽然发表时间相近,又出自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这五本书却没有直接相互参照。然而,因为每本书尝试对一类影片进行探究——野生生物电影、好莱坞叙事电影或独立制作先锋电影——并且对很多影片采用了生态批评视角,对于有兴趣研究电影如何塑造又如何与我们对物质环境的想象进行交互的学者来说,这些书可以作为及时有效的参考。同时,每一本书似乎也在清晰刻画生态电影研究的分界线。例如,英格拉姆的《绿色荧屏》对好莱坞电影批评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出帕特·布里雷顿的《好莱坞乌托邦》(2005)和狄波拉·卡米歇尔选编的《好莱坞西部片之风景:美国电影门类中的生态批评》(2006)等书。博赛和密特曼的研究则成为像辛西娅·克里斯(《观看野生生物》,2006)和路易·维万科(如其2004年发表于《文化动力》的文章《电视影像探险时代的环保工程》)这样的野生生物电影学者们的核心起点。
诚然,即便这五本书已经指向生态电影研究中的不同分支,有些学者进而开始尝试积极打破由传统的体裁关注所带来的界定和假设。随着这些电影种类所采用的制作、发行和接受方式之间的重叠和竞争不断加深,它们所传递的环境保护信息(以及媒体对环保问题的广泛关注)也逐渐增强,如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参见其2008年于《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中的文章《绿色电影批评及其前景》)和薇洛奎特-马里康迪(《构建世界》)等学者以他们正在崭露头角的作品向我们证明,超越了好莱坞、野生动物和独立先锋电影界限的对话如何能够丰富我们对所有影片都具有生态涵义的理解。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电影构成和生态电影批评家的职责、作用的更全面的思考对该学科领域自身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重大问题。这也正是《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的意图和价值所在,一方面将视线转向该领域内理论创新动力的需求,一方面模糊了体裁关注中的历史划界,更为重要的是,在学科向前推进之际,引发读者对伴随生态电影研究各分支间此类分隔和消隐产生的分歧与潜能的思考。
二、生态电影的内涵及外延
《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以理论开篇,以便涵盖生态电影批评家设定生态电影内涵时的视角和方式,以及学者如何可以拓展其外延。打头阵的是斯考特·麦克唐纳的《生态电影体验》,也是他2004年《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期刊中《走向生态电影》一文的修订扩充版。他在文章中首创了生态电影一词,来描述那些提供“现代生活机器内的某种花园——一个逃离惯常消费主义的‘伊甸园似的临时庇护所”的电影,“因为媒介组织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象征”。就像颂歌与激辩对人有所教益一样,麦克唐纳在此主张置身于长时间影片面前的观众同样也会有所收获,而类似安德雷·兹德拉维奇(Andrej·Zdravi)、詹姆斯·本宁(James Benning)及沙伦·洛克哈特(Sharon Lockhart)这样的独立电影制作者所使用的先锋技术手段也可能发挥重塑感知的作用。在实际效果中,对先锋电影的感受可以抵御商业媒体对精神和环境产生的破坏。
大卫·英格拉姆却反对上述立场中的某些方面,在其《生态电影批评中的美学与伦理学》(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Eco—film Criticism)一文中反击道,认知电影学理论为塑造近期生态电影研究成果的美学假定提供了有益的修正。为了强化他的例证,英格拉姆分析了三部审美风格截然不同的影片——《狂躁的梦》(吉德昂·科波尔,2008)(Gideon Koppel,Sleep Furiously),《阳光天堂》(约翰·塞莱斯,2002)(John Sayles,SunshineState)和《南方传奇》(理查德,凯利,2008)(RichardKelly,Southland Tales)。每一部,他都认为既能够激发观众去重塑他们的生态意识感知,又同时对此目标彻底无能为力,而这完全取决于观众先前的倾向和训练。他把文章建构于使审美复杂化的三组对立概念之上以阐释其观点,谓之艺术与通俗电影,现实主义与情节剧,道德论与非道德论。
与英格拉姆一样,安德鲁·哈格曼也担心在生态电影研究中采用教条的审美或道德方式无法成为批评家鉴别并分析所有电影内在冲突的有效工具。因此,他在《生态电影与意识形态:生态批评家梦想井井有条的绿色吗?》(Ecocinema and Ideology:Do Ecocritics Dream of a Clockwork Green?)一文中,通过不同体裁但同样描述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城水资源私有化斗争的影片——纪录片《解构企业》(The Corporation)(2003),剧情片《雨水危机》(Tambien la Lluvia)(2010)和动画短片《水的过去与未来》(Abuela Grillo)(2009),向我们表明所有影片中都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他的论点即,恰是这些印证了我们以生态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有限的对立,警示我们在狭隘地定义生态电影时应该慎之又慎。
如果将生态电影理论化的尝试大多都致力于甄别对电影的生态寓意的衡量,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对电影与世界关系的哲学领悟也应算是其中之一。在文章《流动影像的生态哲学:作为一部人类生物地理形态的装置》(An Ecophilosophy of the Moving Image:Cinema as an Anthrobiogeo—morphic Machine)中,伊瓦克伊夫吸取阿甘本、皮尔士、怀特海、德勒兹、迦塔利和海德格尔思想之精髓,提出了电影的过程一关系理论。在这个模型中,电影成为一部推动我们沿着自然中情感的、叙事的且符号化的装置,揭示着一个个人性、动物性和领地被置于其中并相互联系的世界。通过描绘电影与地球世界中三个生态系统——物质、社会和感知系统——的复杂互动,伊瓦克伊夫呈现了与电影交互的一种不亚于整体论的方法。
以上理论探索并未在第二章“生态电影实践:野生生物和记录影片”中被遗忘,而是因路易·维万科、詹妮弗·拉迪诺、妮可·斯塔罗谢尔斯基和克莱尔·莫莉的努力得以深化。他们参与到了当前对动物性与人性、野生与驯化以及我们与“他者”的电影表现的讨论中来。尽管电影制作本质上讲是人类活动,但正如文化、政治和经济决定着我们把什么搬上荧幕,如何做到,又对这些影像作何反应,被很多电影试图去展现的非人类世界其实也在发挥着决定作用。通过强调文化与物质之间的互动,并打乱那些意图为先前有关所谓自然电影之探讨而去定性的普遍假设,这几篇文章提醒我们,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界线的确是流动的。
在《想起企鹅真好:野生动物电影、对自然的影像塑造,和环境政治》(Penguins are Good to Think With:Wildlife Films,the Imaginary Sha—ping of Nature,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一文中,维万科称,纵观野生动物体裁电影的历史就会发现,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一直用企鹅来反映广泛的政治问题,如艰苦环境中的生存、家庭关系、栖息地毁坏,以及近来的全球变暖。从它们本身来看,维万科指出,想起的是企鹅,而不是野生动物电影中的其他主角并非更好或者更坏。然而,他却由追寻银幕中企鹅的足迹为未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模型,去发现野生动物电影体裁的历史演变如何展示更大范围的文化关注。
詹妮弗·拉迪诺在《跟动物一起工作:关于纪录片电影中的伴生种》(Working with Animals:Regarding Companion Species in Documentary Film)中拓展了对纪录片电影中动物性的研究,利用堂娜·哈拉维颇具影响力的“伴生种”的概念考察了三部纪录片:《又快又贱又失控(Fast,Cheap and out of Control)》(1997)、《灰熊人(Grizzly Man)》(2005)和《香草》(Sweetgrass)(2009)。拉迪诺说明了每部影片如何使一种人文主义(物种主义)的观念去中心化,列举了在工作中与非人类的动物“逐渐在一起”的方式,把非人类的动物作为在共享的环境中共同进化的成员。类似这样自我反思性的纪录片研究了一般的物种界限,对企图仿制、客体化或边缘化非人类动物的倾向提出挑战,延伸了野生动物电影的范畴。
同样是拓宽生态电影批评的疆域,妮可·斯塔罗谢尔斯基在《水流之上:水下电影文化史》(Beyond Fluidity:A Cultural History of Cinema under Water)中把我们的视线转移至水下拍摄的影片。她采用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对1910到1960年的电影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早期的电影中,半水生区域就是少数他者的领地,而在50年代时这些地方变成了少数他者们领土争端和互相取代的区域。到了60年代,电影和电视则依照太空时代的背景将海洋刻画成要去殖民和驯化的地域。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转向其实引导着现代海洋生态电影的隐喻,至今还清晰可见的隐喻,比如在电影制作人詹姆斯·卡梅隆2012年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时所拍摄的影像中。同时,这些早期水下电影也调和了美国作为海事主导力量的崛起,对于演化中的海洋政策也意义深远。
克莱尔·莫莉对束缚电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间广泛的关系也同样深感兴趣。在文章《“自然书写剧本”:商业野生动物电影与生态娱乐》(“Na—ture Writes the Screenplays”:Commercial Wild—life Films and Ecological Entertainment)中,莫莉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迪士尼自然”,迪士尼公司全新的独立电影团队。团队秉承其早期《真实世界历险记》中的精神,致力于制作、收购并传播野生生物电影。她提出,迪士尼在环保主义者与普通大众视野中的差异可以通过考察该公司对“绿色品牌”的打造进行解释。在传媒产业研究的理论视角下,该文聚焦当代企业环保语境中问题百出的自然,因而也顺理成章过渡到了下一章节,在详细研究商业、叙事电影中延伸这些讨论。
在承认好莱坞电影制作存在生态方面问题的前提下,第三章“生态电影实践:好莱坞和虚构叙事电影”着重于此类影片的潜力及其广大的观众群体,以突显主流社会一文化需求与焦虑。在《好莱坞与气候变化》(Hollywood and Climate Change)一文中,史蒂芬·吕斯特坚定认为,像《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和《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nocent Truth)(2006)这样反映气候变化的电影已经通过把全球变暖的科学转换成电影语言而在美国通行的环保语篇中引发了显著的转向。他的文章改编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提出了此类影片清晰呈现的一种“生态的文化逻辑”,而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既被看做是气候变化的诱因,又是潜在的治理途径。
在文章《恋之风景:<荒野生存>、<灰熊人>和<新海角乐园>所拍摄的自然》(Appreciating the Views:Filming Nature in Into the Wild,Griz—zly Man and Into the West)中,帕特·布里雷顿对商业电影采取了更为正面的观点,探究了三部当代电影叙事作品。他认为这几部影片对风景的独特描绘体现了其在呈现自然的治愈形态时的积极主动。《荒野生存》(2007)追踪了一心寻求冒险的年轻男主人公的生态心灵历程,《灰熊人》(2005)审视了一位天真的自然主义者,他不接受荒野中有不应该被打破的界限的存在。而《新海角乐园》(1992)则集中表现了爱尔兰乡下所特有的自由与逃离中的幼稚浪漫与神话赞颂。在它们最后的场景中,布里雷顿指出,它们都可以被解读为反文化与跨文化的生态公路电影,诉说着新一代人对亲身体验自然景色的渴求。
有别于布里雷顿借鉴浪漫主义在荒野自然中寻觅慰藉的传统所选取的影片,卡特·索尔斯的《对魔鬼的同情:20世纪70年代乡村杀人狂电影中的食人乡巴佬》(Sympathy for the Devil:The Cannibalistic Hillbilly in 1970s Rural Slasher Films)一文侧重展现并颠覆把荒野自然当成“恐怖、荒凉的旷野,满是野兽和野人”的较古老的清教传统。索尔斯指出,《德州电锯杀人狂》(Texas Chainsaw Massacre)(1974)和《隔山有眼》(The Hills Have Eyes)(1977)等这些电影中的食人乡巴佬形象,其实不过是城市观众投射他们对未知所怀恐惧的靶子。但是,与更早或较晚时期里把乡下人表现成胆小恶棍的恐怖电影不同,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杀人狂电影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社会与生态政治剧变做出的颠覆性(甚至或许是英勇的)回应,因为里面的“恶棍”可以被看做是系统性环境毁灭、自然资源逐渐减少,以及体制虐待劳动贫民情况下的受害者。
进行这类研究的学者为恐怖电影、公路电影、票房大片和其他门类体裁的商业制作影片提供了细致入微的阅读,向我们表明生态电影无论如何不应被独立制作圈定界线,因此,生态电影批评的视线还可以更加开阔。
在第四章“超越电影”中,萨尔玛·莫娜尼和肖恩·库比特把探索的目光越过了该学术领域内当下思考的界线。基于冉冉兴起的电影节研究领域及其与公共领域理论的相互作用,萨尔玛·莫娜尼的《环保电影艺术节:从电影节研究与生态批评研究的交界处开始探寻》(Environmental Film Festival:Beginning Explora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Film Festival Studies and Ecocritical Studies)一文提出,目前这些电影节的范畴受制于三种类型:官员公共领域、非官员公共领域和集团或商贸展览领域。几乎没有哪个电影节只属于其中单独一类,但分析它们的身份构成可以揭示这些电影节如何在环境与媒介纷繁的大背景下为求生存而妥协的复杂方式,并为对生态电影这些独特功能版块的持续关注制造空间。
最后,肖恩·库比特在《人人知道这什么都不是:数据视觉化和生态批评》(Everybody Knows This is Nowhere:Data Visualization and Ec—ocriticism)中说明,当电影批评家还在被现实影像困扰的时候,环境科学处理的是在实际中往往太无限,太缓慢,抑或又太分散以至于无法被成像以进行观察的。为了向普通大众和科学从业者展示这样的数据,他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视觉化策略。通过将视觉化置于其与民粹主义和人文主义论断之间的关系中开展考察,库比特提出,随着图表形式越来越多的在如《难以忽视的真相》一类的电影中得以应用,一股倾向于把世界归为视觉数据的电影潮流随之出现。这股潮流在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的一系列生态启示电影中被赋予叙事形态,转而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在一组令人难忘的“虚构现实”电影中回归,其中的现实自身被等同于它的数据形式。库比特对经过电影改编的科学数据视觉化和声像化的思考为生态电影批评打开了一扇超越照相现实影像继续前进的大门,也为电影与媒介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三、天地交融:生态电影研究的未来走向
尽管《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选题宽泛,但文集中的几个章节不可能妄图包罗时下学术圈内所有现存的生态电影批评的方式方法,也不应该抱有这样的幻想。在过去几年里,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常是在他们学生的启发下——不断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生态电影研究(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生态媒介研究)正以令人震惊的节奏成长壮大。伴随该领域深入发展的,是学生与学者间通过课堂、会议、期刊和类似于《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这样的文集展开合作的需求将会对我们在共享对话中的参与感至关重要。
虽然《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将焦点对准第一和第二电影(译注:以好莱坞模式制作的电影称为“第一电影”,欧洲式的艺术为“第二电影”)以求更加纵深地探究该领域发展问题中的关键思想。展望未来,我们发现生态电影研究中至少五处重叠交汇点,可以成为振奋人心的前进方向。第一,对第三电影(译注:第三电影泛指第三世界电影工作者所制作的反帝、反殖民、反种族歧视、反剥削压迫等主题的电影。本词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阿根廷制片人费南多·索拉纳斯和屋大维·杰蒂诺在《迈向第三电影》中提出的)和第四电影(译注:第四电影由导演巴利·巴克莱提出,代指少数人口的原住居民在主流文化中对自我表达的尝试)的关注逐渐显著,尤其因为它们亦属于由跨国电影和媒体制作带来的文化与环保问题。谢尔顿·陆和米佳燕选编的《中国的生态电影》(2010),和即将出版的由皮埃塔里·塔阿帕编写的《跨国生态电影》便是近期在这一方向上的破冰之作。娜迪亚·波扎克与莎莉·汉朵芙在《银幕足迹:灯光、相机、自然资源》(2012)中对因纽特电影制作者扎克拉尔斯·库纳克和伊苏玛电视台的描写,及《绘制美洲:当代本土文化的跨国政治学》(2009)分别对第四电影给予了亟需的关注。在深入研究这些课题之时,我们可以充分采纳布里雷顿的认识,把浪漫主义的西部理想视为对此类电影所传递的生态信息的烘托,或者将某些概念改编应用于那些独特地域性和全球化语境兼备的影片,如斯考特·麦克唐纳“重塑感知”的理念,或史蒂芬·吕斯特提出的“生态的文化逻辑”。
第二,包含性别政治的电影也同样值得重视,如在努尔·斯特金的著作《流行文化中的环境保护主义:性别、种族、性欲,和自然之物的政治学》(2009)中所展现的。针对该方向的最新文学生态批评——如以下三篇(部)2010年出版物:格瑞塔·伽德发表于《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中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新动向》,蒂莫西·莫顿发表于《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的《怪异的生态》和斯泰西·阿莱莫的《肉体的本质:科学、环境,与物质自我》(2010)一书——都直指生态电影。在此方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有效运用安德鲁·哈格曼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型、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的哲学分析,或是路易·维万科的历史观来展开对话。
第三,如果读者在卡特·索尔斯对其环境正义的关注独一无二的阐释中找到灵感,可以参考萨尔玛·莫娜尼,卡洛·阿里吉洛和贝琳达·赵合作编写的《给环保镜头上色:电影、新媒体,与公平的可持续性》(Coloring the Environemental Lens:Cinema,New Media,and Just Sustain— ability)——《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学刊》(2011)的特刊,并将此作为钻研性别、种族、民族,以及环境语境中地方与全球主动性的起点。同时,妮可·斯塔罗谢尔斯基的文章也在提醒我们,对环境正义的关注有助于在上述语境与后殖民主义的学科分歧间搭桥铺路。我们诚邀有意拓展这一研究的生态电影批评家阅读《环境正义读本》(2002)、《穷人的环境保护主义》(2004),还有《后殖民生态批评》(2010)等书。詹妮弗·拉迪诺的文章同样也可以作为把环境正义问题和个人探索融入批判性动物研究的一个有趣方向。进而,生态电影也会在对重要文本的持续发掘中得以升华,如《当物种相遇》(2008)及《动物与能动》(2009)。
第四,正如克莱尔·莫莉关于迪士尼自然的文章,萨尔玛·莫娜尼对环保电影艺术节的研究,抑或大卫·英格拉姆采取的认知途径,都表明对生态电影制作、发行和接受的开发还大有空间。在如此这般的探索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因为阅读了即将面世的布朗·泰勒所编《化境与自然灵性》(2013)中针对读者接受的文章,对肖恩·库比特有关数据化论断的研读会被带向怎样深远的思考;而如果再辅以那些探究通俗文化传递与环保立场形成过程中全球化作用的生态批评调查——例如乌苏拉·海瑟2008年出版的《感知地点,感知地球:对世界的环保想象》——又会产生怎样的思索。
第五,在全球对媒体的需求日渐膨胀的同时,电影与媒介的生态足迹也在累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加州政府于2006年共同开展了一项全面调查,其中把好莱坞电影产业列为全州污染大户。正是一定程度上出于来自这项研究的启迪,波扎克在《银幕足迹》一书中追溯了被她称为“碳氢化合物假想”的历史。出于相似的视角,詹妮弗·盖布瑞斯在《数字垃圾:电子产品的自然史》(2011)中就媒体的物质影响这一论题进行了考察,而托比·米勒和理查德·麦克斯韦尔将要出版的《让媒体变绿》(2012)亦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大型电影制片厂近期为加强回收,购买混合动力车辆,以及聘用环保顾问所付出的努力是体现了他们迈向可持续性的积极一步,还是只不过是给企业披上了一件绿色的新衣,都必将是在未来几年中激发辩论和持续调研的众多论题之一。
总而言之,在构成生态电影研究的许多理论与实践分支的重叠中,正在形成这样一种认识,除去对电影生态足迹的某些担忧,我们很多人一直喜爱观看电影,恰恰是因着电影重新构建感知的能力。对生态电影批评家而言,电影与生态电影研究使我们能够分辨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从人类中心的狭隘角度把个体的人本欲望置于道德宇宙的中心。正如《生态电影理论与实践》封面出自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1979年的电影《潜行者》(Stalker)中的画面所阐明的,非人类世界也许不会总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与我们交流,当来自荒野的犬科动物形象横跨这片凄凉的人类荒地之际,观众的目光却暂时从以胎儿姿势卧于画面底端的人类主人公形象身上脱离开去。画面上下两端的分隔让人们的视线越过人类与非人类形象而飘向远处波光粼粼的水面,沉湎在对天空的回忆中。孤立地对事物进行生态批评反思,已然成为电影这面朝向世界的镜子中共有的回忆。
(责任编辑 潘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