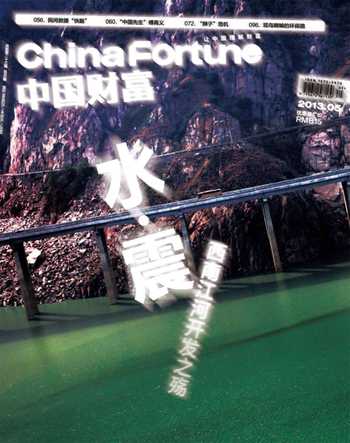他们是第一批社会拓荒者
宋志标
在社会尚未被政府承认其地位的时代,NGO的最大成就就是展现了多一种可能性。可以说,那是一个拓荒的年代。摆在NGO新世代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种新的可能性做出来,继续推动社会从新生走向巩固。老实讲,其中暗藏的挑战比老一辈那时候更难。
在挑选本期书评的对象时,颇费踌躇。社会的大社会格局初成,需要更多的内容扩展其社会属性,这样一本《中国NGO口述史》会否有限制,重又回到狭义NGO的小圈子里去?等到看完全书,疑问全消。一个口述史的研究模式,打通了人与社会的隔膜。
王名教授主编的这本口述史第一辑,在人选上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当事人基本上是大陆NGO的第一代创始人。他们从铁板一块的体制内“分裂”出来,试探性地走进当时并不清晰明朗的社会领域。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是第一批社会拓荒者。由于NGO老一辈的体制特点,在他们将社会机构组织化的过程中,与政府有着相当紧密的合作。从创设所需的资源上讲,可以说是政府在社会领域的延伸。无论是身份的获取、项目的开展甚至NGO的面貌,都有着强烈的政府烙印。徐永光从仕途刹车,创设青基会,乃至于在南都基金会挑大梁,始终都得益于在政府资源上的运用。这是早期NGO领袖的统一印记,也属正常。
交接班问题
因为来源于政府,这些最早的NGO人物本身就是一面旗帜,在获取资源的能力上是新一代从业者无可比拟的。这在将NGO引入大陆的初期,对于在短时间内做成品牌,说服政府,无疑是有优势的。但也有不足,那就是在NGO领导人的交接班上,显露出弱点。
正如梁晓燕所讲,NGO的代际现象,“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组织领导人转换的时候,整个机构的阵痛很厉害”。开创者的时代意义,及时代局限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哪怕到今天,即使机构的专业化能力逐渐取代创始人的资源优势,这个问题也还是高悬不下。
对于这一块的危机感,以及应对的方法,读者可以从梁晓燕那里找到一些解题的线索。
当丘仲辉临危受命,在韩文藻先生病重时接手爱德基金之后,想必也深知此一法门的秘密。丘先生在口述时坦承了新老领导人更替的影响,至少在做事上是大不一样的。
对老一辈的领导人而言,他们希望看到NGO的平稳过渡,在他们不在的日子里,仍可以确信机构的长久存在。而对新世代来说,尽管目标一致,可问题的实质却是:如何减轻老辈不在时的消极影响,把机构从他们的影子里安全地带出来,以求永续发展。所以,肖培琳在谈利智中心时,所讲的重点部门竟然与这类问题意识不谋而合。所幸的是,利智中心实现了令人放心的交班。而这个问题,到底与NGO的管理制度关系不大。
在社会尚未被政府承认其地位的时代,NGO的最大成就就是展现了多一种可能性。可以说,那是一个拓荒的年代。摆在NGO新世代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种新的可能性做出来,继续推动社会从新生走向巩固。老实讲,其中暗藏的挑战比老一辈那时候更难。
当然,交接班的现象与问题,并不意味着老一辈已经走进了历史中。NGO的老一辈除了做实务,在争取舆论、游说政策、提携后进上多有贡献。对内是代际传承,对外仍然是统一“作战”。老辈不离场、不懈怠,也算是有幸。
这一辑的口述史,依据NGO创始一代所记录的,是花费很多笔墨在政府公关方面。包括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得支持与赞助,从一个侧面,比较多地展现了在面对NGO时,政府的思考方式是怎样的,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说服,这对当下也是难得的启示。
NGO的新世代所采用的方法与组织形态,确实与从前有很大不同。依靠传播领域的手段结成组织化,看似成为可能。这种基于人际需求及认同的动力,正是许多NGO新世代脱颖而出的平台。然而,社会本身并未全然长成,处理政府关系依旧是门学问。老辈NGO凭借政府资历积攒了与政府协商的资格,新世代则背依民众与民意,获得某种资格。所以,交班问题不再限于领导人,影射的是社会与政府关系的重新平衡。
这恐怕也是口述史的一个指向,且等待后续的口述给予照应吧。
《打工女孩》
[美] 张彤禾 著 张坤 / 吴怡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彤禾曾经做过《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一直尝试撰写观察社会经济转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的故事。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打工女孩”的故事: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杀戮的艰难》
张娟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这是一本探讨死刑存废话题的书。作为台湾“废除死刑协会”的积极推动者,张娟芬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不同死刑犯的犯罪成因,审判经过,以及执行经历,思考生命、公平、正义等一系列终极命题,帮助读者从新的视角认识死刑制度。对此,张娟芬说:“对于一个向往正义的人,死刑多少构成一种诱惑。如果您心里还是有七个支持与八个反对死刑的理由,老实说,我觉得很正常。但是下次舆论又喊杀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停下来,想一想。”
《随记光阴》
乔海燕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年9月
作者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在本书中,他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人,有为朋友而甘愿下乡的好人,有在被禁锢的时代仍保持独立思考的思想者,有躺在戏台下方就为看女演员裙子里有没有穿内衣的生产队长。他笔下的人物,多半不是知青,而是一个个普通的农民,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更加无助的农民。在大时代掀起的狂风巨浪中,他们载沉载浮,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身份,渐渐被遗忘。
《出梁庄记》
梁鸿 著
花城出版社 2013年4月
梁鸿以跟踪走访的形式,讲述了“梁庄”生命群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城农民。中国有近2.5亿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在文章中,梁鸿发现,“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
《共和的危机》
汉娜·阿伦特 著 郑辟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这是汉娜·阿伦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收入三篇论文《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70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在《论暴力》一文中,阿伦特对权力、权威、强力和暴力作了区分。她把暴力和权力对立起来,认为暴力只能导致破坏,但不能创造出权力,一旦开始便无法控制。所以,暴力行动所产生的最可能的结果便是"一个更为暴力的世界",“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
《古拉格——一部历史》
安妮·阿普尔鲍姆 著 戴大洪 译
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古拉格是“劳改营管理总局”俄语首字母的缩写,泛指它管理下的劳改营。从1929到1953年,超过1400万人曾被囚禁在这里,“鼎盛”时期,476座集中营遍及苏联每个时区。在这本书中,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呈现了一段段回忆录,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前言中,安妮·阿普尔鲍姆说道:“虽然这是一本苏联集中营的书,但它不会将其当做一种孤立的现象来对待。严格来说,古拉格应当归入二十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其时其地还在德国出现了纳粹集中营——特殊的知识分子境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