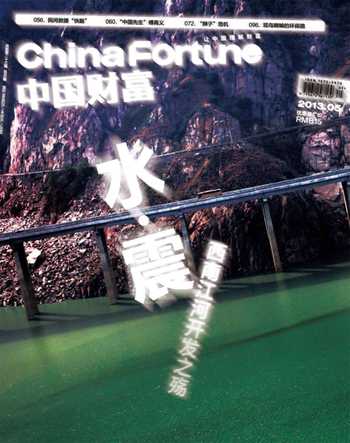什么样的城市化才算“有质量”?
李佳佳
1月刊《中国财富》探讨了城镇化的问题,无独有偶,今年4月上旬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也开设了一场主题关于“城市化的质量”的分论坛。经济学家胡祖六在一片讨论“绿色城市”、“设施建设”的发言中直指户籍制度。
他说,90年代整个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不到15%,但有70%的劳动力人口在农业。你说政府非常关心农业,“三农问题”每届都提,但农民的生活永远不能改善,因为70%的人只能分享15%的附加值,所以农村的绝对贫困是永远不能解决的。
胡祖六以为,城市化不应仅仅是横向流动,而是垂直流动——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就业机会。如果户口制度延续,尽管人可以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子女不能就近入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你甚至不能买房子,所以只能住棚户,相当于中国的贫民窟。“户籍制我只能想到奴隶制可以和它相比,你要改革户籍制?就是取消,没什么好改革的。比如说‘改革奴隶制这种说法行得通吗?要‘废除奴隶制!”
在理性安静的博鳌会场,即使嘉宾发言精彩,见多识广的听众们也通常不会鼓掌,而胡的发言赢得了现场的掌声。我在内心喊了句:真棒!
去年,我作为中国唯一的记者代表,参加美国东西方中心的Jefferson Fellowship项目,主题正是城市化。在和来自全世界的同行分享中国城市化率超越50%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时,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一个月的项目里,我们看到,美国夏威夷的议员因为无法证明是否有必要花纳税人那么多钱,20年都未能通过地铁修建计划;我们看到,弹丸之地新加坡完善的垃圾回收和水循环处理系统;我们还看到,首尔大都市中心将古籍和村落保全得非常完好;当然也看到,广州领先全亚洲乃至全球的BRT系统、绿道、开发区和知识城。
我突然明白,缺了什么。所谓“城市化”绝不仅仅是“硬件”建成了一座座“城市”。我们当然需要地铁、高架路、BRT、开发区,而我们应该更多去关心的恰恰是“软件”。
第二代农民工早已远离土地,也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远离家乡来城市打工只为了赚些钱便回去,他们的身份认同日渐模糊,他们渴望“融入”,渴望被接纳,渴望“平等”。但是,他们得不到。他们永远是城市里“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微薄的打工收入(即使如此还常被拖欠)根本无法负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他们看着万家灯火却感到无比冰冷和疏离,他们成了城市的“蚁族”和“鼠族”。
每年的春节,看看那一张张疲惫、忧伤却无比朴实的面孔,他们只为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没有电脑、不会上网,他们积蓄不多,节俭不舍,他们能做的只有排队,一个通宵、两个通宵,因为这是一年中唯一与家人团聚的时刻。
还有孩子,國家和社会的未来。除了中国,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有“留守儿童”这么一个语汇。他们的成长是孤独的,自卑的,谨小慎微的,他们不敢奢望受到良好而又完整的教育,他们一年甚至N年才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一面,于是会问出:“妈妈,你家在哪里呀?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在论坛上,我的演讲和PPT使得许多外国同行沉默和流泪,他们问我:那么,你觉得什么才叫好的城市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被决定了,那本小小的户口本,隔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在我看来,弥合那条鸿沟,才是真正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