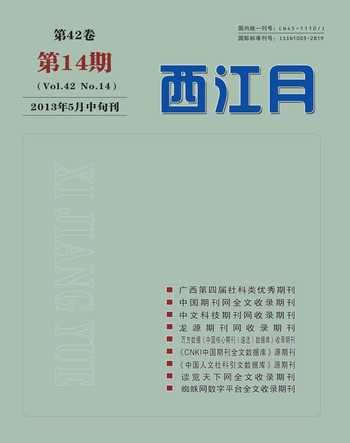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思维模式看文艺创作与批评
李莹波
【摘要】本文着眼于中国古典美学,探析其中包孕的中国人独具魅力的美学思维模式,藉此窥探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美学原则。重点分析了中和思维、整体思维、循环类比思维、气与无极思维等美学思维模式及其对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典美学;中和思维;整体思维;循环类比思维;气与无极
中国古典美学是指以先秦老子的美学思想为起点,总结于清代前期王夫之、叶燮等所建构之美学体系的中国美学思想和理论。[1]孕育于华夏文明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体现出对宇宙、人生和艺术的深刻思考,彰显了一种圆融与无极的思维模式。
一、中和思维方式
“中和”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中和”有这样两层意思:首先,它是指那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状态;其次,它是指人的性情状态、心理状态,朱熹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中国传统美学提炼出了“以和为美”的原则,并将其确立为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普遍准则和最高要求。早在《尚书》所记载的远古时代,就有“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思想萌芽(《尚书·尧典》),在春秋时期,“和”已是非常流行的说法,见于典籍的季札、医和、晏子、子产、单穆公、伶州鸠、史伯、伍举等人的言论中,几乎是言必谈“和”。孔子也赞同这样的说法:“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论语·学而》)董仲舒更是将“中和”之美擢拔到了“天地之道”的高度:“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地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具体到艺术,如古人普遍认为档次较高的艺术样式“乐”,亦如此,《国语·郑语》曰:“和乐如一”,《荀子·乐论》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也”,《乐记·乐论》曰:“乐者,天地之和也”。
二、整体思维方式
中国人历来习惯于将天时、地理、政事、伦理、心理、生理等等都纳入同一结构图式之中,致力于建立与其相感应的整体联系,寻求其同步运行的共同规律,并把这种整体联系和共同规律看得比个别事物还重要,认为个别事物只有置于这种整体联系之中才是合理的、完美的,只有顺应这一共同规律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不但习惯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和整体联系,而且习惯于把握同一事物本身那种天然浑成的整体联系,普遍认为事物的各个部分、各种表现、各项特征都归属于同一个终极实在,都是从中派生出来,因而它们总是勾搭连环、纠结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拆解、难以廓清,表现出一种浑全性、普适性和不可分析性,只有在其圆融整一的有机联系之中才能作出完整、全面的把握。这种整体思维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古典美学。
崇尚那种天真之美,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审美观。六朝以来人们就褒扬“芙蓉出水”式的清真之美,而贬抑“错采镂金”式的雕饰之美,(见锺嵘:《诗品》等)之后李白也提倡“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自然”一品对此进一步作出理论概括:“真予不夺,强得易贫”。苏东坡推崇诗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东坡:《答谢民师书》),认为只要在“空”与“静”的心境中妙造诗语,便“真巧非幻影”。(苏东坡:《送参寥师》)李贽倡“童心”,基于这一认识:“夫童心者,真心也”(李贽:《童心说》)。中国古典美学所说的“真”大致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内涵:其一,“真”与最高的终极实在“道”相通;其二,“真”是事物自身规律纯任自然的表现;其三,“真”是指人的真性情、真精神;其四,“真”也是指像生命一样鲜活生动、生生不息的艺术形式。显而易见,这几个方面内涵并不是一回事,甚至相去甚远、不可通约,分别属于本体论、规律论、心理学和形式论,很难加以归类和合并。然而在传统的整体思维中,只要这些内涵共有同一个精神内核,即使这些内涵的意义域再分歧再悬殊,也不成其为障碍,中国古典美学概念、范畴的语词外壳凭其柔韧的弹性足以容纳这些矛盾抵牾之处,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而上述“真”所包容的各种内涵恰恰具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与事物自然天成、素朴纯全的本真性分相通。已如上述,“真”与“道”相通,源于道家思想,而这一范畴的运用其整体思维的方式也恰恰是道家的精神遗传。道家学说的概念、范畴便极具包容性,如庄子所说的“真”,就整然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意义。[2]
三、循环类比思维
从以上所述可见,中国古典美学是非常讲究圆整和通融的,这正显现了循环思维的特征;而这一点又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逻辑上,它往往将事物的发展演变理解为其状如环的逻辑圆圈。
在这方面清代学者刘熙载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将作家、艺术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创作水平的提高概括为一个迂回曲折、终始相迭的逻辑圆圈。他论词曲创作说:“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又论书法创作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不工求工。不工者,工之极也”,“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钱钟书先生曾引用唐人张志和的《空洞歌》来说明这一思维特点:“无自而然,自然之原。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悫然,其形团栾。”[3]
类比思维在墨子、荀子等人的逻辑学思想中得到了初步的理论概括,其中尤以墨子所论为系统和深入。《墨子·小取篇》开篇就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里指出了论辩的要义在于摹拟概略万物之情状,论列讲求群言的层次,采用“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论辩形式,而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类取,以类予”。
中国人常常借助于类比思维增进审美感受、扩大审美经验,进而形成一些重要的美学学说。孔子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一说,最早用人的道德内涵来比附自然现象的外观形式,并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建立在这种伦理性的类比之上。《荀子》提出“比德”说,更见其自觉性,他伪托孔子之言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乐象说”又是一例,自《乐记》始,中国古典美学就非常重视音乐之“象”,强调音乐的摹仿、再现、造象功能。《乐记》多次论及音乐“成象”、“以象事行”的特点,而它所说的“象”涵盖了自然、社会、物质、精神等各个方面:“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乐象篇》)总之,以“比德说”、“乐象说”为代表的类比思维正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特色。
四、“气”与无极思维
“气”与“道”、“仁”等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哲学范畴。老庄哲学、《易传》、孟子、荀子、汉代的元气自然论、谢赫的“气韵生动”理论,到程朱理学和清·戴震等人的学说中,“气”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且逐渐由哲学思想内化为一种美学思想。
古人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生成与变化的基本元素,是万物的根本,于是形成了“万物归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养成一种由“有限”通往无限、无极的思维模式。
鲁迅说过:“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界的自觉时代。”(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曹丕在理论上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可以说是认识上对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并非只是受制于写作题旨的“达意”和写作对象上的“称物”,更是作家主动脉体气质的投射,而魏晋以后的文学创作追求“滋味”、“神韵”、“传神”、“意境”等则是从实践上对文学产生自觉的表现。
魏晋以来的中国古代美学(文艺审美)认为,文学创作应“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生气远出,不着死灰”,“离形得似,庶几斯人”(司空图语),诗的艺术特色应是“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语);这些认识都是在以“气”论文的氛围下产生的。唐诗的意境,宋词的韵味,元曲的隽永,都与此前尤其是魏晋之前的诗赋那种难以句摘的整体之美有着判然之别,唐诗宋词元曲之美往往是整个作品中以一二句体现出全诗精华,进一步说在一二佳句中又可能是以某一字来作为诗眼尽传精神的。王国维在评词时曾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以局部来代表整体,以个别来统率一般的做法在作文与评文中都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风习,推究起来,它实则是标举“气”的形而上的一面,是以文之“气”来观文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学的自觉体现在文艺理论上是以“气”论文,揭示出文学超越具体字句的形而上的意义的话,那么清代以来对“气”的形而下的一面的强调,突出文学词语审美的功能则可说是对文学的第二次自觉。此外,中国园林建筑等艺术形式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建筑物上挑的“飞檐“,仿佛屋宇振翅欲飞,一窗一牖也是将有限推及无限的画框,所谓“川俯绣户,日月近雕梁”、“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此外中国画的空白也好,建筑上的“飞檐”、窗牖设置也好,它都表现了一种“气”的运动感,如屋檐本给人一种压抑感,但上挑后的“飞檐”又有一种向上的动感,仿佛是一股“气”将屋檐向上托起。[4]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引用和列举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学者的美学思想,从“气”这个角度进一步浅析了中国古典美学之特色,得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指以先秦老子的美学思想为起点,总结于清代前期王夫之、叶燮等所建构之美学体系的中国美学思想和理论。中国古典美学的总体特色在于,其以“气韵”“意象”或“意境”等等审美意象为中心,并以文艺美学(审美文艺学)作为主体内容,而对“美”的本质及其自身范畴的讨论甚少。中国古典美学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在于除了上述基于“气韵”的诗性特点外其自身所具有的“中和”、“整体”、“循环”和“类比”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2]见拙.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1997:139~140.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1.
[4]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Z].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