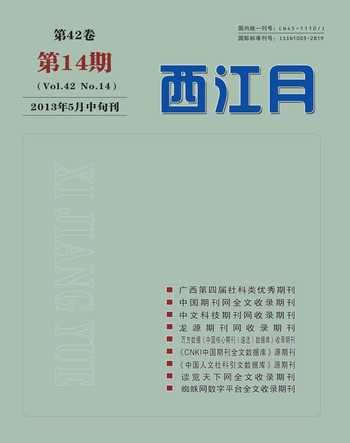铁笼与疯癫
程海燕
【摘要】《毛猿》是尤金·奥尼尔最令人感兴趣的剧作之一,作者对主人公扬克进行了深刻剖析。该剧蕴含了人类生存价值及意义的主题。本文运用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拟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方面对这部剧作进行分析和解读,阐述扬克在“铁笼”般的异化世界里,在监禁下疯癫,最终找不到精神归属的悲剧。
【关键词】尤金·奥尼尔《毛猿》;铁笼;疯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悲剧
美国悲剧大师尤金·奥尼尔一生执著于探索人的精神归属且因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而享誉世界,他倾其一生探索生命意义,他的多个剧作中充满着丰富的直觉感受,表达出本真的生存关怀。他这样阐释《毛猿》(1922)剧中的主人公扬克:“扬克其实就是你,也就是我。他是每一个人。”[1] 在奥尼尔看来,扬克的遭遇是现代人的共同生存困境的悲剧式呈现,扬克的悲哀,是20世纪荒原时代人类的集体悲哀。在人类生态处境日趋恶化的今天,扬克只能在“铁笼”中崩溃,在监禁下疯癫。这种境遇的存在正好同我国著名的生态批评学者鲁枢元所说:“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2]相吻合。本文拟从生态批评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来探讨《毛猿》的意义,将更具有现代启示。
一、 《毛猿》中的自然生态观
首先《毛猿》展现了以派迪为代表的帆船时代和自然文明与以扬克为代表的蒸汽时代和机器文明的尖锐冲突。随着科技的发展,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派迪描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一条船才算得上海洋的一部分,一个人才算得上船的一部分,大海把一切都连接起来,结成一体”。[3]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背后折射出的是各种压制下扭曲的生存态势。司炉工扬克的出场是在波澜壮阔的海上,一艘豪华的横渡大西洋的远洋邮轮里,而扬克的生存空间却是监狱似的烧火房:“……被白色钢铁禁锢的、一条船腹中的一种压缩的空间。一排排的铺位和支撑它们的立柱相互交叉,像一只笼子的钢铁结构,天花板压在人们的头上,他们不能站直……关在笼子里是一个野兽的疯狂而愤怒的挣扎与反抗……” (P95)出现在剧中的“笼子”不只有表面的含义,而且有了监狱的含义,同时还直接将里面的人与动物联系起来,与后面他倒在猩猩所呆的真正的铁笼子形成呼应。这暗示着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底层产业工人不管怎样抗争,都无力摆脱“铁笼”般的异化境况。事实上,如奥尼尔所说,扬克是全体现代人的象征,他毛猿般的强悍体魄代表着人类的原始生命力和创造力,而为扬克和他的同伴们所推动的远洋邮轮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象征。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征服了空间、自然、疾病、愚昧,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他们有理由为此而骄傲,就像第一场戏里的扬克,自信地高喊:“我就是钢——钢——钢!” (P106 )人把自己比做钢铁并不意味着要与物发生认同,而是要在物的对象上使自身的价值得到体现和确证。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事情走向了相反的一极——“本来我是钢铁,我管世界。现在我不是钢铁啦,世界管我啦。”(P146)现代人非但没有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受到主人的尊严,反而作茧自缚,用自己打造的钢铁牢笼囚禁和奴役了自己。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类进入近现代后,人与自然就不得不顺命于近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的奴役。[4] 也正是扬克所向往的钢铁时代的到来,才使得那艘象征现代机器生产的邮船成为一座埋葬水手的地狱。剧中派迪带着忧伤的心情控诉道:“……在这个地狱一般的炉膛口里,我们的脊梁断了,我们的心碎了——喂这个该死的炉子——随着煤—道,把我们的性命也喂进去了,我是在想——就像关在铁笼子里的该死的人猿!”(P104 )派迪已意识到他们在“铁笼”里生活是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他们的遭遇等同于动物园铁笼里的毛猿。派迪的悲哀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尴尬处境,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不和谐状态。人类对大海残酷性的征服和掠夺,水手不再是大海的儿子,不再是深层生态学中“自我实在”的“自我”,而是被异化为“漂泊的陆地”——铁船的一部分。人类悲剧的开始,就在于他们对于自身被物质文明所异化而不自知。
二、《毛猿》中的社会生态观
在《毛猿》中,除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遭到破坏,我们也看到严重的社会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悲剧贯穿该剧的始末。在“铁笼”般的异化世界里,人不但被物所统治,人本身也变成了麻木不仁的“物”。奥尼尔在展示水手群像时,不厌其烦地用一种非人化的词汇来加以描述,他们有着天然的佝偻姿态,他们的胸脯上都是毛茸茸的,他们拥有长臂、力大无穷,凶恶忿恨的小眼睛上面额头低低的向后削去,活像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的模样,他们躁动不安,没有神圣的理想,更没有崇高的德行,有的仅是蛮力和粗俗不堪的语言,在上层社会人们的眼里,他们形同兽类和愚人;他们在被称为“活地狱”的底舱为炉膛口添煤,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劳累的动作,以至于手臂动作失去了常人应有的灵活,变得机械僵硬、整齐划一;他们异口同声说出的字眼有种响亮而刺耳的金属声,听上去他们的嗓子眼就像留声机的喇叭一样。除了底舱这群被异化的水手外,陆地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上层社会的富人、绅士、资本家们,也被异化为一类木偶似的人物。尽管他们养尊处优,但他们脸庞呈现出的是苍白病态、表情冷漠麻木、举止生硬呆板,除了头发、皮肤、眼睛的颜色稍有不同之处,都很相像。可以说,《毛猿》中以扬克为中心展现的荒谬世界中的现代人,都沉沦在集体异化的困境中。
同时,《毛猿》还展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生态悲剧和异化主题。美国社会学家布克津说:“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5]在社会生态关系严重溃败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变得更加冷漠、势利、无情。扬克是一个自以为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人,他精力旺盛,身体彪悍,壮似毛猿,他认为,只有产业工人才“顶事”,他们铸造钢铁、开动机器、推动轮船、创造世界,而他本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鄙视其他水手的弱小无能,这使他成为水手中的局外人。一天,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女儿米尔德里德执意要到底舱参观,米尔德丽德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感到满意和骄傲,并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来烧火舱观看“另一半人”(P111)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在弥漫着煤灰的炉膛口,她看到一排赤身露体的水手在用一种奇异的、笨拙的、摇摆的节奏铲煤,他们的阴影轮廓就像一群蹲着的、低头弯腰带着锁链的大猩猩;扬克一只手里拿着他的铲子,凶恶地在头上挥舞,另一只手捶着胸膛,像猩猩一样大叫。米尔德里德吓得大骂 “这个肮脏的畜牲”(P117),几乎晕死过去。米尔德丽德这极具侮辱性的尖叫把可怜的扬克仅有的那点自尊和自信顷刻间打击得荡然无存。或许这种赤裸裸的揭露过于残忍,他惊呆了,嘴张开,变成了“化石”(P117),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米尔德丽德唤醒了自恋狂妄的扬克,但同时也让他悲哀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在他人的视线里不过是畜生和野兽,是可以随意地被窥视和展示、辱骂和愚弄的毛猿! 他自以为是的世界崩塌了,他不得不开始沉思自己的存在价值:再不能以“毛猿”的身份在社会上立足生存了,必须讨回人的尊严和价值。他发誓对上层阶级进行报复。于是他和勒昂一同上岸,东奔西走,试图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力量与价值,但获得的却只有别人视而不见的目光和冷冷的嘲弄。由于害怕自己被连累,勒昂最终也弃扬克而去。由于找不到米尔德里德,扬克便到纽约街头向富人绅士们挑衅,没占到半点便宜,反被警察送进了监狱。扬克在狱中听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为穷苦工人撑腰的组织,于是一出狱便带着诚意要求加入世界产联,结果遭来一顿毒打。扬克所到之处,感受到的都是漠视与摒弃,因此,“铁笼”中的扬克在现代异化社会中追寻自我价值,只能是徒劳无功地耗尽生命和精力,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毛猿》展现给读者的社会生态失衡,实则是奥尼尔对现代异化社会图景的一个缩影。正是现代文明对自然和社会的统治与奴役,才使得扬克出现“身份危机”而落得“无家可归”的结局。
三、《毛猿》的精神生态观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危机的爆发,除客观自然环境恶化外,追根溯源是由精神生态引发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精神生态则从外转向人的内在生态,也就是从人与自我的角度关照生态文明。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迅速崩溃;人与人,人与社会生态关系的恶化,又使得社会制度和文化创新陷入到一种加速循环的毁灭中。它们在改变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平衡机制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精神生态陷入深度危机。《毛猿》中,水手不仅在形貌上被异化为毛猿,更可悲的是,他们对于自身的异化已麻木不堪,即使像经历两个时代的老水手派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也没能力、也无法打破外在条件的禁锢,而不得不继续被机器所奴役。扬克也只是在自尊受到伤害后才有所醒悟,他潜意识到“身份危机”,于是他要冲破异化般的“铁笼”,开始寻找精神归属。但在扬克历尽艰辛寻求自我的过程中,毛猿形象已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使他不自觉地把每件事都与毛猿意象联系起来。如第六场中,当一个妇女看到橱窗里的一张猴皮时,高兴地叫了起来,扬克听到这叫声,感觉脸上被人重重打了一拳。后来他逐步意识到:他的挣扎无非是从船舱的铁笼,走进关人的监狱笼子,最后死在动物园关兽的铁笼,在日趋高度物化的社会里,监狱无处不在,他的命运只是从这个监狱走向另一个。他无法与权力机构相抗争,他的境遇象征了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最终结局,象征人与现代文明的决裂状态。
当他无法实现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建立时,扬克常常陷入孤独的“思考”。奥尼尔在剧中屡次提及扬克默默地坐下,摆出一副《沉思者》的姿态。劳累了一天,工友们吆喝扬克去洗澡,扬克回答道:“伙计们,别管我。你们没有看见我在思考吗?”(P119)扬克不经意的回答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扬克在他那像毛猿、像兽人的外表下,躯体里还活跃着一个有思想的灵魂。扬克的沉思一方面构成了一种喜剧性的谐谑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别人眼中只是一头动物,却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悲哀。扬克身处社会下层,却幻想上层社会沉思者的阶级地位,以不自觉的身体姿势扮演沉思者,本为一种戏仿行为,在常人眼里实属一种疯疯癫行为。心灵的疯癫正是他抗争无果的下场,扬克的生态悲剧,按照生态批评学者弗洛姆的观点,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古老主题中人的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反映,是人类寻找精神归属却一无所获的悲剧,是 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我关系异化的悲剧。
哪里才是扬克的出路呢?最后一场扬克对大猩猩的诉说和亲近的疯癫之举,给读者这样的诠释:处在无话语权的底层社会里,他也毫无倾诉对象。扬克试图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努力全盘失败后,无法向社会上层控诉,在与他同属一个阵营的底层群体中,也没有工友可以倾诉,走投无路之下,他来到动物园,向大猩猩诉说衷情: “你又怎么会不懂得我的意思呢?难道我们不都是同一个俱乐部、毛猿俱乐部的会员吗……我也是在笼子里——比你更糟——真的——一副可怜相——因为你还有机会冲出去——可是我呢?”(P148)面对大猩猩,扬克要把满腔的愤慨和悲哀发泄出来。扬克哀叹自己是人类中的“毛猿”,在工作的船舱中没有自由和尊严,挣扎出来后到了社会上想有所作为,没想到获得的都是嘲弄、排斥,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自己还不如一只被关在动物园的猩猩。“你可以坐在那儿,梦想过去,绿树林呀。丛林呀……可是我呢——我没有过去可想,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而那又不顶事……我在天地中间,想把它们分开,却又从两方面受尽了夹缝罪。”(P149)扬克内心被接二连三的失败与耻辱折磨着,挣扎在“铁笼”般的社会里,他已经深感自己力量的微不足道,什么都是徒劳的,只能在这地狱般的世界中倍受痛苦的煎熬。最后扬克企图打开铁笼,想和猩猩握手,却被猩猩拼命一搂,肋骨折断。扬克的悲剧实际上就是被统治权威放逐的疯癫者,在人类的荒原中找不到心灵的归宿,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他的疯癫映射了一个被看作是社会异己力量的社会底层人企图追求真实的人性的心路历程,而他的死表征了现代人面临的灾难和生存困境。
四、结论
正如奥尼尔所说:“人的斗争,过去是与众神,但现在却是他本人,与自己的过去,与其企图 ‘有所归属进行搏斗。”[6]通过扬克,奧尼尔传达了他对深陷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生存困境与精神归属的关注和思考。扬克是工业文明、钢铁机器的受害者,在他那看似疯癫的言行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有一定思想纬度的下层人。他由盲目自恋到痛苦、发疯、甚至到最后绝望、死亡,他的疯癫源自对自身处境逐渐清醒的认识,在想有所改变却无能为力。通过《毛猿》奥尼尔唤起读者对人类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本真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6]郭继德编,[美]奥尼尔著.奥尼尔文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23.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
[3]尤金·奥尼尔著,荒芜译.奥尼尔剧作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04. 其余本文所引《毛猿》均出自该版本,只注页码.
[4]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M].Harvard University of Press,2000:255.
[5]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