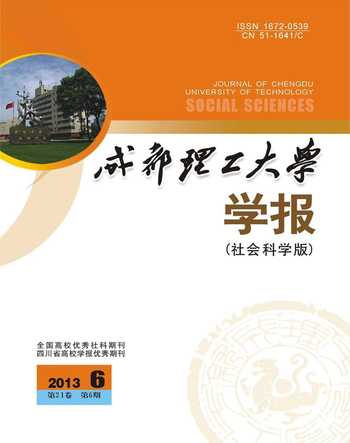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文学中的“苏联”叙事刍议
陈爱香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社会急剧转型,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文学中的“苏联”叙事主要呈现出政治祛魅的特征:褪去神圣光环的十月革命、正义性遭受质疑的卫国战争、被消解的乌托邦神话体制等在文学中得以书写。作家通过这种陌生化的手法诉说历史之痛,解构苏联官方话语的宏大叙事。
关键词:“苏联”叙事;俄罗斯文学;政治祛魅;消解;解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8804
自20世纪90年代初蘇联解体后,“苏联”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段历史记忆,思想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和途径来理解这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特殊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语境的全新转换,俄罗斯社会上很多人的情感被一种暴风骤雨般的“控诉”欲望紧紧攫住。这种急迫宣泄的社会心理,体现在文学上便是诉说历史之痛,解构苏联官方话语的宏大叙事。这与苏联解体前后文学的功能转变紧密相关。在苏联时期,文学主要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工具,而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卸下了“文以载道”的铁枷锁,作家也开始质疑与颠覆精英启蒙的阴翳情结。文学在失去了其统治地位的同时,写作空间得到极大的扩展,作家的生存和写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解体后的作家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统一严格控制,有了自己创作的空间,于是产生了对大写历史的深刻质疑以及对大写历史的有意颠覆。
一、祛魅化的革命:神圣意义的消解
十月革命是苏联历史的开端,因而对苏联体制合理性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十月革命的合法性是后设的,它是在革命成功之后通过苏联国家机器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宣传教育部门的强力运作,并借助于历史书写逐渐形成的。在苏联意识形态控制下,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文学作品、历史教材都承认十月革命在俄罗斯民族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肯定十月革命是俄罗斯人民正确的选择。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俄国日历上都用红色标出来。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就这样被设定了,十月革命走进文学中成为一类主要的正统叙事。但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复杂的、与混乱和痛苦相伴的。毋庸置疑,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但与此同时,动荡、慌乱和痛苦与之紧紧相随。而苏联官方却无视这一切,只允许对十月革命进行片面的、神话式的赞扬,禁止作家全面地表现复杂的历史事件。十月革命作为俄罗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和苏联历史的开端,是解体初期的作家们试图重新认识的对象之一。
在哈里托诺夫的小说《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这部小说中,十月革命的严肃性和正义性被彻底解构。哈利托诺夫用几则关于外省小城斯托尔别涅茨市驻扎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事迹”来消解正史对十月革命的轰轰烈烈的描述。主人公利扎温在一本记载斯托尔别涅茨市革命事件的旧书中发现了很多趣事。这座小城中所取得的革命成功极富戏剧性:前来当地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只有三位,当时驻扎的当权者的兵力有一个团,但是由于团长军官们把“从列车上涌到停车场,但并没打算进城的所有百姓误认为武装部队”[1],因而他们未作任何抵抗尝试,便都销声匿迹了。但轻而易举取得革命胜利之后的斯托尔别涅茨市反而陷入打砸抢、酗酒狂欢、火灾的混乱中。无序、不公、暴力成为革命之夜叙写的关键词,而这一切在苏联官修历史上被有意识地遮蔽了。小说中强调说档案馆被烧毁了,而且这不是最后一次被烧毁,此言述别有深意,即对官修历史的真实性的质疑。小说甚至还呈现了官修历史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斯托尔别涅茨支部领导费奥尔多·佩列舍伊金原本是甘申工厂的独眼账房先生,死后被提升为工人且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在火灾中的意外死亡被苏联的“正史”编撰者说成死于“镇压反革命偷袭”而名留青史。小说通过对官修历史制造过程的呈现来消解官方话语的真实性。在奥库扎瓦的《被取消的演出》小说中,通过主人公伊万·伊万内奇的回忆,再现了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十月革命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的不同生活道路和他们的遭遇。在这个家庭中,有革命者,也有白卫军军官,还有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小说着重叙述了主人公父母的坎坷命运:两人原本都是理性主义者,突然转变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成为高级干部,20世纪30年代遭逮捕、撤职与流放。在主人公眼中,父辈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过是 “一场被取消的演出”。
除了直接褪去十月革命的神圣光环以外,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还出现一类对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的讽刺性书写。如叶罗菲耶夫的《与白痴一起生活》中的白痴,不仅和列宁的名字相同(他的名字叫沃瓦,而俄罗斯人都熟知这是列宁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而且他的面貌与手势跟列宁一模一样,小说所描述的这位沃瓦,言语不清,只会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而且他给收养他的家庭带来无尽的麻烦。读者从这部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嘲讽列宁的显在意蕴。而在扎罗哈图的《解放印度的长征》中,列宁并非死在俄罗斯,而是被派去解放印度时牺牲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转变成各种动物。这部小说不仅肆无忌惮地亵渎列宁名字的光辉,而且还对世界革命的思想予以尖锐的嘲讽。
二、祛魅化的战争:正义性受质疑
在苏联官方话语中,卫国战争的正义性是毋庸置疑的。军事题材的小说成就斐然,历经三次浪潮。弘扬英雄主义精神、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人道主义精神是这一时期关于卫国战争叙事的主基调。虽然某些作品对战争发生过程中的苏军内部矛盾也有所反映,但还没有对战争的正义性和卫国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呈现出怀疑。在“改革”年代,尽管有很多作家对苏联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是他们尚不敢肆无忌惮地否定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及其伟大意义。苏联解体后,弗拉基莫夫、阿斯塔菲耶夫、巴克拉诺夫等作家就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卫国战争,他们抹杀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大肆渲染战争的残酷与不人道,凸显战争的残酷性。
在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中,卫国战争不再具有瑰丽鲜艳的色彩,而是蒙着极其晦暗的色调。苏联将军们巨大的心灵痛苦不是来自敌人的进攻,而是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和防范,内部同僚、战友的轻蔑、奚落和敌视。战争自始至终,反间谍机关除奸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工作人员总像阴影一样缠绕在苏军将领的身边,他们不仅粗暴地干涉前方的战事,还监督指挥官们的一言一行。军队锄奸部的斯维特洛奥科夫上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作品中有大量的笔墨来叙写他的“胡作非为,他狡猾、奸诈而且凶残,善于做表面文章,升迁速度很快。他利用人性中的弱点,很快地将担心自己性命危险的司机西罗京、对自己地位感到屈辱而对将军心存嫉妒的副官顿斯科伊上校纳入自己的圈套,从而将科布里索夫将军设置在整个锄奸部的层层监护之中,酿造了一种乌烟瘴气的环境气氛。张捷曾评论说:“弗拉基莫夫不惜有意加浓色彩,用大量篇幅写锄奸部军官的胡作非为,实际上把此人写成了所谓的‘极权主义制度在战时的集中体现者”[2]。在作者的笔下,战争已经成为内部人自己争斗的竞技场,作者用“黑暗的水流”形容苏军内部的你争我斗,正义和伟大已经失去了其根本性意义。阿斯塔菲耶夫在《该诅咒和处死的》这部小说中,用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将苏德之间的战争写得残酷无比,令人厌恶与可怕:血淋淋的杀戮场面、尸体上翻腾的蛆虫、尸体下做窝的耗子……小说没有叙写红军的英雄事迹,反而着重呈现红军指挥的混乱、战士的无谓牺牲、官兵的贪生怕死、政工人员的无能专横。在作者看来,这场战争没有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分,只不过是一场由“领袖们”挑起的丧失理智的互相残杀。而在巴克拉诺夫的小说《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中,作者将斯大林与希特勒视为同类,认为二者如同“两只统一尺码的靴子”。他们之间开展的战争,亦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小说凸显的是战争的灾难性后果。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叙写战争的作家中,有一些如阿斯塔菲耶夫、巴克拉诺夫等是亲自上过战场的,他们对战争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苏联时代他们也写过一些呈现苏联正面性的作品,但是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他们一改往日的态度,对二战中的苏军予以尽情的嘲讽,竭力渲染战争的残酷性与悲剧性,以此质疑战争的正义性,褪去卫国战争的神圣光环。
三、祛魅化的体制:乌托邦话语的解构
在苏联官方話语的主宰下,乌托邦神话体制在不断地完善和巩固。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虚假景象,借助官方话语,造就了一个乌托邦美好新世界。而事实上,在这个滥用权力、没有法制、充满了僵死的教条与空洞口号的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个性、情感、真诚、信任、内心的宁静和谐和道德上的美,这正是90年代初期马卡宁、奥库扎瓦、佩列文等作家对苏联极权体制下现实的评价,他们以此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所建构的魅力谎言进行解构。
在马卡宁小说《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以下简称《审讯桌》)中,小说鲜明地批判了压抑个性的苏联审查制度。在小说中,这样一张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是每个苏联公民受到审问时经常要面对的桌子。而接受审问几乎成为每个苏联人基本的生活经验。主人公已经年过半百,对于这样的审问已经历了无数次。在又一次将被审问的前夜,他回想起自己这大半生都是在一次次的受审中度过的。不用说犯了政治错误,即使是想调动工作或短期出国旅游,也会遭遇到没完没了的讯问,而每一次都会被问得像抽出了灵魂一般惊慌失措。想到明天又要进行的吉凶未卜的审问,主人公辗转不眠,终于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审讯桌》里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整篇都是由主人公的心绪、感想的片段组成。“我”—— 一个苏联普通公民的代表,总是处于受审问的境地。大到政治问题,小到个人隐私,无不被盘问得仔仔细细,令人张口结舌,尊严扫地。这简直是一场精神上的磨难。在日复一日审问的消耗中,人的个性被彻底粉碎。小说通过“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这种俄罗斯人普遍熟悉的象征性摆设,批判了苏联社会践踏人的心灵、毁灭个性自由的审查制度。
在奥库扎瓦的《被取消的演出》中,通过两个革命者对“人民”的涵义的探讨来消解了官方话语的合理性与权威性。
还有瓦洛佳,他的大哥,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说;“……你们要和谁留在这里呢?……”
“和人民。”沙利科说。
“和人民?”瓦洛佳喊了起来,厌恶地噘了噘自己的嘴唇;“那你们和人民商量过吗?
“和人民也不是总需要商量,”沙利科缓和地说,“人民也许不明白他今天需要的是什么。他明天就会明白的,到时候他会说谢谢的……”
“可你在哪里看到人民了?”瓦洛佳问道。
沙利科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手势指着窗外,那里有三三两两的行人。
“小傻瓜……”瓦洛佳笑了起来,“这是市民!”接着他又大声地说:“你们怎么这样无知……” [3]
革命者以“为人民”的旗号进行革命,而瓦洛佳这样一个老革命对当局者的行动产生质疑时,沙利科祭出了人民之旗,但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人民到底是指谁,他指着窗外“三三两两的行人”来回答关于人民的问题。这一答案让瓦洛佳发笑,他觉得革命者在“人民”问题上也是相当的无知。在瓦洛佳的质疑声中,革命与人民的必然联系在文本中轰然坍塌。小说将革命者对当局树立的崇高概念“人民”的困惑展示出来,可以说淋漓尽致地解构了苏联崇高话语。
佩列文的《奥蒙·瑞》则把苏维埃时代的一切几乎都写成是欺骗。主人公从小幻想当飞行员,于是考入了以著名的无脚飞行将军马列西耶夫命名的航空学校,后被选派到克格勃所属的秘密宇航学校接受登月飞行训练,可是所谓的登月飞行只是为了进行欺骗性宣传而在地下铁道废弃的线路上所作的一次滑稽表演。小说对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嘲笑,把主管这项工作的两位上校写成瞎子,并说他们是专门培养瞎眼政工人员的保尔·柯察金高级军政学校毕业的。在作者的笔下,过去的一切都显得滑稽可笑,英雄人物、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苏联人民引以自豪的宇航成就,无一不受到讽刺和嘲弄。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文学中“苏联”叙事呈现出政治祛魅的特征,它们以历史陌生化的方式,展现了另外一种苏联——比如革命的暴力性、卫国战争的血腥性、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小说通过这种陌生化的手法全面解构了政治理想崇高而神圣的虚幻性因素,满足在历史中压抑已久、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尚不可实现的政治、文化、美学愿望,以对历史的“灾难”化改写化解了历史的“神圣性”。这与解体初期人们清算历史的急切心情有关,当时的社会政治热点借文学得到了最快的宣泄与最为形象的表达。“苏联”被人们控诉、反思,被从文化、国民性、甚至体制等方面进行追问时,它的文学表述的意义在每个特定的时间、空间、社会环境、特殊人群中是不同的,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子。在这种质疑与解构中,理想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作家笔下成为了一种奢侈话语,传统的启蒙主义立场以及洋溢着理想激情的救世行为已经消隐缺席,作品中失却了指向未来的坚定的现代性理想,结果导致了意义的放逐。
参考文献:
[1][俄]哈利托诺夫.命运线[M].严永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95.
[2]张捷.当今俄罗斯文坛扫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83.
[3][俄]奥库扎瓦.被取消的演出[M].林立,唐敬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164-165.
编辑:畦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