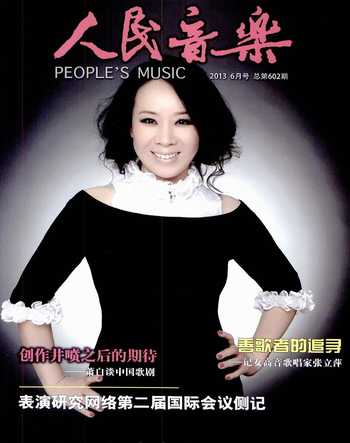永远的记忆
2012年4月访美期间,突然接到家中电话说杨儒怀先生在我出国后第二天住院了。虽然先生久病多次住院,但冥冥之中却感到这次有一丝不祥。于是,我迅速联系师母,得知先生确实病情加重。在焦急和惦念中我终于挨过了漫长的20天,没想到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得到先生病危的消息。我赶到先生病榻前,含着眼泪轻声呼唤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应,2012年5月10日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先生真的就这样走了。那天我在先生家里,看着他面带微笑的遗像浮想联翩。先生一生清廉,家里空间狭小,没有地方设灵堂,大家送来的鲜花只能放在光线黯淡的门厅餐桌上。看到这一切,我不禁泪如泉涌。这么多年,先生与师母一直居住在约60平米的房子里。其中,先生的工作间仅10平米左右,正中间摆放了一张写字台,靠墙立着书柜、钢琴、一个小茶几、两个单人沙发还得分两面墙摆放。毫不夸张地说,剩余的空间只能站立两个人。再看那张陈旧的写字台,由于四周摆满书籍,原本较大的空间只留有不足0.40平米的一小块地方。凡去过家里的人都说这房子实在是太小了,有人说进先生家要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也有人说去先生家一次不要超过三个人;还有人根本不相信先生只有这一处房子……难怪,在住房标准普遍提高的今天谁会不这样议论呢。而了解先生的人无不佩服先生的一身傲骨、两袖清风,无怨无悔地在这窄小的环境里辛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正是在这间书房里,我领略了先生学富五车、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大师风采;也正是在这间书房里,先生帮助我打开了学术思路,奠定了专业根基,找到了前进方向!
与先生相识相知、进而成为他的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当年我们在沈阳音乐学院读书时就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杨儒怀教授。毕业留校后,听到关于杨先生神话般的传说就更多了,如杨先生治学严格,对学生要求很高,想考他的研究生很难等等。的确有很多同学去中央音乐学院考研都败下阵来,于是我也打消了念头。后来我有幸借到曹家韵老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学生)手里的中央音乐学院作品分析教材(油印版),从那时起了解了杨先生的教科书,第一次知道作品分析还有这样的教材,还有这样的教法,它好似一盏明灯,指引我在教学中打开了新的思路。那时虽然还没有深入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但已经获益良多。我萌发了要去拼一下杨先生研究生的念头。198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首届全国作品分析研讨会上,我荣幸地见到了这位健步如飞、思维敏捷、快言快语的杨先生。与他交谈中深感先生不仅学识渊博,也是一位真挚热情、富有责任心的好老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提出想拜先生为师、报考他的研究生,没想到先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增加了信心,并同时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做杨先生的学生很不容易,要有“拼命”精神。不久后,我就开始了与先生的专业学习。
人人都知先生从不收学费,当年我在考研前的准备阶段,经常来先生家里上课,每次都是三个小时,先生讲作品、弹作品,时不时在书架里查找作品,一次课下来乐谱和书籍会堆成一座小山。可每次我预备的学费先生却从来不要,而且很不高兴地说“我从不收学费”。当时我心里很不安,也百思不得其解正常的劳动所得为何拒收啊。后来慢慢读懂了先生,对于他来说,与学生研究作品、探讨学术、驰骋于音乐的海洋是无比圣洁高尚的事,如何能用金钱来衡量!多年来我只能以鲜花赠予先生,而先生送与我的却是用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知识和信心!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有幸成为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后来又成为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记得入学后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出乎意料,是带我了解图书馆。当时还不是信息化的管理,他对图书馆的每一层楼、每个书库、每个阅览室、每种外文刊物的特色以及如何通过卡片迅速查找书刊等进行详细介绍,这对我后来在学习中有效地使用图书馆帮助极大。再后来,我毕业调到中国音乐学院工作时,先生也曾带我来到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暗访”,为我进入新的学术环境做准备。这一点使我想起先生经常说过的一句话:“胡大夫(师母,人民医院著名眼科医生)离开医院就不能工作,如果我离开图书馆也是无所事事。”
回想当年,我是带着问题来上学的,并且对导师的学术观点并不是都能理解。因此,同导师课堂讨论便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音乐语言陈述结构的论述和分析,常常是争论的焦点。记得有一次就肖邦前奏曲作品28之8这首小品,在曲式结构和陈述结构两个层面的关系上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完全明白和接受了导师的理论指向。可以说对导师的很多重要学术观点,如曲式功能的理论、曲式结构与陈述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音乐分析中质量互变原理等等都是在讨论中逐渐深入并理解的。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全国作品分析研讨会上,杨先生大会主题发言题目就是《作品分析教学体系的完善与革新》。他开门见山地就一些教科书以讲授曲式结构为中心、忽视创作的实际过程与步骤、把各种不同的曲式结构看作毫无关系的独立现象等等问题提出批评,并提出音乐创作首先面临的三个问题,即:表现音乐内容的基本手段、发展音乐主题的基本手法以及前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的音乐陈述结构形式。他的这些重要理论后来成为《音乐的分析与创作》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这部著作后来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理论评奖的金奖。在与先生的学习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先生就是先生,他真是把学问做通了。杨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是对中外音乐分析理论的梳理和完善,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上千部中外音乐作品的分析以及对大量中外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多年创作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西方的拱形再现原则、中国的起承转合原则……在杨先生看来都可融汇为艺术发展的普遍和共同规律。杨先生曾参与中央音乐学院编写《音乐百科全书》的攻关项目,他承担对“曲式”条目的编写,就“曲式”条目的定义在上课时曾与笔者反复推敲、逐字斟酌,最后定稿为:“音乐作品中具有不同陈述功能的完整独立的段落,按照某种特定的原则,前后有机地组合起来所形成的结构框架,即为该音乐作品的曲式。在结构框架中被组合起来的段落称之为‘部,因此‘部是曲式组成的基本单位。”由于《音乐百科全书》至今没有出版,这个定义还未能与读者见面,但却一直珍藏在我的学习笔记中,并指导着我的教学与研究。今天也许有人会说不能孤立研究曲式,而先生的教科书始终倡导的就是“音乐的分析与创作”须紧紧相连;也有人会说曲式已不适于现代音乐分析,而先生对艺术发展原则的论述恰恰可以指导一切创作……先生真正建立起了有机、完善、并能与创作实践紧密相联的、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分析理论体系!
先生的成就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我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对什么事都感到新鲜。圣诞节的晚上,几个同学很有兴致地去了宣武教堂,回来路过先生的家,大家异口同声要去给先生拜年,并顺便送去早已准备好的贺年卡。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踏进先生家门时,眼前看到的根本没有什么圣诞节,而是先生伏案看乐谱的情景,音响中播放着布鲁赫小提琴协奏曲,伴着飘然冥想的音乐,衬着灰暗的灯光,瞬间我觉得先生的形象特别高大。他一生不图享乐、生活节俭,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事业中,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先生的勤奋表现在很多方面,先生常说他是图书馆的顾问,每期外文资料、音乐书谱一到馆,都是经他指导分类上架。先生说他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学术前沿。中央音乐学院经常组织国内外专家讲学,包括他的弟子回国讲学,先生都坐在下面认真地听讲,有时还积极提问交流。尽管他不曾踏出国门,但在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方面永远是最前沿的,这种勤奋务实的学习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他的抽屉里存有千余张各类音乐作品研究和分析卡片,而对于研究过的大部分作品先生都能随口说出其曲式结构以及创作特点,这一点确实让学生们无比佩服,自叹年轻的脑子记忆力远不如年长的先生。大家都知道先生有一流的外文水平,他读英文的速度几乎如同我们读中文一样。在我读博士期间,我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对斯特拉文斯基晚期序列音乐的研究,阅读外文资料成为我的主要作业之一。当时每周我都会背着厚厚的乐谱和外文书籍回家,尽管花了大量时间,也用了“啃骨头”的精神,但有些内容仍然不能解释清楚,被我留出来的部分便成了导师的“作业”。让我感动的是,先生不仅认真研读,及时给予帮助,有时还会安慰我说:“这是高级英文,比较难懂。”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斯特拉文斯基序列音乐研究》能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并顺利通过,首先要感谢先生的深入指导。
导师对我的影响不仅是专业上的,在为师做人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热爱教学,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我毕业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去看先生,而每次打电话或者偶尔去先生家总是带着教学问题去请教。其实我的内心十分愧疚,然而先生却从不责怪,一如既往地准备好香浓的咖啡等待着我。那些年在先生的书房里与他谈学问真是一种幸福和享受,是先生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其实,先生不仅对自己的学生有问必答,对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是百问不厌。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对先生曾有过幽默的评价:“去先生家讨教问题最好选择上午11点,不然就很难结束啦。”在他家经常听他在电话里安排与学生见面,有本院的、有外地的,有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有西方音乐史专业的、有视唱练耳专业的、有钢琴、大提琴……为了教学与应对上门求教的学生,先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且又乐此不疲。学生们都知道先生每次上大课必是西服革履,提前进入教室。先生上课永远精神饱满,三节连上,从不喝水。他在讲台上时而板书、时而弹琴,先生的钢琴视奏能力之强,连十二音的作品也不放过,经常惹得同学们发出赞叹的笑声。在我印象中他身体很好,一般很少生病也很少外出,所以杨先生很少停课或者调课,唯一停课的时候就是作为第七、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参加政协会议,而每次参会前会给我们留出更多的作业,回来后先兴致勃勃地介绍会议的趣闻,然后再加长课时补回所缺的课。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们也从不耽误课,有时遇到事情想请个假时,一想起先生便会打消这个念头……。
先生晚年由于一直服用抑制癌细胞的药物,对脑子伤害很大,记忆力明显减退,语言表达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然而他对专业的思考和与学生的业务交流却始终没有停止过。2009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音乐分析大会上,他坚持上台发言,其实对先生而言已是勉为其难,看到台上这位瘦弱老人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谈着他终生为之研究奋斗的音乐分析理论,莘莘学子们无不为之感动。台下热烈的掌声告诉我们,那15分钟的发言也许没有往日的精彩,但留下的却是永远的精神!2011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为先生举办了从教6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时先生的身体和记忆力更差了,然而他以惊人的毅力参加了“杨儒怀教授教学科研成果研究”的全部研讨,认真听取每个人的发言,还不时地与发言者呼应。研讨会结束时先生主动起立向大家鞠躬致谢,那一刻先生的脑力与体力如同一个健康人,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治学精神、为人处世与音容笑貌将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留在他教过的众多学生们的心里!
亲爱的杨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高佳佳 博士,中国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作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