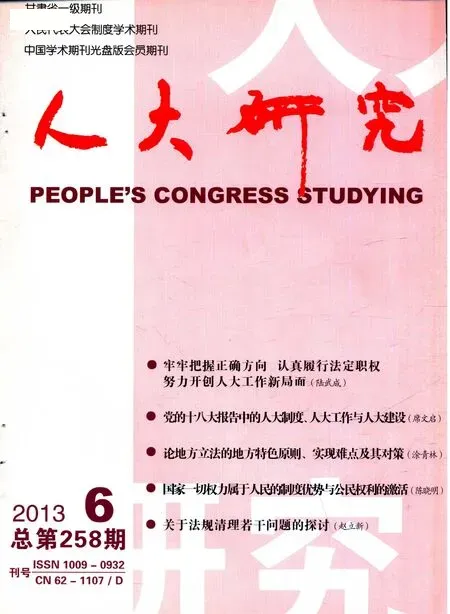行政问责地方立法的差异以及所折射的问题张朝霞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 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
1. 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
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只笼统地规定了其立法依据是有关法律、法规。《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根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甘肃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根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来说,各地将《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作为立法的基本依据。
但是,各地立法依据很不统一,有的以党纪,有的以法律,有的以地方规章为依据。立法依据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实体内容的区别。由于国家层面对行政问责的多种形式的规范,加剧了地方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分歧。什么法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合法、合理的依据这需要进一步明确。
2. 问责对象的分歧较大
《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第二条规定其问责对象是:本市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称:“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甘肃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第二条规定其问责对象是:全省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问责对象行政负责人具体包括: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领导班子正副职和各州、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正副职。《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在附则中规定: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中由行政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和专职从事社会团体工作的行政人员,以及比照公务员管理的部门、中直驻吉林省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本自治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前款所称工作人员包括在编人员和聘任人员。
可见,有的地方立法将组织作为问责的主体,有的将人作为问责的主体;有的地方立法只将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公务员作为问责的主体,有的还将法律、法规授权、受委托的组织工作人员作为问责的主体;有的地方立法将公务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作为问责的主体,有的还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中由行政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和专职从事社会团体工作的行政人员作为问责的主体;有的地方立法将领导作为问责的主体,有的将普通群众作为问责的主体。
可见,谁应成为问责的主体,在我国各地立法中并不统一,有较大的分歧。
3.存在着重复立法的现象
如《甘肃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第九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行为过程中,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各种情形。然而,2004年10月1日的《甘肃省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就类似问题,作了规定。如果对行政许可过错责任问责,到底适用哪一个办法,让人无所适从。
长政发〔2008〕35号《长沙市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办法》的立法依据之一是2003年颁布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的通知》,而2010年出台《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又废除了2003年颁布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的通知》,问责时,到底适用《长沙市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办法》还是《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让执行人非常费解。
重复立法,就会导致与其他法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造成政出多门、无所适从,一定程度上可能在实践中弱化上位法的严格实施。
4. 地方立法中行政问责与相关问责制度存在衔接问题
同一行为一个法律规定可以提起行政问责,另一个法律规定可以提起行政处分,于是产生了法律竞合的问题,那么到底给何种处理?如关于对行政许可中的违法行为,《甘肃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行为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要“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行政问责与行政处分是否能相互替代?行政人员按照《问责办法》被予以行政问责,是否还要根据他所违法违纪的行为予以适当的处分?实践中,执法人员对法律竞合现象难以分辨,在制作法律文书、确定案由及适用法律时,会把握不定,造成适用法律困难。
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根据国家层面的立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和2007年6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当给予行政处分,而根据地方行政问责立法又要对其行政问责。那么这里的行政处分中的“警告”与行政问责中“告诫、通报批评”是否属于一个等级?行政处分中“撤职”与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是否属于一个等级?行政处分中“降级”是否能与行政问责中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适用?
地方立法行政问责与上位法的行政处分如何衔接,行政问责的期限是多长时间,许多地方立法对此问题留下立法空白。
2009 年5 月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行政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是可以单一执行,还是可以共同执行?有的地方立法行政问责立法还面临着使现有的党内问责相关法规和行政问责立法相互衔接配合的问题。
5. 行政问责本质上是同体问责
《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第三条规定:“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市行政问责工作。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施。” 第四条规定:“市和区、县监察机关在行政问责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对行政机关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本行政机关或者任免机关。”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负责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没有设立监察机构的,由行政机关指定相关部门负责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履行与监察机构相同的职责。需要给予问责对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办理。需要取消执法资格的,由发证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从这些地方立法都可以看出问责的主体是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地方立法行政问责本质上是同体问责。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制度设计,忽视了社会力量对行政问责的监督和问责信息的公开,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同时,容易异化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的工具。
6. 行政问责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第六条规定行政问责的方式可以视情况单独或合并适用。在第七条和第八条又规定了从重、从轻的条件。什么样的情况可单独适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合并适用?从重的责任方式是什么?从轻的责任方式是什么?甘肃、北京、哈尔滨等地的立法都反映出这类问题。如此规定都表现出行政问责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行政问责方式的采用缺少法定因素的制约。
7. 缺乏明确规范的问责程序
正当有效的问责程序是区分人治与法治的根本,是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关键,因此,必须追求问责程序的完善。只有具备了完善的问责程序,才能使行政问责在正当程序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防止行政问责的随意性和制度的扭曲。虽然我国地方立法行政问责数量不断扩大、内容越发丰富,但是仍然存在着程序不够完善的缺陷。如,监察机关、人大、公民、媒体、社会组织如何启动行政问责?启动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问责调查的程序是什么?调查机关的确立程序、调查人员的组成、调查的方式和调查结果的提交等是什么?调查确认过程中的申辩、听证、申诉等程序是什么?等等问题,都缺乏详细规定。
8.缺乏异体问责及相应问责措施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人大、司法等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缺乏外部约束,其问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令人质疑。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也是因为地方立法的效力低下,国家权力之间的合理分配、相互制约的问题是个宪政问题,必须由中央立法作出规定。
9.对财政控制权没有规定问责
在我国,政府权力的自我扩张、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追逐,是扰乱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祸乱之源。在财政方面,表现为大规模的预算超收、大规模的预算超支;一些行政机关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摊派、私设“小金库”;“三公”消费猖獗、屡禁不止;年终突击花钱、挥霍浪费严重等等现象。这些情况,由来已久,近年来还有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趋势。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年年呼吁、年年提出批评和对策,有些地方和部门依然我行我素。而在西方国家对财政控制权进行监督问责是对政府问责的“核心”的问题。如果没有牵住财政控制权问责的这个“牛鼻子”,这个建设责任法治政府最核心和关键的要素,行政问责范围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受到严重制约的,由此也导致对问责制的立法效果不能令人持有乐观的态度。
综上所述,地方立法对我国行政问责作了一定的规范,但是由于各地认识的差异,对问责的诸多问题存在不同理解,表现出种种立法不和的问题。同时,由于地方立法的局限性,不能对异体问责作出明确规定。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去解决。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甘肃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甘肃省科技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机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05ZCRA218〕。本文本刊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