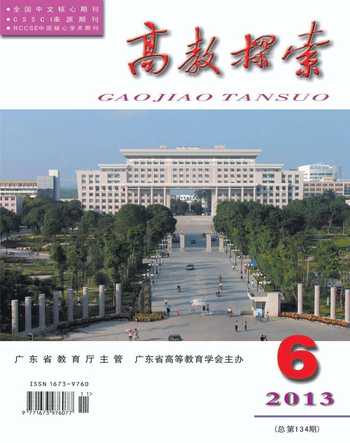大众化时代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建
曾维陆
摘要: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精神主要体现为成就人格的育人精神,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启智醒世的批判精神。大众化时代的大学,商业主义盛行,行政主义至上,技术主义泛滥,传统大学精神失落了。为重建大学精神,应重新勘定大学发展理念,重树对大学精神的信仰,以制度创新实现大学自治,通过讲述大学故事唤醒大学精神记忆。
关键词:大众化;大学精神;失落;重建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自身文化创造过程中沉淀、提炼下来,并为大学人所认同的一套价值观念和群体意识。它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大学的生命之泉,对于提升一所大学的形象、特色、风格和水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同时也是大学凝聚力、感召力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大学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
一、大学文化的精神意蕴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大学文化的精神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就人格的育人精神
育人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大学应比一般学校更侧重于健全人格的培养而非系统知识的传授,培育完整人格的是大学的根本目标。雅斯贝尔斯曾在《什么是教育》中强调:“一般学校要与大学分开,普通学校总是把知识全盘教给学生,而大学则无此义务。”[1]德国的洪堡也认为大学是培养“完人”的地方。何谓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达:“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高度的正直、体谅与包容;他处处替他的对手们设身处地的着想,替他们辨正错误,他对于人类理性的弱点与优点、范围与限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是不信奉宗教的,他高深的见解和开阔的心胸必使他不至于讥刺宗教,或有反宗教的行为;他一定很聪明,所以他虽然无信,却不至流于武断或盲动。”[2]可见,一个人受过大学教育,意味着他是知性、德性统一的人,是一个有着广博文化教养、适宜行为举止和科学思维方式的人,是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大学不仅仅局限于专业教育,教给学生一门将来在社会上谋生的技艺,更应该从各个可能的渠道,培养学生丰盈完整的内在。
(二)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曾经精辟地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追求真理、发展知识的精神传统,来自“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的柏林大学。其创立者洪堡认为大学的作用不能仅限于传授知识、保存和传递已有的传统文化,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学生则应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大学应该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这是柏林大学在不到半个世纪里,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的根本原因。同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大学人有为真理而献身的勇气和信仰,使之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在承认理性的权威之前,不承认有任何权威。因此,“大学乃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理、探索与发现、试验与思索的最高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3]正是对学问的孜孜以求,对真理的不息探索,孕育着大学发展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它们是大学功能实现的必不可少的保证。
(三)启智醒世的批判精神
大学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一切荒谬现象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深刻地指出了“知识人”的使命:“所谓‘知识人,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4]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是‘扰乱现状的人”,“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种族的和性别的特权意识。……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神祇的崇拜,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5]可以说,批判是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是否具有批判精神是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关键。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通过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6]大学汇集了大批知识分子,通过对社会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批判,使大学具有公共良心和独立品格,为知识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同时也引导社会的发展,增进人类的福祉。
二、大学精神的失落
因为培育人格、追求真理和独立批判,大学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也拥有了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在人们心目中占据着神圣的位置。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扩招和扩张,许多大学的文化旨趣悄然发生了的改变,大学精神失落了。
(一)商业主义盛行
大学是育人的场所,是追求学问的场所。大学虽然基于社会,但总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有距离的批判,因而对世俗文化起着引领着作用。而如今,在商业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大学已难以保持其“象牙塔”气质,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产业化的行列。为了“做大做强”,追求规模效应,许多大学引进商业运作模式,升格、并校、建新校区、建大学城;为招生更改专业名称、开设热门专业、扩大招生规模……而师资、设施、教学和管理却跟不上扩张的步伐,大楼、大面积、大数字的背后是教学质量的低迷。在生存压力下,教授做学问“为稻粱谋”,为追逐利益许多大学人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道德操守。
追名逐利不仅危害学术自身,也使大学的育人精神失落。浮躁、虚假的学术空气对学生人格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许多大学生并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大学这一重要的人生发展阶段,抄袭作业、考试作弊不认为可耻,混学分、混文凭也不觉得虚度年华。学生不关心学问只关心学分,不关心导师是否认真治学,只关心是否通过考试,这种心态也正中无心治学的教授下怀,而那种严谨治学的教师被视为“假正经”而不受欢迎,师生之间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商业主义语境中,学生被视为教育流水线下的“产品”,毕业率、就业率、考研率被当做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很多学校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一方面降低或变相降低考试的学术标准,另一方面方便学生找工作、考研,将四年课程提前三年完成。课程挤占了学生自主探究和广泛阅读的时间,大学学习被简化为上课和考试。在许多大学生眼中,学外语、计算机和其他实用技能的功用要远远超过阅读经典,“考证”、“考研”成为大学生生活的缩影。所谓“读书”,读的最多的是教材或考试辅导书,图书馆成为备考的大自习室。
在商业主义的语境中,大学教师的角色也很暧昧,兼职、开公司、办辅导班……美其名曰为社会服务,实质上已异化为商人。许多大学的研究生称自己导师为“老板”,师生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
(二)行政主义至上
大众化时代的大学已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和精神贵族自治的共同体,而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环节。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教育权力和教育权利分配的政治原则高于学术自治原则,政治因素的入侵使大学越来越难以避免日益扩张的国家权力的染指。不仅“政治正确”给学术自由和社会批判设置了“禁区”,而且在大众化民粹主义“教育公平”诉求下,从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到专业设置、招生,再到课程设置、学业管理乃至课堂教学,大学的自主性都受到挑战,大学逐渐沦为国家权力部门的附庸。以此相适应,大学内部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行政机构也上升为大学的主导。正如韩水法先生指出的:“它们(大学的基本学术单位)所具有的自主性相当薄弱。这主要体现为行政主导。基本学术单位的主要管理方式,从教学、学术到其他事务,都是行政决定式的,而不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通过共同参与完成的,亦即民主的方式决定的。”[7]以行政来主导教学和科研,教学和学术研究优劣的标准掌握在行政部门而不是教师手里,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机制,使得教学和学术研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给大学教学的质量和学术研究的质量带来严重的影响。更严重的是,行政权力的扩张进一步助长了官本位思想,极大地腐蚀着大学的精神,使大学有蜕变为官场的危险。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大学什么都关心——谈经费、谈人事、谈机构,就是不谈教育本身。”[8]安心做学问的大学教授似乎越来越少了,有些教授将学术研究当做谋取官职的手段;有些学者将学术资本与权力资本交换,获取个人利益……毋庸置疑,行政主义已构成当下高校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行政至上不仅遮蔽了大学人的求真意识,而且长官意志导致学术自由空间的萎缩和学者独立人格的匮乏,极大地弱化了大学人的批判精神。传统知识分子心怀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9]的社会关怀意识,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三)技术主义泛滥
科学技术在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确立了技术理性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在大学里,技术主义也无孔不入,教学、科研、管理都打着“科学化”烙印,否则难以获得合法的地位。
大学教学本应该是师生之间围绕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切磋交流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情境性、生成性和个性,但在大众化时代,大规模班级教学实质上已使大学教学蜕变成高等知识灌输的过程。为了保证“有效教学”,需要一套“科学的”、“规范的”、“具可操作性的”教学程序和技术。于是大学里建立起了从备课、上课、布置作业到考试的技术规范,任何即兴的、随意的、模糊的、或个性的教学活动都因其无法证明其有效性而受到质疑。技术主义也因为其“铁面无私”、“价值中立”、“可操作性”而省去了大学管理者面临的人际矛盾调解的麻烦,因而备受管理者的欢迎。如职称评定问题是关系到每位大学教师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成为大学教师矛盾的焦点。由于不同教师所从事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不同,管理者不可能具有跨学科、跨领域洞察教师学术水平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统一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标准,量化技术正好体现了这一“科学精神”。“让数字说话,数字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质性的评价都引起是否公正的怀疑。于是技术主义的量化管理大行其道,也成为行政主义外行管理内行的制胜法宝。
然而量化管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因为很多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因素无法予以量化。对教学来说,不同学科、不同课程的课堂各有不同,不同教师的授课风格也本应该多种多样,个性化的教学能使学生得到不同的濡染,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而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投入极大心智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的产品制造并不相同。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的科研项目在付出的劳动量和质方面都有不同,很难用相同的标准来予以度量。在量化管理之下,一切管理和评价都变得简单易行,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心智即可应对。然而它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损害却是相当大的,使教学失去了个性化的色彩,也使学术研究对量的追求超过了对质量的关注。在竞争压力下,大学人变得越来越浮躁,“十年磨一剑”真做学问的人会因其成果数量远远不够而难以在学术界立足,热爱真理,追求真知的大学精神变得黯淡了。
大学对技术主义的依赖还体现在各种“表格管理”上,课题申报、重点学科申报、课题结题、出版资助、课程申请、本科生实习、本科生论文指导、个人信息调查等等,事无巨细,都要填表,表格数量极其繁多,使教师把大量时间用在填表当中。学术的真正进步,学生人格的真正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被遮蔽了。
三、大学精神的重建
(一)重新勘定大学发展的理念
面对商业主义对大学的冲击,需要大学人自身保持清醒的意识,每个大学人都应该深入地思考“大学何为”的问题。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教育产业化”,就需要大学人能够以自身关于大学功能、性质、任务的理性认识,对其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保持理智的清醒。有了明晰的大学理念,大学的运作才能步入正轨,大学的发展才有保证。
无论在任何时代,大学都应以育人为本,这意味着大学在传授知识与技艺的同时,要唤醒学生内在的精神力量,把他们培养成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具有科学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以及适宜行为方式的现代人。大学也是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为真理而生,大学精神是一种崇尚真理的文化。这意味着大学必须敢于突破一切既定观念和教条的束缚,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始终有独立人格的坚守,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这种对真理的无条件追求,也是大学批判精神的体现。大学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为学术,并不意味着大学漠视社会公正。大学人对社会的关注不仅应该指向社会公正,而且需要对诸如战争、疾病、环境、气候、全球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社会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专业的思考澄清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误区,增进智识,起到对一种思想启蒙的作用。
(二)重树对大学精神的信仰
对大学精神的信仰,是大学发展的强大的内驱力。只有大学精神成为大学人的信仰,大学才能成为研究高深知识的机构,成为思想批判的中心,成为守护真理的场所,成为健全人格的锻造之地。大学人只有树立对大学精神的信仰,才能在各种挫折面前矢志不渝。
这方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战火与硝烟中当中,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之中,在经历重重磨难之时,西南联大依然恪守大学的精神传统,遵循大学的规则,其中所体现的卓越的大学精神,成为中国的大学历史上最绚烂的篇章,也为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当下商业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中,重树对大学精神的信仰,大学人才能抵挡各种外在的诱惑,以一份超功利的关怀,不怕吃苦、甘于寂寞、执著、冷静、拒绝媚俗和媚雅、远离浮躁与浮夸,以人格去培育人格,保持深厚的使命感和社会关怀,去除功利主义对学术研究过程的遮蔽,使学术研究的过程成为研究者的心路历程。
(三)以制度创新实现大学的自治
大学精神的重建有赖于大学自治。换言之,大学自治是实现大学精神最根本的保障。所谓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排除外来干预,遵循自己的治理方式,独立处理内部事务。大学自治是处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遵循的重要准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基础。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大学就通过行会或修道院的形式远离社会政治,确立了理性、辩论的学术传统和社团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自治得到法律的确认。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和约翰·M·哈兰在他们的协同意见中阐述了大学自治的主张,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个大学中,知识就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它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之工具,大学将不再会对它自己的本质保持忠诚。”[10]后来,各国纷纷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这一规则。我国最系统地阐释大学自治的是蔡元培先生。他考察了国外大学后认为,只有在国家“不管”的情况下,大学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1922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独立议》,以倡导教育特别是大学要“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党政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只有大学自治,才能保障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1915宣言》中对学术自由立下三个原则:(1)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者有言论自由;(2)除非不胜职守和道德败坏,教授职位必须得到保证生计应有的长期或终身雇佣合同的保障;(3)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11]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社会长远利益的需要,也是大学直接面向社会服务并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大学自治必须依赖制度变革来实现,首先是高校外部制度环境的建构,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明确政府该管什么,高校真正能自主的又是什么。其次是高校内部制度环境的建构,核心是解决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目标在于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校长及行政管理机构,学术权力的主体是教授群体,其组织形式为由教授组成的各级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学校有关学术的重大问题应当拥有决策权和审议权。以制度变革为依托来实现大学自治,关键在立法保障。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术自治,均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落实,或要求大学向司法部门提供《大学章程》、《大学宪章》作为大学自治的基本规范,或者通过相关立法予以确认。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四)讲述大学的故事,恢复大学精神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有无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素质一把标尺。记忆虽然总是指向于过去,但功用却在于当下和未来。因此,记忆既是历史,也是生命。一所大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对其历史的记忆。大学精神就承载于大学校史之中。校史作为一群人共同的记忆,对于培育大学精神非常重要。校史往往积淀着某种历经岁月冲刷仍能保持活力的文化质素,蕴含着自己的办学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也承载着一代代大学人对大学精神的守望,彰显着学人和人师的风采。因此,进行校史教育是培育和弘扬大学精神的基础和前提。
校史教育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建立校史馆,编订校史,拟定校徽校训,编印校史宣讲资料。通过这些方式,使校史深入人心,让大学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还是行政教辅后勤人员,都能在校史教育中了解、领悟、践履和弘扬大学精神。除此之外,叙事也是唤醒大学精神记忆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正如陈平原所说:“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念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12]当然,故事的讲授主体不一定是校方,还可以是大学生。大学精神也就是靠大学生之间茶余饭后的聊天得以流传的。有些故事虽然只是不可证实的传说,但同样不失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50.
[2]转引自李英.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探讨纽曼的大学理念[J].教书育人.2008(4):8-11.
[3]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9.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
[5][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5.
[6][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7.
[7]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J].读书,2005(4):3-13.
[8]董云川.找回大学精神[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7.
[9]转引自白欲晓.从《横渠易说》到《正蒙》——张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和发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46-51.
[10]杨东平.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演变和创新[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5):3-10.
[11]杨东平.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特质[J] .中国高等教育,2003 (23) :15-16.
[12]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3.
(责任编辑于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