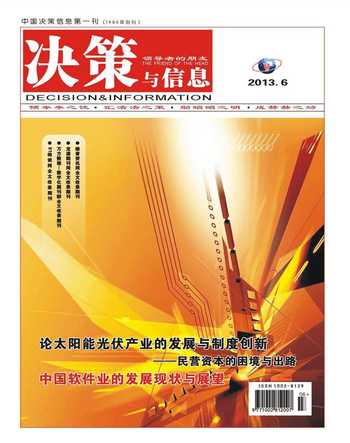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思考
汪芯羽
摘 要 一直以来,毒品犯罪都是我国重点打击的对象,而将毒品犯罪严刑峻法也是我国始终坚持的目标。我国作为少有的几个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国家,频繁和普遍的适用死刑,也给司法和社会带来一定的困扰,为了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兼顾宽严相济的政策,文章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概括近年来导致毒品犯罪案件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毒品犯罪 死刑 死缓 从宽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毒品犯罪作为当今社会的三大公害之一,被世人所鄙视和唾弃。作为亚文化产生的原因之一,毒品犯罪还可能引发其他犯罪的产生,给社会造成重大危害。正因如此,打击毒品犯罪成为我国始终坚持的目标。目前,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分子的量刑体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规定毒品犯罪必须受到刑事处罚。第二,较重的处罚措施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提供有力保障。第三,财产刑的适用,粉碎毒品犯罪的敛财目的。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的处罚还多以重刑为主,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也不在少数。由于现行法律对毒品犯罪的死刑标准规定不明确,导致死刑改判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目前,影响毒品犯罪案件死刑改判的主要因素有:主从犯关系,立功和自首,特请引诱,认罪态度,社会危害性,认定罪名错误,初犯和偶犯,以贩养吸,数量和含量等。
一、毒品犯罪罪名认定错误
对于罪名的选择上,要根据犯罪情节,区分轻重差异。对于同一宗毒品案件,被告人实施了A行为,却有可能被认定为B种犯罪行为,这样就导致实践中出现判定上的偏差。如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的翟某走私毒品一案。毒品通过刘某入境,翟某在龙某的授意下,将龙某的毒资4万元转交给他人。在这样的事实前提下,一审法院将上诉人的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实在是有失偏颇。
对于毒品犯罪因为罪名认定错误而被改判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在审判时,由于司法机关的原因导致罪名认定错误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比如翟某走私、运输毒品一案中被告人的一审辩护律师已经向司法机关提出过不应认定为走私、运输毒品罪,但司法机关并没有考虑其意见,判决书和起诉书基本一致。司法机关的行为直接构成罪名的认定错误,从而导致对于罪行认定上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二、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各项情节
根据在南宁召开的全国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并以此制定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规定了毒品犯罪法定或者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而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具体情形。
(一)自首、立功情形。
《纪要》规定自首、立功的情形可以被考虑为从宽处罚的情节,这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相照应。
由于毒品犯罪的高隐蔽、大危害的特征,毒品犯罪分子的自首往往会大大的节约司法成本、快速提高司法效率。不仅如此,自首情节作为认罪态度好的标准之一,直接反映犯罪分子的可改造性,所以,对于自首的毒品犯罪分子宽大处理是符合情理的。比如2002年云南省王某走私毒品15400克被判死刑一案中,王某在公安机关盘查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但一审并未认定,二审予以认定,并改判为死缓。
除了自首以外,立功也是作为从宽考量的情节。司法机关难以将上、下家同时抓获,通常会利用毒贩的交代来获取线索,从而有效的打击犯罪。《纪要》规定,当被告人帮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分子时,就可以认定被告人立功。比如梁某运输、贩卖毒品490克,一、二审法院均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最高法院复核时认为被告人协助抓获罪行同样严重的同案犯,系立功,因此,改判梁某死缓。
但是,并非所有的立功都要在量刑时予以从宽处理。立功本身只作为一个酌定情节,对于那些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是不予考虑的。在毒品犯罪死刑案件中,立功制度的具体适用问题应该遵从以下规则:对从犯检举主犯的,符合立功条件时,应当从宽处罚;但是对于主犯或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检举从犯的,则要根据主犯或首要分子在全案中的作用,区别处理。如果毒品数量不是很大,原则上可从宽处罚;如果数量很大,罪行极其恶劣的,可以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有重大立功,可以根据案情从轻处罚或者是判处死缓。
(二)特情引诱。
《纪要》规定特情引诱也是作为考察情节之一,在毒品案件中的适用已是常事。其特殊性使得毒品基本上控制在警方的掌握中,不会流入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也大大降低。目前存在的特情引诱包括:犯意引诱、数量引诱、间接引诱、机会引诱这四种情况,对于每一种情形的规定也有不同。
第一,犯意引诱。适用犯意引诱必须要满足一定条件:特情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或者是这类人所指派的特定个体;特情主动实施了引诱行为;行为人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是特情引诱产生的。《纪要》中指出,对于这种情况,量刑时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无论其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如2010年钟某贩卖毒品案中,提出购买要求的下家毫无理由的消失无踪,不排除存在特情引诱的可能性。二审法院考虑了这一情形,最终改判为死缓。另外,犯意引诱中存在一类特殊情形:特情同时为行为人安排上、下家,以便他们进行毒品犯罪活动,这被称为“双套引诱”或是“双重引诱”。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很小,实施的客观犯罪行为也来自于特情的唆使,因此,其危害性极小,在处理时,甚至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第二,数量引诱。由于行为人原本就具有犯罪故意,特情的出现并不改变行为人将要实施的客观行为。只是说,有可能行为人本来准备贩卖的毒品数量并未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但是在特情的引诱之后,行为人最终实施的数量达到了判处死刑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从轻处罚,即便达到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如王某贩毒案中,王某贩卖毒品588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法院没有核准该案,原因是特情引诱的408克造成了达到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一、二审法院对于这一情节的忽略,险些导致一场严重的司法错误。
第三,间接引诱,指受特情引诱的被告人的行为又引起了原本没有毒品犯意的其他人产生毒品犯罪故意,并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参照上述两种情形处理。总的来说,间接引诱情形下犯罪人实施的客观行为往往是在警方的操控下进行的,也应从宽处理。
第四,机会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就有毒品犯罪的故意和行为,特情引诱仅仅是给行为人提供了机会或条件,进而发生了犯罪。机会引诱与犯意引诱、数量引诱、间接引诱不同,上述三种情况中特情所起到的作用相对而言大得多。机会引诱中的特情只是给本身就会实施犯罪行为,并且具有主观恶意的行为人提供了一个更加便利的机会而已。本质上就没有教唆犯罪的性质,当然,在处理上也不能从宽。
(三)以贩养吸。
以贩养吸也是考量情形之一,然而,实践中却很难将这种情况下的持有行为与贩卖行为区别开来。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毒品数量超过死刑标准的以贩养吸的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根据疑罪从无,不宜认定为贩卖毒品。特别是在适用死刑时,更应考虑吸食情节,慎用死刑。比如2004年宋某贩毒案,吸毒人员宋某向王某购买海洛因1000克,分两次交易。在第二次交易毒品400克的过程中被抓获。一、二审中,宋某均表示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但一、二审判决均以贩卖毒品罪对宋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复核程序中,最高法院认为,没有确实无误的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系贩卖毒品,只能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改判无期徒刑。除此之外,《纪要》还规定,为获得吸食毒品而参与走私、运输毒品的,也不宜判处死刑。比如郑某走私毒品案,吸毒人员郑某走私海洛因365克,一、二审法院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法院复核时认为不排除行为人自己吸食的可能性,综合全案,改判死缓。
(四)初犯、偶犯。
《纪要》规定初犯、偶犯的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在毒品数量刚刚达到死刑标准,而又不具备从重处罚情节时,是不宜将这类犯罪群体判处死刑的。比如2003年的何某运输毒品死刑案中,上诉人何某的上诉理由之一就是其为初犯,在二审法院将其死刑改判为死缓时也考虑了这一情节。
(五)共同犯罪情形。
毒品犯罪常表现为共同犯罪的形式,特别是在毒品犯罪的死刑案件中,多以人数众多、分工明确、组织固定的犯罪集团存在。由于组织成员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定罪量刑,因此,主从关系理所当然成为量刑考量因素之一。但是往往在共同犯罪的毒品案件中,主从关系难以区分,这也导致法院错判的可能。目前,审判中对于共同犯罪主从关系的认定,多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比如,在江某运输毒品案,行为人江某受武某邀请运输毒品900克,一审法院没有分清主从关系,直接判处二人死刑立即执行,十分草率。二审认为,江某是在受邀请下运输毒品,起辅助作用,判处江某死缓。
在毒品共同犯罪的案件中,还存在两种特殊的情形:第一,当共同犯罪中所有行为人的作用难以区分,主从关系难以确定,毒品数量刚达死刑标准,从仁道主义出发,结合刑法的谦抑性,可以不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当共同犯罪涉及家庭成员的情况下,如果同一案件中,已经有家庭成员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即便也起主要作用(但是这种主要作用一定不能比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些家庭成员的作用重),也没必要同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毒品数量、含量的考虑
对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应做出毒品含量鉴定。毒品含量低的,应酌情考虑。对于掺假后毒品数量才达到或超过判处死刑标准,没有其他从重情节的,原则上不得判处死刑。对于新型毒品,虽然没有明确的数量规定,但在判处死刑时也要慎重。在毒品数量刚刚达死刑的数量标准时,还必须结合犯罪分子的其他方面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在毒品犯罪中死刑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在量刑时,要做到宽严相济,充分考虑到主从犯关系、立功和自首、特请引诱、认罪态度、初犯和偶犯、以贩养吸、数量和含量等各个情节之间的关系。争取在严刑峻法中做到合理适当的“慎杀、少杀”,减少相似案情不同判决的可能。
(作者:西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刑事法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安住.毒品犯罪适用死刑学说与司法经验的案例解读[J].法学评论(双月刊),2010:4.
[2]梅传强、徐艳.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5):86.
[3]刘红月.毒品犯罪控制下交付的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9(5):76.
[4]何家弘.证据调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5]陈兴良.刑法的启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