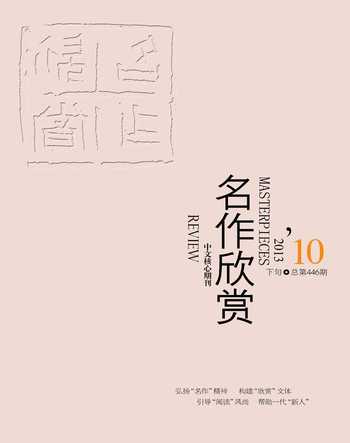五月诗花次第开
摘 要:“五月诗社”是新加坡当代文坛颇负盛名的华文诗歌社团。多年来,诗社创作成就突出,其中,《五月抒情诗选》《五月乡土诗选》《五月现代诗选》等选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五月诗人的创作风貌和创作能量。本文从中选取淡莹的《伞内·伞外》、梁钺的《鱼尾狮》、华之风的《挂一枚月亮在家中》等三首代表作进行深入解读,通过阐析“唯美的抒情”“怪异的乡土”“失重的现代”等不同诗意,来领略五月诗人的风采,并尝试发掘海外华文诗坛的经典意味。
关键词:“五月诗社” 经典解读 抒情 乡土 现代
“五月诗社”是新加坡当代文坛颇负盛名的华文诗歌社团,它成立于1978年10月,先后有南子、谢清、流川、文恺、王润华、淡莹、贺兰宁、梁钺、郭永秀、林也、华之风、希尼尔、伍木、奔星等知名诗人参与其中。几十年来,诗社不断壮大,创作日渐丰富,影响也渐趋深远。尽管诗社成员创作风格各具特色,甚至同一诗人在不同阶段的创作也迥然有异,但诗人们因共同的文学理念抱团结社,自然会在整体的创作风貌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有论者曾说:“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深厚内涵,以及对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和运用”是五月诗人创作的共同点之一,他们“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互相融合,形成了自己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譹?訛。此论颇为中肯,因为细细研读五月诗人们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大都将中华文化内核与西方文学精神有效结合在一起,在传统与现代、持守与新变等多重合力中开拓出一条独特的诗意之径,为新加坡华文诗坛辟出了一方亮丽的风景。
为展示诗社同人的创作实绩,多年来诗社已出版了二十余本诗集,其中既有单个诗人的专辑,也有多位诗人的合集。在诸本合集中,《五月抒情诗选》《五月乡土诗选》《五月现代诗选》是颇具分量也颇有影响的选本。这三本诗选在很大程度上既呈现出五月诗人的创作风貌,也展示出五月诗人的创作能量。本文拟从中各选取一首代表作进行深入解读,借此领略五月诗人的风采,并尝试发掘海外华文诗坛的经典意味。
一、唯美的抒情——淡莹的《伞内·伞外》解读
淡莹,原名刘宝珍,祖籍广东梅县,1943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现工作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淡莹是五月诗社中一位刚柔相济的女诗人,她的诗作既有铁马西风、刚硬凌厉的一面,如《五千年》《西楚霸王》《夜读好诗》等佳作;同时也有杏花春雨、柔情万种的一面,如《忘情》《发上岁月》《伞内·伞外》等诗歌。尤其是《伞内·伞外》这首爱情诗,更以其优美的诗意和唯美的抒情而脍炙人口。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玲珑的三摺花伞/一节又一节/把热带的雨季/乍然旋开了/
我不知该往何处/会你,伞内,还是伞外/然后共撑一小块晴天/让淅沥的雨声/轻轻且富韵律地/敲打着古老的回忆/
听雨的青涩年龄/管它是否已尾随/喧噪了一个夏季的/蝉叫,陷进泥潭/只要撑着伞内的春/我们便拥有一切,包括/沼泽里笨拙的蛙鸣/
二月底三月初/我摺起伞外的雨季/你敢不敢也摺起我/收在贴胸的口袋里/黄昏时,在望园楼/看一抹霞色/如何从我双颊飞起/染红湖上一轮落日/?譺?訛
作为一首玲珑精致、清新纯美的爱情小诗,我以为它的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题旨贯通、意脉流畅的结构美。诗题“伞内·伞外”,显示出“伞”在全诗中的纲领性作用。于是,诗歌围绕“伞”这一意象,构筑了晴和雨、摺与撑、外与内、人与景几对相互关联、相映成趣的互动场景。诗的首节以“玲珑的三摺花伞”破题,描写本来摺起的花伞,在雨季到来的时刻“乍然旋开”。紧接着,诗人以“我不知该往何处/会你,伞内,还是伞外”再次呼应题目,并在轻轻的点题之后叙写伞内的温馨和伞外的风景。伞内是春意盎然的晴天,伞外是喧嚣不已的雨季;伞内是浓情蜜意的恋人,伞外是蛙鸣蝉唱的合奏。还是围绕着伞,诗歌两次写到“撑”,也两次写到“摺”,撑开的是晴天也是爱意,摺起的是花伞也是柔情;撑开时心花如雨季般开放,摺起时情意如霞光般鲜艳。总而言之,诗歌紧扣伞的节奏,在收放开合之间,将动作的推进、景物的变化、情感的律动娓娓道来,既显得层次分明、曲折有致,又显得文脉流贯、一气呵成。诗歌结构的紧凑与精巧,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进一步说,“伞”作为全诗的纲领性意象,甚至就是女主人公的象征:玲珑多摺的花伞妙喻美丽多情的少女,花伞旋开热带的雨季喻示少女敞开炽热的情怀,伞内伞外的两重境界则是少女内心世界与外在情感表露的映照。如此解读下来,当诗人轻问“你敢不敢也摺起我/收在贴胸的口袋里”
时,就有伞与人浑然一体、妙合无垠的效果。
二是动静有致、虚实相生的意境美。诗歌塑造的伞内伞外的两个世界,充满着亦动亦静、动静相映的情
趣。摺起的伞是静的,而当雨季到来、乍然旋开时,却充满着强烈的动感。淅沥的雨声,喧噪的蝉叫,笨拙的蛙鸣,这些自然的天籁无疑是动态的;然而伞内的恋人相依相偎、甜蜜旖旎,无疑又洋溢着醉人的静美。将伞摺起、同时也将雨季摺起,透显出一种风停雨散、云开日出的转变与欣喜,自然是一种动态的季候与情感的双重节律;而恋人相拥于楼头、沉迷于湖光山色、陶醉于浓情蜜意,应是一个听得见相互心跳的静谧场景。诗歌就是这样在一动一静、动静交融的节奏中铺陈出跌宕起伏的情意,令人真切地体验到一种张弛有度的情感力量。另外,诗歌在动静相宜的情致中还营造出一种虚实相生的意境。这种意境既有化虚为实,也有化实为虚,虚实结合,相生相宜。先看化虚为实,如“雨季”只是一个名词概念,一个抽象的季候,“旋开”是张伞的具体动作,“把热带的雨季/乍然旋开”,两相搭配,就是虚者实之,化虚为实。其他如“撑着伞内的春”“摺起伞外的雨季”“敲打着古老的回忆”等也是如此。再看化虚为实,如“年龄”是抽象名词,而“青涩”则为具象的形容词,“听雨的青涩年龄”则不仅把雨拟人化,而且把抽象的年龄具象化,从而塑造出鲜明的视觉形象。其他如“贴胸的口袋”一句,也是把深深爱意化作具体情节,令人在具象化的言语牵引中似可触摸那如水的柔情。诗歌就是在虚虚实实之间,氤氲出空灵隽永的诗味。
三是话语蕴藉、情趣盎然的诗性美。依照文学的经典律则,话语蕴藉应是文学作品最本质的特征之一。追求含蓄深蕴的审美意味,创造无限阔大的想象空间,是无数文学家孜孜不倦的追求。在这方面,《伞内·伞外》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这首诗的话语蕴藉首先体现在语言的陌生化,即打破语言惯例,将话语放在反常的情景中展开。如诗歌一开篇就不按常理写雨季来临,人们须张开花伞避雨,而是一反常规的着笔,写三摺花伞“把热带的雨季/乍然旋开了”。同样在诗歌的结尾,不说晚霞映红了湖水、映红了姑娘娇羞的容颜,反而写“一抹霞色/从我双颊飞起/染红湖上一轮落日”。这样从反面下笔,不仅从语言上创造了一种新鲜奇异、令人回味的效果,而且从内蕴上营造了一种回环往复、委婉别致的情景。更进一步说,这样一种陌生化表达,还非常吻合热恋少女那种含蓄深邈的情致,从而使人与物、情与景形成了一种相互契合的诗意关联。其次体现在双关语的运用。这对恋人紧相依偎,“共撑一小块晴天”,一起听“轻轻且富韵律”的淅沥雨声。这里“晴天”谐音“情天”,妙语双关,寓意丰富,令人不禁想起刘禹锡笔下“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境界,以及韩愈笔下“人间自是有情天”的感叹——这种“雨中共撑晴天”的情境,一方面突出了爱情的温馨、心情的亮丽,另一方面也在谐音复义中透显出一层知性的机趣和智慧的光辉。第三体现在拟物手法的运用。诗的最后一节描写道,雨季已过,雨伞已收摺。诗人问恋人敢不敢摺起自己,“收在贴胸的口袋里”,这样殷殷询问,显然是希望自己能像花伞一样被恋人摺起贴胸收藏,以便时时相伴,永不分离。这种妙乎其想的诗思,一往情深而又轻言娓娓,不仅将抽象的情思具象化,而且通过当场“现挂”的途径,将内心的渴望与外在的事物顺势关联,从而构建出一种情景交融、意象飞动的审美空间。
综上所述,《伞内·伞外》的确不愧为一首融古典情怀于现代手法的精美含蓄的爱情诗。甜美的恋情、华美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共同创造出一种无比美好的诗意境界。诗人西川曾经说过:“美好的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譻?訛是的,当我们在淡莹的诗中体验着美好的诗意,我们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人与世界发生了诗意的相遇。在这相遇的一刻,我们的心灵在诗意的浸润中有了微妙的改变,我们眼中的世界也在诗意的弥漫中变得更加迷人。
二、怪异的乡土——梁钺的《鱼尾狮》解读
梁钺,原名梁春芳,1950年出生于新加坡。梁钺在“五月诗社”中被称为“苦吟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丰富的文化寻根意识。所谓现实关怀,是指他对“地理乡土”的钟情,即梁钺的诗歌是立足新加坡本土的诗歌,诗中既有蕉风椰雨、热带风情的形象描写,也有狮城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体验和对现代人生的审美观照。所谓文化寻根,是指他对“文化乡土”的追寻。梁钺是一个深具文化自觉的诗人,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血脉,对他们这些移民后代来说,文化更是一种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所以他的诗歌充满着对文化乡土的思考与寻觅。《鱼尾狮》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说你是狮吧/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纵横千山万岭之上/说你是鱼吧/你却无鳃,无鳃你就不能/遨游四海三洋之下/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不能两栖水陆之间/
前面是海,后面是陆/你呆立在栅栏里/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像/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赞赏你,如何美化你/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鱼狮交配的怪胎/
我忍不住去探望你/忍不住要对你垂泪/因为啊,因为历史的门槛外/我也是鱼尾狮/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还有两眶决堤的泪……/?譼?訛
在这首诗中,“鱼尾狮”与“乡土”到底具有怎样的关联?让我们先来看看鱼尾狮的特殊面目。关于鱼尾狮,“百度百科”这样解释:“鱼尾狮是一种虚构的鱼身狮头的动物。它于1964年由当时的Van Kleef水族馆馆长Fraser Brunner先生所设计。两年后被新加坡旅游局采用作为标志,一直沿用至今。而这期间,鱼尾狮已成为新加坡的代表。……造型趣味而极富创意的鱼尾狮,全身洁白、双眼含笑、毛发丰美、鳞片鲜活。白色水花日夜不停地从狮口喷洒而出,流向河水,奔向大
海,为新加坡河畔一带的景致营造了美好的气氛。”由此可见,鱼尾狮不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旅游景点,而且已上升为具有图腾意义的国家象征。这样一个被寄寓了丰富意蕴并被置于特殊地位的雕塑,自然会引起文学家的热情关注。有论者在梳理新加坡文学中有关鱼尾狮的各种描写之后这样总结:“鱼尾狮已经的确成为了新加坡华文文学中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意象。”?譽?訛新加坡知名学者王润华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今天的新加坡人,几乎人人都发现自己像一只鱼尾狮,是一只怪异的不知名的动物。新加坡的文化思想的发展,新加坡个人的成长,都正面临这种困境,因为新加坡正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三文治社会里,自己是新加坡华人,却没有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甚至不懂华文。新加坡华人受英文教育,却没有西方优秀文化的涵养,只学到个人主义自私的缺点。……因此,‘鱼尾狮的意象便成为作家探讨新加坡人困境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个基型意象,它的确很恰当地代表目前新加坡人所面临的困境。”?譾?訛
综合上述观点可知,在许多文人眼中,鱼尾狮是一个具有新加坡本土色彩的、象征着新加坡人现实文化困境的基型意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鱼尾狮与乡土建立了内在意脉上的关联,因为“乡土”一词从来不是枯燥的地理概念,而是生动的人类生活、鲜活的文化样态以及丰富的精神追求。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梁钺通过对鱼尾狮的诗意刻画表达了自己对“文化乡土”的现实理解。这种理解的核心在于:他脚下的乡土在文化结构上就像鱼尾狮一样是一个杂交的怪胎!
这一怪胎之怪首先体现在形体的残缺。当众多观赏者专注于狮头鱼尾的奇妙组合之时,作为流散者的诗人却独具慧眼地发现,这一合成是以丧失为前提的。狮头下面是鱼尾,意味着狮身狮腿的丢弃;鱼尾上面是狮头,意味着鱼头鱼鳃的阙如。以两个残缺不全的形体拼贴成一个全新的物体,不可能有自然天成的新质,只可能有强扭成型的怪异。这种情态,多像处于中西方文化夹缝中的新加坡华人啊,就像王润华所感叹的那样,他们既丢弃了中华文化的内核,又没有获得西方文化的精华,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怪物。
这一怪胎之怪其次体现在功能的丧失。狮是山中之王,此刻却失去了纵横千山万岭的双腿;鱼是水中之仙,此刻却失去了遨游四海三洋的双腮。诗歌用三个“不能”揭示出这个组合体在拼凑过程中抛却固有功能的真相。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人们在想象的还原中领略到这一雕塑在形体的分裂中还隐含着内在功能的丢失和生命能量的萎缩。事实上,这一世相也是新加坡华族移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离开了孕育生命活力的文化原乡,生活于被欧风美雨处处侵袭而渐感陌生的异域,又有几个移民能有如鱼得水的快乐、如虎还林的潇洒?
这一怪胎之怪还体现在空间的固化。诗歌描写到,鱼尾狮“呆立在栅栏里”,前不能入海,后不能进山,只能枯立岸边,终日吐着苦水。这一状况,恰恰是移民群体夹缝中生存的一种镜像。在新加坡这一特殊的文化空间里,多种异质文化的力量相互牵扯、相互竞逐,人们在文化角力中往往进退失据,不知所措。
正是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揭示,诗人从鱼尾狮中窥探出“文化乡土”的特质,即“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像”的杂交怪胎。而“一肚子苦水”“两行决堤的泪”则意味着诗人对这种现实境况的强烈否定。从中可见,诗人在处身乡土的同时又不满于乡土的文化氛围,批判乡土的同时又无法摆脱乡土上各种文化的逼仄——诗人就是在这多重矛盾的揭示中,逐渐将怪异的雕塑演化为乡土的镜像,让人们从文化杂交的荒诞组合中看到了文化传统的丧失和精神之根的萎缩。正如台湾诗评家所说:“诗人梁钺从这尊‘半狮半鱼的‘鱼尾狮身上寄寓自己对新加坡华族族性和传统文化产生变异的思考,蕴含着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满腔的悲苦情怀。”?譿?訛在写作手法上,诗歌呈现出一种层进式的对话结构——诗人和鱼尾狮之间由远距离的互看,到近距离的沟通,再到零距离的融为一体,这样步步递进,构筑了诗歌扣人心弦的感染力。具体来说,诗的第一节更多显示出一种看客姿态,诗人似乎在自言自语中点评鱼尾狮“非狮非鱼”的尴尬;第二节则像镜头一样缓缓推进,逐步显示出鱼尾狮的吊诡本质——“怪胎”,第三节则悄悄消除了二者之间的评点和比较距离,慢慢地合二为一,一句“我也是鱼尾狮”,将主体与对象的暗合显露无遗。这样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较好地将个体的感觉经验转化为群体的命运忧思,令人印象深刻。另外,诗歌隔行押韵的设计,也强化了诗歌的抒情效果。“鳃”“胎”“海”“外”这些“开口呼”韵脚词的使用,强化了情绪宣泄的力度,使诗歌情感的抒发具有强烈的迸发力。
同是五月诗人的伍木(张森林)在一篇论述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文章中曾说道:“梁钺通过《茶如是说》和《鱼尾狮》展现苦吟诗人的形象,……他的作品流露出一股深刻的黍离之伤,展现出豪气干云的文化脊梁。”?讀?訛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梁钺诗歌创作的中肯评价。
三、失重的现代——华之风的《挂一枚月亮在家中》解读
华之风,原名蔡志礼,祖籍福建安溪,1958年出生于新加坡,现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华之风1985年3月加入“五月诗社”,是诗社同仁中新生代的代表。其诗作旨趣主要体现为对传统的钟情和对现代的反思,代表作《挂一枚月亮在家中》可以说非常集中地呈现出他的这种艺术追求。
挂一枚月亮在家中/好让流落闹市/沾满俗尘的心情/得以赤裸裸的/沐一场月光浴/
挂一枚月亮在家中/好让电视机前的妻和我/共嚼一卷悲欢离合/另加一小碟/加了蜜糖的月光/好让横陈睡房的卧姿/得以重续千年以前/嫦娥未圆的梦/
挂一枚月亮在家中/好让照过历史兴衰的清辉/也俯视书架上那几册/面容枯槁的线装书/映一映遗民们/不忘前朝衣冠的情操/好让白天不见蔚蓝/夜里失落星空的眼睛/有一枚高悬的信念/可以仰望/
挂一枚月亮在家中/好让输入电脑程序的思维/偶尔自修一些/基本的外星文外/还会时时惦着唐诗/惦着宋词/以及缭绕着月亮的/墨香/?讁?訛
诗歌反复咏叹着要“挂一枚月亮在家中”,显而易见,“月亮”是一个笼罩全诗的特殊意象。那么,这个意象的特殊意蕴表现在哪里呢?诗人曾在自己的诗集《月是一盏传统的灯》的后记里写道,月亮“是母族文化传统精神,是我诗观体系里所形成的一种象征式的意象,同时也是一种可以仰望的信念”?輥?輮?訛。依据诗人的自白来解读诗歌,我们可以得知月亮是信念的象征。这种信念,在诗歌中有着多层面的表现。在诗的第一节,月亮喻示着一种清雅的情感;在诗的第二节,月亮应是一种悠远的梦想;而在第三节中,月亮成为一种高悬的信仰;诗的最后一节,月亮则象征着一种优良的传统。情感、梦想、信仰、传统,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容,是人类生命厚度的体现。诗人对它们的反复召唤,恰恰是因为诗人所处的现代社会正在将它们淡化或者驱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新加坡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以及都市化和商业化的深入,新加坡社会的现代性特征也日渐明显。市场触角无孔不入,商品资讯极其丰富,感官主义到处泛滥,平面文化恣意横行,种种现象,不仅全方位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许多传统的人文观念,导致价值判断的错乱和生活伦理的危机。华之风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对精神的衰退和信仰的失落表现出极大的痛心,并试图用人文传统和理想信念来重建人们的灵魂,拯救失重的社会。于是,他以笔为旗,呼唤用信念的月光,照亮人类的心灵家园。
为了全面呈现这一深刻题旨,诗人特别注意营造诗歌的整体张力。关于诗的张力,美国新批评派诗评家阿伦·泰特曾说过:“诗的意义,全在于诗的张力;诗的张力就是我们在诗中所能找到的一切外延力和内涵力的完整的有机体。”?輥?輯?訛也就是说,诗的张力就是诗歌内敛的思想内涵与外射的情绪力量通过语言和结构的特殊运作而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往往是孕育和凝聚诗意并使之不断扩展和升腾的强大气场。《挂一枚月亮在家中》一诗可以说通过多种技巧的运用经营出繁复多样的张力形态。
首先,诗歌通过建构反常关系来形成张力。关系,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遵从着各种自然规律,本已构建出多种多样的逻辑关联,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规与惯例,比如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草木荣枯等等。然而诗歌为了题旨表达或情感呈现的需要,有意打破定势,构建反常关系,创造一个假定性的艺术世界,就容易形成艺术张力。比如,“挂一枚月亮在家中”,月升月落,本有大自然自身的节奏,怎么可能让人把它当作灯笼一样常挂家中?然而诗人反复咏叹,似乎如一巨人提着月亮游走人间。这就形成了诗歌的张力:通过艺术的情景虚拟折射出对现实的状态揭示,这种转换的审美动力源就是诗人对现代社会精神贫乏、信仰失落的忧思与批判。同样的例子还有“流落闹市的心情”,心情怎可流落?然而恰恰是这种反常表达,把现代人无处寻找精神家园的痛苦非常巧妙地凸显出来。
其次,具象与抽象有机结合造就张力。好的诗歌往往都会营造优美的意象,而意象本身就包括具体的事物形象和抽象的智性哲理,两者结合巧妙往往生发出丰富的张力。《挂一枚月亮在家中》一诗中这样的组合很多,比如让“月光”来沐浴“心情”,让“卧姿”来重续“梦想”,让“眼睛”来仰望“信念”,让“墨香”来浸润“思维”,前者都是具象,后者都是抽象,两方面结合,生发出绵绵不尽的诗意。除此之外,诗中用“月亮”象征信念,用唐诗宋词象征传统,则是在更高的结构层面将具象与抽象融为一体,使之成为贯通全诗的意脉。进一步说,具象是实体的,抽象是虚幻的,将具象与抽象结合,也就是喻示用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来填充现代人空虚的心灵。
第三,语言组合的跳跃产生张力。跳跃是诗歌语言组合最常见的美学特征,没有跳跃就没有意义的跨度,没有想象的回旋。通过跳跃,诗歌在挣脱常见的语用逻辑后,往往通过新奇的语言重组来孕育无限的张力。
《挂一枚月亮在家中》首先表现出语词搭配的跳跃性,如“共嚼一卷悲欢离合/另加一小碟/加了蜜糖的月光”一句,其中“嚼”与“悲欢离合”、“蜜糖”与“月光”的组合,就跨越了惯有的关联,给人一种跳脱无碍的新鲜感;同时这一句还蕴含着感觉的跳跃,即通过视觉与味觉的交错,编织出一种特殊的情绪张力。其次表现出时间的跳跃性,如“好让横陈睡房的卧姿/得以重续千年以前/嫦娥未圆的梦”,将现实的追求与亘古的梦想连接起来,含蕴出无限伸展的意义空间。而且正是这种时间的跨越,使平面化的现代社会与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想象中得以接续,从而很好地呼应了题旨。
综上所述,诗人通过多种手段的运用,着意营造出诗歌丰盈的张力,让读者在品读之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绵远悠长的生长性。这种不断增值的诗意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诗歌一种历久弥新的审美特征。
“五月诗社”是海外华文诗坛难得一见的创作群
体,几十年来,诗社以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对纯诗理念的坚守、对人文关怀的倡导和对艺术创新的追求而闻名于新加坡文坛。在这些共同信念的基础上,诗社同仁们创作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诗歌作品。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应是海外华文诗歌经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陈贤茂:《新加坡五月诗社的艺术追求》,《华文文学》1991年第3期,第39页。
[新加坡]淡莹:《太极诗谱》,七洋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西川:《关于诗学的九个问题》,《新华文摘》1996年第2期,第130页。
④ 熊国华选编:《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诗歌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⑤ 朱崇科:《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3页。
⑥ 王润华:《鱼尾狮神话:新加坡后殖民诗歌典范》,《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页。
⑦ 许惠芬:《梁钺〈鱼尾狮〉析论》,选自杨松年、杨宗翰主编:《跨国界诗想:世华新诗评析》,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⑧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第98页。
⑨⑩ 华之风:《月是一盏传统的灯》,七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第148页。
?輥?輯?訛 阿伦·泰特:《诗的张力》,载史亮编:《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批准号:11&ZD111)之子课题“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解读”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陈涵平,文艺学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及海外华文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