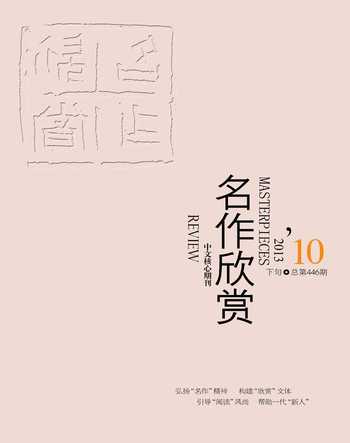亦真亦幻色彩斑斓 虚实相生光怪陆离
摘 要:新时期中国小说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并且在借鉴与学习中逐步创造,中国当代作家对魔幻意象的巧妙营构使其文学作品独具审美价值与魅力,彰显了“中国化”的魔幻现实主义。本文从美学角度对魔幻意象进行阐释、分析,解读其中的主题内涵与人文情怀。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小说 魔幻意象 美学内涵
魔幻现实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共同倾向。它与传统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主要特征是魔幻性,也就是现实的魔幻化和魔幻化的现实,变现实为幻想又不失其真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新时期中国小说尤其是“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我们解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时,魔幻意象作为一个独特的审美价值横亘在文本之中,赋予了作品更多重要的美学功能。那么,对魔幻意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美学阐释,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分析文本,把握文本的审美价值。就魔幻意象,笔者分别从三个方面来透视与解读。
一、魔幻意象的隐喻性与多义性
魔幻意象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隐喻性,也可以说是象征性。如庞德所说的“光芒四射的中心或光束”,“从它之中,通过它,进入它,种种思想源源不断地喷突奔涌”①。因此我们在解读文本时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魔幻意象本身,而应该鞭辟入里,深入挖掘承载着多重隐喻性的魔幻意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寓意。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这原上曾经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还有晶莹剔透的白角。正是这一个古老的传说,从此有了白鹿原。作者将现实民间故事涂上魔幻神秘色彩,又不失真实。“白鹿”如神灵一般,实际上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符号,体现人性中“善良”“正义”“美好”的一面。它不仅寄寓着作者对历史碎片记忆的诗情,也寄寓了一代农民的向往和憧憬。作为农民心中的集体无意识的表征,“白鹿”也就成为一种无形的信仰,是白鹿原历遭劫难而不致毁灭的强大精神信念。魔幻意象的隐喻性不仅使文学的思想内涵更加深刻,而且在艺术上也使小说文本超越了时空。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亦真亦幻与虚实相生,以及本身所呈现出天然的神秘性都促使了文本中魔幻意象的多
义性。魔幻意象的多义性,使读者在阅读视野中对文本的理解有了多元的阐释空间。例如莫言小说《蛙》,作品描述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小说主人公的姑妈)的一生来反映中国当代乡村几十年的生育史,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在小说结尾的戏剧部分,作者借蝌蚪之口与姑姑的一段对话这样描述:
姑姑:叫什么题目来着?
蝌蚪:《蛙》。
姑姑:是娃娃的“娃”,还是青蛙的“蛙”?
蝌蚪: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②
可见“蛙”不仅只是作为一个题目存在着,更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多重魔幻意象。
首先,“蛙”暗指“娃”。作品中,姑姑万心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乡村医生,她不知救活了多少妇女和孩子,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与威望,并有着“送子娘娘”的美称。后来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作为党员的姑姑成为了铁面无私的执行者,她追捕超生的妇女,并让已有孩子的男人做结扎避孕。她亲手阻止了两千八百多个孩子降临于这世上,这时她成为了村民眼中的“魔鬼”,已不再是当初的“送子娘娘”。这一切都与“娃娃”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如同一个悖论横亘在文本之中,这也是《蛙》的主题之一,即人类的生生不息的繁衍本能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
其次,“蛙”暗指“哇”。作者将蛙叫声比作了婴儿的哇哇的啼哭声。在作品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常言道蛙声如鼓,但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的初生婴儿在哭。”③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将“蛙”的意象延伸扩展了,使它有了人的生命与情感迹象,仿佛是那两千八百多无辜的生灵以群体合唱的方式抱怨着,发泄着,诉说着各自不幸的冤情。蛙鸣声抑或婴儿的啼哭声此起彼伏,哀恸悲凉。
再次,“蛙”暗指“娲,女娲”。姑姑万心一生都没有孩子,当她退休后在家反思和回顾自己的过去时,对于曾亲手扼杀了两千八百多个无辜的生灵,顿时感到恐惧不安与愧疚自责。姑姑与姑父亲手捏出了两千八百多个可爱的小泥人,都是按照姑姑记忆中那些婴儿的模样来捏的,并把他们摆到广场上,送给前来拜佛求子的夫妇们。姑姑渴望用这种方式来赎罪,弥补过错,使自己摆脱罪恶感。他们捏泥人的行为恰如上古神话中的女娲,抟土造人,充满了一种神话色彩。
二、魔幻意象的悖谬性
新时期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很大程度上都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手法,使人物性格特征、言语活动都带有奇幻性与荒诞性特征,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变化莫测,当然这些因素也促使了魔幻意象悖谬性的产生。藏族作家阿来在谈论他的小说《尘埃落定》时,就承认其中的“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解读。“在我怀念或者根据某种激情臆造的故乡中,人是主体。即或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也显得相当简洁有力。”④
在《尘埃落定》中“傻又不傻”的二少爷就是一个充满悖谬性的意象符号。二少爷是麦其土司与汉族女子媾和的产物,是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结合体。在土司家族人们的眼里,二少爷是一个智商缺陷的“傻子”,其实“傻子”这种智力上的缺陷暗指不断走向败落、行将灭亡的土司文化;但在外人看来,二少爷一点也不傻,是一个聪明人,具有超人的智慧与能力,处事不惊。他的这种大智若愚与卓尔不群的行为表现隐喻着外来文明的活力与生命力的象征。他亲身经历了麦其土司家族由兴盛转向衰败的过程,也正是承载着“傻子”与“智慧”的二少爷目睹了这两种不同文化与不同文明的对立与冲突。因此,“傻子”是一个富有张力与悖谬性的意象符号,他的存在就是一个矛盾体:呆傻与聪明,本地文明与外来文明,旧制度与新制度,败落与新生……
三、魔幻意象的诗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诗缘情”这一说,诗性的内涵与人文终极关怀紧密相连。朱光潜曾说过:“文学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诗。”?譽?訛在新时期中国小说所营造的魔幻意象中也呈现出奇特的诗性特征与审美特质,使新时期中国小说在艺术表现与思想意蕴上都增添了许多朦胧的诗意美。”例如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有一段描述:
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譾?訛
作者运用类似白描的手法将心灵的图景以梦幻般的感觉跃然于纸上,将“红萝卜”这个意象进行了理想化的勾勒,并赋予它灵性与神秘色彩,“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苞孕着银色液体”,好似带有几分灵性与情感。它象征着一种人性渴望之美,一种精神的亮色,它与黑孩生活周围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也寓意着一个光明、美好、理想的精神家园,这正是被褫夺爱与幸福的黑孩所需要、向往的终极关怀。可见它是一个充盈着诗意的意象,使作品整体在读者面前营造着一种朦胧的诗意感,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与审美享受。莫言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这篇作品时曾这样说:“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含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含蓄美。”⑦
新时期中国文学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刺激和深刻的影响下,作家们在写作技巧与形式等方面借鉴和吸收了欧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营养与精华,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的创作特点,创造出新时期中国文学独特的魔幻故事,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新时期中国小说将自身文化的魅力与外来文学的新鲜血液巧妙地结合起来,展示出色彩斑斓的神奇与魔幻。魔幻意象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组成,它本身具有复杂的美学意蕴与审美价值,我们对其进行细致的阐释,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解读新时期中国小说作品,加深我们对文本意义的多元理解,并提升我们的审美能力。
[英]R.S.弗内斯:《表现主义》,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阿来:《尘埃落定·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443页。
孔范今,施站军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 陈黎明.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小说[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2] 李杭春.中国现当代文学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3] 曾利君.新时期文学魔幻写作的两大本土化策略[J].文学评论,2010(2).
[4] 杨剑龙,朱叶熔,陈鲁芳,赵磊,张欣.意象建构中的浓墨重彩——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J].理论与创作,2010(2).
作 者:黄敬军,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