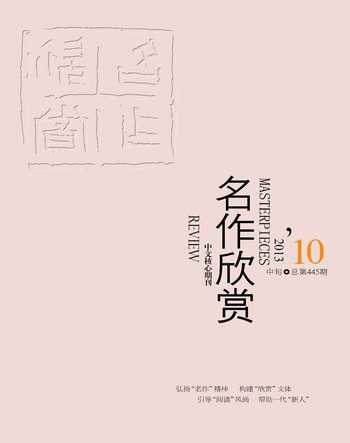从《等待戈多》探究荒诞派戏剧特征
摘 要: 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巴黎上演,引起巨大反响。从此,一个新的戏剧流派——荒诞剧在欧洲崛起了。荒诞派作家则看重人生的荒诞性,人活着实际看似就是一场梦,人的努力既是无意义的也是无用处的,人的存在与不存在都是荒谬的。荒诞派戏剧有以下几个特征:荒诞抽象的主题,支离破碎的舞台形象,奇特怪异的道具功能。
关键词: 贝克特 《等待戈多》荒诞派 特征
荒诞派戏剧从本质上来讲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戏剧领域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但它又区别于存在主义文学:在存在主义作家的眼里,世界是荒谬的,但人应当履行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并且通过“存在”去寻找自我,因此在其作品中,语言是非常明晰而且富有哲理性。相比之下,荒诞派作家则把人生的荒诞性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人活着就是一场梦,而且人的存在抑或不存在都是荒谬的,甚至人的努力既无意义也没有什么用处。
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巴黎上演,引起巨大反响。从此,一个新的戏剧流派——荒诞剧在欧洲崛起了。
在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里一共有两幕。两个浑身发臭、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角色。他们在乡间小道的一棵枯树下焦急无奈地等待戈多。但是接下来的第二天,他们又在原来的地方等待戈多。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毫无希望地等待着,靠无聊的动作和类似梦呓一样的对话来无奈地消磨时光。在剧终,戈多始终没有来,虽然我们了解到一个小男孩——戈多的使者接连两个晚上都过来传讯给他们说:“戈多先生今晚不来了,明天准来。”①最后他们似乎绝望了,但是两次上吊都未成功。他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继续等待,而且是永无休止地等待。
荒诞派戏剧致力于把荒诞性的存在定格为成破碎不堪的舞台形象,从而能彻底破除传统戏剧的戏剧性、准确性的语言、有逻辑性的章法结构以及理性的人物行为,用以表现荒诞的世界和痛苦的人生。荒诞派戏剧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主题的荒诞抽象性。在荒诞派作家的眼中,世界是荒谬滑稽的,所以人活着是毫无意义的。丑恶与恐怖的现实,痛苦与绝望的人生,就成了荒诞派戏剧亘古不变的鲜明主题。“广义上来论,荒诞派剧作家的作品和其主题,反映的都是人类在荒诞处境中所感到衍生出的抽象的苦闷心理。”②此剧的主题不是戈多而是等待,是等待这一行为所具有的人的状况的本质性的和特征性的方面。《等待戈多》侧重的是对“等待”这一状态的描绘。“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这实在糟透了。”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永无休止的等待——时间停留在这一刻,毫无意义的一刻。作者运用戏剧手段渲染的也不是等待的目的,而是等待的过程。这种等待具有多义性特征:它意味着碌碌无为的人生,机械重复的平常琐碎不堪的动作;它象征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希望,这个希望又是抽取具体内容,形而上学,无象无形的希望。
剧中人物身份不同,均无个性可言,他们只是不同等级、身份的代表。没有任何个性特点,没有性格变化,甚至没有变化发展的个人行为。一切都是静态的、重复的。小之于两个苦老头从脱靴找寻开始,但靴内什么也没有,然而仍要一味反复地寻找,期待里边什么东西被发现。大之于等待戈多的来临,其实什么也没有来临,来的几个人都不是所谓的戈多先生。表面上说来,戈多是个人,但是谁也似乎又无法确定。他们想向戈多要求的一种泛泛的乞求,一种祈祷,如果具体到什么也是说不清楚的。戈多,指的是谁?代表着什么?这是该剧最大的悬疑点。剧中的两个小老头把自己的命运拴在戈多身上,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处境,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既不清楚也不了解,也不知戈多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只是莫名其妙地相信“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在这儿等着”。虽然到剧本的最后,两个主人公还是在等待,而且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等待,但是这种等待在开始的时候是一种盲目的无目的无意义的一种生存状态,结束时的等待却有别于最初的等待;虽然两个人等来的最终结果都是一种无意义,但是却是由最初的无意识到了后来有意识的等待,这似乎也是一种意义。剧本揭示了荒诞的世界与痛苦的人生,现代的西方人努力希望自己能改变自己的目前生活处境,但是由于各种现实因素而又难以实现自己愿望的悲观绝望心理,都在两个流浪汉毫无希望永无休止的无名等待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
2.舞台形象的支离破碎。荒诞派戏剧作家们认定世界的“荒诞”本质,因此戏剧所要表现的核心内容应该是“非理性”的。因此在其作品中,他们努力刻意地去打破传统的戏剧约定常规,从而形成荒诞派戏剧既没有常规戏剧结构的基本格局,又无传统意义上的时间空间观念;作品的人物形象没有鲜明的人物性格,而其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也被淡化。荒诞派戏剧通过塑造荒诞怪异、支离破碎的舞台人物形象,目的就是表现人生是一个无头无尾、毫无意义、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在创作形式上,传统戏剧的陈规被贝克特彻底地打破了,剧本可以周而复始地演下去,因为从整体而言剧本的情节是不具备完整连贯性的特征,结尾是开端的再次重复,在剧本中我们找不到具体明确的时间、地点。剧中人物被贝克特刻意弱化淡化了,在整部剧作中没有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人物的历史背景几乎是一片空白模糊,而其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显得抽象、模糊。人物都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存在,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作为生活实质和直喻世界的舞台象征被呈现出来。
作者把舞台上出现的一切事物都荒诞化、非理想化了。一条荒凉冷寂的大路。先是出现了记忆模糊的、说话颠三倒四的、行为荒唐可笑的流浪汉。传信的小男孩,第二次出场不知上一次是不是自己。幸运儿在全剧中只说过一次话,却是一篇神咒似的奇文。波卓一夜工夫就变成了瞎子,却不知是何时何地瞎的。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苦苦地等待戈多,却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等待。每一次都没有什么逻辑,也不遵守规则,似乎完全是一种偶然,而且只受偶然性的支配。作者故意使连贯性的情节冲突淡化,割裂戏剧情节的连贯性、逻辑性和顺序性,用一组组跳跃、变幻的象征性场面来代替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以一个个机械拼凑的喻义形象来组织情节线索。在此剧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中心事件,没有矛盾冲突,仅用“等待戈多”这个抽象的意念来组合全剧,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一套起承转合的戏剧模式。“什么也没发生”一语为该剧定了格。戏剧人物行为的无为和等待的希望,锁定了该剧的基调。剧情的静止、不变和简单重复,又强化了这种基调。
从戏剧结构上说,此剧的第一幕和第二幕的内容是重复的,结构上采用了一种反复再现的手法。人物语言的重复■嗦,增强了作品的荒诞感。而且结构上,第二幕几乎就是第一幕的完全的重复,打破了传统戏剧以剧情转折、突变和组织戏剧高潮来吸引观众的常规。
3.道具功能的奇特怪异性。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家尤奈斯库曾经如是说过:“我试图通过物化把我的人物的局促不安加以外化,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变成视觉形象……我就是这样试图伸延戏剧语言的。”③纯粹戏剧性是被荒诞派剧作家所极力倡导的,认为艺术家要想把握世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直喻的信息传递方式。戏剧的直观艺术特点通过荒诞派戏剧的道具被发挥到极致,从而其产生的荒诞效果令人匪夷所思。他们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通过道具转化为具体的视觉形象。所以他们尤其看重简单道具的象征意义和舞台布景突出来的荒诞性,目的是外化剧中人物精神状态。人物感情被外化是荒诞派作家的努力方向之一,他们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并用各种各样的舞台手段方式,从而使得舞台上的形象、道具、灯光能够直接地“说话”。人物的痛苦、恐怖的内心都被鲜明形象地表现出来,而所借用的手段就是充满梦幻模糊意识和疯癫的外观和莫名其妙而诡异的舞台布景。此种披着荒诞外衣所隐藏的痛苦和恐怖表现得更加深沉强烈,是不少西方人心理特质准确而真实的写照。在荒诞派剧作中,道具是一种不受制于人主体性的能自己说自己的语言。
在《等待戈多》中,作者用空荡的舞台象征世界的冷漠荒凉,以秃树一夜之间长出嫩叶表示世界的荒诞不可理解。苦老头反复用以抛接玩弄的帽子,象征人类残存的尊严即将丧失;波佐的折叠凳子象征着人类的权力宝座已经虚弱动摇。这一切似乎都在演绎着存在主义的一个哲理命题:“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④ 在贝克特的戏剧里,人物行动被无意义的语言所取代,环境、人物、情节、动作的描写都被缩写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因此他的舞台是简洁而空旷的。
贝克特的荒诞剧作,展现了人生的虚无与绝望的主题,将存在主义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之哲学命题,宣泄、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具体的社会主题,他所追求的是表现那些关于存在的最基本的元素,如时间、等待、孤独、异化、死亡,等等,表现了纯粹的生存状态。在剧作《等待戈多》中,既没有英雄人物,也没有典型性格,甚至连完整的人物形象都没有。唯一的要求在于艺术上造成滑稽的漫画效果,把人生的荒诞性凝固成舞台形象。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们把日常现实肢解开来,使之变形,显得奇形怪状。把感情表现得极度夸张,把人物的对话引向极端。在这场《等待戈多》的混乱之中,只有一样东西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们在这里等待戈多的到来。贝克特试图在这个剧本中表现宇宙和人的存在状况的荒诞、无意义。他认为外部世界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剧中世界只是一个长着光秃秃的树的荒原。虽然人在这个境界中处于孤独无助的狼狈境地,然而他们仍然坚持在微弱的希望之光中等待。
① 贝克特:《等待戈多》,余中先、郭昌京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英]马丁·埃斯林:《荒诞派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
③ 朱虹:《荒诞派戏剧集·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张耕:《现代西方戏剧名家名著选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作 者:霍舒缓, 广西大学2011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