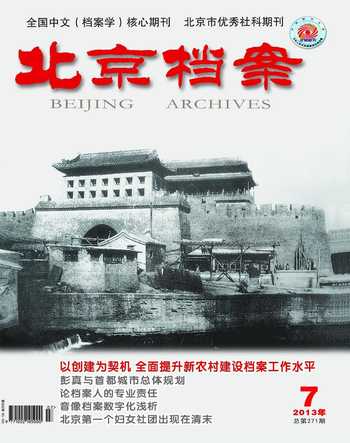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的广东会馆(三)
张卫东
在北京盛行的广东音乐
北京素来有喜好广东音乐的民间组织,其实这种组织最初也是经广东会馆传播开的。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君盘、刘树楠为翔千学堂和实践女子学校筹款,在天乐园(大众剧场)举行义演,2月14日晚,上演的节目中就有广东音乐以及管弦合奏、箫笛合奏、喇叭单奏等。
扬琴也是经过广东会馆的举子们传来,最初叫“洋琴”,后改称“扬琴”。这种乐器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爱,早年在口语上还叫“蝴蝶琴”、“打琴”。后来被广泛地用在北方曲艺中,不但在梅花大鼓中使用,还能独奏。民国年间翟青山使用扬琴主奏,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曲种“单琴大鼓”,后经关学曾继承改称“北京琴书”。扬琴已经是北京俗曲演唱中的主奏乐器,却少有人知道它是经广东会馆传来的。
民国后的广东音乐在北京更是盛行,多是居住在广东会馆的学生带到学校中。后来的汇文、崇实、育英等中学也都有广东音乐社团,中国大学还有独立的音乐艺术团。参加这一时期的演奏者多数已经是地道的北京人参与了,现年90多岁的满族老画家穆家麒就是当年汇文中学的乐手。广东音乐在北京发展至今,却成为几乎没有几个广东籍的群体,这种艺术在北京可谓是南花北移。因广东省是孙中山先生的家乡,所以民国以来把广东音乐称为“国乐”。现在喜好广东音乐的民间组织在北京还有一两家,至于在公园演奏的爱好者就更多了。
北京松风国乐社成立于1944年9月,由当时北大学生杨雨金、冯葆富、王贻炬等发起创办,还有社员崔文治、罗廉、臧尔忠、倪宝恕、罗作新、李淳、裴新生、席福盛、白祥麟、邓振瀛、翟峻岑、蓝宝年、孙宝正、刘实、邝宇忠、雷庆文、吴川、周璞、白子洁、马殿驺等。该社每周六晚和周日下午及晚上活动,在王贻炬的父亲家里。
这个乐社有近10年的活动经历,是北京民间的公益性组织,为社会上义务培养了不少民乐人才,其中一些成员步入了专业音乐团体及音乐院校。松风国乐社如同北京推广广东民间音乐的一所学校,他们还不断研究印制学习资料,曾经编印了《粤乐彙粹》、《丝竹乐曲集》等4册。李凌著的《广东小曲》曾引用《粤乐彙粹》部分素材,广东音乐家甘尚时与天津音乐学院赵砚臣,以及余其伟所著的一些有关广东音乐书籍中,都对“松风”资料做了引用。松风广东音乐社经过近10年的积累,乐曲达数百首之多;还曾在北平电台、胜利电台、华声电台、联合电台等直播演奏节目。
解放后,松风国乐社以吹打乐《闻胜起舞》、《拿天鹅》,以及合奏《翠湖春晓》等曲目,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演出,由北京师范大学杨大钧教授指导排练。新华电台当即为这几段乐曲录音,播送后,听众反响强烈,因为这个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传播覆盖面很广。后来电台还吸收了乐社的王贻炬为文艺科成员,自1949年8月1日起正式录制批量节目,以“北京业余国乐研究社”的名字取代原来的“松风”。从此这个乐社的演奏水平日益提高,还录制了广东音乐《秋水龙吟》,以及丝竹乐合奏《万年欢》等唱片出版发行。“松风”于1954年夏停止活动,但原来录制的广东音乐以及丝竹音乐仍不时继续播放。
1984年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松风”国乐建社40周年座谈会,后来在北京的一些“松风”老社员们又开始恢复了活动,还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怡情雅趣》、《长寿天地》等栏目中,展示过他们的演奏。
现在北京还有喜好广东音乐的民间丝竹社团,多半是经原来松风老人们传承。广东音乐能在北京有民间爱好组织与岭南音乐文化分不开,但最重要的是有“松风”这个民间乐社薪火相传。
广东传来的昆弋锣鼓“广家伙”
北京的广东会馆目前只存中山会馆戏台,原来南横街粤东新馆、韩家潭广东会馆等处也都有固定戏台,其他会馆一般可以临时搭台演出,所以当年在会馆演戏是常见的事。广东省自明代就传入昆腔和弋阳腔,后来结合当地语音风格逐渐演变成如今广东地方戏特色。
弋阳腔传入北京应是明代中期,曾经与昆腔合流逐渐形成北京弋腔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高腔”、“京腔”以及“京高腔”等名称。它只用锣鼓击节,众人帮腔的形式演唱,没有丝竹相伴。虽说弋腔出自江西,但锣鼓却来自广东,弋腔很可能不是直接来自江西,或许是经杭州、广东传到北京,所以就与会馆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北京戏曲界便称高腔锣鼓为“广家伙”。
目前多数剧种的打击乐器多以金、木为主体,总体上按照五行分类,故将打击乐称之为“武乐”。“金”是指铜制的锣、钹类,“木”是指以鼓师手中的指挥乐器檀板和鼓楗子。戏曲的重要打击乐器——单皮,亦称板鼓;是以木做胎外包猪革加白铜钉制成,当属木金合成。通常以板鼓指挥其他锣鼓为演唱打击节奏,虽然中国各类剧种丰富,但在使用打击乐方面是共同的。
“广家伙”是高腔戏的节奏支柱,它在配合身段、上下出场时,都要按照不同行当的人物身份和感情加以锣鼓点子配合,如同剧中人心脏跳动的节奏一般,用以表现剧中的矛盾冲突和武打类技术表演。
旧时,北京的戏班演出开始必有“打通儿”的程式,就是以打击乐作开场锣鼓演奏。这种形式共分为三通儿锣鼓。第一为“高通儿”,就是用“广家伙”打击的高腔锣鼓。第二为“苏通儿”,是从苏州传来的昆曲锣鼓,梨园行习称为打“苏家伙”;也就是后世继承的京剧锣鼓。
第三为“吹通儿”,是以昆曲吹奏的曲牌夹杂打击乐等混牌子。
这些演奏形式,一来是为招揽生意,二来是使观众和演员们进入戏剧氛围。京剧的打击乐极为复杂,首先就是它的来源众多。
北京高腔锣鼓用的这种“广家伙”是为演唱作为击节的主奏打击乐器,乐队的鼓师和其他乐师边打击锣鼓边帮腔演唱,使唱腔和打击乐完美结合。这种形式现已不见于北京舞台,只能在传世的部分录音和一些老艺人口中才能了解大概。掌握打击乐的锣鼓技能一般不能看谱演奏,一定要将各种锣鼓点子以口头形式背诵,如诵念经文一般,所以旧时戏班称打击乐的锣鼓点子为“锣鼓经”。
北京旧时梨园行中素有“锣鼓经要是不会背,这辈子打不对。心里有锣鼓经,巧练准能成!”的口头禅。其实即便能背会锣鼓经也未必能打好锣鼓,还要在打击乐的基本功上下工夫。作为演员也需要会背诵锣鼓经,它是统治整出戏的灵根。每个锣鼓点子都是震撼观众和剧中人物内心的标点符号,而每个符号都要由演员控制强弱起伏。打击乐在剧中还有烘托气氛和人物情绪,以及时间、情景、环境等技术功能,有时还要夹杂管弦类文乐来表现。戏中表现时间多用“起更”锣鼓,几下更鼓就是一夜,这种时空转换是利用中国传统写意法,就是“斗转星移”。用锣鼓打击组合表现江、河、湖、海的水流湍急,是为演员在舞台虚拟表演提供铺垫,而另一部分的真实环境则由观众配合剧情想象而成。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通过打击乐亦能表现,这种借助手段是传统戏剧中的经典,比当今利用声、光、电等舞美手段高明得多。
不同剧种的打击乐有不同主奏锣鼓,昆曲一般由板鼓、大锣、小锣、铙钹以及堂鼓组成。京剧继承昆曲打击乐程式,另有河北梆子、评剧、豫剧等剧种亦略相同。“广家伙”由板鼓、大筛、大铙、大钹、小钹、小锣、大堂鼓等组成。它的锣鼓经很是丰富,念出来与“苏家伙”有所不同。同样是“五击头”,苏家伙是:哐、切、哐、切、哐;而广家伙的锣鼓经则是:嗟、咚、嗟、咚、嗟。高腔“广家伙”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剧种,它是演唱中的主奏乐器。
在北京类似这种广家伙的锣鼓在民间还有一种打击乐,就是为狮子、五虎棍、少林拳等香会社火伴奏的“文场”。这是一个由7个人组成的游行式乐队,有单皮、镲锅、小堂鼓、两对大铙、两对大钹组成。这种打击乐也是属于广家伙范畴,有些锣鼓经与高腔鼓点如出一辙。
北京高腔早已不见于舞台,但在部分的昆腔中还有保留。在河北丝弦中也使用“广家伙”,目前受京剧影响已经改用京剧锣鼓。现在广东的传统粤剧、正字戏、白字戏、潮剧等还保留有部分高腔锣鼓,但“广家伙”的演奏形式在其他剧种中已经难得一见了。
广东会馆在北京的终结
广东会馆多数是为科举服务,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后便骤然萧条。虽然,民国初年暂时繁荣,但随着民国十七年(1928)的国都南迁,在京的广东籍政治人物随国民政府搬到南京,导致北京的广东会馆管理失控,甚至违背制度将空房租赁给外乡人。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官府恶霸们相互勾结瓜分会馆公产,以致后来在京的广东会馆竟没有细致账目记录资产。1949年,几乎所有会馆都成为多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全然没有当年的那种幽雅气度。
根据现存资料记载,1956年时,北京的广东会馆共有大小房产2908间半,除原崇文区袁崇焕墓堂以及祠堂由文物部门接管,其他多是由房管局接收作为居民住房。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北京,自此居民在院里搭建地震棚,而后谁也不会回拆,因此本来就已成为大杂院的会馆文化几乎淹没得无影无形。2000年3月,随着北京城市改造的蓝图展开,经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会馆建筑最终被无奈地拆除。广东会馆只剩下一座中山会馆,龙潭湖畔依然屹立着康有为为袁督师撰写的碑记和祠堂,广渠门内的袁崇焕墓堂尚在,但在此看守了三百年的佘氏家族已被迁出。
现在的北京依然飘洒着岭南文化,但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香港风情。旧时会馆传来的科举文风东流一去,衣食住行等也随着新时代的推移改变成更为便捷的方式。
(作者系国家一级昆曲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