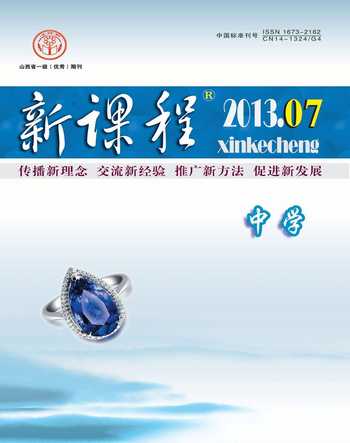阅读对话,唤醒学生的发展自觉
沈磊
摘 要:阅读教学中深层意义上的对话能引领学生历经精神层面的体认、创生以及重构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而不断地唤醒其内心的发展自觉,最终完成教育的使命。
关键词:阅读对话;体认;创生;重构
教育的使命,就是唤醒学生内心的发展自觉。而阅读对话,当是高中语文教学唤醒学生发展自觉的一种主要方式。“对话”,它原先是一个文学理论名词,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因而新课标所提出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不能只停留在教学信息等交流反馈的浅层面,而应该逐步进入到情理、心魂等交融建构的“深水区”。从本质上说,阅读教学中的对话应该主要指向对话主体:学生精神层面的体认、创生与重构,从而获得促使自我不断主动发展的内驱力。
一、唤醒精神之体认
体认,指体察、认识,还包括认可、认同的意思。本文所谓的“体认”,主要指通过阅读对话引领学生认识自我或重新正确认识自我,从而明确自己所处的时空与基因谱系,明确自己所承载的使命与价值担当。无论是阿波罗神庙那个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还是狄俄尼索斯的“忘掉你自己”,其实在这种矛盾中所体现出的都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强烈自觉。洞察体认自我,是创生与重构的前提,也是阅读对话唤醒学生发展的第一步。而这恰是以往“教师带着文本走向学生”或“教师带着学生走向文本”的阅读教学所严重缺失的,学生的诉求被漠视,心灵被禁锢,自我被遮蔽,发展被弱化。
而人如何认识自己?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在《重新认识你自己》中认为:“‘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我无法透过抽象的思考来认识自己,‘我必须在我的具体存在中,认出我之为我,而非理想的我。”他还从一个人对自己脸孔的认识与镜子的关系中,抽象出“人总是在镜像中反观自身”这样一个哲学结论。而文学在这方面正提供了具有突破性的广袤的历史文化时空,可以让人通过阅读对话置身其中去认识自我获得真知。经过作家艺术加工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而且语言媒介使得那些难以把握的、模糊不清的情感和思绪,都能在作品中得到明确定性。“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来了解自己的情感,通过人物的思绪发现自己的思绪,使人们借助于人物这面镜子,看到自己身上一些未曾察觉、或未曾了解以及未曾完全了解的东西,从而对自己有更加全面、深入、透彻的了解。”由此,我们更应该追求“学生带着文本走向教师”的深层对话,让学生不断地在曹雪芹、鲁迅、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一个个镜像中观照自我,寻回那曾失落的真我。当然,我们要注意避免成为纪伯伦小说《认识自我》中赛艾姆那样的人,只是单纯幻想,只是自我安慰,只是认识表面。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认识自我应该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
二、唤醒精神之创生
创生,即创造产生,生而成长。此即通过阅读对话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促使学生通过判断和选择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心灵,去规划未来的蓝图,去谱写自己的人生,去拓展精神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一个博观而厚积的能动过程,也将为精神自我的重新建构打下坚实基础。简而言之,文学作品具有“参照”功能,其描绘的生活多为“应然”的人生图景,渗透了作家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当我们与之深入对话时,往往会在审美愉悦中不知不觉地认同了作家的价值倾向,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德国心理学家里普斯和谷鲁斯的“内模仿说”认为,人在全神贯注地欣赏审美对象时,因为审美对象与某种心理品质相类似,就会引起人的相应的感情。然后人又把这种感情外射到对象身上,使得对象仿佛有生命。受这种心理错觉的牵引,人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行一种心理甚至肌肉的“内模仿”运动,以此达到与审美对象的契合、同构。比如,欣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段时,人们不知不觉会挺起胸膛,握紧拳头,全身心充满义勇豪爽之气。如此,读者方能在“去蔽”的本真世界中听到真理的声音,看见启悟的光芒。而这还只是被动地生发,主动地创生还需要借助文本的不确定点或空白与文本、作者等展开对话。召唤性是文学文本最根本的结构特征。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这种由意义不确定与空白构成的就是“召唤结构”,即指文本具有一种引诱和激发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它召唤读者把文学作品中包含的不确定点或空白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文本便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精神之创生也就更有张力。比如,李密《陈情表》“孝情”背后可能隐藏的“忠臣不事二君”的伦理观就颇值得玩味。抓实文本空白点,从字里行间去挖掘作者的未尽之言、未表之情、未传之意,将使读者的精神世界无限丰富起来。
三、唤醒精神之重构
按王省民在《选择·突破·重新建构》中的观点,重新建构是创造性思维的一种基本方式,就是及时有效地抓住新的质,建立起新的思维支架,扩充新的价值领域,完善和充实新的思想体系,为理论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本文所说的“重构”,则是指通过阅读对话在多维创生的基础上遵循自我的内在需求,按照生命个体发展的基本逻辑体系,将恣意漫生的各种思想、理念、精神等优化组合,爬罗剔抉,破旧立新,淬炼重塑出自我新的价值体系。简而言之,即实现从前两个阶段认识自己、丰富自己到现阶段改造自己、完善自己的根本性转变,在审美愉悦激荡中完善道德理性:“人应如何”。
伊瑟尔的“召唤结构”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的阅读期待,但被唤起的阅读期待并未被满足,而是被打破,从而迫使读者建立新的视野。这就为精神重构提供了可能,而强烈的自我意识则又召唤着读者必须要从不同的阅读对话中获得的各种庞杂的精神元素中走出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全新道路来。否则,读者只能在非系统的、混乱无序的创生中感受一种虚假的繁荣,而无法确立自我的中心。同时,我们要注意避免自我的重构走向异端,这就需要教师在阅读对话中引导学生去进行个性化解读,而非自由化阅读。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虽然已经离开了原作者,但总还葆有创作者的抹不去的巨大影子。我们对作品的解读不能以“作者意图”为唯一的准绳,但也不能简单地说“作者死了”(罗兰·巴特语)。正如德国文艺理论家姚斯认为的,艺术作品“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召唤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因此,阅读的过程,必然是创造性地破译文本中所隐含的种种“密码”的过程。创造性始终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的阅读对话,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否则终究沦为哗众取宠的“大话”抑或“消解”,只能走向虚无。
参考文献:
[1]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177.
[2]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2l.
(作者单位 江苏省震泽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