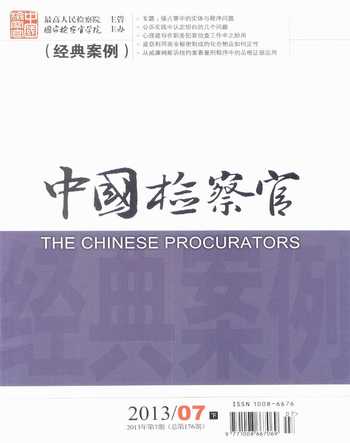在公共场所捡拾遗忘物的行为定性
胡乩生
【典型案例】汪某(本案失主)于2006年3月26日14时许,携带一个手机包装盒(内装一部当日新购买的三星D608型手机及电池)到某银行营业厅办理存款,在填写单据时将该包装盒放在供客户填写单据的桌子上,填好单据后汪某到银行柜台去办理存款业务,将包装盒落在营业厅的桌子上忘记带走,汪某办理完存款业务后,即离开银行。江某(本案犯罪嫌疑人)于同日15时许。也到该银行办理业务,在填写开户申请单时发现桌子上有一手机包装盒,江某即认为该手机为他人的遗失物,遂将盒子内的手机及电池取出带走。失主汪某此后返回银行取走手机包装盒,旋即发现包装盒内的手机及电池丢失,汪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察根据银行内的监控录像及从银行纸篓内提取的江某所填写的单据等证据,查找到了江某,江某遂将手机及电池交出退还给汪某。经价格鉴定,手机价值为人民币2800元。公安机关以江某涉嫌盗窃罪立案侦查,某区检察院以江某涉嫌犯盗窃罪向某区法院提起公诉;、后在法院审理期间。检察院以证据变化为由撤回起诉。最终对江某作无罪处理。
一、分歧意见
刑法意义上,对本案中江某的行为性质及处理方式,存在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构成盗窃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认为侵占他人遗忘物的行为属于侵占罪的性质,但数额未达到侵占罪的起刑点,不构成侵占罪:三是认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二、江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侵占罪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江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首先需要确定案件中的手机属于遗忘物还是遗失物。
遗忘物与遗失物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后果,在刑法意义上,只有他人的“遗忘物”才能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遗忘物与遗失物的概念。但通常认为,“遗忘物”是指当事人由于一时粗心而失去占有,但能够凭借记忆等线索而较明确地去查找的财物,也就是说,失主对“遗忘物”知道何时何地丢的,也比较容易找回来。而“遗失物”则不同,失主只知道财物丢失但是不确定丢失的时间地点。本案中,失主汪某将新购买的手机遗落在银行桌子上,丧失了对手机的实际控制。但汪某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应该记得新购手机并带去银行的情况,当发现手机丢失后,也能够回忆起手机丢失的时间和地点。事实上,汪某发现手机不见后很快就到银行来寻找,这也足以印证手机不属于遗失物、而是遗忘物。
本案尽管符合侵占罪中犯罪对象的要件要求,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并不能构成侵占罪:
首先,涉案手机的价值未达到侵占罪“数额较大”的入罪数额标准。构成侵占罪,尚需满足“数额较大”的要求。以北京市为例。该案发生于2006年,根据北京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八种侵犯财产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京高法发(1998)第188号),侵占罪的“数额较大”为一万元以上二。本案中涉案手机价值仅仅为2800元,未达到侵占罪的入罪门槛。
其次,江某没有“拒不归还”的情形。虽然失主汪某通过警察的介入才查找到嫌疑人江某,但由于江某随即将手机归还给了失主汪某,而不是拒绝归还。所以江某没有“拒不归还”这一构成侵占罪的必备要件。
三、江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江某在公共场所将他人遗忘的手机从包装盒中取出拿走的行为,具有较强的盗窃罪的特征。但综合事实与证据,并结合事前事后的具体情形,不应认定其构成盗窃罪。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涉案手机处于无人占有的状态。银行的营业厅是一个开放的、人流量很大的交易等候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每个人应该看管好自己的财物。其他人没有义务和责任去照看他人的财物或者所有权(占有权)状态不确定的物品。应该说,这部手机客观上处于一种无人对其实施有效控制的“占有”不确定状态。
可能有人会认为,客户遗落在银行营业场所的财物应该是由银行进行“占有”,因为银行营业场所具有严密的保安措施,有义务和能力保护客户的财物安全。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因为银行及其员工既没有受到汪某的委托,在客观上也不能实际控制这部手机,无法有效占有。事实上,本案中银行及其员工(含营业厅的保安员)一直都没有发现营业厅桌子上这部手机的存在。所以,这部被遗落的手机并不是当然地处在银行的占有之下。
其次,江某拿手机的行为是捡拾而非窃取。“窃取”与“捡拾”都是取得物品占有的方式,但具有明显不同的法律性质。前者涉嫌盗窃,后者则无关犯罪。本案中,江某到银行营业厅后发现了这部无人看管的手机,其从盒中取出手机并拿走、却将包装盒留在桌子上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具有害怕被别人发现的心理状态,但却不能因此而认为构成秘密窃取。人们习惯于认为放在屋子里的东西都是有人实际控制的,而往往忽略对屋子空间的法律属性及财物的实际占有状态的具体分析。本案中,事发在营业厅这一公共场所。涉案手机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且不为任何人所实际控制,江某拿走手机的行为是完全公开的。而且,如果推断江某的举动是“偷”,则只能认为当时的手机是在银行的“占有”下,则会导致“江某盗窃金融机构”这样严重的法律论断,而这个结论显然超出了公众的预期范围。
四、案后余思
(一)避免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等惯性思维模式
这个案件作为盗窃案进入了刑事诉讼环节,并进入了法院审理程序。这一过程是值得思考的。
长期以来,有的司法工作者容易先入为主,带着有罪推定的心态,动用刑事手段来解决不应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普通纠纷问题。虽然我国法律已将无罪推定明确,但由于传统习惯与经验做法的影响,使得有些本不应升格为刑事案件的矛盾和纠纷被简单化地升格处理。本案中一个普通的捡拾财物行为被作为刑事案件办理,清晰的反映了上述倾向。虽然警方的行为在开始是正当的——基于失主的报警,警方介入调查,找到拿走手机的江某,但在江某归还手机之后,警方仍然立案侦查,并移送审查起诉。这一过程反映出警方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的方式单一和程序僵化。
警方坚持以刑事案件查办,也反映出公安机关立案容易销案难的实际状况。即使办案人员也认为不宜做刑事案继续处理的,由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考核考评机制。使得承办人也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去停止已经启动的刑事程序。这在客观上需要检察机关发挥好监督作用,确保无罪的人不被刑事追究。
(二)深入贯彻“平和理性、文明规范”的执法观,强化证据客观意识,确保检察执法效果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平正义。这要求加大法律监督力度,深入贯彻“平和理性、文明规范”的执法观,全面全程落实无罪推定的要求,强化客观证据意识。避免单纯套用法条的简单化执法,避免只用刑法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机械化执法。要创新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模式,坚决摒弃检察院只是“侦查、起诉、审判”流水线上的一个流程的错误定位。坚决做好法律的监督者。要将不应进人刑事程序的案件坚决剔除掉、要坚决把握好在批捕、起诉环节发挥好既是诉讼程序参与者、又是法律监督者的双重定位,依法做好诉讼监督,保障检察执法效果。